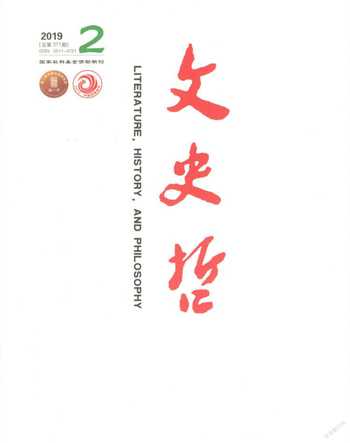学科话语体系锻造: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
苏力
有关打造有中国特色同时有普遍意义的法学学科体系,有些想法,二十多年前在笔者第一本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自序中,就有所涉及。
在当时看来,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很有可能,到下个世纪初叶,就经济总规模来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复兴已不可避免。……
这也许是现代中国对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与这一贡献相比,任何理论学术都会黯然失色,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不会是最后的解说。尽管如此,解说却是重要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解说使他能够把本来是无序的世界化为有序,从而似乎“有意义”;而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从一定的视角来看,社会的形成其实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诸多解说相互冲突、磨合、融合的过程,并进而获得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相对确定的解说,因此也就影响了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构成“制度”,形成文化的共同体。
就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说,中国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前两个学科)都从外国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识,甚至就连这些学科划分本身也是进口的。然而,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也许,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作出我们的贡献。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尽管西方学者和前辈学者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视角、理论、模式、命题和概念,但是假如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人类历史不是重复往返的,假如具体的现实生活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假如每个人的体验都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都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偏见”,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昔日的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作出我们的贡献。
这种贡献并不是以我们的经验体悟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些脚注,充实或补充他们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给予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
必须指出,关注本土问题并不是如同某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的学者那样,试图从中国传统或社会中寻找某些据说是具有“现代性的因素”。……这种做法仍然是以西方的某些理论、观点、思想、命题甚至概念作为现代的和学术的标准,因此一切他们认为值得弘扬的,仅仅是因为这些因素是符合外国的某个或某些理论或做法。……如果一切值得弘扬的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仅仅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国的某种理论或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外国照搬,有什么理由要从中国文化之中寻求那些所谓的“萌芽”呢?这种做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
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且真诚的关怀与信任;相信并假定:过去的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的和理论的概括;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不断反思,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有足够说服力的新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中国的法学的成熟还有漫长的道路。然而,这也不能使我们有理由拒绝面对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
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有关打造中国特色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学学科体系的问题基本没变,但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以及法学研究格局,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社会新变量,令我对这个问题多了些想法。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法治实践已有很多成就:各类立法基本完成,法律解注颇为细致,法学教育俨然显学,学术论著产出增长。只是若置身于人类的智识传统,笔者仍然觉得,中国的法学很难同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相匹配。或许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各类法律操作需求,总体上必定实务导向的法学多年来一直更关注法律和法律学说(教义)的移植与借鉴。借助着中国的政法体制和实践,大致有效应对了许多法律难题,法学的学术架势甚或品格整体上也确实增强了。甚至,近年来智库研究也促使中国法学人似乎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实法律问题。但总体而言,从我个人的经验判断,当代中国仍然缺乏深深扎根于中国但智识上生动强悍的法学研究。
与先前不一样的是,如今笔者不再把学术与智识当作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了。
当年我把打造法学的智识品质(也即普遍意义)这个问题看得太容易了。似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变革,只需要拓宽学术视野或更多地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在这个思想和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和扩展的世界中,似乎学者们只要注意吸纳新知,调整学术关注,感知涌动于各自生活世界的中国经验,梳理其中的纠结,辨析和提炼其中的智识争点,讲清个中道理,就能提升學术品质,不断生产出基于中国的具体经验却透出些许普遍意义的成果,久而久之,就会拓展并最终重塑法学的基本格局。但这有点浪漫。
更加浪漫的还有,笔者高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中国学人的学术心态或学术生态可能有的那种塑造力,也高估了智识本身对学人、学术市场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塑造力。与此同时,又严重低估了市场和金钱对法律学术、法律实践的侵蚀与分化,更是大大低估了法学的学科体系其实也是个制度,会顽强地再生产与维护着既有的学科格局和范式。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大趋势的推动下,因为法律的社会功能,也因其他相关的更经验、常常也是更本土的社会科学导向的研究成果的促动,笔者一方面预期,现有法学体系内的内部张力会增长,一定会促使法学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法学新领域的发生和拓展;另一方面,觉得法学内部的张力也会更多地折磨那些有更强智识偏好和更自觉理论追求的法律人,甚至有可能令他们更加纠结。就此而言,未来法学发展的整体状况未必比1990年代更加乐观。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甚至令我对打造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学体系的必要性或可能性多了一丝怀疑。如果,法律规则或制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有效处理人脑很难有效处理的复杂信息,或是节省人们交往过程中对巨量信息的需求,那么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法律规则或制度着重关注的核心问题至少会以各种方式被人工智能覆盖。换言之,至少在先前因信息不充分而难以规制的领域,如今则可能有效规制了;有些之前依法依规无法或很难执行的案件,因信息充分、可靠和及时,如今则可以有效执行了,典型如政府八部门联合发布规定,对特定严重失信人限制乘坐火车、飞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还可能令部分原先高度疑难的案件不再疑难。在某些案件中机器人法官可能替代传统法官断案,即便不必定更明智,却可能消除或弱化当事人的猜忌,增强司法的公信力。这意味着,在有些问题或领域中有可能从基于规则的治理逐渐转向基于信息的治理或干预。只要功能足以替代,有些先前的法律规则、原则和教义就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搁置、遗忘甚或废弃。传统合同法中有关要约与承诺的一系列教义,就因互联网通信事实上被搁置了,有可能被遗忘并最终被废弃,而一些新的权利和规则会应运而生。而只要众多法律规则以不同方式予以变更,从而出现新的规则甚至新的领域,那么法学体系客观上就会重构。
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学学科体系的打造,一定不是哪个或哪些学人的事业,甚至也不是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扶持就可有效推进,它其实与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紧密相关。甚至还不仅是政治法律的实践,它也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变革紧密纠缠。这里涉及的不是或不只是对以往法律知识的复述、传承、积累和整合(这还可能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努力来追求和获得),也不仅是法律知识的发现和创造,甚至涉及众多非知识的因素,如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对法律及相关领域的重新划分、组合、勾连或剥离,可能因某个或某些难以预期的变量的风云际会而意外出现或发生。
这类例子在我们身边已经不时出现。如微信,短短几年间,文字留言、语音留言、视频聊天、图片分享、微信支付以及公众号,不仅完全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也改造了传统的电信行业,它化解或弱化了原先的某些法律问题,典型如“话费”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体的法律问题,如个人隐私问题、自媒体问题、微信证据问题。对新问题的法律应对可能借助于先前的法学体系,借助于对现有法学知识的演绎,但并非出自现有的法学体系或法学知识,这些应对总体上会更多地来自对经验世界的因果判断和利害考量。
如果人工智能进一步发达,我甚至不得不怀疑,法学人还能否比人工智能更成功地打造有中国特色同时有普遍意义的法学学科体系?!如果“阿尔法狗”的出现根本改变了人类对围棋的理解格局,那么,就没有理由排除在相當程度上改变法学话语体系的“贝塔猫”的出现。而且,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产生出来的法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会同时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吗?这两个词会不会是一个二律背反?
沿着这条思路深入思考的最后结果,非但不会强化法律学人的学术行动力,从逻辑上看,很吊诡地,这种思考更可能弱化甚至湮灭法学人的学术追求和创造冲动。
但也不必定如此。至少有两个人性因素,令人类不大可能在人工智能或大数据等科学技术进步面前完全放弃智识的追求。首先,尽管人工智能大数据展示了巨大潜能,我们还是不敢肯定科学技术就不会出错,足以保证“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因此,有重大缺陷或不足的人类智识追求,至少有时会是人类的紧急出口之一。我们有责任注意保留这个紧急通道不被堵塞。
其次,即便“阿尔法狗”改变了人类对围棋的理解,令围棋国手的智识成为笑话,它还是不能消除人类个体在下围棋过程中——只要不作弊——获得的快乐,仍会有人坚持下围棋。同样,即便人工智能发展出了更有解说力和实践效果的法学话语与法学体系,也不必然要求或规定法律学人就应当或必须从此放弃智识追求。甚至都不是为了什么高大上的“坚守”或“信仰”;就因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因此,对于认真、务实且有所追求的中国学人来说,打造中国特色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个说法,或许就如同张载当年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样,只因为这是某些学人内心深处自发的一种使命感,一种志存高远的追求,即便它无法实现,即便它无力操作。学人只能在其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中务实地研究那些实在的问题,尽可能做能做的事,而不是做想做的事。至少这也会是个提醒,要求中国人文社科学人更多自省和自觉,坚持中国本位,关心中国问题,对问题的所有相关语境条件始终保持敏感,具体地理解和总结中国的经验。
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不可能只关注中国;相反,它一定要求有足够开阔的国际视野,包括社会的、历史的和文明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当代中国的独特性一定是在国际比较、在历史比较、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文明的比较中呈现出来。就此而言,中国问题在理解、认知和表达上不会是自身独立而无所旁及的。基于中国经验的解说必须具有一般意义,即在不同文化的学人之间,在不同学科之间,是可以经验感受和理性理解的。这就要求并规定了,这种解说总体上应当是经验导向和因果导向的。论说方式应当或终将走向社会科学,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它一定要讲道理,这是打造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一个关键。
但在微观的层面,这一追求都只能依赖学人各自的自主选择。我们必须清楚,没有人能对其努力的结果给予承诺和保证,既然有所选择和坚持,就必须准备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如此,就一定会有所发现、突破或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那样,“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甚至,很难说这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认命”。
世界上有些事只能“认命”。这不令人轻松,却还是可能让人从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