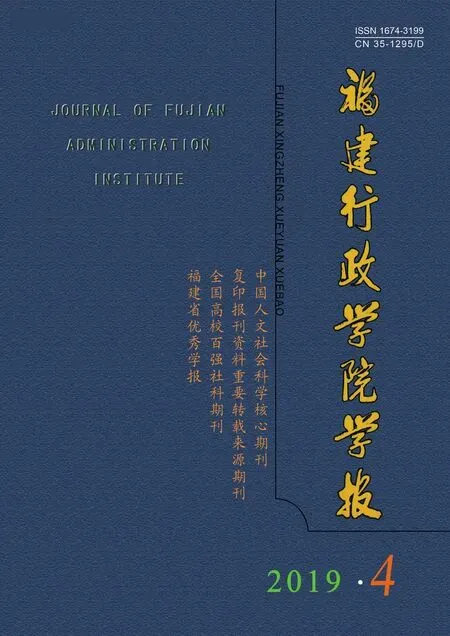农村居民家庭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闽南地区抽样问卷调查的分析
汤兆云
(华侨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般来说,养老关系到供养者和被供养者,其内容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等。经济供养是养老的前提条件,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则建立在经济供养的基础上。相对来说,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尽如人意,心理上也容易焦虑不安,情绪波动较大。老年人不仅需要经济、生活方面的供养照料,更需要精神方面的慰藉,选择恰当的养老方式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从养老的经济来源看,养老可划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一般认为,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在经济供养上,它是代际之间的经济转移,主要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自然完成保障过程。[1]家庭养老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模式。基于传统尊老文化和我国农村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家庭成员在老年人生活中的特有作用,家庭依然是我国农村目前乃至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养老的基石。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4年我国64.2%的农村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帮助,属于家庭养老。[2]1996年8月,北京市进行的一份关于206位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调查数据显示,近九成与子女分开居住的高龄老年人在生活中感到孤独和寂寞。[3]虽然核心家庭规模缩小、老年人寿命延长等原因,加重了家庭赡养老人的负担[4],但是基于家庭养老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功能,家庭养老可以弱化但不会消亡,即使目前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保障的“国家计划”与提供一定社会交往渠道的“社区服务”,都难以替代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5]因此,在我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一步建构制度伦理框架,在全社会弘扬积极向上的尊老敬老精神,扶持家庭养老,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关于全面推进家庭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家庭养老服务在城市社区普遍展开,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背景下,国家也一直强调要发挥家庭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中的基础性作用。2008年1月,《意见》强调:全面推进家庭养老服务,是破解我国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切实提高广大老年人生命、生活质量的重要出路;是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优良传统,尊重老年人情感和心理需求的人性化选择;是促进家庭和谐、社区和谐和代际和谐,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扩大就业渠道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要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形势,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现有研究成果对家庭养老的历史传统、重要意义等都作了重要探讨。但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农村家庭养老的主体和客体都发生较大的变化,并且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决定着家庭养老的被供养者和供养者的主观感受(意愿养老方式)和客观情况(实际养老方式)也存在差异性。基于此,本文以闽南地区抽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村家庭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的意愿养老方式和实际养老方式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态势和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10月对闽南地区泉州市、厦门市和漳州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600份(泉州市、厦门市和漳州市各200份),回收问卷568份,回收率为94.67%;其中有效问卷526份,有效率为87.67%。调查对象分为养老的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分别选择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和30~60周岁的成年人。调查样本按照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1)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是指将抽样过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使用的抽样方法往往不同,即将各种抽样方法结合使用。本次调查第一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市(泉州市、厦门市和漳州市);第二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县(市、区),分别包括泉州市下辖的丰泽区、洛江区、南安市,厦门市下辖的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漳州市下辖的龙海市县、云霄县、漳浦县;第三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乡镇(街道);第四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村委会。方法抽取。
(二)样本分析
调查问卷的自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婚姻)状况、经济收入、现有子女(兄弟姐妹)情况(养老的被供养者填写现有子女情况,供养者填写现有兄弟姐妹情况)等几个因素;因变量分为意愿养老方式和实际养老方式两种情况(见表1)。
本次问卷调查的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主要情况如下:(1)养老被供养者男性人数比例(61.6%)稍高于供养者(52.4%)。(2)60~69岁这一年龄阶的被供养者比例高达96.3%,而供养者主要集中在40~59岁这一年龄阶(75.5%)。(3)基于年龄原因,供养者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被供养者,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供养者比例比被供养者高出了18.7个百分点。(4)就健康状况而言,被供养者的身体状况程度不佳,选择“一般”“多病”两项的比例高达75.9%。(5)被供养者的婚姻状况以在婚为主(84.4%),离婚和丧偶比例为15.6%;供养者的婚姻状况以初婚为主(80.5%),未婚、再婚及离婚为19.5%。(6)经济收入情况分为富裕、一般、不好三种情况,由调查者根据自身主观感受填写。被供养者对“富裕”程度的感受明显高于供养者,两者相差31.1个百分点。这可能跟老年人对物质的期望值较低有关。(7)被供养者子女以二个或二个以上为主,比例为78.3%;而供养者的现有兄弟姐妹主要以一个或二个为主(73.8%),多兄弟姐妹的比例也占26.2%。
调查数据同时显示,对养老的被供养者、供养者来说,在意愿养老、实际养老的三种方式(分别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中,家庭养老都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的意愿家庭养老方式和实际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差别较大。养老被供养者的意愿养老方式比实际养老方式高出了12.5个百分点,供养者的意愿养老方式比实际养老方式高出了4.4个百分点。而就意愿养老方式来说,被供养者选择家庭养老方式比例比供养者高出了5.1个百分点;而实际养老方式,被供养者选择家庭养老方式比例比供养者低了3.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家庭实际养老方式与意愿养老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它是养老被供养者、供养者两者互动影响下作出的最终决策。在这一双向选择过程中,养老被供养者处于被动地位,供养者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虽然养老的被供养者意愿家庭养老这一方式,但是其供养者因工作、住房、经济、抚养子女等原因,更多时候身不由已,被供养者只能接受事实上的非家庭养老方式。这并非是供养者不愿意选择家庭养老这一方式,而是“子欲养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三、农村居民家庭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养老被供养者、供养者对于意愿家庭养老和实际家庭养老方式选择情况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SPSS.18统计软件分析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实际家庭养老选择方式与其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分析,定量探讨不同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一)养老被供养者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对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被供养者的意愿家庭养老方式和实际家庭养老方式与其自变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如果以养老被供养者“意愿养老方式”选择家庭养老方式作为因变量,与其性别(P=0.00<0.05)、年龄组(P=0.01<0.05)、健康状况(P=0.01<0.05)、家庭(婚姻)状况(P=0.00<0.05)等自变量之间的Spearman的rh相关系数分别为—0.189、—0.187、—0.201、—0.198;与其受教育程度(P=0.00<0.05)、经济水平(P=0.00<0.05)、现有子女数量(P=0.01<0.05)等自变量之间的Spearman的rh相关系数分别为0.187、0.195、0.205、0.208。也就是说,女性、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婚姻)状况越不如意的养老被供养者选择家庭养老的意愿越大,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情况越好、现有子女越多的养老被供养者选择家庭养老的意愿越小。如以养老被供养者“实际养老方式”选择家庭养老作为因变量,与其年龄组(P=0.01<0.05)、健康状况(P=0.00<0.05)、家庭(婚姻)状况(P=0.00<0.05)、现有子女数量(P=0.01<0.05)等自变量之间的Spearman的rh相关系数分别为—0.201、—0.205、—0.208、—0.199;与其性别(P=0.01<0.05)、受教育 程度(P=0.01<0.05)、经济情况(P=0.00<0.05)等自变量之间的Spearman的rh相关系数分别为0.185、0.190、0.189。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婚姻)状况越不如意、现有子女情况越多的养老被供养者,其选择家庭作为实际养老方式的比例越低;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和经济情况越好的养老被供养者,其选择家庭作为实际养老方式的比例越高。这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权在于养老供养方这一结论。
(二)供养者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相对于养老被供养者的选择来说,养老供养者“意愿养老方式”与其性别(P=0.01<0.05)、受教育程度(P=0.01<0.05)、经济情况(P=0.01<0.05)等自变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Spearman的rh相关系数分别为0.211、0.215、0.208。也就是说,养老供养者较多意愿和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以及经济情况较好的老人生活在一起。但实际上,女性、年龄较大、健康状况较差等老年人较多的是处于家庭养老这一形式(在P>0.05或P>0.01的情况下,两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处于相对弱势的老年人更需要其子女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等养老,而家庭养老这一形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一点也可以从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对于实际家庭养老的选择结果与其自变量之间的逻辑回归分析看出(见表2)。如果以养老被供养者的健康状况作为协变量,数据分析显示,健康状况越差的养老被供养者意愿家庭养老方式、实际家庭养老方式的比例越高,且养老供养者意愿家庭养老方式、实际家庭养老方式的比例也越高。
基于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对于实际家庭养老的选择结果与其性别、年龄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婚姻)状况、经济情况、现有子女(兄弟姐妹)等自变量之间有着明显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女性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实际选择家庭养老方式的比例分别高于男性16.0、15.0个百分点;以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教育程度较高的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实际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分别比教育程度较低者少21.0%、26.0%。这一结论也佐证了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在实际养老方式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表2 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实际家庭养老选择方式与其影响因素逻辑回归结果
注:表中回归系数B1、B2分别表示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对于实际家庭养老的选择结果与其自变量的系数。
(三)家庭养老方式最终决策分析
以上调查数据及分析结论显示,虽然养老被供养者和养老供养者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或多或少受到其自变量的影响,但家庭养老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养老被供养者、供养者的意愿养老方式分别为70.8%、65.7%,实际养老方式比例分别为比例分别为58.3%、61.3%)。这一比例和目前农村地区的现实养老情况也基本上是吻合的。2016年8月28日,《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8.8%。调查数据同时还显示,养老被供养者的意愿养老方式分别有29.2%、34.3%选择了非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而其实际养老方式分别有41.7%、38.7%选择了非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正如前面分析所示,家庭养老方式是养老被供养者和供养者双向选择的结果,且供养者发挥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村落空心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构建合适的农村居民养老的制度框架,未雨绸缪地应对农村居民家庭养老这一传统方式日益弱化而出现的巨大现实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四、研究结论与分析
基于闽南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农村家庭实际养老方式与意愿养老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在养老的多种形式中,家庭养老仍处于主要地位。这一选择结果是养老被供养者与供养者互动影响下的最终决策。其主要原因有:(1)商业养老模式难以普及。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社会养老保险业务以来,商业养老发展速度较快,保费收入年增长率在30.0%以上,但是农村地区的商业养老保险年增长率不超过5.0%。有数据表明,只有16.5%的农村居民有意愿购买商业保险,远低于48.8%的选择儿女赡养养老方式、28.3%的个人储蓄养老方式。[6]74目前及将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模式难以普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农村传统上的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第二,相当部分的农民群体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加重了家庭养老的份量。调查数据显示,65.2%的农村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了解一点”,有23.6%的人“不了解”,只有11.2%的人“比较了解”,近50.0%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本质和功能了解“甚少”。[6]66第三,目前农民收入的现状难以使商业养老模式大面积铺开。2004年、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平均每人分别为923.9元、1 700.1元,2009年比2004年增长了84.01%;而同一时期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 936.4元、5 153.2元,增长幅度只有75.49%,低于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幅度。特别地,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支出为6 333.9元,已经超出实际收入总额,大多数农民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的经济能力。(2)社会养老保障功能不足。“保基本”是我国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基本原则,由此决定了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是比较低的。目前,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可以得到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约为120元/月。相对于物价和消费水平来说,是比较低的,对于提高60周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一般来说,养老主体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是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地,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百善孝为先”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里,经济因素对于养老方式的影响必然会在“文化滞后”现象的制约下大打折扣,产生一段时期的滞后现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转型进程的加快,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养老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特别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以及人口生育率水平的下降,我国总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水平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高位水平上运行,对于经济状况并不好的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养老方式将越来越处于艰难地位。一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是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2)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之后相当长时期,才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定专门针对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除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外,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人口还无法纳入到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对广大农村人口的部分特殊对象,如“五保户”“灾民”“贫困户”等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救助和保障。在完成对城镇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后,建立健全覆盖农业人口在内的现代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未来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构建须考虑到养老被供养者、供养者的现实情况,并考虑到两者在养老方式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被供养者的保障水平,提高他们养老保险金待遇。只有提高养老被供养者的经济地位,才能使他们拥有除家庭养老方式之外的更多养老方式的选择主动权,并减轻养老供养者的负担。另一方面,在目前农村居民家庭养老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是大势所趋,也是发达国家解决农村居民养老的主要路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村养老被供养者的养老金待遇,并减轻养老供养者的经济负担。这一方面,可以借鉴世界银行提出的老年经济安全“五支柱”模式[7]:即夯实非缴费型的“零支柱”,实行随收随付制的财务模式,其养老保险金支出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以达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兜底”作用;健全缴费型的“第一支柱”,通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制度框架,建立国家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财务模式,为农村居民提供最低生活水平的终身保障;由于农村居民没有固定的职位,相应的职业年金制度(“第二支柱”)可以不予以考虑;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个人的商业保险和理财,建立健全“第三支柱”,以达到提高年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目的;农村居民“第四支柱”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其子女的供养费、亲戚的资金资助和家庭间的资金移转,应健全伦理性的家庭保险养老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