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徒传承”到“导师制”的演绎
■ 陈凯峰
传统的“教”多为师徒间的口传身授的传授方式,人居营造的“鲁班经”也是这样传承于世。
第一,人类的文化发展客观上需要“师承”。
首先,生存空间的营构始于生物本能,也发展于仿构及模仿行为。人类在进化形成的同时,也与所有的动物一样而本能地寻觅自己的生存空间,窟、巢等不同形态的“穴”便是人类最初的居住空间, “以待风雨”(《易传·系辞》载语),是 “建筑”的本原功能。后世不同文化区的人类尽管有不同的“建筑”创构,但出于本能意识的功能目的却是相同或相似的,取所处环境的天然材料,构相近于天然洞穴的“上栋下宇”的“居穴”建筑(参见中古美洲玛雅人的树巢居穴遗构),也就成为地球人居的共性特征,并由此演化发展为后世传统的人类建筑。而本能仿构的信息传递,开启了人类传承教育的先河。

图40-1 人类空间营构行为及认识示意例图
其次,人类非本能的符号开启了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却也碍于载体的不易传递。以现代人类学的概念而言,地球物种进化在形成人类的同时,信息传递的交流方式也有了相应的进化演变,“符号”的出现便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标识。人类信息传递演于动物的肢体动作,“手势语”开启了人类语言之肇端,而后经由“声音语”演进而来的“字符语”,便形成了严格意义的人类语言,语音、语字及语义的确立实现了人类的语言文字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字符”也就成为人类思维信息的一种基本载述方式,并由此而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进或推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各大洲的文明区还不约而同地以“象形文字”为最早的文字形式,各文明区的“字符”都写实于所处环境的物质存在,包括自然物质存在和人类创造存在,后世人们对各“字符”图样的读识,也以“象形”认识为最基本的依据。就比如任何人类群体或个体都离不开的“建筑”,便可能是人类“字符”最早的表述对象,而仿构于自然窟巢的“巢居”应该就是“建筑”最初的一种“象形”字符,如以木构架撑起的一个有重叠空间的象形“上栋下宇”的可规避风雨的围护体“字符”(参见如中国文明早期象形字符图40-1右), 就可能是写实的“重屋” (汉 《说文解字》 释 “楼”用语)建筑的空间描述。而后由此演进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字,便是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只是文字的载体形式有限, 如西亚的“ (泥板)楔文”、 中国的“ (甲骨)刻文”等,再如中国传统早期的刻文成卷的“竹简”“木牍”等,如此极为不易的载文状况影响了信息传递及教育的存在与发展。
再次,空间营构“技艺”既是物质的创造行为,也是意识的表现行为。仅从表面上而言,空间只是生存生活功能需求的满足,似乎只要能有“上栋下宇”的结构、并能满足“以待风雨”的功能,这样的空间创构就是建筑了,就有了其创造的物质意义(参见图40-2左)。其实,就本质而论,建筑更是生存生活方式的体现,特别是文明得到高度发展、并成为“传统”后,人类生存生活都有了一定的社会规范模式,则人居的空间营构就是其行为模式的相应体现。如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秩序的“尊卑”意识概念,同样的空间大小,就有方位与朝向的不同“尊卑”等级的区分,并被视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礼”制(参见图40-2右)。那么,空间营造的技艺就不只是空间的物质形态本身,还应有诸如礼制的意识形态蕴涵,后者更注重“心授”的“师承”。

图40-2 建筑空间营构“物意”结合示意图
可见,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其文化的演进是由一代代人的传承累加形成的,即便是先圣“有巢氏”、先贤“鲁班”等,“教民构巢”,也都只是缘于后世传说,理性而论,其实都是“师承”先辈的成果。
第二,“师承”是一个文化整体,是其“专”的行为动作及行为意识的整体“传承”。
人类社会逐渐繁盛,“师承”成为文化演进的一种基本方式,由此也逐渐有了个体发展的专业取向与趋势,文化便也陆续分化出了诸多的专业构成内容, 故有“师承”教育的“贵以专”之说。无论怎么分专业,其终要“合作”于社会却是不变的原则,所有的“百业”“百工”都有同一工作对象,那就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这一共存体的构成内容或要素也就有其共性特征,并同存于人类创造的“人居”空间里,而成为“同一”的规划体。
于是,人居“同一体”空间骨架的建筑,以现代建筑科学理论的概念而言,就是为了满足社会构成的“百业”功能而营造的。那么,其所“师承”之“专”的对象,就应该是一个人居社会空间的整体,以及这一社会整体的各功能构成的所有内容;而且,对“对象”的认识,也应该有“功能”构成内容与“营造”技艺行为两方面的整体“师承”概念。
一方面是社会“功能”内容的整体性认识的“传承”,这是人居建筑的基本前提。
“人居”是人类窃取自然空间而围构的三维体,“社会”就栖身于这三维体中;而人类的“社会”是一个混杂的复合体,许许多多大小构成交错叠合而近乎混乱,似乎只要人居有“空间”便可以是社会的构成体。于是,人类创造了“人居建筑”,为社会的各构成体提供所需的“空间”,而任何社会构成体均可对“人居建筑”提出所需的“空间”要求,这“空间”要求或许便是“人居建筑”的功能任务或营造前提。因此,认识“社会”是营造者所必须的,当然也应该是营造者职身“受教”的基本内容。
人类社会主要发源和发展于族群聚约后的定居农耕,而后随着定居社会群体的膨胀及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迅猛的发展,这也反过来加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以农耕及渔牧等为主体的“百工”“百业”的传统社会便逐渐形成,且同时有了“六官”或“六部”等的上层管理机构,人类社会空间就是由这“百工”“百业”及“六官”或“六部”等的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官民所居有。在中国传统时期,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官民及社会活动所居有的空间是有“礼制”要求的,除了人居大格局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礼·冬官·匠人》载)及后来演成的“前市后朝”的空间形制外,建筑小空间的“百工”“百业”及六官或六部等同样有功能形制的各种具体要求,其中,尤以“市”的功能大致为人居社会“百业”“百态”的活动中心(参见图40-3左)。这是营造者的匠人或建筑师不可偏废的基本认识,也当然就是其业前“受教”的基本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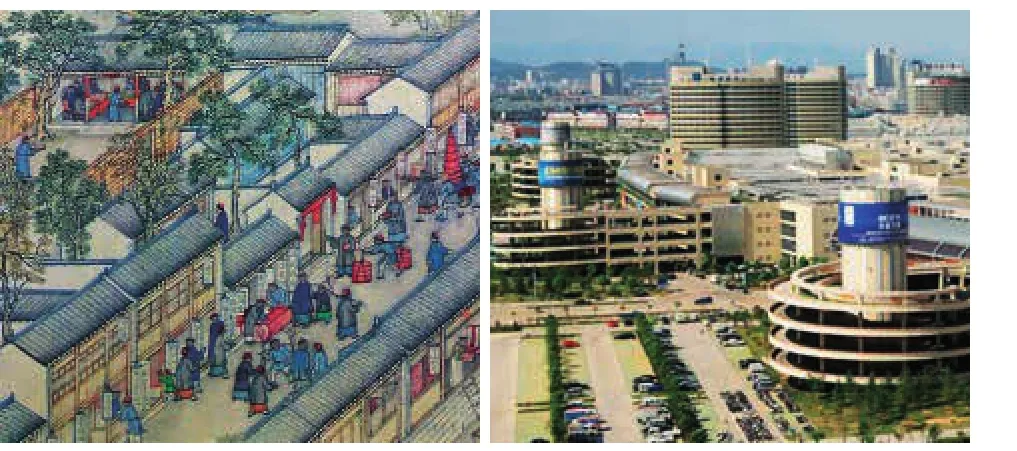
图40-3 人居社会“功能”内容示意例图
近现代后,最显著的社会发展变化就是“百工”“百业”的演化,并根源于工业革命的变革。“工业革命”不仅是社会生产效能的提高,更主要的是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生产有了“工业”的新内容,并有逐渐居社会主导位置的发展趋势,人类世界也因之而出现了“近现代化”的社会演变导向。而后,社会构成的产业、市场乃至科学、教育等都演化为以“工业”主导的结构体系,人居建筑的空间满足也就由此而变“传统”为“现代”的功能内容及形式。最明确的就是建筑功能类型的新类别概念的形成:居住建筑、办公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交通建筑、工业建筑、农业建筑等(参见图40-3右)。现代社会的人居空间就由这些建筑构成,其不同功能的有效满足,同样是营造者“受教”并以此认识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是人居“营造”行为的整体性认识的“传承”,这是人居建筑的合理构成。
现代建筑学理论的奠基者、古罗马建筑师M·维特鲁威认为:“建筑师应当擅长文笔,熟习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律学家的论述,具有天文学或天体理论的知识”。现代建筑学理论便大致是“师承”这一概念,来作“建筑师的培养”教育的。
以现代文化科学的概念而言,M·维特鲁威先生这一“培养”论述的要求是涵盖了人类文化的三大基本层次的,既有形体几何学、人体医学、天体天文学的自然科学知识的要求,也有历史、音乐、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的要求,还要有“哲学”这一人文科学知识的要求,甚至还应当有文、图的基础功底,其要求非常全面。这也应该是M·维特鲁威先生对“建筑师的培养”教育的基本观点,并被后世传统乃至现代所推崇,奉为建筑师教育的经典要旨。
这也正如近代中国“理学”思想家曾国藩所说的: “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曾国藩家书》载语)。建筑师的培养又何尝不是这样?
第三,师徒传承在于其文化深层的“心领”,“技艺”的精髓就在其中,现代教育的“导师制”便缘于此。
明初大学者解缙在论述书法时曾言:“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春雨杂述》载语)。其实不仅是“书法”,中国传统的“百工”“百艺”的承袭,基本上都奉行师、徒上下辈之间的“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以得其“精(要)”的传承。人居社会的空间创造,是人类社会的世代累积所形成的,那就更非仅“建筑”空间的简单叠加。否则,功能空间的“建筑”又怎么能满足日渐发展的有机社会的需求?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人居是随社会的膨胀发展而扩展的,似乎只要有空间数量的直观增加就可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则其空间形体传授的教、学方式也相应简便易行。
印度国土面积仅约298万平方公里,2015年后却已超过了13亿人(此后人口仍呈增长态势),其人口密度超436人/平方公里;再如日本东京,城市面积约2155平方公里,城市居有人口在2010年后就超过1300万人,此后人口增长趋缓,但其城市的人口密度已超6000人/平方公里(参见图40-4左)。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住宅建筑套型主要是30~75平方米,每个套型内的居住人口则或多或少不等;改革开放40年后,住宅建筑套型的建设大多都在90平方米以上,且主要是面对“三口之家”的典型家庭(参见图40-4右)。人们由此认识的人居建筑,似乎就只是社会空间需求的增长,建设者便也仅给予相应的空间满足而已,现代“功能主义”的教育也就是空间形体的叠加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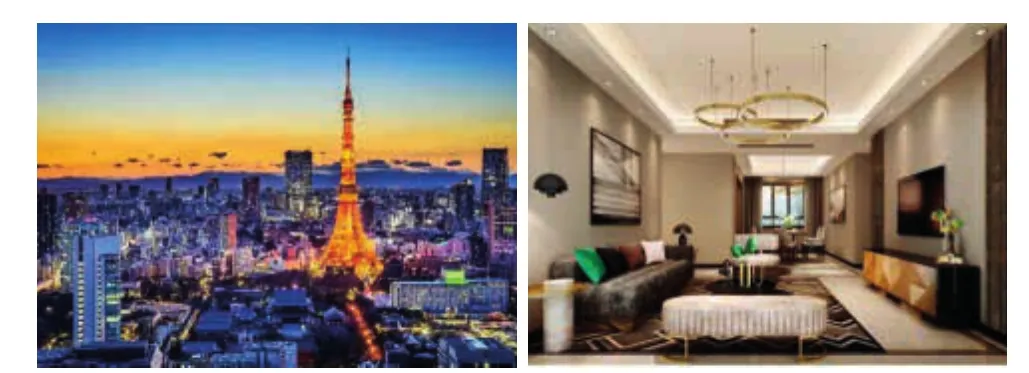
图40-4 人居建筑“空间”认识示意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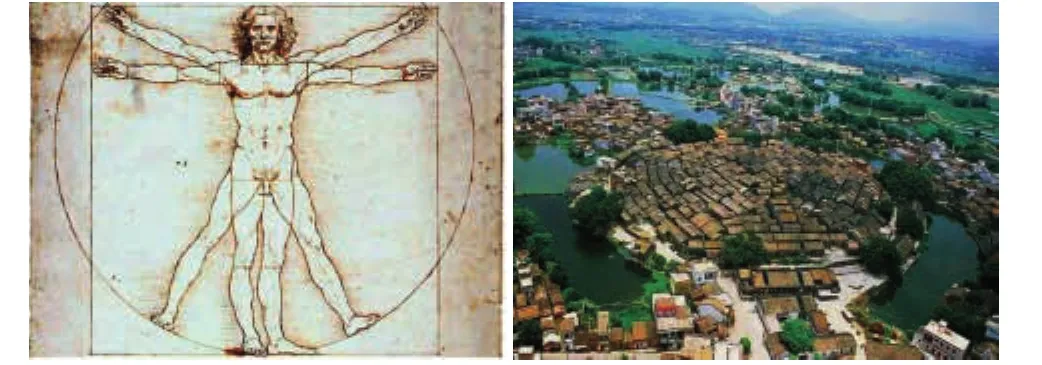
图40-5 人居建筑“本质”认识示意图
人居建筑是有本质内涵的,这一内涵并非任何技艺可形之的,一般教、学的口传身授只能是形体空间的传授,而内涵真谛无形,恐怕只能心领。至于现代专业教育的“导师制”,虽然演于西方近代文明,但中国文明的“师徒传承”的教、学方式早已有之,且在人居的营造上尤为显著,先秦鲁班而后的历代匠人,为中国传统人居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仅遗存至今,可“申遗”的项目就已不可胜数,而这些创造者的匠人,谁人不是“师徒传承”而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