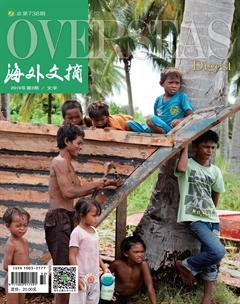平安寺过年记
石野
大年三十下午,我陪母亲从大冶城关赶回那个叫石应高的村庄,住进了平安寺里,准备在寺里过年。
寺庙不大,但古雅。看庙的平时只有一位出家的老师傅。其实,十多年间,平安寺里已经病逝两位师傅,其中,本村的释法通师傅刚刚去世才一年。这一年间,庙里没有遇到合适的师傅,就委托村里一远房大婶每天进庙燃香点烛。母亲欣喜地告诉我:“近日又来了一位新师傅,人不错。平时庙里来往香客不多,大多是四周村子里的乡亲,与其他一些金碧辉煌的庙宇相比,我们这座小庙实在太简陋,但庙里香火从未断过。虽然面积也不大,然而名气还不小。”也许正是缘于“平安”两个字吧。
平安寺的名气自然缘自父亲。祖父去世早,父亲从十六岁时开始养家,伯父去外地当兵后,他更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帮助祖母扶养两个未成年的叔叔。三十岁时,因为有一次做八仙(抬死者安葬)时伤了腰,导致后来无法从事重体力活儿,加上家庭贫困,长年多病,五十多岁时就时常住入庙里。后来也不知何故,竟痴迷佛法,常居山庙,最终驻留距大冶十几公里外的东方山。东方山为鄂东名山,因为汉朝文学家东方朔曾隐居于此山而名声在外。父亲那年进了东方山寺,受大戒而出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家人士。出家后的父亲,身体似乎稍有好转,一直到那年秋末检查出癌症。父亲从京城回归家乡一个月后,就病逝于这座刚建起来的新寺庙里。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夜,一百多名僧人为父亲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坐花缸(亦称坐化缸)仪式:成佛的坐化。六年后,父亲的坟茔,亦在岁月摇曳中,竖起了一座六米高的青塔,坐北朝东,伫立于清晨和黄昏中,默默地等候着我们这些亲人。一向与人为善的父亲,就这样留下了这座平安寺,成为村人四季祈福的合法宗教场所。
新来的师傅叫曹爱,法号释印爱,七十五岁,中等个子。大约要过年了吧,她显得那么精神抖擞,看上去也就六十岁。此时一身干净僧衣,在大门外双手合十恭候我们娘俩。慈眉善目的老人半月前才入住平安寺。之前本村的释法通师傅在此守庙十几年,去年因病去世。释印爱师傅寻上门时,称极喜爱这“平安”两字,愿意在此静心念佛。老人原本有两个儿子,但娶媳妇后,竟然都遗弃了生母,长达十几年不归。失望之余,老人遂遁入佛门。
老远望见母亲,老人如同见到亲人,亲热地招呼着迎了上来。一进寺院,母亲就与师傅一起忙着打扫卫生,给神龛的香炉增添香火。母亲在陀佛像面前烧了一炷香、磕了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师傅则在一边敲三声木鱼。
我撂下大包小包后,則开始在寺庙的前后门贴上自己写的对联,在前庭后院挂上了几只红灯笼,帮助母亲在每尊菩萨像前摆上红蜡烛。这样一到夜晚,就会烛光辉煌。今夜的红蜡烛不仅是供烛,更是岁烛,颇有喜庆的意味。
我特意在父亲灵位前点燃了三炷香,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凝视着父亲笑眯眯的遗像,我不由热泪盈盈起来。要是父亲此时还活着,该有多好!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面黄肌瘦但慈眉善目的父亲,依然如生前那样,手持青色佛珠,笑逐颜开地与我对话。凝望着父亲,父亲生前的种种教诲,如雨如烟般在我的眼前翻腾。这时我才发觉,窗外又下起了雨夹雪。细雨霏霏,绵绵蒙蒙。雪粒如籽,沙沙作响。
春节期间天公不作美,总是小雨霏霏,偶见雨夹雪。我却渴望能下场大雪,渴望看到被大雪压弯的大小树枝在风中抖动着春的独特喜悦。没有下雪的春节,似乎少了份情趣。
小时候过年,父母亲总要给我们兄弟置身新衣服,特别是母亲,白天要忙碌田头上的农活儿,凛冽的冬夜里总是在暗淡的灯光下熬到很晚,一针一线地为几个孩子赶做过年的棉鞋。每到年三十,母亲总会像变戏法般把亲手做的棉鞋和袜子递到我们兄妹手中,或是摆在枕边。除夕晚上,无论多冷,我们一定会好好洗个澡,再换上母亲为我们早就准备好的新衣服及新鞋袜。穿上散发着阳光气息的新衣服,浑身洋溢着甜滋滋的母爱。这样,大年初一就可以焕然一新地去给长辈拜年了。
令我惊喜的是,尚未吃年夜饭,母亲居然又递给我和师傅各一双新鞋袜,乐得师傅不停地念“阿弥陀佛”。我的棉鞋(又叫暖鞋)和棉袜都是黑色。棉鞋是用千层布制作的,厚厚的鞋底缀满了密密麻麻的针脚,那更是母亲手指套顶针,一针一线制作出来的。棉袜子也是母亲用棉线织出来的。我看到师傅的棉鞋和袜子是青色的,难怪老人家穿上后,乐不可支地直赞叹母亲的好手艺,称自己十好几年都没有穿这么暖和的棉鞋了。是呀,这做工复杂的鞋袜,真不知要花费母亲多少个日夜!在什么都可以网购到家的时代,还有谁会一针一线地为子女做鞋袜呢?但我的母亲依然不改初衷,依然每年如此,一定会在严寒中为长年在外的儿子制作暖鞋棉袜。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这个大年夜,只有我才能深深体会到母亲的深沉爱意。只是,我又如何“报得三春晖”呢?我所能做到的是,最好能常回家,多陪母亲坐坐,比如年前,我婉言谢绝了朋友邀请我去东南亚和海南过年的盛情,毅然决然地赶回家乡,陪老母亲过年。从十几岁离乡当兵,到我在南方、北方做记者这些年,我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状,总成为母亲最大的牵挂。因此,在我这游子的心中,能陪母亲过年,能陪母亲一起到远离尘嚣的庙里过年,比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旅游都要温暖。
母亲常说,年好过,日子不好过。过年无需铺张浪费。无论采取何方式,只要轻松快乐就行。其实,过年对于我,正如母亲所唠叨的那样:平安,平淡。记得鲁迅先生在《过年》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连放了三夜的花爆。”可见先生对于旧历年一向是很平淡的。比如眼前的释印爱师傅,早是古稀老人,却遭到儿子的抛弃,打击可谓大矣,老人似乎当一切都没有发生,依然笑对人生。老人根本不愿人供养。幸而有当地政府的低保,幸而她身体健康,尚能下地种菜。在无人照料之下,独立自主,执着地居于庙堂,烧香拜佛,念经吃素,把每个平淡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香火缭绕。
在她的世界中,唯有佛堂才是她最好的栖息之地。亦如我的母亲。母亲常年吃素,无论日子如何坎坷,总能以平淡之心过好每一天。家人的平安,才是她最大的安慰。母亲对生活的平淡心态,不仅是入庙过年,平常每一天,照旧恬静如磐,平淡如水,把大半生的日子过得如村头那一脉袅袅升起的炊烟。
我们在佛乐悠然中迎来了除夕夜。吃团圆饭,燃放爆竹,围火守岁。年三十的夜晚,我们一起动手,做了八菜一汤。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心灵手巧的母亲,还特意用白菜、胡萝卜作素馅,包了几十个芋头圆,象征着团团圆圆。
夜色渐浓。窗外是喧嚣的灯火,在冬夜里跳动着,映衬着乡村最美丽的大年夜。我特意用笔记本电脑,在佛堂里播放出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当年,这位女歌手在事业顶峰时刻,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皈依佛门,放弃了让许多人都羡慕的富足生活,对此事的议论,甚嚣尘上。像当年林妹妹陈晓旭那样,她退出充满利益和诱惑的娱乐圈,独自享受心灵的充实,这更是一种大雅的生活。
我看到两位老人听得很入神,又特意搜索出李娜出家后演唱的佛教歌曲《大悲咒》,禅意浓浓,令人清心定神,也让我在平安寺轻柔的佛曲中,感受到了人间朴素的平和。
年夜饭后,我们仨围着蔸子火“守岁”。 蔸子是我从老屋檐下翻找出来的,至少有十好几年了,一点就着,为除夕夜增添了独特的温暖。熊熊燃烧的围塘之火黄昏时就架起来了。这种温暖也只能在乡村才享受得到。
乡下过年的高潮是除夕之夜。正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庙里没有电视,我特意在火塘边打开笔记本,请两位老人共同观看春晚。晚上8点,春晚开始了。我大喊两位老人快来看,不想都摇头说,刚开始都是歌舞,没看头,等会看看相声和小品。两人只是虔诚地跪在佛像前闭目念经。我又喊了几次,两人依然沉迷于佛语中。直到蔡明、潘长江及葛优主演的小品《“儿子”来了》,才吸引住她们。三个喜剧大咖的跨界合作,让人捧腹,亦令人沉思。母亲看到光头葛优演的那个专骗老年人血汗钱的坏蛋,终于被戴上手铐时,竟激动得站起来鼓掌,连连叫好。母亲之所以激愤,是因为几年前在北京陪同我时,在通州某小区被两名操河南口音的女骗子,以信佛之名骗走了两万多元现金。虽报案,但一直也无果,母亲气得三天都没吃饭。这也是母亲一生中被骗得最惨的一次。平时恨不得把一分钱当着两分使的母亲,又想起了此事,不由得耿耿于怀。
母亲与我一样,认为今年春晚中,只有这揭露骗子以不法手段牟取暴利的小品好看。她对师傅感慨道:可惜这样的节目太少了。后来,我看到网友对今年春晚的评价,竟大多与母亲的观点相近。看来,久居佛堂的母亲,只念过几年书的母亲,文艺鉴赏能力还真不低呢!
除夕夜中,還有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燃放鞭炮和焰火。近些年,因为环保和消防安全,大城市早禁燃禁放,连许多小县城也仿效起来。没有鞭炮烟花过年,让年味淡了许多。但在乡下过年,却不受任何约束,可以逍遥自在地燃放。
春晚迎接新年倒计时的数数儿声响起,新一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快乐得像顽童似的,敏捷地在门外燃起了万字头的鞭炮。为防鞭炮落地打湿,我特意用一根长竹竿挑起,吊下来很长的一串,燃起来,像一条跳跃的火龙,渐缩渐短,留下满地的碎红。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不由想起了王安石那句有名的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燃放烟花当然更精彩。一大箱烟花,我拉着母亲、释印爱师傅以及几位乡邻一起来热闹,可他们都畏缩不前。我就独自点燃烟火,一串接一串。噗噗噗,叭叭叭,砰砰砰,像飞鸟,像星星,像火箭,随着阵阵轻烟飞向夜空,把雨夜装饰得一片璀璨。特别是那直冲云霄的烟花,一朵接一朵,硕大而灿烂,富足而平和,把乡下人朴素的祈盼,绽放成一片通明。美好的生活,总是这么有盼头!
获知平安寺来了新师傅,又听说在京城做记者的我也入住寺庙陪母亲过年,闻讯而来的乡亲一拨又一拨。他们送来的吃食真是无所不有:京果、酥糖、芝麻饼等精美糕点,自家蒸的印子粑、高粱粑和糍粑,有豆腐、藕夹,有的还拎来香气扑鼻的芝麻油、花生油,以及绿色盎然的莴笋和萝卜。都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并不宽敞的平安寺,堆满了半边墙脚的各种食物,散发着浓浓的年味。乡邻的深情厚谊,比起响彻云霄的爆竹烟花、歌舞升平的喧闹春晚,更令人欣喜。我这长年漂泊京都的游子,真切感受到了淳朴的乡情,亦品尝到了最令人动心的独特年味。庙里不断有人进来,亦有人离去。直到午夜一时,还有几个乡亲围着炉火,与师傅和母亲讨论佛法和吃素的话题,令这难忘的大年夜过得轻松而快乐。
佛堂里回旋着李娜那首有名的《南无阿弥陀佛》。安心聆听,渐渐让心灵平静,让人身心倍感轻松。近处听佛曲,心里总会有共鸣,不再想不快的琐碎;远处听之,热闹非凡,由不得你不向往远方的诗意。佛乐中,一年的烦恼和不快,似乎渐渐消失。
子夜两点。佛乐声声中,忙碌了一天的我,早困得低枝倒挂,倒头便入梦。后半夜醒来时,小雨已停。我倚床聆听万籁俱寂的山村夜曲,在烛火的清香中,我不可遏制地思念起父亲,同时亦回忆起平安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2004年深秋,从京城回乡探亲的我,陡然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消瘦了许多,而且在与我聊天时,时不时地用手按着右腹部,很痛苦的样子。我陡然一惊,赶紧问是怎么回事?父亲向来是很坚强的,此时在我这长子面前显示这些动作,肯定是疼得实在忍受不住了。
父亲勉强笑笑,安慰我说:不要紧,又不是一天疼,估计是胃病又犯了。父亲除了在家做农活儿,还经常外出做泥工,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年轻时就有了胃病,但怎么也好不了。如果真的是胃病犯了,也不可能疼得这么厉害呀!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当天下午即拽着父亲去市医院检查。
经B超、CT等一系列检查,一位熟悉的医生将我拉到一边,悄然告知我一个震惊的消息:父亲已是肝癌晚期!我被这可怕的消息击得差点瘫倒在地。我不顾众多亲友的劝说,当晚又火急火燎地拉着父亲坐上了前往北京的软卧火车。父亲显然没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有多么严重,只是不停地唠叨软卧车票太贵了,都可以够他将二楼的几个玻璃窗装上了。我家那建起了三年的新房子,别说装修,就是二楼的玻璃窗上都没有安上玻璃,此时秋风凉了,秋风裹挟着落叶直往水泥板上窜。
- 海外文摘·文学版的其它文章
- 纽约紫水晶(大结局)
- 塑造一个独特的现实世界(创作谈)
- 眼池
- 余光里的人
- 毕业晚会
- N次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