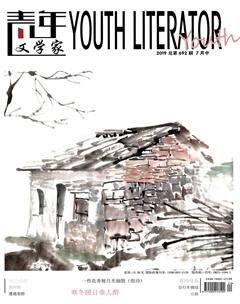浅析《文心雕龙·物色》的生态美学
摘 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是对心物关系的探讨,也是对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进一步阐述,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意义。在魏晋时期,文人对自然态度的转变及自然作为审美客体地位的上升,推进着人与自然健康良好的和谐互动,刘勰在这部文学理论著作中也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自然观。我们将古人已经觉醒却未定名的生态理论萌芽诱发,以今日的生态美学的眼光来对古人的感知进行再认识。本文按照《物色》篇的行文思路,探究刘勰对于心物关系和谐交融及互动中有着逻辑上的递进过程,以生态美学的视角来进一步审视《物色》中逐步升级的生态思想。
关键词:物色;生态;自然
作者简介:刘红玲(1992.7-),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产业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生态美学的要旨就是对“自然”的重视及唤归,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生命的源头,是无限希望的物质寄托,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美学的题中之义 。刘勰在开篇的《原道》中就提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认为自然是文学的本源,并且将自然的觀念贯注于这部文学理论著作之中,可见自然在刘勰心中的至高地位。《明诗》中,刘勰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人有七情,为物所感发触动,进而作诗于胸中,以解情感之欢畅忧愁。当谢灵运走向日出月落,走向洲岛林鸟,走向绿嶂山峦,自然在他的诗中是“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的具象描绘;当陶渊明寄情山水田园,无谓官场纷争,“悠然见南山”也映照出他内心的洒脱与淡然。在刘勰之前的钟嵘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陆机在《文赋》中提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都指出物对于人的感发触动。在《物色》中,刘勰全面地论述了心与物的关系以及审美主客体的交融与互动,是对物我关系的全面解读,是对于前人理论的一种超越和进步。
童庆炳指出,《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多个理论命题是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3]王岳川在《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中指出,要“从生态文化角度重新阐释阅读传统文学经典,从中解读出被遮蔽的生态文化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并且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诗意审美关系[4]。因此,我们将古人已经觉醒却未定名的生态理论萌芽诱发,以今日的生态美学的眼光来对古人的感知进行再认识。本文按照《物色》篇的行文思路,探究刘勰对于心物关系和谐交融及互动中有着逻辑上的递进过程,以生态美学的视角来进一步审视《物色》中逐步升级的生态思想。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5]《物色》的开篇就显示出了丰富的美学意义。季节的更替,景物的变化使人情思摇动。这其中既表达了春秋四季更替对景物的影响,即为 “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6]又表达出季节景物的变化对人的主观情思的影响,即为“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7]当外界景物对审美主体的情感有所触发,不同的景物引起不同的情绪体验,情之所起,发而为辞。“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里所体现的就是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是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触动,以及审美主体对客体作出的审美反应。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对于双方审美关系的重新构建,而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定位是否恰当。刘成纪《物象美学》提出,人是“作为一切自然关系总和的审美者”[8],很自然的是,我们自人类文明的开始,都试图去征服自然甚至奴役自然,这种从本源来的错误定位,致使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中一直充满着各种的矛盾。只有将自然从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让自然实现独立的地位,显示审美主客体的平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才是美学存在的真正根基,这种平等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使美学意义上的主体改变了单向度的追求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我扩张,转而追求人与对象世界在交互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双向的沟通和交流。”[9]因此,当审美主体不再一味追求自我的满足与自由,不再一味使其成为审美主体附庸,重视客体作为另一主体的存在,才能最大可能发掘出客体的存在价值。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平等的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交融乃至互动的前提和基础。这正是刘勰所说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中人与自然双向主体性的情感互通。
二、人与自然的交融
“随物宛转,与心徘徊” 是心物关系在和谐之上的交融,具有丰富的生态美学意义。当审美主体与客体达成了和谐的关系,二者在平等的交互性主体地位里可实现进一步的交融互通。这里刘勰提出了对于主客二体内在的规定性,作者在对自然景物进行描绘的时候,要遵循自然客体的内在规律与特点,同时在作者将自然付诸于笔墨时,又要保持作者内心的尺度,用自我的情感去感受自然,表达自然。在以尊重相互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同时,重视客体的特点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是刘勰在心物交融说中的深刻内涵。
人作为审美主体要以心驭物,但不要过度地驾驭物“主体的充分自由是以对自然物象自由展示美的权利的剥夺为前提,审美化的再造是建立在对物象世界固有的审美品质的不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充满了随意性的审美冲动。”[10] 当主体一旦实现完全的自由,自然又被沦为了人类的附庸,这样和谐关系的构建又一次崩塌,对内在的规定性是物我关系能够持续稳定沟通的有力保障。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宣扬主体驭物的主动性时,也要控制主体对自身在进行审美活动时“随意性的审美冲动”。如何实现心物关系的平等对话,主体对自身审美冲动的克制是其中奥义。“随物宛转,与心徘徊”是心物关系动态的进一步阐发,是物我和谐生态思想基础之上的升级。
三、人与自然的互动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11]刘勰将人与自然高度的情感互通与互动浓缩在末尾的赞中,刘勰并未将物固化,认为自然是带有生命带有话语权的存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是人与自然在建立了和谐共存的关系中进行你来我往的平等交流,让物我二体在情感上形成共振,是生态思想的高度反映。“兴”强调物作用于心,由物触发情感体验进而进行文学创作,“兴”与“比”不同,“比”是由心及物,主体的内心已有了主观情思,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與选择。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提出,比与兴的差别在于心与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区别,心与物作用的先后使其性质出现了根本上的差别[12]。“兴”中包含了更多自然作用于人类的情感,一方面强调审美主体相对主导的审美地位的同时,自然也为作者投射出强烈的情感触发因子,这种直观感性的情感互动,是自然相对于人类另一主体地位的昭示。在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后,又在彼此的交融中进行情感的互动,人类给自然以反馈,形成良好的互动循环。
我们以当代生态美学的眼光来解读《文心雕龙·物色》中的自然观,对其中包含的生态美学及心物关系逐步递进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与解读,我们依旧可以认识到古人对于自然态度的变化,自然地位的改变以及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控制审美主体的审美冲动,来达到对审美客体的挖掘。人与自然是人类永恒要面对的问题,在人类对物质的持续要求与被满足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生态问题被全世界注目的今天,以生态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传统经典对我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5][6][7][1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3-695.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5.
[3]童庆炳.刘勰《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6):265-270.
[4]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38.
[8][9][10]刘成纪.物象美学[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213-214.
[1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