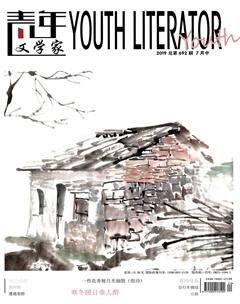从荒诞角度浅析默尔索的形象特征
摘 要:《局外人》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与荒诞文学代表人物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塑造默爾索这个惊世骇俗、离经叛道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人与社会之间的背离,展示了默尔索对抗这种荒诞性社会的悲剧一生。本文首先阐释“荒诞”的哲学含义,接着描述笔者对于默尔索荒诞表现的初印象,进而从三方面浅析默尔索冷漠外表下回归本真的形象特征。
关键词:加缪;局外人;荒诞;默尔索
作者简介:姚时雨(1998.5-),女,汉族,河北石家庄元氏县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2016级法语专业,本科生,学习方向:法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3
一、“荒诞”的释义
荒诞(absurd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absurdus,意为曲调不和(discordant),其前缀ab表示加强,后缀surdus意为“聋的(sourd)”,在荒诞哲学中表示一种与世界隔离、与世人无法相互理解的实际体验,人身处于一种陌生的境况,感到无所适从、无法融入。
加缪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早年丧父,在阿尔及利亚贫民区和母亲过着困苦的生活,少年时期罹患肺结核的遭遇也许让加缪意识到死亡离自己的距离,在加缪此后的作品,如《快乐的死》、《局外人》、《误会》、《鼠疫》中,死亡的阴影总是不断闪现,所幸地中海的阳光与旖旎风光给予了加缪精神慰藉。然而,四十年代加缪因与工作的报社观点不同而返回阿尔及利亚,在一所私立小学教书,小城缓慢而单调的生活让他感到孑然而郁郁,荒诞三部曲《局外人》、《卡里古拉》、《西西弗神话》也在此时诞生。
“在人类的诉求与世界不合理沉默的对峙中,荒诞产生了。”[1]人类渴望得到幸福,盼望着充分享受生活,然而人生必有终点,死亡的必然性让人意识到生命的宝贵和脆弱,“它毁灭了生命中任何基本的确定性”[2],人失去了坦然处之的安全感和立足点,然而日常生活的重复与机械性使人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怀疑,如果人生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中度过,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忍受这种无意义?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荒诞之感油然而生。
二、默尔索荒诞的表面形象
在小说《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Meursault)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用“我不知道”、“我无所谓”的漠然态度表达着他对人情世故的浑不在意,他与碌碌红尘之间似乎有一道透明的墙壁,世人无法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也对自我之外的世界不感兴趣。
“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太清楚。”
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语气中的冷漠与平静让正常人无法坦然接受。而这种冷淡与漠不关心却是默尔索的常态:在母亲的停尸房守夜前喝牛奶咖啡,抽烟,打盹,而母亲的院友进来默哀哭泣,沉浸在悲痛的氛围中时,默尔索却显得犹如舞台之外的观众般打量着他们的神态,思维游离于悲痛的气氛之外,他感到疲惫,集体静默使他难受,他甚至无意识地沉入了睡眠,心情似乎并没有被母亲的去世影响。在棺木下葬之前,他仍然有心情喝一杯“美味的牛奶咖啡”,欣赏着养老院外晴朗美丽的风景,在面容肃穆的送葬队伍中,默尔索却因忍受天气燥热而烦闷不堪,最后终于可以“怀着能在床上酣睡十二个小时的愉悦心情”返回市区。
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让人感觉怪异而难以接受,然而默尔索显然不以为意,他回城后迅速回归了正常生活,工作,游泳,即使在守丧期,仍然与偶然重逢的女同事迅速沉入爱欲。与一些可有可无的朋友平淡相交,对老板发出的升职邀请不冷不热,对女友的结婚请求随意点头,对正义或不公的事情作壁上观,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认为一切都无关紧要。而这种怪异的游离于人群之外的漠然态度终于触碰到了这个社会对他容忍的极限。
默尔索在海边散步时偶然遇见刚刚与自己及朋友发生冲突的人,在与之漫长的对峙中,燥热的温度与刺目的阳光时默尔索烦闷而无法忍受,仅仅是内心的烦躁便使默尔索开了枪,苦难之门被叩响,而他平静而麻木的生活也随着审判的到来就此结束。
至此结束的内容塑造了一个麻木甚至无情,怪异甚至荒诞的人物形象,他的思绪游离,对一切都毫无兴趣,得过且过,与社会与人群格格不入。
三、默尔索回归本真的形象特征
1、直抒胸臆
法庭上,按部就班的例行审判很快完成了,默尔索对罪行供认不讳,审判团很快就对他失去了兴趣,然而正当“过失杀人”的情势不错时,转折出现了:在一次接一次的审判中,调查方向从枪杀转移到了默尔索对母亲去世的态度上,加缪讽刺道:“在我们这个社会,所有在母亲葬礼上不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检察官高声宣告:“我要指控这个人在将他母亲下葬时怀着一颗杀人的心!” 养老院的守门人、院长、母亲的院友以及默尔索的其他朋友邻居都被审问,而默尔索在葬礼上的“不良表现”也被群起而攻之,不合理的调查把他推向了一个荒谬的结局:他被指责,被定罪,被判处了死刑。
然而,荒诞的真的是默尔索吗?当律师问他是否爱自己的母亲时,他回答:“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当然爱自己的母亲。” 但他为什么任由母亲在养老院生活三年而很少去看望她呢?因为他的工资不足以使年老的母亲得到良好的服侍,而养老院可以;母亲和他待在一起时总显得孤独而无话可说,却可以和养老院的院友相谈甚欢,甚至有了晚年的恋人。他又为什么可以如此淡漠地面对母亲的去世呢?在默尔索看来,既然母亲在养老院度过了最后平静而又幸福的生活,她的死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种祥和的解脱,有什么必要为此哭泣呢?
默尔索在世人眼里的格格不入,其实是他对自己以及对别人都贯彻到底的坦然与诚实,他不会为了简化生活、避免误会而矫饰或夸张,他从不说谎,不说谎并不一定代表不说假话,而是不掩饰,不掩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不顾忌社会当中约定俗成的固定看法,坦白直率地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他正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需求与情感,以此为依据做出所有的选择,并为做出的选择坦然承担后果。而这立即让社会觉得受到了蔑视与挑战。”
默尔索的“荒诞”是建立在“正常”的社会之上,而当默尔索的荒诞得到“平反”后,与之相对的社会的荒诞性不言而喻:當默尔索因母亲去世而向老板请假时,非但没有得到慰问,还为老板满脸的不情愿而不得不辩解道:“这不是我的错。”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异化到只有冷漠无情的雇佣关系。而判处了默尔索死刑的法庭宣称着此人“丧失人性”,然而默尔索丧失的究竟是人性,还是虚与委蛇而毫无意义的世俗标准?
在审判中,默尔索认识到了审判过程的不合理,他对此感到失望和厌烦,但选择了不辩解,不参与的消极态度,然而对于审判员的指控和神父的规劝始终保持了坚决的对抗与不妥协。直到最终,处刑前夜,在神父喋喋不休地说教下,默尔索终于愤怒地爆发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对方虚伪而空洞,活着就像死了,“而我,我虽然一无所有,却能把握我自己,把握我的所有,甚至生命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曾经过着这样的生活,也有过另外一种生活的自由,我做过一些事,也有做另一些的自由。”[3]默尔索执拗地坚持着对自己的忠诚,他并非浑浑噩噩,反而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荒诞性,然而荒诞无法消除,即使是形体的自杀也只是为了逃避而选择更大的荒诞[4]57,而默尔索却选择了直面荒诞,在处处受制、被人非议的环境中仍然忠于自己的真性情。
2、“现在”
加缪的第一本小说是写于1936年至1938年的《快乐的死》,然而此书完成之际,《局外人》的轮廓已渐渐清晰,最终加缪选择了发表《局外人》,而《快乐的死》直到加缪去世才出版,对此“甚至可以比喻为:《快乐的死》的幼虫变成了《局外人》的蝴蝶。”[4]31《快乐的死》中,主人公梅尔索为了得到快乐奔波不定后终于感叹道:“快乐的生活并不能更长或更短。当下快乐就是快乐,仅此而已。”[5]129《局外人》虽然没有在追求快乐上使用过度笔墨,默尔索却代替梅尔索践行了这一准则:不被与母亲在一起的旧日时光所束缚,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游泳、约会;也不为未来担忧,对老板发出的去巴黎工作的回应是“都无所谓”,老板意兴阑珊地评价他“毫无雄心”,对此,加缪的确评价他“没有任何英雄主义的抱负”,他唯一在意的只有当下的快乐与享受,对于世人汲汲于出人头地、为了虚无的未来而牺牲了当下幸福的生活方式显得毫无兴趣,“情感上的期望总是假的,所以该以最容易的方式过活——别勉强自己。”[5]131
“他们皆害怕死亡,因为死亡会为人生带来惩罚,而这人生是他们未曾参与的。他们从来不曾好好活着,所以活得不够。而死是一种姿态,使拼命想止渴的旅人从此再也找不到水。”[5]146《局外人》中的神甫、审判者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按部就班,在大众中随波逐流而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也意识不到要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思想陷于囹圄而不自知。默尔索在行刑前嘲讽:“即使他还活着,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默尔索却可以把握自己的一切,包括把握现在,根据自己真实的心意走出当下每一步。
荒诞产生的要素之一即人寄希望于未来、靠未来生活实为自欺,而这剥夺了“现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正是人在‘现在的具体境况中通过行动创造的。拒绝未来、摈弃‘明天是人对‘无意义的反抗。”[2]
3、亲近自然
虽然贫穷与肺病让加缪的人生初期布满阴影,但加缪的故乡阿尔及利亚位于风光绮丽的地中海沿岸,那里的阳光和大海让加缪体验到自然界的丰盛与壮丽,也给予了他难以忘怀的心灵慰藉,大自然的和谐景象因而经常出现在加缪作品中,他“在小说、剧本中多次以月亮、海洋、星辰、山水、夜空等,象征幸福的境界。”[4]40如《鼠疫》中,里厄医生在并肩作战反抗鼠疫的朋友塔鲁袒露心声后与之一起来到了海边游泳,里厄感到“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他的周身”[6]261并“猜测出塔鲁也有着相同的幸福感”。[6]261《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同样热爱游泳,他热爱温醇的阳光,热爱岩石后清凉的海水,从母亲葬礼返回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去了海滨浴场;除此之外,他对于身体的欲望也毫不掩饰,尽情享受,他很快被玛丽丰盈柔软的身体和棕色健康的皮肤所吸引,对玛丽的披肩发和色彩鲜艳的连衣裙赞不绝口,与玛丽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恣意嬉戏。
加缪评道:“因此默尔索对我来说远非麻木不仁,他只是一个坦诚的可怜人,他热爱着不留阴影的阳光。”从默尔索与自然界的亲近与契合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加掩饰,接近自然状态的人,他怀着一腔对大自然、对美好事物的真挚热情,与人性扭曲的社会划开了一条鲜明的沟壑。他面对大自然如此,与人交往时亦如此:20世纪前半叶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高度组织化和机械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战乱频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冷酷,而默尔索没有被社会异化所影响、所扭曲,而是保持着纯真朴实的天性,在面对质疑时仍坚持自己自由诚挚的本心。他以这般孑然独立,返璞归真的形象出现,其影响不啻于一盏指示灯,指引着内心空虚,无处立足的人们。
四、结语
默尔索对坦诚的贯彻,即忠于自己的真情实感。他感受到自己与世人的隔阂,清楚地明白自己生存环境的荒谬,却仍能直视它,拒绝畏惧它,并从中找到生存的享受和乐趣;而对于自欺欺人、甘于蒙蔽自我而安身于不合理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他宁愿献出生命,也不愿屈服。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社会常常因拘泥于陈规陋习而无视了人性的存在。一个个体的人,在现实世界中,往往无端地要承受很多强加到自己身上的意义,被无情地夺去自己应有的自由与真实。面对一个强大的公众社会,个人除迎合和自甘沉沦到群体中之外,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然而默尔索这个在荒诞的世界中央不肯屈服的形象,即使不是灯塔,也在幽暗的现实中点起了一盏小小的灯火,当有貌似合理的压迫出现时,能让我们多一点勇气直面自己,找到生存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lber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p.97.
[2]蔡丽琴,饶红玉,李敏.论加缪荒诞哲学及其意义:哲学史研究,2008年.
[3][法]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馨文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142.
[4]傅佩荣. 荒谬之外:加缪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5][法]阿尔贝·加缪.快乐的死.梁若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6][法]阿尔贝·加缪.鼠疫.郭宏安,顾方济,徐志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