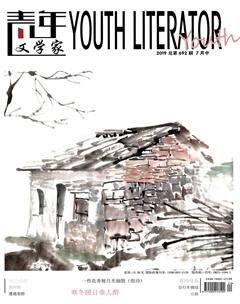“Q”
摘 要: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间距》秉承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有效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和技巧,书写出了现代都市人失落的悲哀和人生的空虚感,以及在混沌之余倾泻出来的温暖的底色。实现了现代主义文学在当代语境下的新表达。
关键词:《间距》;“Q”;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张小霞(1994-),女,汉族,山西省忻州市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一)
合上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间距》,拉拉杂杂的人物关系都随风而逝,盘根错节光影闪回都尘埃落定,阅读界面中的影像简单明了,只有一个“Q”,“O”附加一个“、”。
《间距》行文中在不停地画“O”,以时间线、空间线的形式不断往叙事的宇宙抛出线索,最终又一条又一条地回收到原点。
文章开篇是一个酒局,一帮写东西的人凑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吃有闹。然而酒酣饭饱后,就各奔东西,不知所终,当被要求回忆酒场时,甚至不记得同桌人姓甚名谁:“我对面?没印象。”在个人的维度里,一顿饭而已,吃完拉完就完。
整篇小说的主线是“我”和外号“疯马”的朋友合作写一部谍战片。文章按时间顺序依次推进:“我”接到项目—找枪手“疯马”—雇佣助理—确定议题—策划大纲—商榷细节,就在一切有序进行时,“我”突然被告知“文总被抓了,你这个项目得停掉。”[1](P117)一个简短、粗暴的命令甩出,几天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整个事件的表层意义被消解,一切清零,回到原点。
小说的结尾饶有兴味:“(疯马)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又睡着了。”[1](P120)睡觉意味着旧有事物的结束,意味着现实的隐身,意味着情绪理路从头出发。疯马通过频繁的睡眠在现实中掩埋自己,麻醉自己,逃避自己,在每一个现实与理想近身肉搏即将失控的当口,有效地实现对现实自我的清空,让焦虑消弭于无形。“O”的不断书写使文本处处透着欲说还休的虚无感:“活着,没有意义地活着。生活中根本无所谓重要的事情。生,无所谓。死亦无所谓。存在,也就只是存在。——一切都是不重要的。”[2](P51)徒劳,作为一个关键词,在文本的流动逻辑中时隐时现。而徒劳的終端,仍然有一个出口在预设着自己,这也是小说终末留下的一个开放式隐喻。当北京这个场所不再能承载升出月亮的使命时,寻求空间的扩张无疑是一个可考虑的选择。
“疯马”以梦构筑起了“O”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中也并非真空。我们时时能看到从门缝中倾泻出的一丝光亮。梦中,疯马总是与妈妈对话,并且曾深情地说道:“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1](P111)在虚无荒唐的世界中这句极富感情的梦呓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人击碎,让人在夹杂着疼痛和震撼的余味里沉醉良久。疯马,32岁,远飘北京,居无定所,就像“O”做成的风筝,看似自由自在,逍遥洒脱。然而通过细察,就会发现“O”中一直有根若隐若现的线从中心生发出来牵引着他,让他牵肠挂肚。也正是这根线维系着他生存的意义,使他暗淡的生活有了一抹明丽的色彩。故而,“Q”天然地区别于“O”,这一点虽小但意义重大,它是故事的窗口、人物的退路、情感的缓冲点。
(二)
《间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现代主义文学在当代语境下的新表达。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以竞争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意在表现竞争给人带来的心理紊乱,揭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混乱、无序、梦呓、碎片只是心灵外象。然而,在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不少作品却抛开内容而学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技巧。从而,使得作品气脉不畅,形神分离,给人以强烈的炫技感。游戏文学让作家过足了瘾,但读者并不欣赏。
双雪涛的《间距》跳出了这样的阈限,秉承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使得技巧在意识的作用下被感知和利用,有效地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融合。全文笼罩着虚无荒诞的氛围:策划多日的剧本因一句话而前功尽弃,相处多时的伙伴因计划中止而各奔东西,疯马醒了睡,睡了醒,无始无终,即始即终。一切似乎都有意义,但又确乎毫无意义。所有的这一切只指向一个事实:在这个不断发生着什么的世界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个世界在被剥夺了曾经是它的中心和目的的东西,失去了被普遍接受的统合秩序后开始变得混乱无序,一种全新的审美图式——荒诞也应运而生了。编剧无缘由地殴打了女助理,女助理接受了道歉,却也出于公道,要求还他一酒瓶。编剧痛快地答应了,因而被砸得鲜血淋漓。女助理砸完编剧后主动送他去医院,编剧在医院里包扎好就带着那个像棉签一样的脑袋回到饭局继续吃喝。这场闹剧的上演微缩镜般地展示了现代人病态的精神症状,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手法折射了现代生活的混乱喧嚣。同为现代语境下的读者在感觉可笑之余又可会心于其中的酸楚,共鸣于文本中映射的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生发出某种带着绝望色晕的微妙情绪。
技巧手法为文本结构而存在,混乱的文本世界召唤着现代的表现手法。小说开篇写道“我有个朋友叫疯马。”[1](P99)这种单刀直入、预设叙事主体的做法源自《圣经·旧约》,是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表现手法,意在证实其人其事的存在,让事件本身迫近读者的阅读视域。其次,作者的拼贴技巧也堪称一绝。文中碎片化的内容散落全篇,作者以时间为线进行串联,实现了完美的拼贴。编剧与女助理的故事、间距说、疯马的梦呓,这些碎片犹如一颗颗葡萄,叮铃桄榔地挂在主线这根葡萄藤上,这样的拼贴并没有因为内容芜杂而遮蔽每个碎片的意义,相反,却因意义饱满、内蕴丰富、清晰明了而耐人咀嚼。再次,文中重复手法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作者多次写到疯马的睡。吃了就睡、醉了就睡、翻身就睡、倒头就睡,睡得浑浑噩噩、不知所以。这样多次重复的描写暗示了疯马日复一日都是如此度过,沉浸在睡梦中耗尽自己的青春,醉生梦死某种意义上成为他最好的注解。
另外,文中还充斥着大量的象征手法。月亮,供人遥想仰望,象征梦想。地球,每天脚踏足蹬,象征现实。笔架山,“疯马”的另一维存在,象征著逐梦的超拔欲求。“疯马”的梦呓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妈妈,他回不去了,通往大陆的路也经常被淹没。”[1](P114)一语道出现代人在梦想和现实的罅隙中挣扎的痛苦与求生的艰难。“他”代指笔架山,笔架山作为月亮的儿子为什么要回到大陆?显然,在这个隐喻中,笔架山生于大陆,大陆是“他”的家乡。此时,笔架山象征着一个个身负梦想来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他们都是月亮的儿子,来到喧嚣的尘寰追求梦想中的荣光,然而在受到城市文明的排斥、回首怅望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在竞逐的道路上奔跑得太久,故乡已经成为了他乡,遥隔甚远,再也回不去了。这个故乡不止是现实层面的地域,也是精神的“伊甸园”。年轻人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渐渐入了物欲与名利的罗网,内心失去了原初的底色,离最初白璧无瑕的灵魂也就渐行渐远了。制片人找到“我”做找枪手写戏的买卖时,我先是以“鸠占鹊巢”投以鄙弃,在对方开出高价后又改口应承,这个放置于开头的细节不能不说是这个象征的现实投影。“潮汐是月亮的信啊。”月亮与地球保持着间距,这来源于引力与斥力的微妙平衡,而潮汐则是在这种冷酷的平衡中一个温暖的意外,引力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暗夜里战胜了斥力,在地球的表面泛起涟漪,在喻体的映像上说,梦想与理想主义也在某种悲情的生活角落,获得了与现实的短暂缠绵。月亮象征着梦想,大城市因其物质强势产生了引力,吸引着地球上向往美好的青年引颈翘望,为它而在黑夜里奔走。“我要是能把月亮拉过来,我就能回家了。”[1](P114)把月亮拉过来意味着实现了梦想,然而在小说的视野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种愿望的虚无。“疯马”曾对我说:“我睡一觉就走,但是不会离开北京。”[1](P119)不离京,不是因迷恋而不舍,而是虽失意却不甘。在梦呓的月光拨开“谍战片”的现实霾雾,我们看到了“疯马”内心执拗的期待:梦想达成,风光还乡。或许在他的梦想定义里,不止有功成名就,还有博尔赫斯那般迷幻的艺术造境的达成。即使这个梦想未能轻易触碰,也要力争“复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正如他们讨论剧本时提及的,共产主义对于女主人公是遥远的话,至少也要企望着“新世界”。而现实的镣铐总是冰冷的,剧本女主人公最终不能在爱情里热情地死去,缅想剧情的他们也在资金断裂声前茫然地停下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疯马的梦景与梦魇时的狂暴、剧本与构思剧本的这帮年轻人,都是两个互相映照的镜子,处在符号撞击式的二元嵌套结构中。正是这种二元逻辑里我们看到,在原本自由的梦中“疯马”也失去了飞翔的勇气。“他用手拍着自己的头说:'我只有这么小啊!'”[1](P114)一声叹息显露了“疯马”内心的伤痛。常年北漂,他已磨光了年少轻狂的锐气,不再自信满满、意气风发,现实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小”——卑微、无力。一面是志得意满的梦想,一面是狰狞可怖的现实,这大概才是真正的间距吧。
(三)
当然,《间距》中也有败笔。作为“O”上逸出的那一点“、”画得格外的别扭,深度有余但表现不足。“疯马”对妈妈的惦念都以梦呓的方式显现在读者面前,单一的表达方式略显笨拙。而且为了表露“疯马”的内心世界,作者多次设置“我”碰巧听到“疯马”梦呓的情节,这样的表达使作为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我”勉强承担了全知的透视视角。勉为其难的设置使文章缺乏真实性。最为匪夷所思的一点是“我”与梦中的“疯马”能够形成对话,梦中的“疯马”对于“我”的提问应答自如。“疯马”的梦呓也超乎寻常,非但不散乱而且常常完整清晰、语句绵长、富有诗意:“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潮汐是月亮的信啊。”心灵絮语在梦呓中表达确实更富有冲击力,但应该如何表达还需要深思熟虑,期待作者更好的诠释方式。
《间距》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新阐释。它继承了80年代先锋文学的余绪,也发掘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属性。当代中国社会语境暗合了现代主义文学生发的土壤,期待写作者能重扛现代主义文学的大纛,书写当代心灵史。
参考文献:
[1]双雪涛:《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王晓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