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胺酮
辛西娅·孔斯 罗伯特·兰格内斯

约翰·曼恩在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内
| 派对毒品成为救命之药 |
乔·赖特毫不怀疑是氯胺酮(俗称“k粉”)救了他的命。赖特今年34岁,是一名中学教师,每天都会坐在打字机前写诗,可他多年来饱受自杀冲动的困扰。在纽约州史泰登岛读中学时,他的头脑中就萌生了这种念头,读大一时变得更加强烈。“这是一种内心独白,不断跟自己强调人活着其实毫无意义。”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被自己的大脑伏击了一样。”
大学二年级之后的那个暑假,他第一次试图自杀。当时,他吞下了整整一瓶安眠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服用百忧解、左洛复、安非他酮及其他抗抑郁药,但自杀的念头从未完全消除。他曾用卷笔刀片割伤自己的胳膊和腿,有时还用烟头烫自己。
2016年,赖特决定再试一次。这次他混合了几种药物并磨成粉末,正当他准备将这些粉末倒进水里喝下去时,他的宠物狗突然跳到了他的大腿上,让他幡然醒悟过来。震惊之余,他决定改变这种状态,想办法自救,并开始搜索这方面的信息。偶然間,他发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用药物治疗严重抑郁和自杀倾向的研究,就是注射氯胺酮——一种有着数十年历史的麻醉剂,同时也是一种声名狼藉的派对毒品。
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注射氯胺酮的感觉如同做梦一般:有点奇怪,而且精神愉悦。他几乎立刻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变得更愿意接受治疗。不出一年,他结婚了。如今他表示,负面情绪已经远离了他而且可以控制,自杀的念头基本上已经消失。“如果他们事先告诉我这种疗法将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绝对不会相信。它还没被批准用于治疗具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这不合常理。”赖特说。
没有获批的理由并不完全是医疗原因。在过去30年,制药公司对至少10种用于治疗严重经前综合征(PMS)、社交焦虑障碍和多种其他疾病的抗抑郁药进行了数百次试验。他们几乎从未做过的一件事就是在处于自杀边缘的重症患者身上测试这些药物,其中有出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考虑:医生不想给打算自杀的人提供安慰剂;也有出于声誉方面的考虑:如果有患者在药物试验过程中自杀,会影响该药物的销售前景。
在自杀现象层出不穷的美国,这种风险收益计算发生了变化。从1999年到2016年,自杀率上升了30%,如今已是导致10到34岁人口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而全球趋势正好相反:自杀率正在下降。财富差距日益扩大、退伍军人遭受战争创伤、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及易于获得枪支——这些都被认为是导致美国自杀率上升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突破性的缓解。
但对于治疗自杀倾向的方法终于有了严肃的探索,其核心就是氯胺酮,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制药行业现在看到了出路。首款基于氯胺酮的药物来自强生公司,该药物可能获批成为难治型抑郁症的治疗药物,并在两年之内获批用于缓解自杀念头。在研制针对自杀倾向的速效抗抑郁药方面,艾尔建公司也不甘落后。如此种种,构成了科研领域近年来最具希望的篇章之一。
| 药效好到令人难以置信 |
纽约西奈山医学院院长丹尼斯·查尼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很多家人照片、证书以及在长期科研生涯中获得的奖项。其中,墙上挂着的一件东西与众不同:治疗自杀倾向的氯胺酮鼻喷剂的专利证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药物的开发过程也是查尼职业生涯的写照。
“如果我们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完全错过氯胺酮的抗抑郁效果。”
20世纪90年代,查尼是一位精神病学教授,在耶鲁大学指导当时的副教授约翰·克里斯塔尔,并试图弄清楚血清素缺乏对抑郁症的发病有何影响。在当时,研究抑郁症都是围绕着血清素进行的。1987年获批的百忧解是第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它开创了一个被业内人士称为“跟风药物”研发的时代,这种研究旨在改良现有药物,而非开发新药。在这个狭窄的领域里,制药公司接二连三地推出重磅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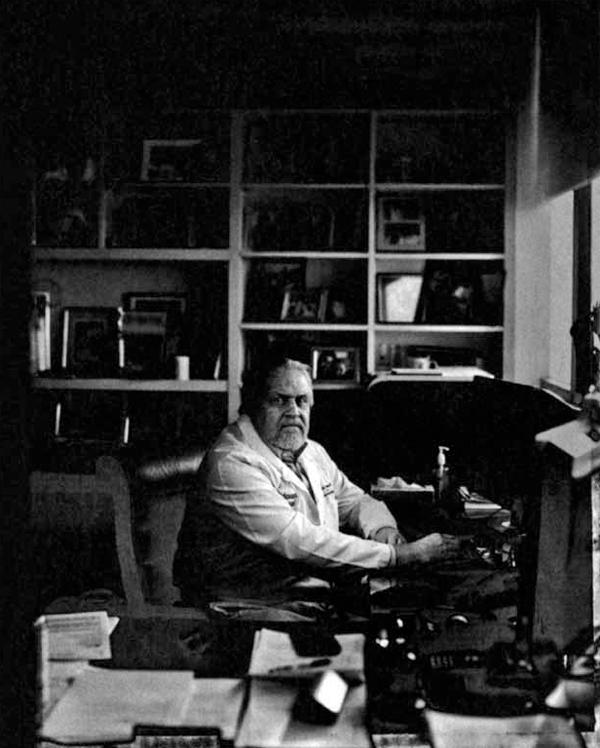
查尼在西奈山医学院的办公室内
查尼是一位抑郁症专家,克里斯塔尔对研究精神分裂症感兴趣。好奇心把他们引向了同一个目标:谷氨酸系统。该系统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可以帮助脑细胞进行交流。它被认为对学习和记忆的形成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尔则称其为“高阶大脑主要的信息高速公路”。他和查尼已在利用氯胺酮暂时制造出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以便更好地理解谷氨酸在该症状当中扮演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中期,二人决定在9位患者(最终有两人退出)身上进行一次单剂量氯胺酮试验,从而观察抑郁症患者对这种药物会产生何种反应,试验地点选定在康涅狄格州西黑文市的耶鲁大学附属机构——康涅狄格州老兵医院。
氯胺酮在麻醉学领域之外的名气——如果有的话,真可谓臭名昭著。街头吸毒者有时吸食的剂量足以让他们陷入所谓的“K洞”,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无法与外界互动。一天当中,这种纯粹是为了自嗨而服用的剂量或许百倍于查尼和克里斯塔尔打算给患者使用的剂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对患者进行72小时监测,远超氯胺酮会对行为产生明显影响的两小时时长,这么做只是为了不错过任何可能出现的消极作用。
施药4小时后,研究人员对患者做检查,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查尼说:“让我们惊讶的是,患者开始表示他们感到好一些了,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有好转了。”这可是前所未闻的。要知道抗抑郁药要过数周乃至数月时间才能起效,而且药物在大约1/3患者身上不能表现出足够的疗效。“我们感到震惊,把这个研究结果压了好几年都没有发表。”如今已是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的克里斯塔尔说。
当查尼和克里斯塔尔最终在2000年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或许是因为试验的规模太小,结果又太理想,以至于看上去不像是真的;或许和氯胺酮作为非法药品的不佳名声有关;又或许是因为副作用,这方面总是存在问题:氯胺酮会让患者陷入精神游离状态,即患者感觉自己的意识和身体是分离的。
不过,所有这些因素或许都不如赤裸裸的经济现实来得重要,制药行业才不会投入数亿美元,对像氯胺酮这样一种又老旧又便宜的药品大张旗鼓地进行研究。1970年,氯胺酮在美国获批上市,而研发它的最初目的只是将其作为麻醉剂苯环利定(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PCP或天使粉)的一种更安全的替代品。
开发一种早就失去专利保护的药物鲜少能带来利润,即使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用途。可不知为何,即便背负着所有这些包袱,对氯胺酮的研究依然取得了进展。这项在当时几乎不打算发表的小型研究,如今已被引用了2000多次。
| 自杀者的大脑与众不同 |
在医学中,自杀被描述为是由一系列精神障碍和艰难情况所引发的结果——这种悲剧可能存在很多根源。严重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都是已知的风险因素。童年创伤或遭受虐待可能也是一个诱因,或许还包括遗传风险因素。
通过这些事实,生于澳大利亚、拥有神经化学博士学位的精神病专家约翰·曼恩取得了飞跃性进展。他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自杀有很多诱因,那么所有倾向于自杀的大脑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此后,他做了一些最引人关注的工作来阐释研究人员所谓的自杀生物学。这个说法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大胆的想法——除了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还有一种潜在的、生理上的自杀敏感。
1978年,曼恩移居纽约。到了1982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开始收集自杀者的大脑。他招募了维多利亚·阿朗戈,现在是自杀生物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在当时,研究死者脑组织的做法已经不流行了,而曼恩想要重启这方面的研究。
他们先是把这项工作和收集的大脑带到匹兹堡大学,然后在1994年又带到哥伦比亚大学。现在他们已经收集了大约1000颗人类大脑——其中一些来自于自杀者,另外的大脑则作为对比物——整齐地摆放在大约零下80摄氏度的冰柜里。
20世紀90年代初期,曼恩和阿朗戈发现,自杀的抑郁症患者大脑某些区域的血清素有微妙变化。曼恩还记得他和阿朗戈及神经生理学家马克·安德伍德坐在一起,分析这些受到缺陷影响的大脑区域。安德伍德是阿朗戈的丈夫,也是她的长期研究伙伴。他们耗费心血,想要揭开自杀者大脑中的秘密,却收效甚微,直到有一天才恍然大悟:这和一项著名的精神病学案例研究中所描述的大脑区域是一样的。
1848年,一位名叫菲尼亚斯·盖奇的美国铁路工人在装填炸药时,因炸药提前爆炸,他的头盖骨被一根长约1.1米的铁夯刺穿。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盖奇的性格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在一篇论文中,医生写道,盖奇的“动物习性”显露出来,还用“最粗俗的亵渎之语”来说话。现代研究表明,这根铁夯破坏了大脑中涉及抑制功能的关键区域——和自杀的抑郁症患者发生改变的大脑区域一样。
对于曼恩和阿朗戈团队来说,这揭示了这样一个情况: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和正常人的大脑差异在解剖学上很重要。
“大多数人会抑制自杀倾向。他们会找到一个不去自杀的理由。”安德伍德表示,然而由于大脑中的某些区域发生了微妙变化,有自杀倾向的人“找不到不去自杀的理由”。
大约8年前,曼恩看到氯胺酮研究在科学界的其他领域突飞猛进,就把这种药物纳入了自己的工作当中。在一次试验中,他的团队发现,和对照药物相比,氯胺酮疗法可在24小时内更有效地减轻自杀念头。至为关键的是,他们还发现,氯胺酮的抗自杀效果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该药的抗抑郁效果,这帮助支持了他们的论点:自杀冲动并非是抑郁症的必然副产品。正是由曼恩的同事迈克尔·格鲁内鲍姆领导的这项研究,让乔·赖特成为氯胺酮疗法的信徒。
| 被重新纳入商业药物研发领域 |
200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聘请查尼主持情绪障碍和实验药物两项研究。对他来说,这是推进氯胺酮研究的完美场所。在这里,他复制了和同事们在耶鲁大学的研究成果。在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NIH的一个小组发现,病人在接受单一剂量的氯胺酮用药两小时之内,产生了“强烈且迅速的抗抑郁效果”。负责这项研究的是研究员小卡洛斯·萨拉特,他目前在NIH负责氯胺酮和自杀方面的研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结果。”萨拉特说。

曼恩收集的部分大脑
2009年在西奈山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念头在施药后24小时之内大幅度消退。第二年,萨拉特团队的研究则显示,这种药在40分钟之内就能发挥抗自杀效果。
最终,氯胺酮被重新纳入商业药物研发领域。2009年,强生公司挖走了NIH杰出的氯胺酮研究员侯赛尼·曼吉,让他负责公司的神经科学部门。在挖角时,强生公司没有明确提出让他将氯胺酮开发成一种新药,但在上任几年之后,曼吉决定介入这个领域。这一次是鼻喷剂形式的艾氯胺酮——氯胺酮的化学近亲。这种药将被允许专利保护。而且这种鼻喷剂消除了静脉注射给药可能带来的问题。首先一条就是,精神科医生通常不具备在办公室管理静脉注射药物的条件。

自杀生物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维多利亚·阿朗戈
科研的车轮缓慢转动时,一些医生——主要是精神科医生和麻醉师——已经在采取行动了。大約是在2012年,他们开始创办氯胺酮诊所。如今美国的几个主要大都会区已经涌现出数十家这样的诊所。医疗保险通常不会涵盖这个领域,但在这些诊所,人们可以支付大约500美元注射这种药物。
2018年9月,美国氯胺酮医师协会召开了第一次关于氯胺酮非传统用法的医学会议。
“你们真的是在救死扶伤啊!”在奥斯汀一间大约坐了100人的会议室里,从麻醉师转做氯胺酮供应商的史蒂文·曼德尔如此说道。这些人大部分是医生和护士,他们聚集在这里,聆听曼德尔及其他早期采用者畅谈他们如何使用这种药物。发言者在讲到该药效果的一些逸闻趣事时,时不时被听众的阵阵喝彩声打断。
| 或将卖得很贵 |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2017年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分册》上的一份共识声明称,关于氯胺酮的用法,“迫切需要一些指导”。作者特别担心的是,关于情绪障碍症患者长期使用该药物的安全性问题缺乏相关数据,并指出,医学界对其长期影响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
在当下,试图自杀的病人常常在入院几天之后就能出院,从而造成一种风险局面:或许还未完全恢复的患者带着一堆抗抑郁药回家,这些药物即便管用,可能也要耗时数周才能提振患者情绪。
一家氯胺酮诊所则是这种危险境况的解决之道,前提是你负担得起费用。对于缅因州饱受双相情感障碍痛苦的53岁居民丹娜·曼宁来说,500美元是不能承受之重。她说:“我每天都想死了算了。”
“这就好比你肩扛50磅重担,氯胺酮帮你卸掉了40磅。”
曼宁曾在2013年过量混合服用阿普唑仑和百忧解等药物自杀。在那之后,她尝试了几乎每一种获准上市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药物,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抑制情绪波动。2010年,抑郁症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让她几乎不能起床,不得不辞去病案专家的工作。电休克疗法是对药物没有反应的抑郁症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此法在她身上也不起作用。
最终,她的精神病医生在翻遍各种医学文献之后,建议她尝试氯胺酮。医生甚至帮她从州医疗补助计划里报销诊疗费用。她一共接受了4次注射,每周一次,然后就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州,这里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可以就近照顾她。
曼宁表示,在接受氯胺酮治疗之后的最初几周,是15年来“我唯一可以说自己感觉正常的时候”。“这就好比你肩扛50磅重担,氯胺酮帮你卸掉了40磅。”
如今曼宁又回到了缅因州,抑郁症也复发了。她现在的医疗保险不能报销氯胺酮。她每个月靠着1300美元的残障补助金生活。“明明知道该怎么治,我却不能接受治疗。单用‘沮丧一词远不足以形容这种感受。”她说。
在科学家看来,氯胺酮是一种“脏药”——它可以同时影响大脑中的许多通路和系统,因此很难找出它在用药后见效的患者身上的确切工作原理。这也是研究人员继续寻找这种药物更好版本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新版本可以获得专利。如果强生公司的艾氯胺酮打入市场,氯胺酮研究领域的先驱和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将从中获益。在查尼办公室的专利证书上可以看到3个名字:耶鲁大学的克里斯塔尔、NIH的萨拉特和西奈山医学院的查尼,他们都能从这种药物的销售收入中获取专利费。强生公司没有就该药的可能定价发表过任何评论,但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自百忧解问世以来抗抑郁药史上最重大的突破将卖得很贵。
氯胺酮和其近亲艾氯胺酮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这一点仍是人们激辩的主题。从本质上看,这些药物似乎给那些因压力和抑郁而受损的大脑提供了一个快速的分子复位按钮。氯胺酮和艾氯胺酮都会释放出谷氨酸盐。反过来,这种物质可能会刺激某些大脑区域的突触或神经连结的增长,这些大脑区域可能在情绪及感知快乐的能力方面发挥着作用。或许,这种药物是通过增强那些脑回路来阻止自杀,同时重建必要的抑制功能,让人们打消自杀念头。
可在阿片类药物危机发生后,人们最大的忧虑也许就是,对氯胺酮类药物的使用过于放松控制,可能会导致一场新的药品滥用危机。这也是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对艾尔建公司的速效抗抑郁药rapastinel热烈期盼的原因所在,该药在试验方面还落后于艾氯胺酮大约一年时间。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药可能和氯胺酮一样,作用于大脑中的同一个目标,但其作用方式更加巧妙,或许可以避免精神游离的副作用以及被滥用的可能性。
“一旦在黑暗中发现了某种有用的东西,你就一定得弄清楚:你能把它变得更好、更快、更安全吗?”艾尔建公司副总裁阿明·塞盖迪说。
[译自美国《彭博商业周刊》]
责任编辑: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