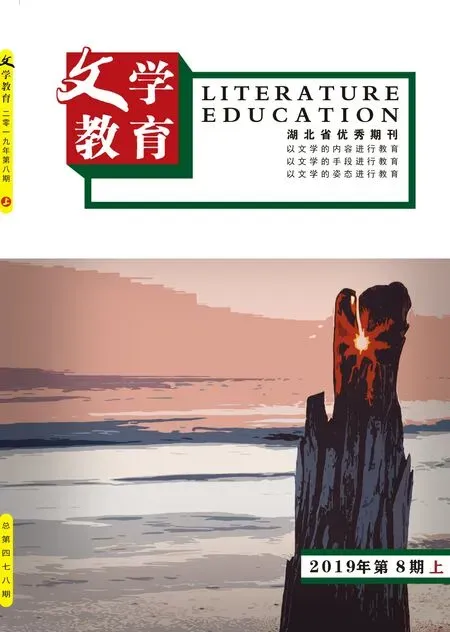永远的先锋
——对话东西
周新民
周新民:我了解到,你是出生在乡村,有哪些因素推动你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东 西:我似乎有点写作天赋。小学时,常写顺口溜或者山歌,被老师选抄到墙报上。读高中时,作文偶尔得到语文老师表扬。看完电影写影评,放进县城电影院的投稿箱,署名“田代琳”的影评被印贴在电影院的橱窗里,还得到电影院奖的四张电影票,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于是,我到图书馆借小说来读,读着读着,就有了做作家的冲动,想把自己遇到的不平写出来。但那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一个念想。
后来考上河池师专中文专业,遇到韦启良和李果河老师,他们本身在写,也竭力鼓动学生们写。看到老师不停地拿稿费,手痒心急,开始悄悄写作,参加学校的“新笛文学社”,听作家老师讲课,参加征文活动。继而,诗歌获奖一次,散文获奖一次。信心爆棚。半夜三更起来写小说,幻想像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喻杉那样一夜成名。稿件一放进邮筒,脑海里就出现画面,想象这篇稿件如何历尽千山万水,到达编辑手里,又如何被编辑赏识,同意发表。十天半月,稿件没发,被退回来了。于是,又改投第二家,还是没发。休息一段时间,找找原因,再写第二篇。那时不敢投太高级的杂志,只投地市级或省级公开发行刊物。内刊发了许多,公开刊物只发表过一首小诗,在《河池日报》副刊上,赏八元稿费。领稿费时,柜台里的阿姨问,你的文章发表了?我自豪地点头。她说不简单呀。那年我十八岁。
现在回想,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恐怕有如下五个原因:一是过早地了解了人间百态,乡村的生活是叙事的,张家长李家短,我七八岁时都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像今天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每天都有新情节,而且还出人意料。这些生活中的故事,一点也不比书上的故事逊色,黄色的尤甚;二是我有满腔的悲愤和委屈,这和家庭成分不好有关,读书时常被同学欺负,有了文字组装能力后,就想把委屈写出来;三是母亲勤劳、善良,她非常辛苦,却一直供我读书,我无以报答,总想用笔来写写她,写她的辛苦和艰难;四是作家这个神圣职业的吸引,那时的作家深受读者爱戴,他们可以为民请命,为民代言,还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像鲁迅,以笔为刀;五是欣逢文学最好时代,有老师们的鼓励,有编辑们认真的退稿信,还有远远超出工资的稿费回报。
周新民:你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广西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的《龙滩的孩子们》。后来又发表了《孤头山》、《醉山》、《稀客》、《秋天的瓦钵》、《回家》、《祖先》、《地喘气》等小说。我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创作,你都是用本名“田代琳”发表的。从一九九二年开始,你用笔名“东西”发表作品。我把你用本名发表作品的时段定位为创作起步时期。你曾说“这个时期没有目标,没有定法”。你能回忆下这个时期你尝试了哪些方法吗?
东 西:读大专的时候,常到图书馆翻看最新文学杂志。当时中国文坛被扯得最多的就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家是贾平凹、韩少功、阿城、何立伟等等。他们所写的乡村与我的家乡相似,一草一木被他们雕刻,乡村的风俗被他们详细描述。越看越有亲切感,特别是平凹先生的《腊月·正月》,仿佛就在写我的村庄,里面人物姓氏与我的村庄人物姓氏巧合地部分吻合,我就想原来我身边也有文学资源,原来越土的越有价值。当时,作家们写乡土题材就像今天的“八〇后”写城市题材一样时髦,这大大提振了我写作的信心。虽然,我没有写过类似于“寻根文学”的作品,但我曾经在日记上,笨拙地记录过乡村的生活,甚至记录过一只鸡如何从我面前走过。后来,阅读了先锋小说,莫言的、马原的、余华的、苏童的、格非的、吕新的……由此上溯,阅读了卡夫卡、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加缪、萨特……那时被罗布-格里耶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震晕,羡慕嫉妒恨,觉得这样的小说才叫小说,由此迷恋先锋小说或者新小说,渴望写出主题深刻、细节精巧、语言独特的作品。
周新民:你早期的作品,如《稀客》、《回家》表现出较强的先锋文学气息。这些文学作品的先锋气质主要体现在语言上,你在这个时期文学语言跳跃性比较强。我们知道,一九八〇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主要注重叙事形式,像马原、格非、孙甘露、苏童均是如此。你为何选择文学语言作为先锋实验的突破口?
东 西:我不喜欢教科书的语言,不想让自己的语言被格式化。看过许多传统小说,觉得冗长,既无曲折情节,也无出人意料的细节,连语言也味同嚼蜡。这样的小说一扯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大都是写三个以上家庭之间的争斗,人物比电话号码本上的还多。评论家说这叫史诗般的作品。但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对人心没有提炼,对现实没有概括,甚至连主题都宽到无边。为什么新小说一刀见血?因为有作家的精心提炼。所以,自己写的时候就想避开冗长乏味,来点新奇,正好先锋小说横空出世,于是就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那时候,我还拿不出别的创新能力,比如思想的、结构的等等,但在语言上来点创新似乎还有可能。
周新民:从你的创作谈中我注意到,你这个时期的先锋文学实验和你的阅读有着紧密的关系。你曾说,“于是,我撇开教科书开列的大师们,专门去读一些我过去闻所未闻的著作,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我开始以创新和不守规矩为乐趣。”你能回忆你在这个时期阅读过了哪些“过去闻所未闻的著作”?这些著作怎样影响了你的小说创作?
东 西:在我读中文专业的时候,沈从文的小说被教科书屏蔽。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媒体开始大肆地介绍他,表扬他,吹捧他,我便找他的小说来翻,一翻就觉得他的小说真实,人物不虚假不浮夸,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沈从文的笔下是准确的,是符合人性的。小说中平凡的人,就像我的邻居。小说中描写的山水,仿如我的家乡。我对乡土的眷恋和热爱,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找到了证据。

周新民
再比如卡夫卡,在教科书中也只是短短的一节,就点了一下他的《变形记》。但他敢把人变成甲虫,仅此一点,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找他的小说来系统地读,才发现他的犀利。他了解人性,看透别人也看透自己,是绝望的写作。而我,对未来虽抱幻想,却不敢乐观。我喜欢卡夫卡看问题的角度,喜欢他的犀利,鲁迅跟他有得一比,是鲁迅的作品让我学会如何处理现实题材,他的深刻是我的榜样。
福克纳的“绕”和“比喻”,对我有过启发。马尔克斯的奇崛与想象,特别是他外祖母讲故事的那种叙述调子,很实用。加缪的冷,萨特的深,我都一度想学。罗布-格里耶的出人意料,莫言早期作品中飞扬的想象力,贾平凹的乡土气息,苏童早期的叙述才华,余华的简洁有力,韩少功持续不断的创新,都曾在我的身上发生过化学反应。我从许多作家身上学艺,凡是我阅读过的,都可能影响过我,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但我更喜欢有探索精神、创意能力强的作家。
周新民:我以为《天灯》是你创作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作品。这篇小说同样是一篇先锋小说,它由四个部分“大火”、“稀奇”、“枯牛”、“散席”组成,构成了空间并置关系。《城外》也是一部致力于打破故事时间的小说。《幻想村庄》则采用“元小说”的叙事方法。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在小说形式上开拓。而这些作品发表的时间是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间,这个时间段被看做是中国先锋小说开始退潮时期,你为何还是如此醉心于小说叙事形式的探讨呢?
东 西:我一直以为小说就是“发明创造”,总觉得自己可以把小说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每构思一篇小说,我都想找一种新的形式。先锋小说被评论界定义为一个流派,但我心目中的先锋小说却是永远的。比如王蒙老师写的意识流小说,算不算先锋?莫言的《红高粱》既打破了传统的抗战题材写作,又在叙述上天马行空泥沙俱下,这算不算先锋?韩少功的辞典体小说呢?应该算先锋吧。凡对写作形式有贡献的,都理应视为先锋写作。现在也还有先锋小说作家,他们潜伏在作家中,潜伏在网络上。他们默默地拓宽写作空间,却无人喝彩,但他们是文学的“发明家”。所以,写先锋小说或者说先锋写作是一个作家不退休的标志,也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周新民:《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发表对你来讲,是具有标志性的。这篇作品不仅仅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还拉开了你小说创作一个新阶段的帷幕。这篇小说开始关注人物的内心隐秘世界。你为何从小说形式探索一下跳到了关注人物的内心隐秘世界呢?其深层次原因何在?
东 西:把聋哑盲三个人放在一个家庭里,也算是一种形式探索吧?但这种形式却得益于现实的刺激。我迷信小说产生于思考和切身感受,而在表达时若能找到恰当的形式,那就大功告成。表面上《没有语言的生活》写得老实了,但试图写出点新意来的想法却是一以贯之的。小说形式的探索,一定要与内容有关,否则就沦落“为形式而形式”了。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可能会为一种新的形式而激动。后来,所谓后来,就是我开始思考“写作为何”的时候,我不再为单纯的形式而激动了。我得先激动内容或者主题,然后再找一个合适的形式。比如《没有语言的生活》,我想表达“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状态,结果盲聋哑这种形式就出现了。写《后悔录》的时候,我最先激动的是“后悔”,好像还没有任何人用二十万字来写过“后悔”,于是我要写,写曾广贤三十年的后悔。有了“后悔”,就找它与现实的关系,虽然他一直认为所有的错都是自己的错,对别人对社会没有一句控诉,但你看完之后,就会发现,一个人过着三十年后悔的生活,难道我们或者这个社会没有一点责任吗?即便是这个不那么先锋的小说,我也在找适合它的形式。首先我找到“如果”,第一句就是,“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那我就开始讲了。”最后一章全是“如果”,曾广贤把自己的选择全部倒回去叙述了一遍,如果我不这样,那就不会这样……“如果”是后悔的关键词。开始,读者知道曾广贤在跟一个人讲述他的故事,慢慢地读者会发觉,听故事的人是个女的,后来又会发现这个女的收费,再后来才知道听曾广贤讲后悔的是一个风尘女子,这个讲述或者叙述的过程就像镜头从特写慢慢拉开,最后变成全景。讲与听的关系,暗示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至于关注人物的内心,似乎从前的小说也关注,可能没那么明显。只要写人物,就一定会注意人物的内心。内心比天空还宽广,是文学的富矿。人物的所有动作都由内心生发。我在一篇创作谈里曾说过,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呢?首先,它是内心的秘密,正如福克纳所说:“必须发自肺腑,方能真正唤起共鸣。”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放的是内部参考,下层放的是绝密文件。假若我是一个懒汉,就会停留在顶层,照搬生活,贩卖常识,用文字把读者知道的记录一遍,但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绝密翻出来为止。这好像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就像卡夫卡敢把人变成甲虫,纳博科夫敢挑战道德禁令。
周新民:以《没有语言的生活》为发端,你的小说充满了非常态的人物形象:有一些生理残缺者,如装着假腿假眼假牙的高动(《跟踪高动》)、瘸腿的马雄(《慢慢成长》)、软骨人邓加(《我们正在变成好人》)等;还有一些身体器官非常态的人,如目光能拉长的刘井(《目光愈拉愈长》)、嗜食的王小肯(((肚子的记忆》)、不会微笑的人们(《把嘴角挂在耳边》);此外,还有一些是心理畸形者,如对丈夫是否有外遇不断猜疑与求证的招婷婷(《猜到尽头》)、偏执暗恋邻居嫂子的春雷(《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连妻子都要双份的老赵(《双份老赵》)等。你为何集中笔墨塑造了这样一些非常态的人物呢?
东 西:这些小说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并非集中笔墨来写非常态人物。小说像树上的瘤,抑或平静水面的一个旋涡,再淡一点,至少也应该是水面的涟漪。如果一个人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既无痛感,也不困难,所有的行为都在准则之中,那这样的人物写一个就够了,因为他们都差不多。而你列举的以上人物,却千差万别,他们分别代表了我心灵的某一小块,也有可能代表了读者心灵的某一小块。或许我已憋成内伤,才会冒出这么多非常态人物来。你要是不把他们拧到一起,我都忘了他们是非常态人物。有人评价《没有语言的生活》时说他们身体虽然残缺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是健全的。因此,这些非常态人物是拿来跟我们所谓的健全人进行对比的。我们过着有语言的生活,但语言却泛滥成灾。他们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却心有灵犀。
周新民:自《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你的小说致力于思想领域的开拓。有三个关键词最能概括你的思想主旨:自我认同危机、焦虑、荒诞。我们下面来一一探讨和分析。首先,你的小说充分地表现了当下社会的自我认同的危机。《离开》、《不要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后悔录》等充分地表现了现代社会自我认同的危机。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专注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危机的中国小说家并不多见。
东 西:《不要问我》中的卫国,因为证件的丢失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最后他害怕自己把自己忘了,就背自己的简历。这不是设计,是写到此处时突然爆发的灵感。我好像也害怕自己把自己忘了,非常不自信。有时魂不守舍,仿佛自己离开了自己。有时后悔,悔到肠子都青。米金德通过找小蜜来寻求认同,我通过写作来寻找认同。为什么喜欢加缪的《局外人》,因为我一直都仿佛在局外。从小我被“高大上”、“伟光正”排斥,是坏分子的后代。而这个坏分子出身,仅仅是因为祖上勤劳,积有田产。一个曾经被排斥的人当然渴望被认同,而被认同何其难也。反向,这个被排斥者,也很难认同别人。
周新民:《睡觉》、《好像要出事了》、《猜到尽头》、《双份老赵》等小说开始关注人的生存焦虑。你选择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有何深层考虑?
东 西:这种关注是无意识的,我没有专门去写焦虑,甚至你不提出来,我都没有意识到。你这么一总结,我就想起最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叫《请勿谈论庄天海》,讲的是谁都不认识这个人,但谁都不能谈论他,谁谈论他谁就倒霉。看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睡觉》到现在的《请勿谈论庄天海》,我的焦虑还在继续。我的创作灵感大部分来自于体验和思考,凡是能让我脊背震颤的感悟或者事件,往往能写成小说。《猜到尽头》里的招婷婷,她莫名其妙地怀疑丈夫有外遇,但苦于没有证据,于是一直猜下去。她为什么要猜?因为社会风气使然,就像《我为什么没有小蜜》中的米金德因为没有小蜜而焦虑那样,招婷婷焦虑的是丈夫可能有外遇。既然有人把拥有小蜜当做必然,那就会有人追问爱情和婚姻是否可靠?招婷婷的焦虑来自于现实的压迫。所以,这些焦虑的小说,也都来自于对人的不信任和对现实的恐惧。我的写作观是:把自己当实验品,放到现实里去体验。只要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一定会感受到来自现实的压力,有了压力,你就一定会焦虑。
周新民:《后悔录》、《把嘴角挂在耳边》、《慢慢成长》等小说表现了生存的荒诞性。说实话,中国作家在表现荒诞感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而你在荒诞感的艺术表现上显然要超出很多作家。你的小说在对荒诞感的表现上是否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在表现荒诞性生存时,你主要采用了哪些方法?
东 西:小的时候,我母亲因为成分问题,被拉去公社批斗,批斗她的理由是唆使我父亲不去修公路,而此刻我父亲就在修路的工地上。当时我坐在喇叭下听那几个积极分子揭批我母亲,拧紧眉头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荒唐?另一条罪状,批我母亲带头捡青籽(可以卖钱),而其实我家一粒青籽都没捡,倒是揭批我母亲的邻居家门前正晒着几簸箕青籽。那时,我不到十岁,就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荒唐(那时候还不知道荒诞一词),一下就理解了什么是颠倒黑白,什么是指鹿为马。读高中时,我就想写作,想成为作家,其原因就是觉得这个世界黑白颠倒了,我要把它写出来。有人认为“文革”里发生的某些事是荒诞的,但现在我的研究生都不知道什么是“文革”,这是不是荒诞?简直是太荒诞了。即便我们跳过“文革”,今天现实中的荒诞比垃圾还多,俯首即是。有时我甚至觉得是荒诞把我逼上了写作之路。开始写荒诞的时候,我并不那么自信,但看了卡夫卡的小说之后,才发现这种写作简直就是写中国现实的最佳方法。重读他的作品,篇篇都指向我们今天的现实,好像他是中国籍作家,还活在我们中间。至于在表现荒诞性生存时我用了哪些写作方法?还是评论家的分析更可靠。也许,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生存的我们,写作时根本不需要什么表现荒诞生存的方法,照搬生活就够了,甚至生活远比小说更加荒诞。最后这十二个字,十多年前我说过,余华和阎连科也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