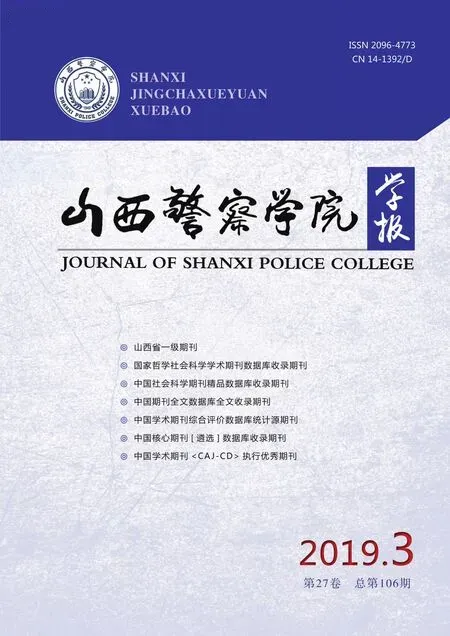论秦汉律中不孝罪的认定
——从杜泸女子甲和奸案到春秋决狱
□陈玉婷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不孝罪是秦汉时期的典型罪名。不孝罪由父母向官府告诉,谒杀不孝的子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曰:“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原)之不?不当环(原),亟执勿失。”[1]在父母向官府告诉子息不孝的诉讼模式下,不孝的认定多由父母自由心证,法律所认可和保障父母对子女不孝的告诉权利,一般不加以限制。《奏谳书》中大夫昌笞奴相如案中,[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汉中守谳:公大夫昌笞奴相如,以辜死,先自告。相如故民,当免作少府,昌与相如约,弗免,已狱治不当爲昌错告不孝,疑罪。廷报:错告,当治。”昌先私自将奴相如笞打致死,为规避法律的惩罚,告相如不孝,为谳所否定。这也是目前可见的简牍文献中唯一一例对父母告子不孝进行限制的案例,否定该告诉是基于昌规避法律而非告诉本身有不当之处,也并不涉及对不孝本身的认定。而在杜泸女子甲和奸案中,针对女子甲是否构成不孝之次的敖悍,廷尉展开了讨论,由此可以一窥秦至汉初对不孝罪的认定,故而本文试图将杜泸女子甲和奸案与春秋决议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寻春秋决狱在“不孝”的认定上的实质变更。
一 杜泸女子甲和奸案中的“次不孝”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杜泸女子甲和奸一案案情如下:

作为一份完整的法律文书,上述文书的内容包括:律文引用、案件基本事实、告—捕—当—议。该案的事实包括:1.丧夫未葬的杜泸女子甲与男子丙和奸;2.婆婆丁在第二天早晨告发甲;3.吏逮捕甲。该案的中心在对女子甲和奸的定性上,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是的话构成何罪。倘若该和奸行为发生在丁生前,根据《二年律令·收律》第192简:“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女子甲和男子丙均应被处完城旦舂。而该和奸行为发生在丈夫乙去世尚未下葬的期间,此时甲虽然处于无夫状态,但是未下葬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使得甲区别于一般寡妇。丁母作为甲的姑婆,告发甲的和奸行为,正是基于该行为发生于特殊时间,认为甲的行为构成犯罪,但这一判断不存在明文的法律规范,仅是基于朴素的法律意识做出的。该案件的核心问题为:和奸行为发生之时,寡居的妻子对已故的丈夫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当所引用的律文如下:
故律:夫死以男为后。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为后。

“故律”是指已不再发生法律效率的律文,说明该案例编纂进入《奏谳书》时,该律文已不再生效。《置后律》中的遗产继承顺序为:子男、父母、妻、子女,依次顺位继承,妻子有继承丈夫遗产的可能性。在《置后律》所列出的亲属中,除妻子是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连结外,其他均有直系血缘关系,故除妻子外其他亲属与被继承人之间均可成立孝的关系:父母—被继承人、被继承人—子男、被继承人—子女。此时“孝”的义务与血缘产生遗产继承关系相统一,即在《置后律》语境下,子息基于法律规定能获得被继承人的遗产,故而有向被继承人尽“孝”的义务,妻子由此产生类比的可能性。而关于归宁的律文,起到了补强作用,进一步说明妻子的法律地位类似于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同时,在期限的规定中,父母、妻子为30日,大父母、同产为15日。这说明,在亲属关系中,父母关系和夫妻关系处在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仅次于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当的推理得出如下结论:
皆曰:律,死置后之次;妻次父母;妻死归宁,与父母同法。以律置后之次人事计之,夫异尊于妻,妻事夫,及服其丧,资当次父母如律。妻之为后次夫、父母,夫、父母死,未葬,奸丧旁者,当不孝,不孝弃市;不孝之次,当黥为城旦舂;敖悍,完之。当之,妻尊夫,当次父母,而甲夫死,不悲哀,与男子和奸丧旁,致次不孝,敖悍之律二章。
其中推出“夫异尊于妻”的根据是“律置后之次人事计之”,即以置后律中继承顺序定尊卑。这一推理的过程为:当被继承人死亡时,被继承人的儿子享有财产继承权,而被继承人儿子的妻子不在继承人范围内,故而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丈夫作为对父亲第一顺位的遗产继承人,其地位远远高于妻子。家庭内尊卑地位可做排序:父>母>夫>妻。由此得出:1.夫妻关系与父母子女关系均为家庭关系中核心和特殊的关系;2.父母子女关系与夫妻关系相比,均存在一方异尊于另一方的情况;3.妻子需要侍奉丈夫,丈夫死后需要服丧,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相同。故而夫妻关系可比照父母子女关系论处,子女对父母需要承担“孝”的义务,故而妻子对丈夫也有类似的义务。引用这一律文进行法律关系的界定和梳理,其本质上是承认法律上“孝”的义务来源于财产的继承。这是典型的从律文—律文推理方式,也是秦律所使用的典型推理方法,即严格限定在律文条文的规范内。此案甲成立的罪名是“次不孝”,适用“敖悍之律二章”,罪名为“敖悍”,最终定刑为完城旦舂。不孝之次非不孝,属于不孝罪外围的与不孝罪相关的罪名。“捕者虽弗案校上,甲当完为舂,告杜论甲。”指明“当”认为此案程序存在瑕疵,但是并不影响量刑。
“议”对“当”进行了否定。“议”并未对“当”所做的对女子甲行为的定性进行否定,而是结合当时的律文对“当”的逻辑本身的漏洞进行反驳,使用类似于后世的“举重以明轻”的方法进行论证。议先对不孝父兄进行解释,明确不孝罪的边界:
律曰:不孝弃市。有生父而弗食三日,吏且何以论子?廷尉鷇等曰:不当论。有(又)曰:有父死,不祠其家三日,子当何论?廷尉鷇等曰:当弃市。有子不听生父教,谁与不听死父教罪重?鷇等曰:不听死父教毋罪。
对生父不善并不当然构成不孝罪,“生父弗食三日”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不论处,而不对死父进行祭祀构成不孝,适用“不孝弃市”的律文规定。其内在逻辑为生父不食三日并不会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而对死父不进行祭祀,则因严重违反了公序良俗构成犯罪。故而在父弗食这一问题上,对死父的不敬要重于对生父的不敬。而在“不听父教”这一问题上,即忤逆父亲的意志,违反死父的意志不构成犯罪,生父的意志重于死父的意志。议强调对父不善应结合具体情形分析,同一行为在不同情况下性质不同,并不当然构成“不孝”。进而展开对本案例涉及的夫妻关系进行论述:
有(又)曰:夫生而自嫁,罪谁与夫死而自嫁罪重?廷尉鷇等曰:夫生而自嫁,及取(娶)者,皆黥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娶)者毋罪。有(又)曰:欺生夫,谁与欺死夫罪重?鷇等曰:欺死夫毋论。有(又)曰:夫为吏居官,妻居家,日与它男子奸,吏捕之弗得,囗之,何论?鷇等曰:不当论。曰:廷尉、史议皆以欺死父罪轻于侵欺生父,侵生夫罪轻于侵欺死夫,囗囗囗囗囗囗囗与男子奸旁,捕者弗案校上,独完为舂,不亦重虖?
夫死婚姻关系自动解除,嫁娶不构成犯罪。同样的,欺死夫也不构成犯罪。而在一些情况下,程序不正当对结果造成影响。在夫为吏,妻子在家中与男子和奸,未被抓捕归案,则不当论。这说明至少在丈夫没有足够的证据以及未被抓捕归案的情况下,不当论。通过欺死夫罪轻于欺生夫,“捕者弗案校上”存在瑕疵,从而驳斥了“当”的量刑。由此可总结出当时通过法律对“不孝”所做出的解释:1.对不孝的对象的扩大解释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进行推理。该案对不孝的对象做的扩大解释的依据为《置后律》,即妻对夫负有“孝”的义务是因为妻有继承丈夫财产的权利,无论继承是否实际发生。2.扩大后的对象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扩大前的对象所享有的权利。该案对不孝的行为是否量刑,以听父教作为类比,采用类似于后世“举重以明轻”的方法进行类比;3.本案涉及的不孝罪内容:不听生父教、不祀死父;居丧不谨;4.采用的推理是完全从律文—律文的推理方式,对“不孝”的行为从外观上进行界定,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二、春秋决狱案例中的不孝
目前可见的春秋决议案例中,涉及到不孝共有三个。相比杜泸女子甲和奸案,这三个案例主要是将汉初不属于不孝罪的殴父罪中引入“孝”的因素进行考量,从而变更判决结果。
案例一: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在该案中,甲误杖父亲乙,行为符合殴父罪的构成要件。董仲舒注重该案的具体经过,“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正是因为看到父亲与他人争斗,儿子出于维护父亲做出了殴打行为,结果因为认识偏差而误伤父亲。对儿子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判断,引入了孝的因素,丰富了殴父罪的构成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引入主观心理因素,也是根据案情事实所补入,是对在一定案件事实下,将行为人的行为放置在一个社会一般人的角度考量。即,对于一个社会一般人,看到自己的父亲与他人斗殴,参与斗殴帮助父亲,击中他人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在董仲舒所引许止的例子中,许止为父亲进药,父亲因此死亡,一年后许止也伤悲过世,故而许止并无谋害父亲的主观心理。这一结论的得出也是考虑到他之后的行为。“君子原心,赦而不诛”,“原心”传统上认为是对犯罪动机的考虑。但犯罪动机一般指“刺激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起因。”[2]而春秋决狱所要重视的,除了现代刑法上归之于犯罪动机的因素外,还包括犯罪目的,即行为人所做出的行为所追求何种结果。该案是一个典型的故意犯罪,包含有明显的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但是由于其本身合乎儒家经义,不以犯罪论处。就性质而言,这个案例是对汉初完全以客观要件定罪的殴父罪在特殊情况下免于处罚的案例,其核心是对子息的行为引入新的评判标准。
案例二: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该案的基本事实为藏匿养子。该案结果“诏不当坐”,即不以犯罪论处。即在一定情况下将拟制血缘关系上升到血亲关系同等地位。在该案例中,甲对乙实质上尽到了抚养义务,与身生父子已无实质区别。《诗》“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出自《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教诲尔子,式毂似之。”表示非血缘的收养关系中,养父对养子的拳拳照顾之意。董仲舒引用此说明,即使是非身生关系中,也可能存在如同亲生父子一样的养育之恩。从而养父之地位等同于生父,在匿藏养子这一情况下,不当坐。
案例三: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其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该案案情为乙杖打无养育之恩的生父甲。春秋决狱认为乙无罪,因养育之恩绝,乙对甲不再负有“孝”的义务。在本案中,甲是乙的身生父亲,但是并未尽到抚养义务,乙由丙抚养长大。董仲舒认为甲乙“于义绝矣”,不存在事实上的父子关系。联系前案,春秋决狱中,就法律上的父子关系的认定,并不以绝对的血缘关系认定,而是强调抚养义务,即根本上改变了杜泸女子甲和奸案中以血缘和继承关系确立孝的义务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其官。”甲前往官府告子乙,正是秦汉简牍文献所出现的“父母告子不孝”。如果是上文的几个殴父案是将一般罪名引入“孝”和“义”的因素对定罪量刑进行重新审视,不再以单一的客观要件为唯一的考量因素,那本案例则是直接对父亲意志的限制,根本上否定父亲的资格,不孝的认定不再以违背生父的意志为绝对原则。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逻辑链条:父母告子不孝成立的前提是子息确实有忤逆父母的行为,而忤逆成立的前提是父亲对女子负有养育的义务。
三、春秋决狱对“不孝”认定的变更
由以上分析来看,春秋决狱在对上述殴父案的断狱中,将儒家经义中的“孝”引入犯罪的考量中,变更原有司法判决。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决狱是运用于司法审判中对定罪量刑进行变更的一项法律技术,并没有触及到立法层面。这可以视为作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对于儒学进入社会一般群众生活的信仰而做出的尝试,而这一尝试是漫长且需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司法判决中的。故而即使是与不孝无关的牵涉父子关系的罪名中[注]殴父罪在汉初《二年律令》时期不属于不孝罪,殴击父亲是比对父亲“不孝”更加严重的行为,相类似的贼杀、牧杀父母也不属于不孝罪。徐世虹在《秦汉简牍中的不孝罪诉讼》中谈到“《二年律令》35简载:‘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以律文可见,在家庭尊卑关系上适用弃市之刑的行为有三:其一,牧杀父母;其二,殴詈祖父母、父母及其他尊长;其三,父母所告之不孝子。仔细辨别律文即可发现,律文所言前两种行为为‘子牧杀’与‘子殴詈’,而第三种行为并非‘子不孝’,而是‘父母告子不孝’。前两种行为罪名内涵清楚,事有专指,而不孝则数罪集合,事无专指。笔者原文已胪列处谋反令父坐死罪、告父、与大母争尊、以母为妻、不供养行丧服、居丧生子、憎毁后母等不孝行为。如果从律文出发,可知汉初的不孝罪中不包括牧杀、殴詈父母。”参考徐世虹:《秦汉简牍中的不孝罪诉讼》,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3 ):124-129.,将父子关系这一事实引入儒家经义的标准对犯罪事实进行重新界定,成为必然之举。而将抚养孝敬事实引入定罪量刑中,作为法律关系搭建的载体,摒弃了完全以血缘关系作为亲子关系界定的唯一标准,这同时正显示出来一种姿态,即国家权力具有进一步介入家庭伦理关系的正当性,而这一正当性,正为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所需要,使得春秋决狱具有被统治者接受的可能性。
(一)孝的泛血缘化
“《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基于“义”对案件事实进行了重新界定,在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标准下,即使构成犯罪,也可以酌情减免。这一认定是对以血缘作为义务连结点的秦律“识别”技术的否定。秦律对不孝谒杀的规定,即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父母的权利,并为之提供便利,达成其意志的执行,执行者是国家。而引入儒家伦理重新界定父子关系,意味着法律具有调整父子关系的正当性,甚至可以否定父权。当然,法律依然是保障父亲的权威,但是这一保障以父亲履行了必要之义务为前提,子息并不具有无条件服从父权意志的义务。有汉一代以孝治天下,注重孝道,却以限制过度膨胀的父权为改革方向,实则为衡平。一方面,讲求秩序等差有别的帝制构建中,父子作为有等差的身份关系需要得到维护,另一方面,过度膨胀的父权将成为国家试图调整家庭关系的障碍,正是儒家伦理为此提供了调和的可能性。
这一泛血缘化的界定经由司法实践对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指引,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儒家经义的行为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肯定,故而民众将儒家经义作为自身行为之标准,从而父慈子孝不再是美好的道德愿景或者理想蓝图,成为可落实于现实的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方案。父子之“义”中父亲对儿子的抚养与儿子对父亲的孝相统一,甚至前者作为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存在。这对于当时社会被极度压抑的子息而言,无疑是“良法”,对父亲而言,为法律所剥夺的权力以道德的方式得到补偿,虽然需进行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非是不能接受的,从而达成了一致。就不孝罪罪名本身而言,“不孝”不再是完全根据父母的意志来界定的犯罪,而是引入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故而“父母告子不孝谒杀”这一规定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唐律疏议》不孝罪和恶逆罪中对“孝”的规定和解释也不再以笼统的父母意志为标准,而是通过儒家经义对孝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
(二)个案正义的实现
纵观春秋决狱现存的几个案例,其目的是实现个案正义。在法律的运行中,特殊个案需要越过法律规则直接适用法律原则,以达到公平正义的实现。就现存的春秋决狱案例来看,均为出罪的案例,而无入罪的案例。这说明当时的实践者就敏锐地意识到将儒家伦理引入司法实践之目的在于实现个案公正,而非扩大罪名。即作为儒生的董仲舒具有将儒家伦理上升至民众行为准则以实现“治天下”的宏伟理想,但作为司法审判官吏的董仲舒则对引入儒家伦理变更既有判决保持谨慎的态度,采用个案正义的方式而逐步积累民众对于儒家伦理的信仰,从而两个“董仲舒”实现了合二为一。此外,就春秋决狱到底是新创造了一个违法阻却事由还是新设立了定罪量刑的标准,笔者认为是后者。违法阻却事由触发后,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而非“赦免”,更重要的是,违法阻却事由是一个立法层面的问题,司法只负责认定某一事实是否构成违法阻却事由,本身并不对违法阻却事由进行定义,而春秋决狱是一个纯粹司法实践层面的问题,且并不仅仅适用于一个罪名或者部分罪名,而是将对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考量延伸到大部分罪名上,实质上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了变更,矫正了秦律以客观要件为主的罪名构成要件。
(三)武帝时期的引经决狱
除春秋决狱外,将儒家经义运用于司法审判活动的还有张汤,《史记·酷吏列传》载: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杨主之明。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闻)〔间〕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史,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
《汉书·食货志》记载: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
张汤决狱本质上是迎合汉武帝对经义的喜好,在司法审判中贯彻皇帝的意志。就时间上而言,大司农颜异因“腹诽”下狱被杀于元狩六年(前117年),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上书《举贤良应策》,张汤引经治狱的时间与董仲舒活动的时间相重合,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毋宁说秦律以完全的客观标准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根据之弊端早以凸显,引入主观因素丰富犯罪构成要件成为时代的趋势,其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正当的途径将其引入法律中。在这一背景下,出现“腹诽罪”是必然的。“腹诽”可谓是将主观要件发挥到极致的走向完全的主观专断的司法实践。抛开这一案件背后的政治斗争,以法律的眼光去审视,可以说是一次超越法律本身,尝试以完全皇帝的主观好恶进行断狱的尝试。而这样的司法案例必然对司法公正性造成极大的冲击,已有的张汤式的阿谀奉承式的经义决狱即使在司法实践中畅通无阻,也是很难放在台面的。与此相比,董仲舒春秋决狱并未创造出新的罪名,采取以实现个案正义的谨慎方式对法律本身进行变革,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张汤编织的完全突破法律规定的经义决狱的吸收、否定和修正。两者虽然具有外观上的相似性,其本质完全不同。当然,当时同样进行经义决狱的还包括儿宽等人,他们“以古法义决疑大狱”(《汉书·儿宽传》)。无论是工具主义的引经决狱、实践主义的引经决狱还是儒生的春秋决狱,他们并列存在于这一时空中,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司法经验,这些立法经验进一步推动立法,使得儒法关系呈现出既对立又融合的局面,而在这一过程中,春秋决狱作为审判方法的历史使命完成,为后世引礼入法创造了条件。
四、结论
春秋决狱的作用在于衡平,将儒家经义引用到对犯罪的定罪量刑中,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其目的在于通过将秦律中并未纳入考量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纳入对犯罪的认定中,将儒家经义与司法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儒家经义从道德规范成为法律规范,实现对民众行为的指引。正如瞿同祖指出“当时的国法(法家所拟定的法律)已经颁布,臣下不能随意修改,须说服皇帝 得其同意,才能修改一两条,如贾谊之例。极为费事,且无成功把握。故汉时儒家大部分的努力仍在章句之注释及以经义决狱。”[3]儒家试图以实现个案正义为手段,变更法家在司法实践中所导致的严苛后果,使得儒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冨谷至认为,秦汉律到唐律从裁判规范到行为规范的过程。[注]该观点来自冨谷至先生2019年5月23日9:00到12:00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725的讲座报告“中国古代的正义”。而春秋决狱正是具有开端性的事件,将儒家经义作为裁判规则应用于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成为儒家伦理吸收进入立法中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