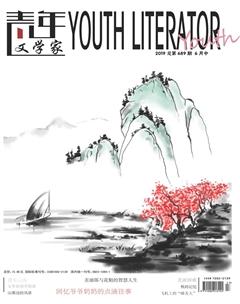《呼啸山庄》中的生态美学意蕴
谭洁凡
摘要:近年来文学评论界对《呼啸山庄》的阐释呈现多元化趋向,多集中于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本文将从生态美学层面对《呼啸山庄》中所出现的自然生态之美,以及自然生态与物化对人性塑造的角度进行文本的重读。
关键词:呼啸山庄;生态美学;自然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156-01
一、荒原情结下的自然生态之美
艾米丽与其家人生活在苦寒单调的约克郡,受荒原环境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艾米丽在作品中更加注重自然生态的描写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追求,充满了对物化社会的对抗以及渴望回归自然,将生活带给她的荒原情结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赋予了文本极大的生态审美意蕴。这种荒原情结表现出对自然的返璞和偏爱。作者自己化身为洛克伍德,来到了“远隔尘嚣的安身之所”[1]四处充满着原始天然雕饰而成生态之美,艾米丽笔下的呼啸山庄的美是乱象丛生中夹带着温和。呼啸山庄处在静谧的大自然之中,缺少人为刻意的美化,赋予了人和自然更大自由。艾米丽笔下的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的童年就是在这荒野中寻求身心的愉悦感,牧师的惩罚都会在这片自由的荒原上消散。
《呼啸山庄》所描绘的自然生态充满活力,艾米丽擅长在动态之中表现鲜活的自然景象,她笔触所涉及的自然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吉顿默礼拜堂的钟声照旧在响,山谷中小溪里,满满当当欢腾奔跳的潺潺流水传来了悦耳的声音。这是在夏日树叶沙沙作响之前美妙的天籁”[2]再如“安静得不仅能听见下而吉默顿那条小河淙淙流水的声音,还能听见山涧流过卵石,穿过它漫不过去的那条大石头中间的小缝隙发出的哗哗、汩汩的响声”[3]泉水溪流的潺潺流动,树叶的沙沙声,鸟鸣,与烟囱上升起的袅袅炊烟构成了一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画面,无不体现着自然景物极强的表现力。西塞尔曾指出艾米丽的作品将人看作是宇宙中的一部分。这种思维冲击了“18世纪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4],应和了当今生态美学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荒原中的人性回归
艾米丽笔下的呼啸山庄是脱离世俗的自然状态,塑造出来的人更像“自然人”,保留着更多的人性本真,例如童年时期的凯瑟琳“情绪总是处在高潮,她嘴里总是不停——唱呀,笑呀,闹个没完……整个教区就数她的眼睛最有神,笑容最甜蜜,脚步最轻灵”[5]。当她第一次来到画眉山庄内心的波动与猜测,她想象着林顿家的孩子也和她一样,显现出了一个孩子的天性,但是随着凯瑟琳、希斯克里夫等人被外界不断的物化以及来自人为的压迫,呼啸山庄的“自然人”逐渐改变。
宗教束缚了人的自然天性。艾米丽虽然生活在牧师家庭,但她钟情于荒原环境,《呼啸山庄》中充满宗教气息,人物语言中也大量存在着宗教典故,这种来自宗教的压迫束缚了天性的释放。在这片自由的自然大地上存在宗教暗含着作者对向自然回归的渴望。《呼啸山庄》有着强烈的反宗教意识,作为本文的“首位第一人称”洛克伍德在第二次访问呼啸山庄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在几本发霉了的书上,凯瑟琳的胡乱涂鸦,她抱怨着欣德利让大家在楼顶上读经。在作者看来一个人的童年时期理应是最贴近自然的,但固定时日的“礼拜天”却遏制了凯瑟琳天性的解放。
艾米丽在创作《呼啸山庄》时有着强烈的回归自然的情思,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的爱情同样是建立在自然天性之上。凯瑟琳选择让老恩萧把马鞭作为礼物,这透露了凯瑟琳想要获得独立的不受人支配的地位的愿望,但这种挑战随着成长逐渐妥协。凯瑟琳误入画眉山庄后“被物化”便失去了本真,而这种物化过程并不是凯瑟琳自愿接受的而是弗朗西斯等人改造的结果。凯瑟琳原本以为林顿家孩子的遭遇和会自己一样,但是当她从窗户望去对于凯瑟琳而言是羡慕这里的富丽堂皇,不会寒冷。初到画眉山庄时凯瑟琳的反映,即本能的欲求并不是其他学者所说的“拜金”,而是一种无功利地渴望。《说文解字》将“美”解释为“羊大为美”,在李泽厚先生的《华夏美学》中也曾提到过我国先民关于美的感悟,美最早与人的味觉密不可分,味觉带来的美感也是最无功利的审美感受之一。同样在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这种对温暖和食物的渴求也是来自人的自然天性。凯瑟琳在画眉山庄养病期间,恩肖太太不断地“用好衣服和奉承话去提高她的自尊心”,在这个物化的过程中凯瑟琳失去了天性。凯瑟琳物化的过程,暗含作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抗。而这种物化是被动的,并未给凯瑟琳带来异化。
艾米丽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人自然天性的丧失含有批判的意味,但在每段故事的结尾又存在着的人性復苏,含有作者回归自然的愿望。在凯瑟琳的结局作者又让人物回归到了自然“凯瑟琳葬身的墓穴不是在礼拜堂里林顿的家族雕花的墓碑下边……它挖在教堂墓地一个旮旯的绿色斜坡上,那里围墙很低,荒原上的石楠和覆盆子爬了过来,泥炭土差不多都把墙埋没了……碑下一块没有雕饰的灰色石头”[6]作者认为凯瑟琳的本性便是属于自然的。在故事的结尾以遵循白然之爱结束了全文高潮。
三、结语
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在的和谐关系是生态美学构建的理论出发点。[7]艾米丽通过记述呼啸山庄这一未被人类“驯化”的“诗意地栖居”,意在呼吁人向自然的回归,同时也存在着作者对自然与工业带来的文明的思考。
参考文献:
[1][2][3][5][6]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页,第158页,第331页,第42页,第171页。
[4][7]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