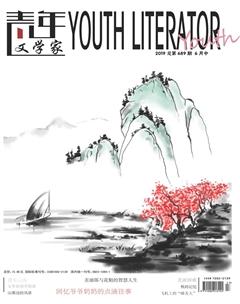分裂与回归
马笑鸽
摘要:“我是谁”疑问的产生是人类试图对自我身份把握和确证的表现,通过镜像、分身等途径构建出“想象的他者”从而达到认知自我的目的。这个过程及结果作为一个线性的时间概念,表现为主体通过分裂而最终达到回归与整合的尝试。本文以《地狱变》为例,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及作者芥川龙之介的悲观人生态度的把握,发掘《地狱变》作为哥特小说背后所展现的文学创作与作者人生观之间的交互,及文本背后“难以救赎”的沉重思想内涵。
关键词:《地狱变》;哥特风格;分身;悲观人生态度;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 -17-124-02
在芥川小说《地狱变》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哥特风格。如良秀作画时对弟子残忍行为的描写,其女儿在火中的场景的刻画,虽然作者用了冷静克制的筆法,但其中的“黑色浪漫主义”特征却不时显现。小说在情节上重暴力和恐怖画而的展现,对丑、恶的事物的刻画;然在主题上,却从中揭示人性的阴暗,进行道德上的探索,颇有一种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意味。由此《地狱变》便由单纯的黑色哥特小说,转为严肃性的悲剧,从中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使读者得到净化与升华,将人从“地狱”中解救出来,得到救赎。但是由于芥川龙之介本人的经历等造成的悲观态度和不安、焦虑情绪,及对国民卑劣人性的深刻把握,“净化”并未实现,作品停留在展现揭露的层而,并未实现“救赎”目的,亦如芥川所言“我相信魔鬼”。
《地狱变》在哥特风格的整体特征下,通过良秀与猴子的分裂对比,大公身上体现出的旁观利己主义,展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挣扎的情绪,以死亡作为结局更是作者悲观人生态度的一种象征性显现。
一、分身与暗恐心理
“我是谁”的追问古已有之,镜像或者分身作为自身客体化的“他者”,在与自我的对抗、冲突和互补中,帮助主体认识自我。弗洛伊德将“分身现象”表述为本我中被压抑的潜意识通过另一种形态的显露,这种阐释在《地狱变》中表现为良秀和猴子的分身关系。
画师良秀在叙述者口中作为残忍冷漠的形象凸显,但是如此冷血丑恶的良秀却非常疼爱其女儿,甚至为了女儿不惜与位高权重的大公争执。但是,随着屏风“地狱变”的逐渐完工,作者对良秀与女儿关系的描写减少,而代之以猴子良秀与侍女之间的“亲人关系”。猴子作为良秀的分身,取代其父亲的角色,是潜意识中爱和善的美好情感的投射;而作为画师的良秀沦为欲望的工具,在追求纯粹艺术中被艺术所支配,结果是自我的部分丧失。
良秀和猴子有相似的而貌特征,在本我和分身的关系中构成一个互补而分裂的结构。他们在故事构成上并无直接的矛盾冲突,而是其女儿作为纽带起连接作用。这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分身设置有所不同,将分身与主体割裂,自我失去了和作为自身客体化的他者之间的接触,便失去了认识自己,反思自我的途径。良秀的存在便被禁锢在画作“地狱变”中,是追求艺术的工具,仅仅作为屏风上残忍场景的创作者得以彰显。其存在环境的黑暗和脆弱性,决定了自我存在的不牢靠性,良秀的不安、焦虑、痛苦感也由此产生。将良秀与芥川联系起来,我们不禁惊叹于作家和人物的一致性。芥川龙之介独特的童年经历,使他不由自主产生逃避感。从周围人惺惺作态的同情,旁观者的利己主义中逃脱,转而进入文学世界。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性及他对于纯文学的极致追求,又使得他受制于艺术,亦如良秀对地狱景象的极致刻画,他们追求纯粹的艺术,但却在自己创造的梦魇中失去方向。芥川作品中对人性阴暗而的深刻揭露,悲观人生态度的流露都是其不安、焦虑、痛苦的表述。
弗洛伊德在阅读哥特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暗恐”概念。指出暗恐的两层含义:一是熟悉的,令人愉悦的;二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其中“疯狂”作为暗恐情绪的母题在《地狱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良秀为了完成“地狱变”对待弟子残忍冷漠;在女儿被烧死的过程中,他完成了画作中最精彩的场景。大公明知道良秀疼爱女儿却要他亲眼见到女儿被火烧死的情景。芥川塑造良秀、大公两个人物形象,刻画其变态的心理和疯狂的行为,却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由于作者极端的刻画,在强烈的对比反差中才凸显了人性的阴暗而及其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广泛认同。正是对日本民众劣根性的深刻把握,才使得他愈发痛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周围的人们很丑恶,白己也很丑恶。目睹这些丑陋而活着是一种痛苦,而且只能强迫自己这样活着。”[1]
二、以毁灭作为必然结果的回归
白良秀画地狱变开始,便是其人性不断丧失的过程,也是他作为父亲和画家双重身份分离的过程。到最后,由猴子良秀承担了父亲的身份,体现的是爱与善等美好情感;画家良秀沦为完成画作的工具,直到最后画下女儿烧死的痛苦场景,身上最后的作为人的情感也失去了。猴子作为良秀的分身,代他履行了父亲的义务与情感,最后跳入火海,与女儿一同丧生。而此时余下的良秀只是作为其艺术追求的抽象,当地狱变最终完成,画师完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其生命也走到尽头。其实在地狱变完结之时,画师良秀就已经消失了,当可证明他存在的环境不复存在,那么他自身的存在也就变得虚无了。所以,第二天良秀作为女儿父亲的身份上吊自尽。在完成画作之后,画师和父亲的身份就完成了统一,归为死去女儿的父亲,而不是作为画师存在。
其实良秀父女的死对良秀来说早有预感,他甚至,在内心深处,隐隐猜到被火烧死的贵妇将会是女儿。在画作快要完结的时候,良秀的情绪越来越坏,经常做噩梦。对女儿的结局他仿佛先验地预测到了,以至于弟子都发现他变得多愁善感,经常躲在没人的地方小声哭。对于已知的结果,却无法改变。画出地狱变必须要亲眼看到贵妇被烧死的场景,大公又绝不会将女儿换成别人。于是纯粹的艺术追求,大公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及隐秘的阴暗心理和父女亲情便构成了一个难以抉择的困境。所能做的也只有在作为画师完成地狱变后,以父亲的身份和女儿一起去地狱,其实哪里又不是地狱呢?良秀无法放弁对艺术的纯粹追求,又难以割舍对女儿的爱,所以死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在最终的死亡中,完成了父亲身份的回归。
自杀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不仅在《地狱变》中体现,在芥川龙之介短暂的生命中亦是如此。他一方面执着于追求文学的纯粹性,不屑于所谓通俗小说的写作,又不断变换文体,可以说每篇作品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穷于应对生活,想要逃离各种媒体、读者,却又难以忍受神经衰弱的痛苦。加之心里对于可能患精神疾病的不安,又逢上姐夫自尽,本来自己已经自顾不暇还要担上照顾姐姐一家的责任。想要逃离却无处可逃,现实世界和精神生活都是沉重的、丑恶的,所以到底如何选择,妥协或者抗争?
在其成名作《鼻子》中,芥川選择了妥协。为了和别人一样,内供找遍办法最终缩小鼻子,可是大家却不满意了,虚假的同情心背后掩藏的是高人一等的心态,是旁观者的利己主义。那么抗争呢?良秀选择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再理会别人的眼光,然而亲情与艺术的冲突却导致良秀不同身份角色的分裂,在最后选择白尽。正如良秀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在芥川这里体现为现实与纯文学、现实与精神的冲突,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中,他最终选择死亡。反抗的结果无疑是失败了。
三、芥川龙之介的悲观人生态度
(一)芥川独特的人生经历
疯子的儿子,似乎使他一直抱有自卑的心态,在别人若有似无的同情心中他看到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阴暗的国民心理;作为舅舅家的养子,所有孩子能表现的任性在他身上就没有了,他对自己处境的敏感认知(在养父母家的“寄居”身份),使他一直处于一种顺从的状态,甚至因为养父母的反对而迫不得已与初恋吉田分手。
父母姐姐的死亡在他心里过早地埋下“死亡情结”的种子,对死亡的害怕和隐秘的向往构成一组矛盾冲突,在其作品中亦有表现。在芥川生命的后期,照顾姐姐一家的重担成为他死亡的催化剂,本来就对生活几近绝望的人又要背负更大的压力,姐夫的自杀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二)对于阴暗人性的深刻认知
“周围的人们很丑恶,自己也很丑恶。目睹这些丑陋而活着是一种痛苦,而且只能强迫自己这样活着。”在芥川这里,活着似乎难以忍受,是一种绝望的挣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把握使他一直处于悲观厌世的状态。在《鼻子》中表现的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地狱变》中大公隐秘的阴暗内心,《齿轮》中处处体现的不安,都成为其结束生命的原因。当生活处处都使人感到绝望,自己又无从获得希望之时,死亡便成了唯一的解脱。
结束语:
《地狱变》一方面采用哥特风格,注重对恐怖场景的刻画,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的冷静客观笔法,又显得含蓄。以画作“地狱变”和绘画的过程相互呼应,通过对人物阴暗心理的描写,冷漠行为的刻画,及主人公良秀的分裂与挣扎,最后选择死亡,捕绘出一个“人间地狱”的景象,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但是由于作者芥川的悲观人生态度,对人性及社会的失望,而终究未能起到净化与升华作用,未能以上帝之爱救赎大众,只是揭露和呈现了堪比地狱的人间。
注释:
[1]高惠勤,魏大海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2005年版,第62页.
参考文献:
[1]李里.爱伦·坡哥特小说中的暗恐研究[J].珠江论丛,2016(1).
[2]周婷.从哥特文学的分身主题看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J].文学教育,2015( 2).
[3]刘士泽.芥川龙之介晚期创作及其自杀原因[N].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4月15日.
[4]陈榕.哥特小说[J].外国文学,2012 (4)
[5](日)芥川龙之介著;楼适夷等译.地狱变[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