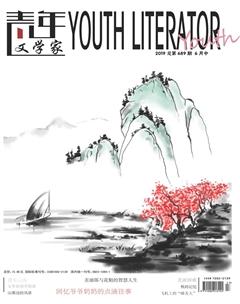《长恨歌》的文本层次研究
原冬青
摘要:《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虽然好评如潮,却也有某些方面的不足,比如语言的过分雕琢,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以及悲剧性不强还需深挖其悲剧意蕴。在童庆炳版的《文学理论》中,将文本层次分为语言、形象和意蕴三个层面,基于此理论,本文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性”的语言,第二部分是扁形人物形象,第三部分是悲剧意蕴。
关键词:《长恨歌》;文学性;扁形人物;悲剧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44-02
引言: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优秀的作家之一,最近她再次被选为上海作协主席,可见她对上海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之大。她的代表作《长恨歌》也更能体现出上海文学的品质,本文基于文本層次的理论,分别从语言、形象及意蕴这三个层面来批评《长恨歌》,以便读者能辩证的阅读该作品。
一、“文学性”的语言
若单从《长恨歌》的剧情设置来看,它无异是一部博人眼球的三流言情小说,如出卖色相的选美、老套的三角恋、军中政要包二奶、和阔少苟合诞下私生女、忘年交的“畸恋”以及狗血的凶杀案等,一部言情小说所需要的情节套路应有尽有。那么《长恨歌》为何没有沦为廉价的玛丽苏剧,反而斩获无数文学奖项,原因就在于王安忆“文学性”的语言拯救了这部作品,使它戴上“纯文学”的桂冠。
“文学性”的概念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他认为文学的自足性源于“文学性”,而“文学性”又源于文学语言及其构造原则,只有“陌生化”的语言才能产生文学性。而《长恨歌》的语言正是符合了这种“陌生化”的审美功能,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表现为语言的雕琢,与语言“陌生化”相对立的是“自动化”,而“白动化”的语言可脱口而出无需进行雕琢。显然在《长恨歌》里,作家对每句话都做了精细化的处理,比如对弄堂的描写“街道和楼房凸显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将弄堂的风景看做一幅水墨画来描写,而作者使用的语言技巧也类似国画中的“细工笔”,笔法绵密细致,精谨细腻,色彩绮丽,一笔一画的渲染涂抹,可见作者文字功底的深厚,但过分的雕琢显得匠气太重而缺乏浑然天成的灵气。甚至连每章节的题目命名都显得刻意雕琢,比如“围炉夜话”、“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外空余黄鹤楼”、“祸起萧墙”、“碧落黄泉”等等,看似是对章回体小说的继承,却没有全部用对偶句来做回目,个别带有古典韵味的题目夹杂在所有小题目中显得不和谐。这也暴露出“雕琢”的弊病,虽然从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文学语言“陌生化”的特点,但过分修饰后的文风显得不够自然,甚至因拖沓冗长而变得失去趣味。
其次表现为语言的议论性(过度阐释),有读者认为《长恨歌》像散文诗,实际上其语言的议论性大于诗性,与其说它像散文诗,不如说像议论性散文。虽然从文体上看这部作品是小说,但作家并没有完全使用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夹杂了大幅度的议论,相较于只注重情节描写的叙述话语增强了读者的感受难度,因此语言的议论性也是语言“陌生化”的表现。
议论性散文的语言具有抒情性、形象性和哲理性的特点。比如文中的一段议论:“外婆看着眼前的工琦瑶,好像能看见四十年以后。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工琦瑶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于一点,就是长得忒好看了。这也是长得好的坏处。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帮着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这段话就像《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有着预示佳人命运走向的作用,可以从语言的议论中感受作者的睿智和深谙世事。但议论性的语言过多,似乎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托盘而出,知一说十,唯恐读者的审美水平有限读不懂,又因为作者在议论时主观意愿太强而剥夺了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削减了读者的阅读快感。
二、扁形人物形象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典型上海弄堂里的典型人物:“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可见王琦瑶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一个“符号”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管是在弄堂,在爱丽丝公寓,还是在平安里,王琦瑶都只具有抽象的象征意义,而不是一个丰满的、具体的,有独特个性人。作为主人公的王琦瑶实际上是个“扁形人物”。
文学创作上有“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之分。把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称为“圆形人物”,把具有简单性格的人物形象之称为“扁形人物”。这种分类是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提出的。他认为“扁形人物”“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总之指那些性格固定,不受环境的影响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类型为符号化、抽象化的人物,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小说中的王琦瑶便具备以上特点。
虽然王琦瑶经历了几段感情,但给人的感觉是:“流水的男人,铁打的王琦瑶。”仿佛王琦瑶在学生时代就已定型,她和同龄人(吴佩珍或蒋丽莉)相比,情商高且早熟,不仅有着不俗的相貌,也很擅长管家,已然是一个少妇该有的模样。但随后的人生经历对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逆来顺受而不自知,明明是主人公,却像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没有歇斯底里的抱怨过,也没春风得意的显摆过,没有变得昂扬斗志,也没变得萎靡不振,还是一副恬淡的少妇的情态。她顺水推舟的甚至麻木的走完余生的路,除了被岁月添了几道皱纹外,心智似乎没有“成长”,精神境界也没有升华或提高。作为旧时代的女知识分子,从她身上没有体现出半点“形而上”的或“积极向善”的东西,也看不到蓬勃迸发的“生命力”,时代在变,她却故步自封永远活在过去,死气沉沉像一件旧家具,纵然精美也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当然也看不到她的人生追求,没有人生追求便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她似乎只会围着男人转,而这种“转”又无关于爱,只是寂寞时的情欲宣泄和孤寂时的意乱情迷。除了男人,她的小世界里只剩下吃喝玩乐,讲究衣着搭配,制作精美的下午茶点心,看似很认真的活,其实充斥着空虚的无聊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靠着美貌谈情说爱,像搓麻将一样蹉跎岁月。一个真实完整的人,要敢爱敢恨,要会哭会笑,而王琦瑶不敢爱也不敢恨,不会哭也不会笑,像个漂亮的牵线人偶,作者只是在卖力的牵线而没有赋予王琦瑶真正的生命,所以纵览全文,王琦瑶是个单调的扁形人物。
三、悲劇意蕴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悲剧的产生,是一切社会矛盾恶化导致的必然和最终结果,具有阶级性和强烈的因果关系。在不停的积累的过程中,这种结果及斗争反抗尤为突出。然而,单从扁平化的王琦瑶本身来看,她的底子太过单薄缺乏厚重感。结局被人杀害只能算一场意外的悲惨事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但如果放眼望去都是王琦瑶时,就充满了深深的悲剧意蕴,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女人在男人的诱惑而前束手就擒。当“自命不凡”的“王琦瑶”遇到能满足她虚荣心的“李主任”时,竟然会像一条见到主人的小狗,巴巴的就跟着走了,她们是怀有期待的被金主买走,当被买走后内心是得意欢喜的。这种自卖自身的欢喜是“物”乃至“宠物”的欢喜,而不是生而为人的欢喜。被男权社会物化非但不反抗还乐在其中,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了。正如文中写道“王琦瑶看见人们恭敬奉承的目光,虽知是狐假虎威,心里也是得意的……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似乎男人的钱权就是最大的磁场,就是最诱人的春药,“王琦瑶们不接触还好,一旦接触就会立刻失去防备、丢盔卸甲、丧失人的尊严、原则和理性,把白己当成美味的祭品,整个献上去任君采撷享用”,纵然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也会抱着是跃龙门的侥幸心理义无反顾的跳下去,只为享受一刻“上流人”的糜烂生活。她们甘心做一只在身体上取悦男人的金丝雀。她们所悲哀的不是失去飞翔的白由,而是对靠“性”维持的“感情”患得患失。所谓心灵上的默契也不过是性爱后的自欺欺人,是对各有所需的掩饰。总之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是那么“顺理成章”的变成情妇,没有经过内心的挣扎,也没有父母的阻挠,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自己交出去下赌注,这种劣根性才是女人悲剧的根源。
第二:女人只在意表而的衰老而缺乏蓬勃的生命力。如文中写道:“她想‘老这个东西真可怕,逃也逃不了,逼着你来的。走在九曲十八绕的水道中,她万念俱灰里只有这一个‘老字刺激着她。”实际上,对于女人来说真正可悲的不是美人迟暮,也不是而对“微微时代”只能酸楚的艳羡,而是缺乏刚建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体现为变幻多端的喜怒哀乐,体现为行为姿态的健康有力,体现为强烈的生命意志,体现为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和热情,体现为永远活蹦乱跳的心。时间可以把工琦瑶们的身体变老,却没有资格把王琦瑶们的心变老,可悲的是很多王琦瑶不仅把自己的心变老还变成“死”的了。文中的王琦瑶,从甘愿做物开始,心就死了一半,也不是完整的心,用她外婆的话说就是“走了样”,当她离开爱丽丝时,把仅剩的一半心也丢在那了。于是今后的几十年她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只剩下干瘪空洞的美丽。即使她与女儿的朋友一起玩乐也只是对青春留念的回光返照,而不是真正变成了年轻人的心态。张永红与她混迹在一起不过是遵守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定律,老克腊被她吸引只是因为得了恋旧癖。如果说和王琦瑶在一起严师母康明逊是散发樟脑丸气息的“前朝遗老”,那么这几个小青年就是“封建落后守旧派”。他们和王琦瑶一样没有生命力,一样拒绝新陈代谢,一边无聊地打发时间一边吃喝等死。当然这种缺乏生命力的人生悲剧不光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
结语:
王安忆的《长恨歌》获得了矛盾文学奖,说明这部小说的含金量很高,但“金无足赤”,该小说也有一些瑕疵,从文本的语言层而上看,其语言过分雕琢以及阐释过度。从文本的形象层而上看,女主角的形象太过单一而不丰满。从文学的深层意蕴上看,只将其当作“悲惨事件”来写,因此深度不够,还需读者和评论者去进行深度挖掘。所以作家要想打动更多的读者,需要注意文本的这三个层面,以便创造出更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3]沈喜阳.论《长恨歌》的半截性[J].当代文坛,2012年第1期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