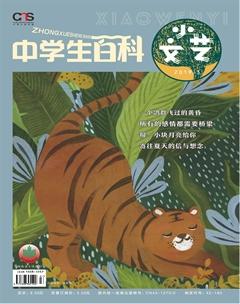我想抱住那团光
暖纪年
1
她站在那里,像高枝上的一朵百合花。
如果不是因为神经质的动作,高老师看起来就像一朵百合花。会议室顶头的光落在她修长的脖颈上,冷光蓝调衬得人很白,似乎还能看见细小的血管。她得有四十多岁了吧,五十应该没有,不过谁说得准,天知道这种永远优雅的精英女性能在保养上下多大功夫。
剪裁良好的白色套装,薄壳银灰的手表,不用刻意但就是很舒服挺拔的站姿……有某种声音清晰地裂开,会议室里像突然绽开了一朵百合花。从缝隙开始,花瓣一丝丝分开,颜色是雪夜的白糅进了一些樱花粉。还星星点点落着小雀斑,空气中一下子洒满了淡淡的清香味儿。能用百合比喻的人还真找不出几个,当然,如果她没有神经质的习惯,就更好了。
此刻,高老师一边慢条斯理地训斥,一边下意识地剥橘子。她是策划,在电视台地位不低,到处都放着她的青橘子,一摞一摞地堆着。她说话的时候,总会捞过一个橘子,指甲一摁戳一个洞,一片片撕掉橘子皮,这还不够,还要把橘子表面白白的经络都捋干净。
桌子上总有碗,要么就是摆着白纸,表面千千净净的橘子,被她连成一条直线摆在上面。剥得太干净了,果肉瑟瑟发抖地挤在一起。她不吃,也没人敢吃,一整排脱了衣服的橘子就光溜溜地摆在那里,有点儿像是在接受审判。
“这次活动策划是谁想的?”
“自己好好反省错在哪里。”
这次办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公益活动。我只是带上相机,和所有实习生一起去学校采访,跟在高中记者站时做采访的流程差不多。那么,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仔细想想,是我的错。我真傻。高考完后我应该尽早考虑复不复读,或者安安稳稳做一条咸鱼,睡最长的觉,做最懒的鱼。如果不是我的错,我就不会闲得发慌,我就不会觉得无聊,就不会大老远地跑来电视台实习。
重新做了策划后,下班已经很晚了,我怕黑,只能在巷子口憋一口气,背着包一路狂奔上楼。结果一打开门,差点控制不住尖叫起来——厕所应该是堵了,满地都是水,地上的东西基本浸湿了。谢天谢地,排插今天没放地上。
疯狂拖地,丢纸巾,用抹布擦干,联系房东。找清洁工……每一步做起来我都有强烈的抵触。社交障碍和回避型人格让我生活在恐惧当中,极度自卑,但又有什么东西摁着我让我往前走——我不敢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人。我坚信这也是我高考大滑坡的原因,我害怕面对,并且知道不解决绝对不能往前走,所以复读大军都热火朝天地开学了,我却逃到当地的小电视台实习,租房子一个人生活。
想找一个没人发现的地方,把自己拎起来,抛进去。
让我躲一躲吧。
我坐在门槛上,瞧着月亮,有一小点儿风把我的衣服吹胀,堵得发慌的感觉终于消散了不少。我重新捞过手机打电话,想起桌子上尴尬袒露的青橘子。
一个,两个,三个……光秃秃地排排坐,怪滑稽的,和我一样。
2
这次是个公益活动,让留守儿童和社会人士对接,一起过生日、做游戏,最后会做一期朗读活动,共同读一首诗。
内心深处。我对这个活动嗤之以鼻。换位思考一下,我愿意在这么小的时候面对电视、面对采访吗?曝光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不过也许是我想多了,哪有这么多问题少年、敏感少女?
“集中注意力,下面我要出题了。”编剧兼记者陈老师也带学生,主要教采访和后期写台本。
“有一所学校,学生出了点事,我们几个人打电话给校方想去采访,校方态度很好,还说要安排人去酒店接我们。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儿不对,果然,校方拍下厚厚几万块在桌子上,告诉我们,学校临时翻脸不接受采访了,我们毫无责任还可以得到很多钱。如果当时在现场的是你们,怎么办?”
有个实习生傻乐着一拍大腿:“老师,我好像有一点点心动。”
陈老师一翻白眼,说道:“当年我带去采访的那个实习生也是,我感觉我看到了他眼里进发的光。”
“正确做法是,告诉对方,”陈老师清清嗓子,“把你们的录音笔关掉。”
对方真的讪讪地取出了录音笔。陈老师说,遇到敏感情况,提防要紧。对方可能想不报道,也可能想阴你一把,你开口说什么,都可以被剪辑,回去就被匿名举报丢工作。
做个采访就像演《甄嬛传》一样,办公室里还是忍不住一片哗然。
“真想接钱的,你就配不上这个行业了。”他说得漫不经心,办公室里却一片寂静。
接下来的策划讨论会,高老师一边顺手剥橘子,摆成一排,一边说了极相似的话:“这是一个公益活动,节目收视重要,但活动本身更重要。我们不是卖惨博眼球,不是标榜多么有爱心,不是施舍,不是揭他人伤疤丰富自身经历,你要配得上‘新闻从业者这几个字。”
听完这段话,我猛然意识到自己错在了哪里。
可是真的能做到吗?
只要打开网络,会有无数信息汹涌而来。我看过颠倒黑白,我看过低俗暖昧,我看过刻意引导……每个人都被庞大信息流裹挟着。甚至每个人都被欺骗过。
人要生活,更要生存;我們想要真相,又害怕真相。
3
考虑到也许还要回去复读,我也偷偷问过编剧,为什么我的议论文这么差,他说我没有真正用心。用他跳离学生多年的身份看,高考作文无非就是围绕那几个大方向出题,也越来越偏向家国情怀,只要我往其中糅合一些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很容易得高分的。问题是,我的正义感是真心的吗?
真心不真心,旁观者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比如说,我对这次的公益活动就不够真心,只是把自己放在“实习玩一趟”的位置上,依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
如果我够真心,我就不该和一群实习生去学校采访,这会反复提醒那些敏感纤细的孩子一我和别人不一样。前面的了解阶段我不该带相机,那样无法真实交流,会让他们看到镜头不自觉地开始“演”,我应该先和他们的班主任和父母联系……
越想越心惊胆战,我到底做错了多少?
参加活动的孩子里有个叫姜姜的,喜欢穿一条开满向日葵的裙子,是所有小孩里最乖巧最漂亮的。同时也是最让人心疼的。通过班主任我知道她的父亲在打工的时候遇上事故不幸去世了,母亲抛下她改嫁。我想对她好一点,但不应该这么明显,这种区别对待反而是揭他人伤疤。
开会过后领导决定重新修改活动环节,希望最后一个朗读环节能够顺利进行。高老师怕活动出错,也参与进来了,一个个联系家长,有些还去了家里了解情况。办公室里,大家心急火燎的。走路都是小跑。
高老师联系回来,有点感慨地和我们聊天。
“这次活动有个小孩的奶奶,特别坚强。她儿子去世了,但死死瞒着不让小孩知道,说他们都去外面打工了。她不定时把衣服拿出来晒,硬生生人前人后没掉过一滴眼泪。”
“那过年呢?过年怎么办?”
“过年她奶奶就假装打电话,埋怨他们两个为什么不回家,故意让小孩听见,知道工作很忙。其实儿子去世,儿媳妇改嫁了,瞒了好久。”
“等等……”我霍然抬起头,“你说的是姜姜?”
高老师想了会儿名字,然后点点头。
我觉得喉咙有点干涩,不知道撞见了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剧情,好半天才犹豫着说:“确定是姜姜?我去学校采访的时候。姜姜早就知道父亲不在了啊。”
“但她奶奶今天说……”
我俩大眼瞪小眼,然后同时愣住。
所以,每次奶奶晒衣服,把被子拍松软的时候,她就睁着漆黑的大眼睛看着;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听着,开开,心心,乖乖巧巧;饭桌上讨论着同一个人,他什么时候回来……她们守着这个美好的梦境,为了给对方一个安心。
对了,姜姜今年才九岁。
下班时间刚到,高老师就刚才的对话消化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说:“后天的朗读活动内容,重新修改一下吧。”
我说:“好。”
4
现场直播的地点很特别,在新华书店的顶楼。玻璃房子的直播间,往后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观,高楼、摩天轮,夜景尤其好看。平常围坐读书的人慢慢聚拢,好奇地看着摄像机。
朗读前,主持人一般都会热身聊聊天,消除紧张和尴尬,比如和直播连线,和“暑期父母”也就是对接的陌生人交换卡片,展示自己的爱好特长。因为节目时长,每人只能有一个小互动。
活动策划的同事熬夜改了又改,我们砍掉别的环节,给姜姜安排了所有的互动,一共三个。
她展示了自己画的向日葵,对接的暑期父亲是个警察,真情实感地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热线连通了姜姜久未见面的姑姑,没说几句她突然掉下眼泪。高老师顿了一下。现场有些紧张,担心连线是一个错误决定。还好,不一会儿她破涕为笑。
今天对于她来说,是温柔美好的一天。
如果把“奶奶和小女孩相互隐瞒”的故事报道出去,这会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故事,可是没有人这样做。工作人员都理解姜姜的眼泪,哪怕现场的观众可能觉得莫名其妙,觉得这个小女孩太紧张。这个故事不会报道出来干扰她的生活,没人拿她的眼泪赚取观众的眼泪。
电视台背后藏着不少秘密,有很多这样的姜姜,有很多背后的故事,不会被报道,也不会被揭开。这个公益活动的目的仅仅是,尝试着在两个本该陌生的人之间,建立长久的联系。
朗读的时候会全场熄灯,一片黑暗中,啪嗒一声,仅有的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上。
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全市灯火次第亮起,车流像海潮,跟着呼吸慢慢涌动着。就像诗歌里说的那样,浪打空城寂寞回。
她……会记得我们吗?这个小小的、精灵一样的孩子,画灿烂向日葵的孩子,会不会记得一群陌生人熬夜赶策划,希望给她一点微亮的火光?会不会记得十二楼高层的玻璃间,空空荡荡却不是孤身一人?会不会记得窗外,长风浩荡。万家灯火?
真心换真心。
这个美好瞬间,解开了我所有的恐惧和不安。
5
我剥开橘子,一个,两个,三个……排成一排,放在白纸上,底下垫着各科高考真题。
面前突然多出了很多只手,我前后左右的同桌忙不迭把橘子拿走了。虽然复读时周围全变成了陌生面孔,但少年人总是一两个月就能混得很熟。
“你為什么总是剥橘子啊?还剥得这么干净。一定要摆成直线。”
“这是我独家的解压方式。”我笑眯眯地从抽屉里再拎出一个橘子。橘子剥开的时候,细小的雾水会洒在空中,气味先是刺鼻的,像把柠檬所有的酸挤在一起落在鼻尖,然后舒展开酸酸甜甜的味道,再用力一吸,是雨过天睛之后的清凉。
我打开窗往外看,一直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久以前,我一个人生活。不久以前:我看到娱乐至上,也看到颠倒黑白;我看到有人哭了,也看到有人笑了;我看到中年人背负家庭,年轻人踽踽独行……有一群人摸爬滚打,但心中总是有一点捻不灭的光。
我想念大家,我想再往前一步,直到抱住那团光。
编辑/谭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