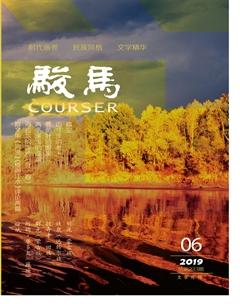踏空
刘泷
白马长阳奔着他走过来,粉白的脸上挂着土样的灰黄。她急急地说,完了,我的股票没有跟上这波上涨的节奏,不但踏空,还套住了,要不要割肉?
他本来是散户,十年前从七千元起家,一路炒来,炒到三十几万,被这家证券公司营业部经理请到了中户室。他知道,这家营业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二十万以下是散户,在大厅里共同拥挤着观看那块幕布一般或红或绿或红红绿绿的电子显示屏,观看那上面的股票市值蹦蹦跳跳、起起伏伏;中户室的客户都是资金在二十万以上五十万以下的人。这里有六台电脑、六张桌子、六个椅子。这些东西依靠着四面墙壁,把中间的地面腾出来,放了一张乒乓球案子和一张棋牌桌;五十万以上的人在大户室。大户室两个人,两台电脑,两套桌椅,而且,有一张很大的茶几,可以让二人抽自己的香烟,喝营业部提供的铁观音;一百万以上的就是公司金卡客户了,是爷,是奶,是太阳,是月亮,一人一屋,连经理都要仰其鼻息的。
他在和其他三位股友打对调儿,见她急急的样子,就把手里的扑克牌扔在桌子上,堆起笑脸来,嗔怪说,割肉?牛市格局未变,割什么肉?你总是沉不住气。
她从裙子的开口处取出一张餐巾纸,揩拭着鼻尖上涔涔的汗珠,说,我被套了五年,好不容易解套,我可不想再次被套。
这时,矗立在营业部楼顶的电子钟响了三下,他和那几个股友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对她说,收盘了,你回去吧。我整理下网上资料,分析下大盘走势。
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网上说,5月28日,市场尽墨,哀鸿遍野,A股逾2000只个股下跌,500多只股票跌停。股民亏得跳楼都“找不到北”,交易时段不禁心如悬旌:“这得跌到啥时候?”到收盘时,长舒一口大气:“终于三点了……”临近收盘,不少营业部见大盘下跌了差不多百分之七,害怕股民心理承受能力顿挫,从而走了极端,急忙在营业大厅的电子显示屏上悬挂出大大的条幅,上书:“后市可期,莫要跳楼!”当天,两市蒸发4万亿,户均浮亏2万元。有股民说:“10分钟,一个月赚的顷刻没了,五个月的工资一天没了!”当然,也有先知先觉者,在暴跌之前就远离了股市。一则消息说,教育机构就职的张先生年近三十,在今年三月份刚刚入股市。他当时的本金10万元,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50万了。张先生说,自己不是什么所谓“高手”,因为入市时间短,没有经历过大震荡,敢于下手,都是什么涨追什么,什么热炒什么,所以赚了不少。作为新股民虽然没有经历过暴跌,但是相信大盘肯定不会一直这样涨下去的。他说:“怕忍不住加仓,5月25日那天就把账户注销了。”他还说:“除了怕把赚了的钱亏进去之外,注销账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炒股影响心情。”张先生还说,饭桌上聊天说股市,晚上下班回家跟证券公司同学打电话让对方推荐股票,还是聊股市。赚钱了当然高兴,但总是提心吊胆的,总想提前能拿点消息。大家都说了中国股市没有规律可言,眼看着一家公司出了一则利空的公告,结果第二天可能出现的是涨停,实在捉摸不透……
他尚在揣摩大盘的下一个目标,揣摩庄家的策略或者战术,中户室另外那五个人已经脸上挂着霜雪悄悄走了。也是,除了十年前“5·30”那次暴跌,股市尽管是熊的领域,尽管疲软了七年,但没有出现像此日这样险些在一天的时间段让整个大盘跌停的窘况。无论散户,无论中户,也无论大户抑或金卡贵宾,只要炒股,他们的心态几乎如出一辙。只要大盘在涨,或小阳或长阳,就一概喜上眉梢,笑靥如花;只要股票在跌,就一概怒目金刚,愁云漫天。
手机上的QQ跳了几下,忽闪,忽闪,像青蛙顶着阳光在空旷的岸上跳,一蹦,一蹦,像雨滴降落,按动了水面的键钮,那水泡、小电灯一样,一闪、一闪。往日,这样的一蹦、一蹦,或者一闪、一闪,是让他喜欢的酵母。无疑,这是白马长阳发过来的,她要和他聊天,他也愿意配合她,和她聊天。
可是,今天他心烦,他郁闷,他纠结,他不愿意和她聊天,他没有聊天的念头和兴趣。是啊,一家伙,三十万折去了三万多,缩水了三万多,能不心烦,能不郁闷,能不纠结吗?
她发过一杯咖啡的图案,问,在吗?
她几乎总是这样,就在他内心失落、沮丧的时刻,突兀地通过QQ送上一杯咖啡来。不知道她这是祝贺、安慰还是幸灾乐祸、黑色幽默。
在。他心不在焉。
明天要不要割肉?
你这个人真絮叨,刚才不是说了吗,挺着。
挺着?真的能涨?不会跌吧?她以为他是巴菲特,以为他是股神呢。巴菲特也曾这样说过,如果你不想持有十年,那你就不要持有哪怕五分钟!
他只好宽慰她,股市上涨的逻辑和下跌的逻辑是一样的,只要牛市格局没变,它的指数就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只要是熊市,那它就只有更低,没有最低。现在是牛市,洗盘和震荡是正常的,洗洗更健康,要充满信心。
嗯。听你的。此刻,她又不是那样喋喋不休了,她变得小鸟依人了。
他是什么時候认识她的呢?想想,也差不多八九年接近十年了。
那些天,股市连续下跌,把他账户的五万元变成了七千元。老婆耐不住了,破口大骂,说他败家子,说他窝囊废,并且,给他留下一封潦草的信,就领着儿子跟随南方一个卖茶叶的男人逃之夭夭。
他一个人喝了几口闷酒,孑然坐在营业部散户大厅里,泪眼迷离地望着电子显示屏绿油油、一行一行、一跳一跳俨然麦苗茁壮不休的数字,无奈地打着瞌睡。酒入愁肠愁更愁,潦倒人随瞌睡虫。行情不好,熊迹弥漫,整个营业部门前冷落马蹄稀。散户大厅更是如此,只有稀稀落落屈指可数几个人。他们有的打瞌睡,有的苶呆呆盯着大盘一动不动,有的躲在一个角落,吸烟。
白马长阳这个时候走进了他的视野。当时,她落寞地来到大厅,逡巡不前,左右睃视,有一些无可奈何,或者,失魂落魄。他瞟一眼她,见她脸颊接近太阳穴的地方有几抹润肤霜盘踞着,好像有个刷涂料的人干活漫不经心,使墙壁的那抹涂料没有完全打开,凸绺着蜷卧在那里。这样,冷眼一瞅,说庸俗就很庸俗,如同一块蝉蜕的惨白悬浮着,有些不雅;说艺术也很艺术,像毕加索的抽象画,好似一小片鸽子的羽毛,深情地,在那里落户。
这个女人有些像阴天的青蛙,气压低了,就要张开嘴巴让下颔如鸡蛋那样膨起来,呱呱说话。她像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一个水中的人,恨不能牢牢地抓着他,贴靠在他的身上。她说,大哥,你也被套了吧?我想,大盘天天绿,你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他说,套了。无所谓,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你的心态真好。我都快撑不住了。我今天割肉了。可是,我还怕大盘明天涨起来,害怕踏空。我赔了很多,我想,等我把那些赔的钱弥补回来,我再不想着赚钱了,我就离开股市!在他眼里,她就像一个怨妇,或者,就像那个祥林嫂,絮絮叨叨的,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
他想,自己毕竟是男人,不能怨天尤人。就说,想炒股票,想在股市赚钱,在股市混,就得豁出去。其实,股市就是个无厘头的地方,涨涨跌跌,起起伏伏,瞬息万变,早晨还是要饭花子,晚上可能就骑马炫耀啦!
大哥,你说得真好。大哥,你叫什么?
我叫,我现在叫阿牛。
阿牛?听这名字就是职业炒股票的,就是个高手。她谄媚地对他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那抹蛰居的润肤霜也耸了两耸,意味深长,好似画出的省略号。
什么呀?我姓熊,股民讨厌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就取了阿牛的名字。炒股票,没有好的名字进行心理暗示,就没有底气。
是啊,是啊。我本来姓白,但为了讨个好彩头,就叫白马长阳。其实,就是想总能抓到白马股,想让大盘天天阳线!
你挺逗的。
什么呀?我这是不自信。
炒股票,不自信不行,太自负,也不行,要顺势而为。
大哥,你说,今年的股市是不是还和去年一样,大跌呀?
未必,国家实施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货币相对宽松,上涨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你能给我推荐一只股票吗?
你还有多少钱?
不多了,十万多赔到两万啦。
噢。那就持有一只股票。在2.46元买进ST秦岭吧。我建议,熊市清醒,牛市糊涂,熊市折腾,牛市捂着,你就坚持,把这股票捂到5元再卖出。
真的能到5元?
能。因为它被冀东水泥重组了,迟早要涨起来。
好,听你的。
唉——时至今日,阿牛还后悔呢,悔青了肠子。他给她推荐了股票,那股票就是不死不活不涨,就是在2.5元上下趴着、赖着,一个星期,二个星期,三个星期,踟蹰不前,裹足不前,就那样耗人,好似熬鹰。白马长阳耗不住了,在电话上,在QQ上,或者在散户大厅,天天和他嘟囔,说,这什么破股票呀,人家都说了,ST不能买,是垃圾股!他说,你先听我几句,再挺一个月,一个月后不涨,我,我再也不给你推荐股票了行不!好在,一个月之后,那只股票涨了,涨到了四块多钱。可是,股票涨了,她又拿不住了,根本不顾阿牛的劝阻,挣了一万元,抛了。果不其然,那股票上了5元,并在6元的位置盘桓了数月,如今早已绝尘而去。
过后,他一直在想,是在股市上与她萍水相逢的,她又不是我的亲人,我又没收咨询费,到底图的什么呢?真是自讨没趣呀!
虽然如此,他是一个心慈面软的人,她要咨询他,他怎么可以装聋作哑、置之不理呢?
我怎么结识了阿牛呢?结识阿牛是一个悲剧还是喜剧呢?夜深人静的时候,白马长阳一个人在大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总会这样扪心问自己。
阿牛这个男人看不出有多坏,但他有男人普遍的特点,色。这可能与他的老婆和那个南方的茶叶商人私奔有关,也可能和她的老公锒铛入狱,她如今孑然一身有关。
他的色,他的挑逗,他的蠢蠢欲动以及潜规则,她都懂。对此,她有时候并不反感,但有时候又很苦恼。
说起来,白马长阳沦落到股市里煎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她老公是王为。之前,王为是一家银行的出纳。2007年下半年,他看到很多同学、朋友甚至同事在股市一路摸爬滚打,神采飞扬,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每当与这些人相聚,这些人动辄就要谈论股票,说A股沪指要上涨到一万点,云云。于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为胆大妄为,竟然私自挪用公款炒股,而且数额颇大,达千万之巨。关键是,股市飞流直下,于2008年夏天,他操作的那些巨资,早就不到一百萬元,严重缩水。王为扛不住了,跑到监管部门自首。这样,他不但丢了公职,还被判了徒刑,到外地一个偏僻的山沟去劳动改造。
王为流徙,但王为用她的名字开了个账户,把家里仅有的十万元拿来炒股,结果也炒成了两万多元,她只好忍痛割爱,斩仓出局了。
平心而论,要不是阿牛指点一二,她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了结。
一度,因为不满她喋喋不休的絮叨,他不再和她说一句话,不再给她出一个点子。
但是,她是个耐不住寂寞的女人。那些被股市滔滔巨浪淹没的钞票,宛如古人沉船下潜的财宝,在海底的一隅,向她频频招手。她火烧火燎,不断向那个方向遥望抑或觊觎。2009年底,她到底经不住股市的诱惑,把卖出ST秦岭后手头那三万多元买了中国中冶。
然而,股市毕竟不是她的家人或者亲戚,股市没有悲悯情怀,没有因为她一个渺小的散户被套得难受就大发慈悲,掉头向上。股市有自己的逻辑,就像她喋喋不休的话语一样,跌跌不休。
一个多月后,她4.4元买的股票已经跌破三元,她再次被深度套牢。无奈,她跑到证券公司营业部的散户大厅,当面问计于阿牛。
其时,阿牛尚在空仓,要抑制自己少看多动的坏毛病,锤炼自己的定力,达到多看少动的境界。但是,面对白马长阳渴求和无助的眼神,他不能连个点子都不出。
他问,为什么买中国中冶呢?
朋友对我说,这是国企。
干什么的?
什么干什么的?
我问这家企业的主营方向。
什么主营?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买?我问它主要从事什么产业?
大约是冶金吧?
他瞥一眼大盘,说,如果是冶金,这个价位不高,如果是中国冶金的龙头,那更不高。
两个人的头颅挤在一起,在营业室的电脑前按下F10翻阅企业资料。它居然主营建筑业,是个综合类国有企业。
她喟叹一声,说,完了,我4元多买的,套上了。她说,唉,这股市忒折磨人,我想好了,以前赔得那些不管了,只要把这个股亏损的一万五千元赚回来,我就远离股市,不再炒了。
他说,我相信国企。现在它不是两块八吗,我也买它,和你作伴,和你共进退。
她说,只要你也买它,我就有信心啦。女人快速瞅了他一眼,里面有些滢滢的东西,流露出内心柔柔的涟漪。
他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后,我们要把钱一点点攒起来,在下面不断接中国中冶,不断摊低成本。
好。听你的!你什么价位卖出?
我?我一定掐着,不翻番不卖出!
真的?真能翻番?
能!
那好,我跟着你,你什么时候卖出,我也什么时候卖出!
一言为定!
之后,是遥遥无期地等待与期盼。五个虚年,四个整年。大盘熊途漫漫,不断踏穿一楼的地板、地下室的地板、地窖的地板,没有穷期。这期间,中国中冶曾几次跌停,一度跌破二元,在一元之上徘徊,险些成为一元以下的“仙股”。
望眼欲穿的漫长如海水退潮,退出2014年的初冬。他的股票解套了。她的股票后来也解套了。她说,我要把这股票卖出,先把现钱攥到手?
他说,再等几天,怎么也得赚两个呀,有漫长的时间成本呢!
等了几天,她说,不成,我都赚了七千元啦,我得卖了!
他责怪说,你这个人就是脆弱。
她迅速卖掉了自己的股票,并反诘他,你是股神呀?你能肯定它不回调吗?你能肯定它不下跌吗?你那么肯定,为什么在2.8元买的它,为什么不在1.52元最低点买?她的话,像喀秋莎火炮,势头和速度密集、凶猛,不给人喘气的机会。
但是,他是技术派,11月9日,中国中冶那根上升途中长长的上影线,极端吓人。于是,在那天,他和她一道,落袋为安。
可是,股市就是这样无厘头,九天之后,中国中冶到达5.56元,他少赚了十一万元!而她,更是少赚了不少。
这期间,他还给她推荐了福日电子、山东钢铁、美好集团等股票。对于山东钢铁,因为下跌了三角钱,她居然在2.91元割肉卖出。而对美好集团呢,当该股涨至3.90元,她每股只赚一元钱,总计赚了三万多时,她不仅自己卖出,还对他鼓噪,卖吧,落袋为安,再跌回去怎么办呀?他是个耳根子软的男人,架不住她的再三鼓噪,最终在4.44元,将其卖出。可是,很快,该股便站在了6元钱之上,仿佛登山,看到他们尚在山下,站在山巅嘲笑着他们。他想,从此坚决不给她谈股票了,不给她推荐股票,用猪毛把自己的耳朵塞上,免得被她消极的噪音污染。
当然,她周边有很多炒股票的男男女女,凭她的不耻下问或者急切,总会找到推荐股票的人。
有人给她推荐股票,他耳根子清静,很是暗自得意、暗自庆幸。
在一个周末,证券公司组织营业部大、中户和成长快的散户精英去郊外福荟寺游玩。让他意外的是,她也来了。在大巴上邂逅,团队的成员,相互只是点了点头,再无话说。
到了福荟寺,她追在他后面说,我新买了三只股票,中国银行、潞安环能和瑞贝卡,除中国银行略微盈利外,都套住了。你给支个招呗?
他说,都是好股票。因为现在是牛市。时间考验真诚,几天或者几个月之后,都会有不俗的表现。
她问,你买的什么?
我就一只股票。
什么?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觉得你的心态好,眼力好,股票靠谱。
他笑了,斜睨着她,说,真要跟我炒呀?
真的。
那我可是要收咨询费的。
收呗。
那我可是要潜规则的。他上去拉住了她的手。
潜规则?那可不行,我可是一个正经的女人,在这方面,是有底线的。
他挠了她手心一下,说,得了吧,我们都是单身,装什么呀?
她白净的脸皮浮上一抹红霞,埋下了头。
他说,连上床都不让,还让我告诉股票,该你的呀?
她说,死阿牛,别卖关子,快告诉我。
他说,我买的獐子岛。
多少钱买的?
十一块八。
还有上涨空间?
有!
到什么地步了?
能到三十三。
啊!那么多?
不信走着瞧。
好,我也买点。
这时,寺院的住持嘉木措·杨走过来,他径直对阿牛说,施主,我看你面善,和佛有缘,跟我走走吧。他说好呀,好呀。路上,嘉木措·杨说,富贵学道难,贫穷布施难。我看你现在很窘困,你就给观世音上柱香吧。他说不,不,我要给寺庙捐一些钱。嘉木措·杨指指功德箱说,好吧。他把裤兜仅有的二百元投进了箱子里。
从福荟寺回城后,她倒是果断,将瑞贝卡卖出,在12.2元买了獐子岛。但她仅仅赚了一元钱,就把獐子岛卖出了,并且央求他给个买股票的建议。他说,不要买那么多的股票,就买潞安环能。她问,多少钱买?那时候,那只股票在14.2元震荡,他說,其实,在14元买也无所谓,我看好这股票,到20元是没问题的。但我建议你在13.80买进。她说,我也不在乎那几分钱,就在13.85埋单了。恰巧,那几天股市低迷,她不但成交了,那股票当天跌到13.6元,在5月28日,竟跌至12元!
在那天,无来由地,他就和她在QQ上争吵起来。是因为28日股市的狂跌吗?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早就有了反目的罅隙?反正,他们争吵得很激烈、很恶劣、很悲催。5月28日后,他检索一下他们俩的QQ记录,当天有这样的对话——
红牛(阿牛):要对潞安环能有信心。你总是急,我说那个瑞贝卡不要卖,先等等,你也天天问卖不卖。
白马(白马长阳):等是等,我看看潞安环能啥时候赠股,赠股不是要降吗,如果降再进点。
红牛:瑞贝卡这小子的到13了。
白马:唉!
红牛:掐着这股票,到20了。你就不能一声不吭掐着等?
白马:当时买时,就奔它能到10去的,我说瑞贝卡。
红牛:整天嚷嚷吵吵,有意思吗?
白马:我也没说卖啊,我就等着呢。
红牛:难怪莫言说,白松黄糠黑有水。
白马:我想这当中怕是有分红,不是除权吗,股价下来。
红牛:就是每十股多3股,0.35元,多大事儿?
白马:要是两万股,不是给6000股吗,然后我再买4000股,不正好3万股了吗?
红牛:嗯。
白马:我咋也找不到它们啥时候赠股的消息,所以问你。
红牛:等着,分红自然就告诉了。
白马:我期待赠股然后再涨。
红牛:我那个獐子岛赚了7个我都没卖,现在10个了。你的看预期。
白马:我知道你这次又赚个盆满钵溢。
红牛:有了预期就得坚持,要吸取中国中冶的教训。
白马:獐子岛到了19.62,说明你没有白等待。
红牛:你是一到要大涨就憋不住,就嚷嚷吵吵。
白马:谁嚷嚷了,股市有跌就有涨,有涨就有跌,谁知道塌方在哪里啊?
红牛:如果你想发财,就不要朝三暮四,就玩一只股票,玩601699,在15.70卖一次,反复玩它,直至到20!
白马:我现在看出来了,国家不会让牛市就这么快结束,所以我坚定信心。那中国银行呢?
红牛:逐渐集中兵力,玩一只股票,不要分散资金。
白马:我有1万股中国银行,它曾到5.29,可惜那天我没在家,没卖,如果在家肯定卖了。我当时就想中国银行到5就卖,瑞贝卡到8就卖,潞安环能到15卖。
红牛:狠下心来,在4.64出了中国银行,就买一只股票。我就一只股票。
白马:嗯,听你的。你的獐子岛我也挺喜欢,也买过,在13.20处卖了。
这是上午的记录,下午,她又在QQ问话了——
白马:把中国银行卖掉吗?
红牛:我给了你建议,以后要学会自己判断。
白马:不会判断。我这把踏空,目前刚刚不赔,不像你又赚了10个。潞安环能让我这把踏空!!
红牛:又嚷嚷!你来我家,和我睡一次,让你知道什么叫闷着。
白马:潮种!那样我宁可远离股市,也不能毁了自己的人格。
红牛:那就好,不要一个劲儿吵吵把火的。炒股不是做爱,不能有了快感你就喊。
白马:我就把中国银行留在股市了,然后潞安环能到了我的目标价位我就抛,然后离开股市。
红牛:你已经说离开股市很多次了。
白马:这次是真的了,不想操那个心了,不过也不全是脱离,我把中国银行留在里面,几年以后再说。
白马: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或者股市真的和国际接轨,中国资本市场真的成熟起来,我想中国银行绝对不会是4元多,我等到那天。
白马:你准备在啥价位上卖獐子岛?
红牛:不卖!
白马:一直拿着?
红牛:嗯。养老,当遗产。
白马:你上次不是说到19吗?
红牛:炒股票要随机应变。
白马:它可真长出息,奔19去了。
红牛:捞着一只好股票不容易,就像捞着一个好女人不容易一样。
白马:你看它和潞安环能哪个更有后劲?
红牛:我都跟你说了,你真啰嗦。
白马:它是中盘股,潞安环能是大盘股,还是它涨起来快。
红牛:我恶毒地说,你这个人有婊子的特征!
白马:你妈了X的!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所有女人都喜欢你,你个潮种!
红牛:我没让你喜欢我,我让你闭嘴。
白马:你等着吧,你会遭报应的。
白马:我根本就瞧不起你,在这方面,你像一个叫春的猫。
红牛:你叫唤一回,我早賣一回,从中国中冶,到美好集团。你就不会不叫唤一回?
白马:如此说来,你们家人都有这个特征,不然不会生出你这么个叫春的畜生,也不会容忍你这把年纪了还到处嚎叫。人呢,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离开你地球照样转。
接着,她退出了他QQ好友名单,把他拉黑了。
他很难受,恨不得跑到她家或营业部散户大厅,去当面骂她几句,或扇她几个耳光。又不是他哭着喊着赖着给她当炒股参谋的,她凭什么如此歇斯底里?为什么连家人都不放过?那个和南方人私奔的养汉老婆该骂!那么,那倒霉儿子呢,怎么把他也捎上了?那一刻,他蓦地想到了这样的话:没有报恩,唯有报应!
是股友一个励志故事,让他放下了包袱:残疾人崔万志,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决心,让自己公司的旗袍在天猫网实现了销售第一的目标,利润上千万。他说,抱怨没有用,一切靠自己。我们所遭遇的委屈、挫折、打击,原来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世界是一面镜子,照射着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子。选择抱怨,我们内心就充满着痛苦、黑暗和绝望,选择感恩,我们的世界就充满着希望、阳光和爱!
此时,那个跑到南方的女人也领着儿子回家了,她把茶叶贩子给她的一沓人民币摔给他,说,阿牛,我们修好吧?他说,你以为这是大车店呀,想回就回想走就走?他哐地摔上门,躲在用电脑炒股票的书房里生闷气。她在外面哀求他,为了儿子,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了,我知道你股票赚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吧?他呼呼地喘气,一声不吭。
半夜,嘉木措·杨给他来电话,说,走吧,跟我去福荟寺清静几天吧?他说,大师,我这几天脱不开身,马踩着车呢。嘉木措·杨胸有成竹,说,我知道。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急则生变,要学会放下,放下才会释然。他看了下股市资料,知道獐子岛要停牌,就说,好吧,到那里吃几天斋饭。他想,反正要等到这股票在33元出局的,索性,摆脱世俗的纷扰,遁世躲它几天。嘉木措说,下楼吧,我的车就在你楼下。
轿车真的停在楼下等他。他坐在车上,望着外面眨着眼睛的星星和星星一般迷幻的路灯,问道,大师,你不是要我皈依佛门吧?嘉木措·杨说,你是红尘中人,我就是讓你去佛门净土洗涤一下,也好多一些佛性童心。
骂一通阿牛,她快要疯了,精神在崩溃的边缘逡巡。晚上,睡不着觉,她接到了王为在远方来的短信:我想你了,来吧。以往,她曾多次收到王为的短信,都狠下心来拒绝了他。这次,她想,真的应该去看看王为了,自己何尝不想他呢?
坐了火车坐汽车,她是在傍晚走进小镇的。
至于那小镇上的景物,她一直也没有看清楚,因而在她的记忆里只是纵横的几条虚幻而冷清的小街,或者干脆只是一些参差排列、色彩单调的几何形体。白马长阳跪在荒草丛中,她很幸运——她找回了一幅梦景,因而她的一个久已疏淡了的梦不期而至:那绿色也是这样地缥缈摇荡,那天空也是这样浩翰无涯,但没有一点儿声音,天上都是灿烂的云彩,一只白色的鸟儿舒展地飞入画面,翅膀一张一收一张一收也没有一点儿声音,从天的这边飞向天的那边。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就有了一座老屋,鸟儿正是朝那儿飞的,那鸟儿飞得洒脱,优美而真切,飞得无拘无束毫不夸张。但那老屋却相当虚幻、缥缈,仿佛只是一种气息的凝结,唯那一种古老房舍的气息确凿存在,鸟儿正是朝那儿飞的,那只白色的鸟儿,飞得没有一点儿声音……这很像一个梦。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梦呢?无关紧要。究竟是过去的经历呢,还是对未来的憧憬?都无关紧要。总之很早,那只鸟很早就飞进过她的梦里,那古老房舍的气息流进她的梦里肯定更早,这梦她做过很多次,但有很久没再做了。
她就醺醉地向那座老屋奔去。鸟儿像一条风筝的飘带,拽曳着她,走进那个宿命的多次在梦里出现的境况。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迎接了他。老汉歪头瞅着贴近山脊的夕阳,说,去那个劳改队呀?今天来不及了,很远的,需要走半天时间的山路呢。你住下吧,这就我一个老汉。老汉皮肤黝黑,两只凸出的门牙,有些华君武漫画的夸张,让她想到了野猪的獠牙。但是,事已至此,她不住下,是不行了。
老汉很热情,给他擀的面条。面条很对她的口味,尤其韭菜和黄瓜丁儿的卤子,符合她清淡、干净的审美。
饭后,老汉为她端来一盆热水,说,丫头,天不早了,洗洗脚,睡下吧。
洗过脚,爬到炕上,才发现,墙壁上,点灯开关的拉线断了,断的很不是地方,断在顶棚的开关附近。
她把老汉喊了进来。老汉说,丫头,你站上去接吧,我年纪大了,给你扶着凳子。他把一个四条腿的木凳端上炕来,摆放一番。
她站上去。她穿着裙子,在暗夜中,两条白皙的小腿发出幽幽的迷人的光泽。她特意喷洒了香奈尔香水,芳香的气息像室外的蝙蝠,在室内翻滚。
老汉悄悄地动了一下凳子。
啊呀!她喊,踏空啦,大爷!但是,凳子仅仅侧歪了一下,那条悬空的木腿就靠实在炕面上了。老汉却在她惊恐的叫喊声中,在她中了他的圈套摇摇晃晃的那一刻,迅疾站起身抱住了她。他抱住了她,他的右手顺势伸进她的裙子里,像按住了电门一样,毫不犹豫地按住了她的那个致命的圆点。她啊的一声就倒了下来,她倒在了老汉的怀抱里。
此刻,她忘记了王为,而阿牛的面孔却在她的眼前痛苦地晃动了几回。阿牛的面孔变形了,是那种抽搐的苦难的模样。
老汉的攻击开始了。是那两颗门牙,率先突破了她的嘴唇。像在炮火的熏陶下,黧黑的敌人打破了前沿阵地的禁锢。
他的那个阳物伟岸,要比王为的大上几号。王为的是小耗子,他的是小兔子。王为的是一把手锤,他的是十八磅的大锤。农村的土炕铺着芦苇的炕席,很热,她如同卧在了铁砧上,被他十八磅的大锤敲打。先是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后是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一下一下,砸,反反复复。她的身体就像一块铁,一块生硬的铁,都要长锈了,荒芜了。他的大锤起起落落,让这块生铁热了起来,让这片土地苏醒过来,俨然铁砣子,在铁夹子的夹持下、翻弄下,在大锤的起落中,死心塌地地接受大锤粗粝的飓风似的呼啸,迅速融化,融化为一摊柔柔的泥巴一样的一团炭红,几近液态。她软了,酥了,陶醉了,心甘情愿接受大锤的击打,并和着大锤的节拍,变圆,变方,变长,变短,死了一般,奄奄一息。
这样,在这座老屋里,她住了三天,让老汉锻造了三天。
第三天一早,老汉说,其实,劳改队距离这里不远,翻过山坡就是,步行,用不了半个小时。
她什么也没说,拖着行李走出来。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走到了小镇的边缘。她爬上一段颓败的城墙,看见了辽阔如海的一片绿色;那是还没有长大还没有开花的向日葵,新鲜稚嫩的叶子牵连起伏铺地接天,晨风和朝阳里闪闪耀耀的新绿如潮如浪,仿佛地动山摇。她像小时候那样旁若无人地跪下来,跪在城墙沿头的荒草里,呆呆地望着。眼前这情景她好像见过,但不知是在哪儿,也想不起可能是在哪儿见过。也许是在过去,也许是在未来。过去遗留在梦里,又或者未来提前走进了梦中吧。她有过类似的体验:一种情景,或者一种感觉,仿佛曾经有过,发生过或者经历过,但是想不起由来,甚至明明知道那是不可能见过的,但无疑又是那么熟悉。这怎么解释呢?也许是前世所见?但更可能是一个久已忘怀了的梦,一个从开始就没有记住的梦,或者是一个白日梦。这是心中的造化。但那梦景变成情绪弥漫在心灵中而没有留在大脑里,凭智力,是很难把它找回来的。
她翻过山坡,找了一天。但她没有找到劳改队,没有找到王为。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她又找到了那座老屋的地界儿。
但是,那座老屋也不见了。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