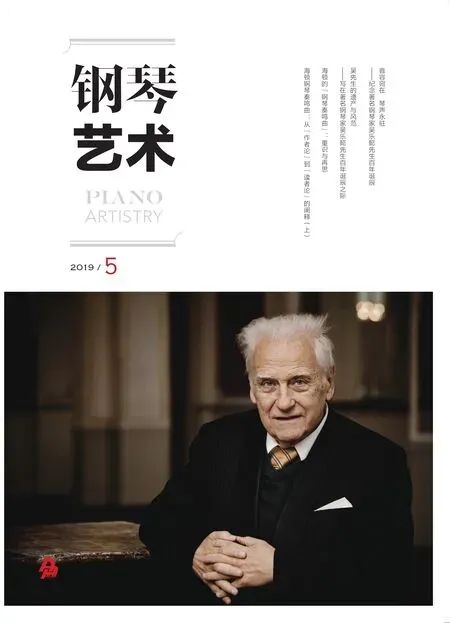海顿钢琴奏鸣曲:从“作者论”到“读者论”的阐释(上)
文/王 遒
阿城在与姜文的对谈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以前的艺术理论注重作者方面,也就是‘作者论’,讲他们的经历,讲他们处的社会环境,等等;后来转到‘读者论’,注重读者的解读,也就是作者的意义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读者的读,读也是创造。其实专论作者,或专论读者,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问题是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其记忆的重组,以及读者在读的时候,引起的个人记忆重组。这两种重组都有相同性质的想象功能,作者和读者,都是‘脑吗啡’的奴隶。”①
所以,很难说究竟是经典本身引发了无休止的解读,还是无穷尽的诠释造就了经典。羽管键琴家兰多夫斯卡有句名言——“你是按你的方式来弹巴赫,我呢,则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演奏巴赫”——这位野心勃勃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于与原作者等同的位置上。
如今唱片工业的宣传似乎同样意在强调读者的重要性。多少唱片封面上赫然印着演奏家的各种头像,而贝多芬、莫扎特名字只出现在封面的一角。的确,若非伟大的演奏家灌录这些作品,对于今天的人而言,它们恐怕只是一张张失去生命力的纸张。
关于海顿及其创作的解读已经汗牛充栋,在这里我们遵循创作——阐释的顺序,以海顿钢琴奏鸣曲为例,来看看我们的海顿,再从诠释者的角度,探寻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一、“摆渡人”海顿: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
尽管一直以来海顿被公认为古典主义时期“维也纳古典乐派”最为重要的三巨头之一,也被誉为“交响曲之父”和“弦乐四重奏奠基人”,但在1900年之后却越来越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身影所遮蔽,多年来,海顿被视为两者的阴影而不是相反。海顿的键盘作品,尤其是奏鸣曲部分,也许是数量上过于庞大(62首),难以保证首首精彩,也许中间还夹杂若干难以确认的“伪作”,或是不符合浪漫主义听众对于音乐作品中复杂矛盾情感的期待,一度越来越少地出现在主流钢琴家的保留曲目单上。事实上,他的这些键盘作品足以堪称古典主义文献中最璀璨的珍珠。幸运的是,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钢琴家们开始发掘海顿作品中令人耀目的光彩。
就海顿奏鸣曲而言,首先我们就会被它的数量和编号方式所困扰。不同版本乐谱的奏鸣曲在数量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我们仍不能确认海顿所创作的钢琴奏鸣曲的总数。较权威的有兰登(Christa Landon)编定的维也纳Urtext版,一共收录了62首奏鸣曲,学界确认其中47首为海顿所作,但对其他部分尚存疑虑,其中大多是早期作品。费德尔(Georg Feder)编订的亨勒Urtext版收录了54首,而文森·丹蒂(Vincent d'Indy)1916年编订的Édition Nationale版本只收录了37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奏鸣曲手稿不完整或已经遗失,另一方面则是有部分作品经研究,确认是他人所写而署上海顿大名的伪作。我们在提到海顿奏鸣曲的编号时,通常会在兰登维也纳版的奏鸣曲序号外另提到“Hob.”的编号,这是“Hoboken”的缩写,源自20世纪荷兰音乐目录学家霍博肯(A.V.Hoboken)对海顿作品目录的编定。而两者之间的序号是不一致的,这常常导致同一首奏鸣曲有两种不同编号间的混淆。除此之外,作品的命名方式也会对非专业人士产生一定误导,海顿手稿中第一部正式题为“Sonata”的是《第20奏鸣曲》。在某些年代较早的版本中,它们会出现“可带小提琴的奏鸣曲”(Sonate avec Violon ad libitum)与“独奏奏鸣曲”两个版本并存的混乱情况。例如,著名的《降E大调第49钢琴奏鸣曲》的André版本就标注为“小提琴奏鸣曲”,海顿自己也在书信中称之为“带长笛或小提琴伴奏的键盘奏鸣曲”(Klaviersonate mit einer Flöte oder Violine begleitet),然而他的手稿却找不到任何伴奏声部的蛛丝马迹。这种多个版本并存的情况有可能出自J.S.巴赫,这位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经常把自己的小提琴协奏曲改写为键盘乐器协奏曲。类似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克列门蒂,人们会发现他也曾发表过想象力丰富的、各种乐器混搭的所谓“钢琴奏鸣曲”。
作为古典主义时期最为典型的音乐形式,奏鸣曲在海顿的器乐独奏作品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而作为古典“三巨头”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位,海顿几乎横跨了后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时期,这使得他的创作风格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海顿少年时进入维也纳的圣斯蒂芬教堂合唱团,以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相对于歌唱,他对于键盘乐器的驾驭或许并没有那样出众,人们很少像谈论莫扎特、贝多芬那样谈论海顿的琴技。米歇尔·布勒内(Michel Brenet)曾说:“海顿并非一位灵巧的演奏者。他最开始为羽管键琴写的作品都是些小曲,是给学生当作练习用的。后来,就钢琴家而言,他的演奏也难以让人感到惊艳。”②对此,海顿则以他一贯的谦逊承认他在钢琴上缺乏“魔力”。
一般而言,1766年被认为是海顿奏鸣曲的一个分界线。他的早期键盘作品主要为羽管键琴而作。它们在风格上深受斯卡拉蒂和C.P.E.巴赫的影响。部分作品仍命名为嬉游曲(Divertimenti)、帕蒂塔(Partita)或独奏曲(Soli),风格更接近巴洛克时期的舞曲。而羽管键琴发声较短的特性,使得海顿大量应用种类繁多的装饰音对旋律进行美化,甚至自创了两种不同的回音记号,被称为“海顿回音”,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巴洛克色彩。由于此时古典奏鸣曲式尚未完善,海顿为此做出的诸多尝试,被后人认为是后巴洛克向古典风格演变的桥梁。但海顿本人对他的早期作品并不欣赏。在给莱比锡出版商的信中,他写道:“那些我年轻时创作的作品,不值得保存。”
1761年,海顿开始担任埃斯特哈齐(Esterházy)宫廷的副乐长,1766年升任乐长。这个奥匈帝国的显赫家族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爱好,并拥有当时欧洲最好的私人乐团。海顿在此职位上全身心的工作了近三十年,获得巨大声誉。
就古典奏鸣曲式的发展而言,海顿开创性的成就是当时任何一个音乐家都无法企及的,特别是发展部。海顿成熟期的作品已经在尝试大量运用模进、转调、性格变奏等手段,并且往往融汇多种手法,加以贯通。这种手法后来在贝多芬那里进一步发扬光大,验证了海顿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随着制琴工业的发展,古钢琴逐渐取代巴洛克时期的羽管键琴而成为主流乐器,日渐灵敏的击弦机以及古钢琴特有的渐强、渐弱的应用,使得乐器的演奏效果更为丰富,这进一步为海顿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1788年,海顿写信给他的出版商阿尔塔里亚(Artaria)时说:“为了给你创作三部键盘奏鸣曲,我不得不购置了一架新的古钢琴……”如果不注意海顿的措辞,便会忽略了字里行间透露的关键信息。在18世纪下半叶,在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羽管键琴(Harpsichord)之外已经出现颇具实用性的早期钢琴(Fortepiano),但作曲家仍用“Clavier”来代表“为键盘乐器所作”,而具体是哪一种键盘乐器却不甚明了,这给现今的人们造成很大困扰。尤其是很多人误认为“Clavier”指代的是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这是有失偏颇的。虽然海顿这三首作品仍然沿用键盘奏鸣曲(Claviersonaten)的名称,但他要添置的却是当时颇为新潮的乐器——早期钢琴(Fortepiano)。先前的乐器形制已经无法满足海顿创作上的需求,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近在眼前了。
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除了乐器的革新,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形式也对海顿奏鸣曲的创作起着巨大的影响。尽管海顿被誉为“交响曲之父”,但许多评论家认为,海顿对弦乐四重奏这种体裁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要超过他对交响曲的贡献。也正是在此期间,海顿在和乐手们的合作中不知不觉地完善了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形式,并把它渗透到奏鸣曲的创作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歌德曾在一封信里形容弦乐四重奏是“四个理性的人之间的对话”,而这种具有逻辑性的对话的方式也正是海顿钢琴奏鸣曲中最常见的,有经验的听众往往会有意识地体会到乐句间、段落间的逻辑关系和情绪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良好的结构平衡感。海顿更是创新地借用了宫廷音乐中的小步舞曲(Menuet),并使之风格更为朴实和民俗化。他甚至通过多变的节奏,将部分小步舞曲乐章变成充满幽默感的“谐谑曲”,这也成为海顿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对演奏者而言,这一时期的海顿奏鸣曲乐章篇幅相对短小,乐句简短明了,节奏多变灵动,自然成为演奏者掌握古典奏鸣曲式结构,并进一步学习大型古典奏鸣曲的最佳曲目。
1790年,对音乐毫无兴趣的埃斯特哈齐家族的新继承人解散了宫廷乐队,尽管保留了海顿的荣誉职位,但他已经无须再为其雇主服务。自此,海顿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迎来了他的艺术高峰期。尤其是随后的两次伦敦之行,对海顿更是影响巨大。伦敦丰富专业的音乐生活和来自亨德尔的雄伟、崇高和戏剧性的传统,对海顿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采用英式击弦机并带有踏板的新式钢琴,更给炫技式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响色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1791年,海顿在伦敦指挥的系列音乐会中,更是首次以钢琴取代羽管键琴。
1794年,海顿第二次赴伦敦,为一位名叫特雷泽·扬森(Therese Jansen)的钢琴家创作了他的最后三首奏鸣曲。这三首“英国奏鸣曲”中的降E大调和C大调两首,无论从篇幅、技巧难度还是戏剧性上都堪称海顿奏鸣曲中的巅峰之作。富于戏剧性的切分节奏、频繁的对位、强烈的明暗对比、突然的停顿及延长音,总能使听众震惊,而快速多变的离调及和声转换,伴随着海顿经典的“假再现”,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他的“恶作剧”嗜好。在C大调的这首作品中,海顿还给出了他在键盘作品中唯一的踏板标记。
二、海顿和莫扎特、贝多芬
海顿的奏鸣曲体现了他无畏的原创性,将多变的音乐手法和恒定的结构准则相结合,把音乐作品中生动、幽默和令人愉悦的一面展现给听众。海顿的创作更多是适应曲式方面的特性,服从音乐材料的指引。通过对单一主题和短小动机的塑造、凭借主调音乐织体的变化、灵活多变的节奏,以及强大的动力性,把纯音乐语汇和高度的想象力、幽默感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又避免了过多地在音乐中掺杂主观情感,从而完美体现了古典主义和谐、平衡的原则。
莫扎特的奏鸣曲继承了海顿古典主义最为精致、典雅、规则的一面,但在同时也代表着一个隐晦的听觉世界,真正的情感被隐匿在无法抵抗的优美旋律下,外在的流畅性仅是一种表象,其下所蕴含着的悲剧性令人动容。这或许和莫扎特长于歌剧创作有关。作为歌剧作曲家,他善于塑造多重角色,这一能力在莫扎特的奏鸣曲中转化成性格各异、明暗交融、无限丰富的主题,并通过无与伦比的歌唱性使之完美地融合为一体。
1781年,海顿和莫扎特相遇后,海顿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莫扎特也对海顿非常尊重,把他当作人生导师看待,甚至还以“老爹”(Papa)相称。尽管海顿比莫扎特大了23岁,但海顿却深受莫扎特的影响,甚至有人把海顿的创作定义为“前莫扎特时代”和“后莫扎特时代”。即便如此,我们仍能清楚地感受到海顿始终以一种合乎理性、遵循惯例、富有逻辑性的洞察力表达着情感,并最终在他那个时代获得艺术与物质上的巨大成功。而成年的莫扎特却同他那个时代决裂,艺术上的坎坷和长期的经济窘迫始终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尽头。
1792年,亦即莫扎特离世一年后,海顿在离开伦敦返回维也纳的途中,于波恩见到了22岁的贝多芬。贝多芬随即移居维也纳,以向海顿求教。临行前,贝多芬的保护人费迪南德·华尔斯坦伯爵(Ferdinand Waldstein)在纪念册上写道:“莫扎特的天分仍在为它托生身体的逝去而哀伤和哭泣。在思如泉涌的海顿身上它只是找到了暂时的寄所而非最后的归宿;它渴望与另一个人结合。经过不懈的努力,你定将从海顿的手里接过莫扎特的精神。”
遗憾的是,两年后贝多芬和海顿就分道扬镳了。这两年海顿一直在全力准备1794年第二次的伦敦之旅,所以贝多芬抱怨从未从海顿那学到些什么。尽管如此,贝多芬的确是继承了海顿的衣钵:无论是在短小动机的塑造上,还是在织体和调性的铺陈上,甚至在幽默性素材的使用手法上都能捕捉到海顿的影子。尤其是在单一主题的凝练上,贝多芬比海顿更节制,通过简单几个音就构建了整个乐章(如《第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正是在海顿和莫扎特的基础之上,贝多芬对奏鸣曲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丰富,并在其中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和巨大的情感冲突。这也导致海顿认为贝多芬的作品雄辩却过于粗鲁,幽默又过于谐谑。
到目前为止,录制过海顿钢琴奏鸣曲全集的钢琴家并不多,大多数人只是录制了他的部分作品,但随着近些年人们对海顿的重新认识,大量新的录音不断在涌现。伴随20世纪70年代英国“本真主义”的兴起,为使人们了解那个时代音乐的本来面目,有一部分演奏家尝试用古乐器来演奏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并颇受好评。
(待续)
注 释:
① 姜文、阿城文,《姜文对阿城》,引自《收获》编辑部主编,《〈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散文卷(2001——200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11页。
② Michel Brenet (Marie Bobillier),Haydn.Paris,1909, p.183.Cf.Carl Parrish, Haydn and the Piano,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Vol.1, No.3(Autumn, 1948), 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