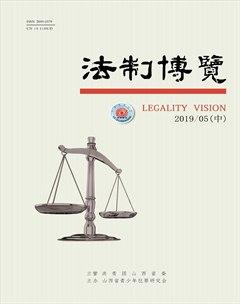“扫黄打非”中举报奖励制度研究
摘 要:最新《“扫黄打非”工作奖励办法》出台,进一步规范了“扫黄打非”工作中的举报奖励制度,标志着“扫黄打非”运动进入新阶段。论文从目前“扫黄打非”工作的困境开始,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分析成因,并结合行政法学中对非强制行政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研究与运用,探讨在传播领域使用举报奖励制度的合理性及缺陷,并结合国外具体做法分析“扫黄打非”工作的法制出路。
关键词:扫黄打非;举报奖励制度;非行政强制行为
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14-0139-02
作者简介:汪杉(1998-),女,汉族,江苏南京人,苏州大学新闻系,本科。
2018年11月20日,《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颁布。该办法由国家版权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财政部联合修订并发布。除了重新规范并细化“扫黄打非”举报奖励制度,其更是完善了“扫黄打非”举报奖励的评定标准、涉及范围、实施程序及监督管理等内容,并且将属于“扫黄打非”举报奖励范围的16种具体情形一一列出。本文将从目前扫黄打非问题的困境开始,结合行政法学中对奖励制度的研究与运用,探讨在传播领域使用举报奖励制度的合理性与不足,并分析扫黄打非奖励机制的未来出路。
一、“扫黄打非”工作目前的困境
(一)内容本身
1.淫秽色情内容边界模糊
198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規定》,从定义上明确区分“淫秽”、“色情”以及夹杂淫秽、色情内容而具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的区别。尽管我国已经通过法规以官方名义对于三种出版物进行界定,但在实际操作上,仍会产生一些失误。由于辨析三种出版物仍需要执行人员的主观判断力,有时会因理解上的差别产生一些将艺术品归类为淫秽色情品的失误;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引进机器识别结合人工审核的新型审核模式,计算机算法下的审核也略显僵硬。且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媒介产品数量多,种类广,有很多产品位于淫秽色情违禁品的中间地带,很难定义其性质,使得“扫黄打非”工作更加困难。
2.假新闻泛滥
在流量可以变现的今天,媒介与受众的关系产生巨大变革,媒体组织选择内容的标准不再是其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而是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需要,新闻从“以受众为核心”开始转变为“以事实为核心”。[1]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成为目前大量新闻信息产生和散布的地方,但也是假新闻泛滥的地方。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院发布的《2018数字新闻研究报告》,由于假新闻泛滥导致的渠道或平台信用危机,社交媒体的新闻发布与索取功能正在被大多数调查者所抛弃。但由于国内网民基数大,尚未培养出可以明确辨别假新闻的媒介素养,“扫黄打非”工作的压力较以往更大。
(二)运动式治理方式存在问题
有人对运动式治理的“轮回式”过程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当某个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事件持续发酵后,有关部门开始介入并发表官方声明,接着便召开紧急会议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联合公检法部门进行检查处罚,再对活动进行总结,接着该“专项治理”结束。[2]但因运动式治理大多为一个周期,导致治理时间短,容易使得违法者投机取巧,在平时违法,而在特定时间内偃旗息鼓。且这样一种治理,客观上限制了常态化治理的发展进程,也使得出版物的市场管理长效机制没有良好的形成氛围,破坏了出版物市场的常态管理。而更加重要的是,运动式治理的临时性、运动性和反复性特点与法治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公平性要求背道而驰。[3]
二、行政举报奖励制度
(一)非强制行政行为的由来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英等国家开展了放松管制改革,指导、合同、激励、扶持这样一些强制力比较弱,更加柔和的行政指导方式便应运而生,逐渐成为管理公共事务的首选项。日本行政法学者盐野宏教授认为:行政机关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时,不应该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定向,采用“提示问题方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实现公共利益。[4]
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开始尝试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得到良好反馈后,逐渐确立这一模式。非政府性质的公共组织,如社区、行业工会、公共事业单位开始进一步承接公共职能,使得行政主体趋于多元化。在政府职能发生转变时,行政观念也同步得到更新:人们更加愿意接受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给付等非强制行政方式,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等则开始有序减弱或退出。
(二)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
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亦称举报悬赏,是属于行政悬赏中的一种。本质上,举报悬赏是行政机关执行的一种带有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实质上是运用物质手段,激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者(举报人)提供信息,并与举报者就行政违法信息进行交易,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交易制度。《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即为该制度具体落实的书面文件。
虽然举报悬赏制度实际上具有双重属性或多重属性,但其法律性质应主要定位为行政合同。[5]作为一种信息有偿交易制度,举报悬赏制度更多着重于“自愿”和“有偿”。举报悬赏中存在要约和承诺的双方合意行为,其实施需要相对人的参与和合作,具体而言,行政机关发出的任何一种举报奖励承诺,如果没有相对人的参与和配合,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合意性正是合同的重要特征。由此可得,举报悬赏制度是通过私法的形式(合同性)来实现公法的目的(行政性),具有外在的契约性和实质的行政性。
目前,举报奖励制度主要在食品药品监管、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80%来自群众举报。[6]群众举报工作开展得好坏,直接关系治理运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这在“扫黄打非”工作中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