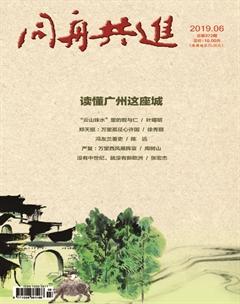郑天挺:万里孤征心
许国 徐秀丽
1939年12月,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推荐郑天挺继任,被郑一口回绝。郑天挺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后参与负责蒙自分校工作,直到1938年7月底蒙自分校结束、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搬到昆明之后,他终于开始了一段最接近学者生活本真的难得时光:授课,读书,写作,与师友畅谈,偶尔远足,不但学问精进,精神也颇为愉快。这一段时光,到1939年底只有一年多,期间又因其表兄张耀曾病逝往返上海两个多月。可见这段时间在郑一生中之宝贵。他的好友也不赞成他出任总务长。罗常培让他考虑一个问题:“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郑承认“此语最诱人”。傅斯年“反对余任总务长尤力”,陈雪屏则转达了北大理学院同仁饶毓泰、江泽涵、吴大猷等人的意见,“均不愿余以此为代价之牺牲”。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拉锯,郑天挺终于接下联大总务长一职,并一直任职到1946年三校复员。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等人之所以反复敦劝,首先因为郑天挺是难得的行政干才。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五位兼任行政职务的同事在劝驾时曾给郑留条曰: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事实上,郑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也颇为自负。格于情势终于接任总务长后,因注重调和弥合,曾有人批评他“无魄力”,郑在日记中说,对此项批评“非所心服也”。他回憶七七事变后独力处理北大善后的经过: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不知所谓有魄力者,亦能如此否也?”除了行政长才,郑天挺的君子人格显然也是众望所归的重要原因。一向交往并不多的清华教授吴宓,在蒙自文学院共事一学期后,给郑一个“贤而才”的评语。北大同仁汤用彤甚至认为郑的“公正”是当时北大仅存的一点维系力。从日记可见,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刚毅坚卓,刻苦耐劳,对联大鞠躬尽瘁,为北大深谋远虑,与朋友坦诚相待,于学术认真努力,待家人温情缱绻,临财不苟,安贫乐道,完美地体现了士君子的高尚人格。
联大之联合不易
西南联大虽然取消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初期(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临时”二字,但三校各自保留原行政架构,各有各的办事处,各有各的校长,各有各的校庆,各有各的研究所,各有各的宿舍区——即使不住宿舍,原各校同事往往住处相邻,交往也更密切。恐怕谁都不认为三校合并的状态会永久存在,而它的结束,将与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正因为这样,顾全大局、通力合作成为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
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述:“三校具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为国难之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谱写了最光辉的篇章,也为后世各种类型的合作树立了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峰。无论当事者还是后世,常从“通家之好”的角度解读合作的成功:清华校长梅贻琦出身南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从清华毕业,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又毕业于北大,等等,有三校或两校经历的教授很多。不过,除了这“通家之好”的基因,还有两个同样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当事人尤其是主事者的胸怀、格局、诚意以及处事才能。二是三校精神上的相通。抗战胜利联大尚未结束之际,政治纷争骤烈,同仁面临分裂,梅贻琦校长在日记中少见地发表了一段对时局和未来的看法,从中可见北清两校精神上的共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毋庸讳言,在临时合作的局面下,三校一定会有各自的打算。事实上,除个人学术前途这个主因之外,郑天挺对联大总务长职位的辞谢和接受,都有从北大角度的考虑。
西南联大的校务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加秘书主任(北大教授杨振声)。校级行政机构有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此时的教务长是北大的樊际昌,训导长是战前无三校任职经历的查良钊。五个学院中,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均为清华教授,而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出自南开。若郑天挺接任清华教授沈履的总务长职务,则北大“强行政弱学术”的形象就更抢眼了。
一向为北大深谋远虑的汤用彤在表示他不赞同郑接任时说:“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郑深服此论,认为“此语确有远见,佩服之至。此老,余向钦其德其学,今日始识其才。”郑天挺向他的老师、北大校长蒋梦麟陈述了“北大不宜再长总务之意”,“师深谅余意,亦不以总务教务全归北大担任为然”。但是,当郑的固拒使梅校长为难,并可能影响北大、清华两校感情和联大合作局面的时候,无论蒋梦麟校长,还是傅斯年、杨振声、周炳琳等师友,均劝他以大局为重,“不妨先就”。总务处位列联大行政机构之首,负“经费人事”之责,在战争环境和三校合并的情况下,经费和人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接长总务之后,郑经常上下午均“到校治事”。他继续担任课程,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研究生,读书写作只能见缝插针,这常使他心焦。
在郑天挺和他的北大同事心中,不是没有自己,也把北大看得很重,但是,联大的重要性显然在个人和北大之上。北大人也颇以胸襟宽阔自豪。1942年7月13日,北大校务会议有一番关于“团结”的话题,虽讲的是北大内部的团结,但用之于联大同样贴切。郑日记中说:“自昭(贺麟)之言最善,以为北大向来最大,不必效法他校,斤斤较量小事。”果然,蒋梦麟校长很自然地谈到了“联大之联合不易,必有一二方面退让容忍始能不破裂。”进而说到他自己之所以对联大事只管外不管内,以及教育部数度拟任命其为校长不就的理由。“并言在教育史上联合大学确属成功,而成功原因由于北大之容忍退让,世人皆已知之,胜利为期不远,联合之局面亦不能久,惟有继续容忍。最后述及今后北大之使命、努力之方向,为词甚长甚动人,在场莫不满意。”蒋对联大成功原因的归纳容有偏颇,但说北大包容大度则可信,清华、南开无疑亦以团结合作为重,不然,西南联大不可能独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