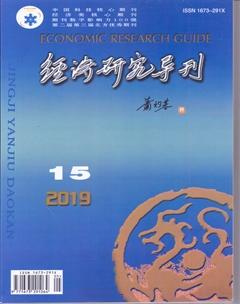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的币值因素
宋振凌
摘 要:金圆券改革和银元券改革所做的稳定币值的制度设计是稳定币值的“锚”。稳定金圆券币值的“锚”是立法规定金圆券发行额上限,而发行额上限能否被遵守完全取决于当局的“自制力”,这就在制度设计上种下了通货膨胀的“因”;稳定银元券币值的“锚”是银元券与银元之间兑现,这对通货膨胀是硬约束,由挤兑来实现,会对当局的发钞冲动形成硬性的妨碍。但是由于战局、银元储备、民众的货币信心等诸多外围因素的影响,导致银元券的贬值同样无法避免。
关键词:金圆券;银元券;改革;币值
中图分类号:F8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5-0097-03
一、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的制度设计与稳定币值
(一)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稳定币值的制度设计
法币体系崩溃后,在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前夕(194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推行金圆券改革,以动员国统区的经济力量支持其内战。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口径是金圆券改革所构建的是金本位制的币制体系[1]。从中国近代币制演进的历程,可以梳理出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宣传口径的用心和逻辑线索:近代以来,直至金本位制于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失败之前,中国官方的币制蓝图和民间舆论都是以金本位制为优,以金本位制为中国币制改革的终极目标;而又由于中国商民对不能兑现的纸币存有戒心,为保障法币的顺利推行,虽然法币改革实际建立的是汇兑本位制,但官方统一口径,坚称法币改革没有放弃银本位制。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称金圆券改革建立的是金本位制的用心所在和背后隐藏的逻辑线索就清晰了:既然民间舆论恒以金本位制为优,则由法币体系的“银本位制”过渡到金圆券体系的“金本位制”就描绘出了中国币制向高等级演进的假象,而由于近代以來又是以金本位制为币制改革的终极目标的,“金本位制”的宣称就更像是近代以来币制理想的实现了;黄金是比白银单位价值更高的天然货币形式,“金本位制”的宣称在舆论上还可以增加商民对金圆券币值的信心。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者,应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兑换金圆券。”[2]这一规定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政权的强制力推行,对此分析如下:
既然金圆券体系禁止民间金银的流通、买卖或持有,那么金圆券就不能自由兑现为等量的黄金和白银,所以金圆券体系运行的既不是金本位也不是银本位制,而只能是不兑现本位。而由于“外国币券”也在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之列,因而也不可能是汇兑本位制。由前述推论可知,金圆券改革构建和施行的是信用本位制。
在信用本位制体系内,在制度设计上,对金圆券发行量的约束机制是两条,一是“十足准备”,二是金圆券发行总量为“20亿元”的上限[3]。
以下对这两条约束的效力展开分析:
金圆券不能兑现为硬通货,那么十足准备和发行量的立法规定就只能取决于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对法律的执行意愿和力度了。但是,这两条约束对南京国民政府就是“软性”的,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局面和法制环境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完全有条件隐瞒实情或者编造数据,以便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破前两条约束超发纸币。直到通货膨胀的情况不可收拾,公众才能有物价飞涨的现实中获知真相。金圆券通货膨胀的过程也证实了上述分析。
金圆券体系崩溃时,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瓦解。于此政局全面糜烂之时,国民政府仍然推出了银元券改革。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实行币制改革代电》,并颁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中华民国国币以银元为单位。银元壹元总重为二六·六九七一公分,成色为千分之八八O,含纯银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为便利行使起见,由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银元兑换券及银元辅币券之发行,应有十足准备……银元兑换券之兑现地点,经财政部核定后,由中央银行公告……银元铸造未充分时,银元兑换券之兑现,得以黄金为之。”[2]
从一段法律条文中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它全面定义银元券改革的本位制性质。“以银元为单位”意味着银元是银元券的发行准备金,“十足准备”意味着银元券是按与银元准备一比一的比例发行;而规定了承诺银元可兑现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上银元券是可以兑现为银元的,是名副其实的“银元兑换券”。从前述分析可见,银元券改革在制度设计上构建的是银本位制,银元券体系回归到了法币改革之前的兑现本位制的范畴。
银元券可兑现意味着银元券的币值要接受市场检验,要成熟市场挤兑的“压力测试”。如前所述,“挤兑”于纸币发行量有硬性约束,只要不改变银元券的可兑现纸币的性质,银元券的超发不可能走得太远。
(二)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稳定币值的制度设计的对比分析
仅从制度构建上来对比,银元券改革与金圆券改革有质的区别,银元券改革比金圆券改革更有“诚意”:金圆券是不能兑现的,不但不能兑现,且商民持有的金银和外币等硬通货都被以“充实金圆券准备”的名义掠夺搜刮;而银元券是银元兑换券,是可以兑换为银元的,在制度设计上没有财富掠夺的空间。
限制物价是不能奏效的,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下,限制物价只会导致名义物价和实际物价的严重差距。限价令下,由于生产无力可图还要亏本,工厂只能停产;由于销售也要亏本,商人将囤积居奇做观望,市场有价无市;经济的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的停滞将迫使当局取消限价令。而一旦物价放开,市场将出现恐慌性抢购,短缺经济的形势下,恐慌性抢购又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很大的供需缺口,“游资趋向于商业与投机方面,工业生产反因资金短绌而萎缩,造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形势。”[4]物价飞涨不可避免,而通货膨胀将以更快的速度恶性发展。限价令好比修筑堤坝高位蓄起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洪水,溃堤之后,“通货膨胀的势头更加猛烈,而制止物价之上涨已非政治压力所能奏效。事实上,由于政府腐败无能,管控的管制措施是不能有效执行的。”[5]
1948年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限价政策被正式宣告放弃。11月11日又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以“金圆券发行限额,另以命令定之”的含糊措词撤销金圆券发行限额的规定;同时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称:“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准许人民持有……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定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与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圆,在金圆未铸成前,得按规定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2]在正式取消限价政策之前,限价政策已见松动,粮食已经可以自由买卖,货物可根据成本定价;在正式取消金圆券限额之前,金圆券超发的事实亦已存在,《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和《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予以法律意义上的承认而已。而对比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重新允许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币,并规定金圆券有条件地兑现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拿掉金圆券发行量上限的立法约束其直接目的并非为了超发纸币,因为在超发金圆券的事实发生时,立法约束并未被国民政府遵守,可见继续超发金圆券也无须拿掉发行量上限的法律规定;如果是直接目的是为了超发纸币,当局无必要同时允许金银外币等被持有,并承诺金圆券有条件地兑现。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拿掉金圆券发行量上限的立法约束其目的是为了追认事实,以扭转欺瞒公众的印象,以配合金圆券本位制的转向,达到挽回公众货币信心的目的。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金圆券通货膨胀失控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挽回公众货币信心的手段是向金本位制转向,允许金圆券有条件地兑现。这与此后银元券本位制改革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即以硬性约束替代软性约束,使得约束力取决于市场挤兑的威胁而不是国民政府的自制力,因为商民对国民政府的自制力的信心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经过法币和金圆券的恶性通胀以后也已完全丧失。
由于银元券是银本位币的兑换券,一旦市场对银元券信心不足,则就出现挤兑现象。矛盾由此显现:在政局全面崩溃的背景下,纸币所代表的流通职能的优势已完全让位于金属货币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的职能。设若银元券在实践层面完全实现承诺的十足准备,随时兑现,则市场将通过挤兑使得银元券完全退出市场流通,银元券改革将失败,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无法接受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银元券的利益在于“随时兑现”实行一段时间,挺过了初期的挤兑风潮后,市场对银元券的信心建立,则南京国民国民政府可以部分準备金发行银元券,情况将回复到法币改革之前币制运作的格局,从而补给财政赤字。如果严格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发行银元券,于南京国民政府是没有利益可言的,它也没有必要在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做此等无益之事了。南京国民政府节节败退,而新政权已明文公告对银元券不予收兑,持有银元券的风险极大,即使完全实现十足准备、随时兑现的承诺也对市场信心无补)。设若部分准备超发银元券,则准备金的空虚将迫使银元券停止兑现。因此,银元券从实施之际,即已经注定失败。
二、发行准备金与金圆券银元券的币值相关性分析
金圆券体系是信用本位制,金圆券不能兑现,金圆券的发行准备金如果不进入市场流通回笼金圆券,仅静态的储备,则与金圆券的币值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可以稳定人心。但由于将准备金实物向公众展示难以操作,则国民政府谎称准备金的数额和真实持有准备金数额对于公众的货币心理影响是相同的。
故而从国民政府的角度而言,金圆券改革实施信用本位制可以收到两重效果:其一,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国民政府能否平衡财政收支和国家收支,如果能够,则金圆券的发行量可以控制,改革可以成功,而如前所述,由于静态存储准备金与稳定币值无关,因而这批准备金可以挪作他用。其二,如果改革失败,则国民政府可以选择:向市场投入准备金回笼金圆券挽回失败或放弃金圆券体系,保留金圆券准备金,用作他途。可见,采取信用本位制的金圆券体系,无论改革成败与否,国民政府都可以获得一笔硬通货。
决心进行币值改革之后,蒋介石就责成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分别拿出一套改革方案。如果采取中央银行提出的方案,金圆券改革的成败仍然取决于国民政府能否平衡财政收支和国家收支,于财政部的方案并无不同,但却不能有一笔额外的硬通货收入。两者相较之下,蒋介石选择财政部的方案。根据金圆券改革的亲历者提供的统计数据,通过金圆券改革,国民政府“在上海一个地方就收兑了黄金一百十多万两,美钞三千四百多万元。还有大量港币、白银及银元,总计在全国搜刮的数目约有两亿美元之巨。”[4]而蒋介石对于金圆券准备金的收集情况是很关心的,“在金圆券发行之初,蒋介石每天晚上要同俞鸿钧通一次长途电话,要俞报告收兑金银外币的数字,其他的事情都不是他所关心的。”[4]
综上所述,金圆券体系的成败不取决于发行准备金的充足与否,而取决于南京国民政府平衡财政的能力。故南京国民政府以筹措金圆券发行准备金的名义搜集硬通货当有“骑墙”之意思,改革如能成功自然更好,如退一步即使失败,也能有一笔硬通货可用。
银元券体系是银本位制,银元券是兑现的,因而银元券的发行准备金对于稳定币值有直接影响。银元券的贬值有多重因素:战争环境和法币、金圆券接连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都使得商民对于银元券币值的怀疑趋向极致,同时短缺经济的情况下以硬通货的物价也会上涨,使得由于银元券贬值后停止兑现反证了银本位制对于通货膨胀的约束作用。
即使是金银和外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币值联系的根本还是物资。金圆券银元券发行之际,中国国内的生产几乎停滞,而战争又消耗和破坏着物资的存量,国民基本的衣食住行也要通过国内物资的存量来补充,国内物资总量不断减少,而战争的恐慌又会刺激国民囤积物资的愿望。在这样的极端短缺经济下,即使是完全以金银外币等硬通货流通而完全没有本国纸币流通,物价同样迅速上涨。
通货膨胀是一种非正常的动员全社会物质资源的方式,超发的纸币投向哪个领域,社会资源就流向该领域。金圆券银元券改革即是以超发纸币的形式,压榨国统区已经十分困难的民间物资,支持国民党政权继续进行内战。其破坏性首先在于它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个体的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受通货膨胀冲击最严重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城市无产者没有的财产甚至有负债,资产阶级的财富的绝大部分是以资产而非纸币的方式存在,而且他们通常都是“有办法”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冲通货膨胀的冲击。上海还有商人利用通货膨胀和物价限制,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以至于蒋介石要派出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只有中产阶级既有一定的储蓄,又缺乏对冲通货膨胀的办法。既畏惧于国民党政权的严令而被迫交出了黄金、白银和外币等硬通货,又没有办法应对随之而起的通货膨胀,从中产阶级迅速成为无产者。
参考文献:
[1] 《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中华民国之货币以金圆为本位币,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十足流通行使。”[G]//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等.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481.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482-515.
[3] 《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之发行,采十足准备制……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等.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482.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07-115.
[5] 张嘉璯.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239.
[责任编辑 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