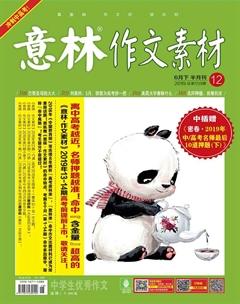把喜欢的诗抄下来
2019-07-08 21:22张晓风
意林·作文素材 2019年12期
张晓风
读初三时,我间接认识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据说她也爱诗。她要过生日的时候,我打算送她一本《徐志摩诗集》。
那时,是没有零用钱的,钱的来源必须靠“意外”,要买一本十元左右的书因而是件大事。于是我盘算又盘算,决定一物两用。我打算早一个月买来,小心地读,读完了,还可以完好如新地送给她。不料一读之后就舍不得了,而霸占礼物也说不过去,想来想去,只好动手来抄,把喜欢的诗抄下来。
这种事古人常做,复印机发明以后就渐成绝响了。但不可解的是,抄完诗集后的我整个和抄书以前的我不一样了。把书送掉的时候,我竟然觉得送出去的只是形体,一切精华早为我所吸取,此后我欲罢不能地抄起书来,例如,向老师借来的冰心的《寄小读者》,或者其他散文、诗、小说,都小心地抄在活页纸上。
感谢贫穷,感谢匮乏,它们使我懂得珍惜,我至今仍深信最好的文学资源来自双目也来自腕底。古代僧人每每刺血抄经,刺血也许不必,但一字一句抄写的经验却是不应该被取代的享受。仿佛玩玉的人,光看玉是不够的,还要放在手上抚触,行家叫“盘玉”。中国文字也充满触觉性,必须一个个放在纸上重新描摹——如果可能,加上吟哦会更好,它的听觉和视觉会一时复苏起来,活力弥弥。
当此之际,文字如果写的是花,则枝枝叶叶芬芳可攀;如果写的是骏马,则嘶声在耳,鞍辔光鲜,真可一跃而去。我的少年时代没有电视,没有电动玩具,但我反而因此可以看见希腊神话中赛克公主的绝世美貌,黄河冰川上的千古诗魂……
(林冬冬摘自《有些女孩,吟了不該吟的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猜你喜欢
疯狂英语·初中版(2023年8期)2023-10-03
客家文博(2022年1期)2022-08-22
汽车与驾驶维修(汽车版)(2019年4期)2019-05-13
东坡赤壁诗词(2018年2期)2018-05-10
文艺生活·中旬刊(2017年8期)2017-09-15
东坡赤壁诗词(2015年3期)2015-08-15
环球时报(2009-09-10)2009-09-10
中国青年(1996年12期)1996-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