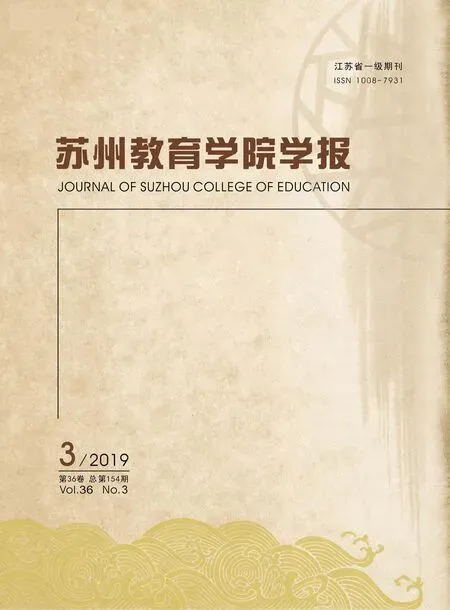傅光明:还原一个俗气十足的“原味儿莎”*
卞若懿(采访,整理)
(杜克大学 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 27705)

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著有《萧乾:未带地图,行旅人生》、《书生本色》、《文坛如江湖》、《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合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独自闲行》、《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戏梦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莎剧的黑历史》等。译有《古韵》、《观察中国》、《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合著)、《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新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一辑(《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等。
2019年1月5日,笔者对新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傅光明先生进行了访谈,以下为访谈整理稿。
卞若懿(以下简称“卞”):您之前的老舍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研究与莎士比亚的译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或重合?之前莎士比亚戏剧的译者似乎都出身于英文专业,您关于老舍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历和背景为您的译本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和特征?
傅光明(以下简称“傅”):若说关联,全赖恩师萧乾先生的引领,若没有他手把手的文学指导,我肯定会走很长弯路。先生所译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也是我喜欢的莎士比亚的入门读物。许多年后,我抱着好玩儿的心态,把这本故事集进行了新译,201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先生在翻译上的这样一种认知,或许是我胆敢翻译的勇气来源,即先生所说的:若把翻译划出十成,理解占四成,表达占六成。开句玩笑,这让我这个中文系出身的人一下子自信了许多。我当然懂先生的深意,拿莎剧中文翻译来说,它是翻译给母语是中文的读者看的,若读起来别扭、拗口,语言跟不上时代,势必影响莎剧的广泛接受。也是从这个角度,当新译的天缘降临,我才敢斗胆一试。说到老舍,记得他说过这样两句话,大致意思:第一句,没指望自己哪天能写成莎士比亚;第二句,莎士比亚若写得慢一点儿会更好。这其实是老舍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第一,莎士比亚写了那么多,从作品数量上自己难以企及;第二,莎士比亚写得太快,有的戏没写好。现在看来,研究萧乾和老舍这两位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学的滋养和文学认知上,这实际上是对我整个人生的全方位的影响。
卞:您提出要呈现一个有别于被定位为高雅文学的,充满了世俗烟火气的“原味儿莎”,这为我们提供了看待莎士比亚作品的全新视角。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关于“原味儿莎”的看法?
傅:先从语言的角度来简单谈一下“原味儿莎”的概念。这本是我的一个玩笑提法,源于我每天都要喝一小盒三元原味酸奶。酸奶有许多口味,我喜欢原味儿。由此,我忽然想反问一句,之前的莎译所呈现的可能是“朱莎”(朱生豪译本)、“梁莎”(梁实秋译本)、“孙莎”(孙大雨译本)、“卞莎”(卞之琳译本)、“方莎”(方平主译本)、“辜莎”(辜正坤主编本),等等,这些都是“原味儿莎”吗?
目前,莎士比亚戏剧在国内被定位为经典文学,没错,莎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被经典化的过程,早已由“通俗”升入“高雅”的艺术殿堂。以中译本来说,这与译本中采用的语言和文体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我怀着顶礼膜拜的心情阅读了“朱译本”。朱前辈英文系出身,是位诗人。他的语言凝练、优雅,尤其对莎剧中韵诗部分的翻译,每行十个汉字,文体整齐漂亮。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方平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2016年,恰逢莎翁忌辰400周年,外研社出版了辜正坤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方、辜“主译”“主编”的两部莎翁全集均是“诗体翻译”。这里,我觉得至少需要思考两个问题:是否漂亮、优雅甚至高贵的中文就意味着对原著的忠实?是否把散文语言断成一行一行的就是诗?再有,比如,有的译者特别爱用现成的汉语成语,我想这得分具体情形。拿《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来说,让这样一个粗俗、没什么文化的没落骑士,一张嘴就是成串的成语显然不妥帖。何况许多成语都带着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有语境,用在莎剧人物身上会显得怪异。
另一方面,高贵文雅的漂亮中文会在国内读者理解莎士比亚作品的定位时产生某种误导。其实,莎翁平均不到半年写一部戏,他主要是为了演出而写戏,绝非为了自己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不朽。他写戏的初衷很简单,作为剧团的“签约作家”,他必须每半年写一部新戏,并由剧团尽快上演。说穿了,在写戏这方面,莎士比亚只是一名受雇的编剧。只有写得又快又好,演出才能卖座,剧团才能挣钱,他作为剧团五大股东之一,也才能分到红利。他想挣大钱在乡下投资房产。实际上,没写几年戏,他就在乡下买了带两个谷仓、两个花园、十个壁炉的豪宅“新地”。当我在这豪宅里逡巡之时,越发由衷地感到,莎翁是被后人尊奉到文学经典的庙堂之上的。遥想当年,在他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他不过是一个浑身烟火气、十分接地气的剧作家。他的戏是平民戏,是通俗戏,尤其1599年“环球剧场”在泰晤士河南岸落成之前,他的戏大都是给社会底层民众看的。因此,无论阅读还是研究莎翁,要想领略“原味儿莎”,便应努力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伊丽莎白时代的语境。
当然,就以福斯塔夫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滑稽的小丑,也不仅仅是一个士兵,他是一个“堕落且没落”的贵族武士(骑士)。他是一位Knight(骑士),而不单单只是一个Soldier(士兵),所以,他身上也还有贵族应有的教养与谈吐,他的幽默机智不仅仅是插科打诨,还时有文采,能信手拈来并文采并茂,像他与大法官辩论时也是伶牙俐齿,在《温莎的快乐夫人们》中调情也是风情万种。同时,他很善于挑战传统思想进行逆向思考:“世人都这么认为,但我偏不这么做。”例如他在《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二场的“论荣誉”独白,就挑战了世俗尊崇、赞赏荣誉的普世价值。在莎翁生活的时代,尽管不同身份阶级使用的语言的规定十分严格——这在莎剧中贵族的诗体语言与中下阶级者的散文体语言中即清晰可见,但底层的人民并非“听”不懂上流社会人士所使用的语言,他们只是无法口说、书写这样华美的文句,但他们十分享受聆听这样的华丽辞藻。所以莎士比亚并非全然地“通俗”,而是雅俗共赏。
卞:在您的译本之前,莎剧已有多个译本,您觉得应当怎样看待这些不同的译本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所起的作用?
傅:这首先涉及一种翻译上的观点,比如,有学者提出莎剧是400多年前的戏,须用古雅、华贵的中文才能更好地体现莎剧原貌。那我想问,是否该用与莎士比亚同年去世的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牡丹亭》式的语言,才更能体现“原味儿莎”?这让我想起鲁迅早在1935年对“复译”——也就是新译——的提倡,而且,他坚决主张,哪怕一部作品已有好几种译本,也必须容纳新译本。这眼界、胸襟多么阔达!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里说:“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鲁大师,乃知音也!
在此,我想举一个来自《哈姆雷特》的例子作简要说明。第三幕第一场,“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该是《哈姆雷特》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台词,它早已成为一句超越了文本语境并广为流传的名人名言。这句台词,最深入人心的中译来自朱生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在英文里,显然没有“值得考虑的”之意。再看梁实秋,此句译为:“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并注释:“因哈姆雷特此时意欲自杀,而他相信人在死后或仍有生活,故有此顾虑不决的独白。”梁实秋的“这是问题”简单而精准。孙大雨的译文为:“是存在还是消亡,问题的所在。”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同样精准。照英文字面意思,还可以译出多种表达,比如,“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或者“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活着,还是死掉,这是个问题。”若按死理儿,“that”还应是“那”而不是“这”。
有趣的是,在1603年印行的“第一四开本”《哈姆雷特》中,此句原文为:“To be,or not to be,I there’s the point.”照此译成中文,应为:“求生,还是求死,我的问题在这儿。”或是:“对我来说,活着还是死去,这点最要命。”或是:“我的症结在于,不知该活,还是去死。”或是:“最要命的是,我不知该继续苟活于世,还是干脆自行了断。”其实,无论哪种表达,均符合剧情中的哈姆雷特在自杀与复仇之间纠结、犹疑、矛盾的复杂心绪。而“值得考虑的”五个字,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哈姆雷特在严肃认真、细致入微地思考着人类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生存”还是“毁灭”的终极叩问,而不是自己的生与死了。
从“第一四开本”的印行时间看,“I there’s the point”应是最早演出时的台词,并极有可能出自莎士比亚之手。诚然,出自演员之口也并非没可能,而“that is the question”显然是修改之后作为定本留存下来。不过,无论the point(关键)还是the question(问题),意思都是“关键问题”。
在这个地方,我把它译成:“活着,还是死去,我的问题在这儿。”同时在此加注释,把这句台词背后丰富的意蕴呈现出来。我认为,这句早已被经典化了的台词,其实无需一个唯一的中译作标准,对这句台词的解读应开放、多元,即它反映的是哈姆雷特的多重纠结,包括生与死、人死后灵魂之存在还是不存在、炼狱之有无、生存还是毁灭、旧教(天主教)还是新教(英格兰国教)……
也由此,我更感到,在莎剧翻译和研究中,我们也应秉持一种多元、开放的学术心态,学习、理解各个译本间的异同,并探究不同译本中所透露出的不同时代环境与译者自身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偏离莎剧的英文文本。如果只以某个中译本作为研究莎剧的底本,那就成了无根之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的莎士比亚翻译、研究。
卞:您新译莎剧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作为译者,您为每部新译的莎剧都写了长篇导读,已先后结集、出版《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①傅光明:《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和《戏梦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②傅光明:《戏梦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这是之前的译本所没有的,您觉得这两部导读合集对读者理解莎士比亚作品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傅:首先,莎剧中有非常多的对古希腊、罗马神话或人名、或典故、或故事的借用、化用,以及许许多多双关语的妙用,莎士比亚活脱脱就是一个双关语大师!除此之外,一些用词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并暗含隐晦的真意。当时,因受到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戏剧的出土与重生再复兴的影响,人人深深向往。再加上欧陆国与国之间贸易频繁密集,也促使许多意大利、丹麦、地中海等地的风土人情传说故事流入英国,蔚为风尚。
以上两点在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中几乎没有体现出来。这自然是由他译莎时的客观条件所限。试想,朱前辈翻译时,手里只有一部不带注释的1914年老“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和一本词典。而到目前为止,不算以前的版本,仅英语世界已有许多为莎迷熟知且津津乐道的莎剧全集,比如颇具代表性的“皇家版”“新剑桥版”等标注着“权威版本”“注释完备”字样的版本。因此,若想真正步入、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从阅读上来说,势必离不开丰富的注释和翔实的导读。
其次,几乎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剧。英国文学教授彼得•米尔沃德牧师曾断言:“几乎《圣经》每一卷都至少有一个字或一句话被莎士比亚用在他的戏里。”
的确,莎士比亚对《圣经》烂熟于心,完全到了信手拈来、出神入化的境地。由于他父母的缘故,他更是兼善天主教(母亲)与英国新教(父亲)的信仰信念与教义教条,例如《哈姆雷特》鬼魂台词中对天主教葬礼仪式(如死前未领圣餐、未涂油膏)的描述、奥菲莉亚因自杀不能受完整葬礼仪式,等等。在全部莎剧中,几乎没有哪一部不包含、不涉及、不引用、不引申《圣经》的引文、典故、释义。仅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不管《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耶稣基督式的心灵救赎,还是《麦克白》中对“偷尝禁果”与“该隐杀弟”两大“原罪”意象、典故的化用,都体现出《圣经》在莎剧中的重要位置。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尽力去寻觅、挖掘、感悟和体会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如何把从《圣经》里获得的艺术灵感,微妙、丰富而复杂地折射到剧情和人物身上。因此,倘若不能领略莎剧中无处不在的《圣经》意蕴,对于理解莎翁,无疑要打折扣。但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由于不具备基督教的宗教背景和对《圣经》的完备知识,若没有译本之外的补充信息,恐怕很难理解不时潜隐在莎剧中的《圣经》意蕴。
从这个角度说,丰富的注释、翔实的导读不失为解读、诠释莎剧的一把钥匙,也是开启他心灵世界精致、灵动的一扇小窗。
卞: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功与其时代背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傅:莎士比亚的成功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显然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天才的戏剧诗人——其实,我现在更愿意用“天才的编剧”来称呼他——莎士比亚幸运地生活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今天回眸历史,会发现当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正进入全盛期,人文主义思想日趋成熟,文学史称之为“伊丽莎白时代”。加上大航海时代商业的兴盛与海盗和殖民地的财富大量涌进,也使封建制度在非战争的情况下有所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诗歌、散文,尤其是戏剧,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这其中,有这样几个时间节点我们需要了解:1558年,25岁的伊丽莎白加冕英格兰女王,六年后的1564年,莎士比亚出生。1567年,“红狮客栈”更名为“红狮剧院”后开张,这是伦敦第一家提供定期戏剧演出的专业剧院。此后,在王室的积极策动下,剧院数量逐渐增多。进入1580年代后,随着各类私人的、公共的、宫廷的剧院不断涌现,大量诗人、作家、职业编剧、舞台演员应运而生,剧作家接近180人,剧本数量超过500部,蔚为可观。这是由于市场需求与稳定的收入吸引大学才子们投身其中,才拉升了整个戏剧演出的水平层次。
出生在这样一个重视戏剧艺术的环境中,莎士比亚真算是为戏而生的幸运儿。1585年,21岁的莎士比亚从他的出生地——英格兰中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小镇——只身来到伦敦,在剧院当学徒、打杂。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莎士比亚亲眼见证了国人血脉喷涌的爱国热情,见证了英国这艘新的世界海上霸主的巨轮扬帆起航,“日不落帝国”开始显露雏形。1589年,25岁的莎士比亚开始写戏。1590年,他成为“内务大臣剧团”的演员、编剧。1599年,莎士比亚所属剧团的“环球剧场”(The Globe)开张。1603年,詹姆斯一世国王继位之后,亲自担任剧团赞助人,“内务大臣剧团”升格为“国王剧团”。这时,莎士比亚已是名满全英的诗人、剧作家,自然也是剧团的金字招牌和大股东。1613年,莎士比亚退休,回到家乡,颐养天年。1616年辞世。这是莎翁大致的戏剧生涯。
卞:莎士比亚戏剧在国内作为青少年必读的经典作品被广泛宣传,在大家普遍的认知中,有没有什么可能出现的误解是您比较在意的?
傅:我们很多时候都惊叹莎士比亚戏剧情节之精巧、人物形象之丰满,但很少有人知道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原型何在。换言之,我们似乎从没有人关心他如何写戏,好像他就是一个天才,生下来就会写戏。因此,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莎士比亚从不原创剧本,而全从别处取材。而且,莎剧很少改编自某个单一故事,在他的剧本中,我们常能同时发现多个“原型故事”。莎剧中的人物形象和剧情还往往受到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的启发。这其实是莎剧的一个特点。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版权保护意识日益强化的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但这种非原创的创作模式,并不应引起我们对于莎士比亚创作天才的怀疑。通过研究和比对,我认为正是莎士比亚精彩的改编与整合,同时,他也对这些作品去芜存菁、兼容并蓄,才赋予了那些滋养他的“原型故事”以新的生命力,使原本平平无奇的故事,凭借情节紧凑、人物性格丰满多样的莎剧留存下来,成为人类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这里,我依然以《哈姆雷特》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原型故事与莎剧之间的关联。我们熟悉《哈姆雷特》,但一般很少有人知道,它至少有三个素材来源:第一个是中世纪丹麦作家、历史学家萨科索•格拉玛蒂克斯(Saxo Grammaticus)在1200年前后用拉丁文写的《丹麦人的业绩》(Historiae Danicae,英文为Danish History《丹麦人的历史》)。这部史书是丹麦中世纪以前最主要的历史文献,包含了丹麦古代的英雄史诗和一部分民间传说与歌谣,其中的卷三、卷四就是《哈姆雷特的故事》(The Hystorie of Hamlet)。虽然这个故事的英文本直到1608年才出版,此时距莎士比亚写完《哈姆雷特》(1601)已过去七年,但我相信莎士比亚很可能事先读过此书的法文版,因为《哈姆雷特》和《哈姆雷特的故事》①参见斯蒂芬·格林布兰特(Stephen Greenblatt)著、辜正坤等译:《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第十章“亡魂呓语”的后半段对于哈姆雷特来源的补充与说明中有许多细节几乎一模一样。这个源于丹麦民间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名叫阿姆雷特(Amleth)的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他的母亲叫格鲁德(Gerutha),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Hamlet)”王子和他的母亲“格特鲁德(Gertrude)”,连名字的拼写都十分相近。
第二个来源,更有可能的是,莎士比亚编剧时直接取材自威廉•佩因特(William Painter,1540—1595)和杰弗里•芬顿(Geoffrey Fenton)分别于1566年和1567年以《悲剧的故事》(Certaine Tragical Discourse)和《快乐宫》(The Palace of Pleasure)为书名出版的意大利小说家马里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的小说《哈姆雷特》的英译本。这个英译本是根据法国人弗朗索瓦•德•贝尔福莱(Francois de Belleforest)在1570年与皮埃尔•鲍埃斯杜(Pierre Boaistuau)合译的小说集《悲剧故事集》(Histories Tragiques)第五卷中转述的该小说《哈姆雷特之历史》(The Historie of Hamblet)再转译的。这篇取材萨克索的故事的小说,增加了哈姆雷特的父王在遭谋杀以前,母亲先与叔叔通奸的情节。这个情节设计,自然毫无保留地移植进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过,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关于王后与克劳迪斯的奸情到底是否在“杀兄娶嫂”之前,似乎只是幽灵的暗示。
第三个来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从“内务大臣剧团”于1594年6月11日在纽纹顿靶场剧院(The Newington Butts Theatre)演出的以哈姆雷特为题材的旧剧嫁接而来。这一所谓“原型《哈姆雷特》”的剧本已经失传,作者不详。但也许是因为英国剧作家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曾于1589年出版过一部著名的复仇悲剧《西班牙的悲剧》(The Spanish Tragedy),并且《哈姆雷特》在设计被谋杀者的幽灵出现和主人公复仇迟疑这两点上与《西班牙的悲剧》完全一样,因此,有人认定失传的“原型《哈姆雷特》”的作者就是基德,而那部剧的名字叫做《乌尔•哈姆雷特》(Ur-Hamlet)。基德于1589年创作此剧,之后该剧一直为“内务大臣剧团”所有。
莎士比亚借鉴并整合了这些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独创的情节,体现了他的深刻思考与戏剧创作方面的不凡天赋。比如,在第五幕第一场增加了“原型《哈姆雷特》”里没有的发生在墓地的戏,堪称神来之笔,也是诠释哈姆雷特作为一个生命孤独者思考生与死的点睛之笔。当他看到掘墓人手里的一个骷髅,说:“现在这蠢驴手里摆弄的也许是个政客的脑袋;这家伙生前可能真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政客。”“从这命运的无常变幻,我们该能看透生命的本质了。难道生命的成长只为变成这些枯骨,让人像木块游戏一样地抛着玩儿?”
通过研究和挖掘,我在每一篇导读开始,就对这些“原型故事”和直接或间接的灵感来源作了梳理。我把九篇导读中梳理“原型故事”的专章结集为《原型故事与莎士比亚》一书,将很快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虽说莎剧无一例外都源于既有的故事框架,但这些“原型故事”又无一不经过他的改编、加工、提炼从而获得艺术升华。说句玩笑话,莎士比亚写戏从许多“债主”那儿借了“原型故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只记住了莎士比亚,若不做专门研究,既没人知道那些“债主”是谁,更没人关心他当初怎么“借”的“债”。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若非借助莎剧,这些“原型故事”或早遗失在历史的暗处。这也再次证明了莎士比亚是个天才!
卞:在莎剧中,“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的情节多次出现,在舞台上的呈现受演员和化妆技术所限,观众可能一望即知是同一个人。现在国内也有很多电视剧里有类似情节,但演员扮相不到位经常被观众吐槽,被当成是剧组不走心和忽悠观众的罪证大加抨击。为什么莎剧中类似情况可以以“戏剧”为由被轻轻放过,甚至可以理解为观众与演员间的一种默契,而现在的电视剧里这样的情况就会被严厉指责?这体现了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关系怎样的变化和不同?莎剧在英国反复上演,每一个演员和剧组都会在舞台表演中注入自己的理解,这些不同版本的表演对于读者和观众理解莎士比亚而言是重要的资料。但是在国内这一部分是很少的。您觉得未来莎士比亚作品的舞台表演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在国内的发展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傅:简言之,这在今天似乎是个无解的难题,而对于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们来说,“易装”是他们惯用的喜剧手段。这是由时代决定的。理由很简单,当时女王治下的英格兰,尽管戏剧开始勃兴,伦敦的剧院越开越多,却明令禁止女性登台表演,因而舞台上的女性角色均由男性扮演。
这为舞台上女扮男的“易装”喜剧提供了天然便利,因为舞台上的“她们”原本就不是女儿身,当“她们”一旦通过“易装”自然天成地“回归”男性,便等于“她们”在以面庞、体型、骨骼、肌肉、身高、嗓音等与生俱来的所有男性特征本色出演①当时多以11—12岁尚未变声的童男扮演青春女性角色如朱丽叶,而像朱丽叶的奶妈等年老女性之角色,则仍由成年男子扮演,因此并非所有女角均有“显著的男性特征”。,扮演“她们”的演员连束胸都不用,对如何消除女性特征绝无后顾之忧。“她们”真身就是男人!假如“她们”愿意,连假胡须都不用戴,胡子会从“她们”脸上滋长出来。在舞台上,“她们”跟“他们”属于雌雄同体,毫无区别。
“易装”喜剧是莎士比亚的拿手好戏,他最精彩的两部“易装”喜剧,当属“四大喜剧”中的《第十二夜》和《皆大欢喜》。在这个层面可以说,莎士比亚只属于他那个时代到剧场看舞台演出的观众。那个时代,在剧场里看戏的观众的心里始终清楚,舞台上的“她们”不仅是由年龄或大或小、相貌或美或丑、身材或高或矮、体型或胖或瘦的男人饰演的女性角色,还经常出演一号主人公。在莎士比亚的喜剧里,最典型莫过于《第十二夜》中的贵族少女薇奥拉,“易装”之后,变身为奥西诺公爵的侍童——“男仆”切萨里奥;《皆大欢喜》中遭放逐的西尼尔老公爵的女儿罗莎琳德,经过“易装”打扮,化身成高大英俊(或许不会使用高大的演员扮此女角)的“美少年”加尼米德。
这本身已是绝佳的喜剧佐料,加之剧中穿插大量由“易装”带来的阴差阳错的误会,以及按剧情所需制造和配置的令人捧腹的闹剧、笑料,浓烈、欢快、热闹的喜剧效果自不待言。比如《第十二夜》,奥西诺公爵爱上伯爵小姐奥利维亚,奥利维亚却爱上替他前来求爱的切萨里奥(薇奥拉),而薇奥拉(切萨里奥)深爱着自己服侍的主人奥西诺;再如《皆大欢喜》,奥兰多与罗莎琳德一见倾心,彼此相爱,等他俩各自逃难避祸,来到阿登森林以后再相逢,相思痴情的奥兰多认不出“易装”成加尼米德的罗莎琳德,而这位女扮男相的英俊少年,为考验奥兰多对“她”的爱是否真心,一定要他向“他”求爱。从中亦可见出两位少女的另一点不同,薇奥拉始终在被动中等待或寻求主动,罗莎琳德则将爱情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若以现代视角观之,会觉得这样的情节十分滑稽,简直幼稚得可笑。所以,这样的喜剧只能发生在剧场里。
英国文艺复兴鼎盛期的莎士比亚,塑造了许多鲜活的、散发着浓郁人文主义气息的女性形象,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娅,《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亚,《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艾米莉亚,《李尔王》中的考狄利亚,等等。但仅就“易装”喜剧而言,最典型、靓丽的女性形象当属薇奥拉和罗莎琳德。诚然,虽不能因莎士比亚写了“易装”喜剧,便把他视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但他已把女性当成像男性一样的人来看待。难能可贵的是,莎士比亚以“易装”喜剧的方式,让舞台上装扮成男性的“她们”以男性的身份替女性发声,尤其发出那些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言说的,甚至羞于启口的内心感受和爱意情愫,其中包括对于男性(男权)的态度和批评。比如,《第十二夜》第二幕第四场,“易装”成切萨里奥的薇奥拉,以男性身份对奥西诺公爵说:“女人对男人会有怎样的爱,我再清楚不过:说实话,和我们一样,她们的爱也出自真心。”“我们男人可能说得更多,誓言更多;但的确,我们对爱的炫耀比爱意更多,因为我们总是证明自己,誓言太多,真爱太少。”在《皆大欢喜》第四幕第一场,身着男装的美少年加尼米德嘴里说着男人的话,言下之意却是女性的真情告白,“她”不信什么爱心恒久不变的鬼话,认为“男人求爱时像四月天,一结婚转眼变成十二月天:少女在少女的时候是五月天,一朝为人妻,天就变了”。
显然,“易装”不仅使舞台表演变得热闹、好看,喜剧效果跃然提升,更使扮演“她们”的男演员,在那么天然地换掉凸显性别特征的女装,挣脱了由女装带来的性别束缚之后,可以自由施展作为男人的智慧、才华和能力。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一刻,“她们”是男人,不是女人。撇开舞台表演不谈,仅就人物形象而论,无论薇奥拉还是罗莎琳德,都是独具风采神韵、卓尔不凡的时代女性,《第十二夜》和《皆大欢喜》也因她俩活色生香、魅力永生。
卞:复仇和报复是在几乎所有莎士比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的一个情节。这种价值观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来源?是宗教还是《汉谟拉比法典》中体现的同态复仇?这和中国的道德观、价值观有什么异同点?这种心态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如何被接受?
傅:无疑,这种价值观一部分源于宗教,一部分源于滋养莎士比亚的古希腊、罗马戏剧家们的影响。拿宗教影响来说,正好可以回应我前面讲到的,若不熟悉《圣经》便难以读懂莎剧。举两个例子,“四大喜剧”之一的《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当萨拉里奥听说安东尼奥有商船在海上遇难,担心他不能如期还钱,便找到夏洛克试图替安东尼奥说情:“即便他到期没还你钱,你也不会要他的肉。拿他一块肉能干什么?”夏洛克断然拒绝:“可以做鱼饵。即使什么饵都做不了,我也能拿它解恨。他曾羞辱我,害得我少赚了几十万块钱;他讥笑我的亏损,嘲讽我的盈利,贬损我的民族,阻挠我的生意,离间我的朋友,激怒我的仇人;他的理由是什么?我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就不长眼睛吗?犹太人就没有双手,没有五脏六腑,没有身体各部位,没有知觉感官,没有兴趣爱好,没有七情六欲吗?犹太人不是跟基督徒一样,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会伤害他;身患同样的疾病,同样的医药能救治他;不是一样要经受严冬的寒冷和盛夏的酷热吗?你若刺破了我们,我们不一样流血吗?你若挠了我们的痒痒肉,我们不也一样发笑吗?你若给我们下毒,我们能不死吗?而你若欺侮了我们,我们能不报复吗?既然别的地方跟你们没有不同,这一点跟你们也是一样的。假如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他会以怎样的仁慈来回应呢?复仇!假如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犹太人又该怎样以基督徒为榜样去忍耐呢?没说的,复仇!你们教了我邪恶,我就得用,假如我不能用得比基督徒更为出色,那将是我的巨大不幸。”夏洛克在此表明,他除了是一个犹太人,更是一个人,一个跟基督徒一样的人!而且,基督徒也有邪恶,也要复仇!
再看“四大悲剧”之一的《奥赛罗》第二幕第一场,伊阿古对奥赛罗的复仇动机来自他怀疑奥赛罗跟他老婆艾米丽亚有奸情,他说“这个念头像毒药一样噬咬着我的五脏六腑”;他甚至怀疑卡西奥跟艾米丽亚也有染。因此,他要让奥赛罗陷入可怕的猜忌:“除非我跟他以妻还妻,出了这口恶气,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也没有任何东西会令我心满意足;即便不能如此,我至少也要让那摩尔人由此产生出一种理智所无法治愈的强烈嫉妒。”“逼得他发疯。”
“以妻还妻”?!没错,这是莎士比亚为鞭辟入里地描绘伊阿古阴毒的邪恶人性,特意为其量体裁衣,专门打造的“伊阿古式”的复仇方式。显然,谙熟《圣经》的莎士比亚是刻意让伊阿古化“摩西律法”为己用,一为凸显他洞悉人间世情的高智商,二为揭示他不惜代价复仇的邪恶手段。
在此,先特别说明一下英文原剧中伊阿古“wife for wife”这句台词,朱生豪译为:“他夺去我的人,我也叫他有了妻子享受不成。”梁实秋译为:“除非是和他拼一个公平交易,以妻对妻。”孙大雨译为:“只等到我同他交一个平手,妻子对妻子。”事实上,只要考虑到伊阿古是故意要盗取《圣经》的弦外之音、意外之味,那么译作“以妻还妻”最为妥帖、精准。它折射的是圣经意象。多妙!
然后,再看《旧约•出埃及记》21:23-25载:“如果孕妇本人受伤害,那人就得以命偿命(life for life),以眼还眼(eye for eye),以牙还牙(tooth for tooth),以手还手(hand for hand),以脚还脚(foot for foot),以烙还烙(burn for burn),以伤还伤(wound for wound),以打还打(stripe for stripe)。”《利未记》24:20载:“人若伤害了别人,要照他怎样待别人来对待他:以骨还骨(fracture for fracture),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申命记》19:21载:“对于这种人,你们不必怜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伊阿古向奥赛罗“复仇”的基督教《旧约》里的价值观,跟夏洛克所信奉的向安东尼奥复仇的犹太《圣经》里的价值观,一模一样!
阅读、欣赏莎剧,要注意到这个层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莎剧中的人物,读懂莎剧。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我最后想说,新译中的丰富注释和详实导读,是读懂莎剧的一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