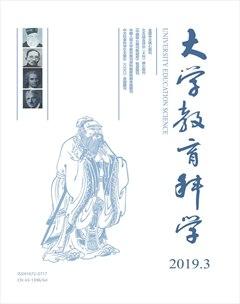儒家“三达德”在大学教育中的意义生成
高晓 吟沐熙
摘要: 知、仁、勇“三达德”,出自儒家经典《中庸》。“三达德”道德体系中每一项单独的价值观,都可以生成对大学教育具有特殊价值的内涵与意义。“不惑之知”可以生成大学教育中关于学问人生的意义;“爱人之仁”通过对人的肯定,为大学教育的可能性提供了原则、依据和要求;“不惧之勇”要求大学教育对真理的追求有所为有所不为。“三达德”是人回归其天性的通达,学生通过这种通达重新获得潜藏于人性之中的美德。大学教育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帮助学生发现并彰显自身的知、仁、勇的完美德性。知、仁、勇三者各有范畴,但又在逻辑上前后连贯,圆融共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共同构成对大学教育的整体道德指导。
关键词:三达德;知;仁;勇;大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3-0037-06
收稿日期:2019-03-07
儒家“三达德”出自《礼记·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意指知、仁、勇这三种品性是普天之下实现德性的途径,也是指一个人一旦具备了知、仁、勇三种品行,就在德性上达到了圆满。儒家学说中有许多关于“三达德”的论述,如:“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知者不惑,仁者不优,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知、仁、勇“三达德”是儒家学说中前后承接、逻辑清晰的完整道德体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不仅对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修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现代从政治到企业到教育的各行各业、各种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到其做人做事的原则与依据。在当代我国倡导大国复兴、召唤中国精神、重视卓越人才培养、重视大学建设的背景下,重温儒家“三达德”思想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三达德”道德体系中每一项单独的价值观,可以生成对大学教育具有特殊价值的内涵与意义,同时三大价值观又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对大学教育的完整道德指导。之所以说“三达德”价值体系对大学教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三达德”的一些原理比较深奥,更加符合大学“高深学问”的特质;还因为“三达德”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君子”,“君子”更加倾向于意指成年人或青年人,而不是儿童。所以“三达德”价值体系更适合于大学教育而不是基础教育。
一、“不惑之知”与大学教育中的学问人生
知,在儒家“三达德”的道德体系中是其它道德的一个起点,它既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人只有具备“知”的能力与智慧,才可以去践行“仁”和“勇”的品德。“知者不惑”的意思是,坚持追求知识的人不会感到迷惑与困惑,他会用自己的知识去解惑。大学教育需要这样不被世事迷惑的知者,和指导世事與人生迷津的知识,即“不惑之知”。将“不惑之知”落实到当下我国大学教育之中,可以生成三种知识的不惑:
(一)博学笃行,达到对学问知识的不惑
在儒家看来,要成为一名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就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这段耳熟能详的话,呈现了学习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或层次。第一阶段,“博学”,是指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由此获得渊博的知识,并籍此打开眼界,开放心灵,扩大胸怀。第二阶段,问、思、辨。在博学的基础上进行怀疑与思考,找出其中的对错。第三阶段,行。在学问思辨之后,去践行那些自己认为是真理的教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学、问、思、辨、行应该是大学师生基本的学术品质。反观我国当下高等教育现实,不难发现大学教育中的种种困境。从学生生源看,大多数新生既不博学也不会思考,尤其是在他们刚入校时。他们以前的学习指向基本上是以考试为目的,对那些有限内容的所谓掌握,也只是停留在记忆和解题做题的层次上。他们并没有经过反思、甄别与选择的训练,越是通过强化训练而能背书解题的学生,就越是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而进入大学。但是,大学教育与其它阶段学生培养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倾向于期待他们的学生能解决问题,而对前者期待倾向于他们的学生能发现和提出命题,并为证明命题制定规则,以此引领专业与公共社会。所以,大学教育要提高水平,就要从源头开始,应具有自我选择生源的权利,通过公正而严格的选拔,录用那些具有学术天分、好学博学、思维活跃、品德高尚并具有远大志向的学生。大学生的培养目标也应该区分于其它阶段的教育,体现更高要求的“学、思、行”的特色。
从教师来看,对“博学笃行”的落实,需要特别重视“行”。在儒家思想中,“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行”就是知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博学慎思之后“笃行之”,从行动上去落实通过学与思而明白的道理规常。《礼记·儒行》有云:“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作为一种道德的知,必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道德与道理的区别在于,道理可以通过学问思辨获得,而道德则需要实践。有些大学教师做出一些有违道德甚至法律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与法律知识,而是对知识的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和对别人说教上。在师生关系上,教师的博学笃行对学生有着重大的影响。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里仁》),意思是善于求知的人见到才高德旺者就会向他学习;而看到才浅少德者就会反省自己是否也是这样。大学中的教师首先应该是学问方面的榜样,现在提倡的“科教融合”一定是建立在教师深厚专业功底之上的。一些有条件的大学为了让学生尽快走上一流学问之道,在本科阶段就请来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或派出本科生进入欧美世界一流大学交流学习,让他们接触世界顶尖大学著名学者。获得了这种机会的学生一般或多或少地会以接触过这些教师为傲。其次,教师还应该是学的德行方面的榜样。现在大学里开设的政治或思想品德课,真正能引起学生兴趣并唤起其情感的并不多。一些专家关于孔子、苏格拉底等内容讲座或许有感染力,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但学生将道德与责任落实到行为上的也很少。所有关于德性的教师的“教”,只有以身作则、长此以往落实于行动,才能起到对学生的“育”的作用。
(二)明辨是非,达到对善恶美丑的不惑
儒家关于“知”的思想体系中,“善”是一个自始至终的追求。《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善”?在持“性善论”的孟子看来,人的心性具有四大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把其中的“是非之心”界定为“知”。这样,“知”就成了一种善。作为道德的“知”,就是要明辨是非,知道对错[1]。落实到大学教育中,“善”就是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学校、到师生都应该清楚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在遇到各种阻力时与不理解时,都要坚持自己的本分。如,学校在处理与上级行政部门关系时,在处理行政与学术关系时,在制定学校政策时,要进行谨慎的独立判断,牢记自己的“通过高深学问培养学生”这一重大使命并积极笃行这一使命。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意思是一个人只有选择与具有仁德品行的人相处,才能说这个人是有知识的[2]。大学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大学也许无法去苛求一个有利于学术的外部自由环境,可是大学可以向“善”者学习从而创造“善”的内部环境。
大学应当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盲从某些临时性政策的命令,不追逐短暂的市场潮流,甚至不必模仿国外一些大学的各种运动,脚踏实地同时又志存高远,从学生出发同时又担负人类理想,关注社会同时又适当地远离世俗[3]。学校应该这样,大学的师生们更应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与独立性,所谓“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中国特色的大学,所以大学对学生的在道德学问上的要求甚至要超过古之君子的要求,使他们通过长期与学问真理这种“善”打交道,达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的圣贤境界。而这种积善成德,对大学生来说,他们从入校的那一天起就应开始修养,否则就难以成为真正的精英。
(三)知天命,达到对“自己”人生意义的不惑
在儒家“三达德”思想体系中,“人”是最初的出发点与最终的目的,也是“知”的意义所在。所以,“知”,首先就意味着知道自己[4]。怎样才能知道自己?“自己”是一个相对于他者的概念。相对于“天”而言,自己是天人关系的一部分;相对于“人”而言,自己是人人关系的一部分。“自己”是天地万物关系中的唯一的道德体认者[5]。所以,要认识“自己”,在孔子看来,首先就要“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学而》)。这个不能逾的“矩”,就是“天命”,而“知天命”“耳顺”和“不逾矩”的行为,就是君子寻找自己和成为自己所行的道。
“知天命”落实到我国当代大学教育之中,意味着要帮助学生寻找学习知识的目的,获得关于自己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学习并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自己获幸福的一种方式[6]。儒家的天命观告诉我们,任何人与事物都只是天命的一部分。每一个通过不同方式行的“道”,最终都是为了在天地万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得其所,各发其份。与天地万物、与他人和谐相处,这才是“知己”的真正意义。秉承“天命”而生的人之天性,本就各种各样,有的宜于做高深学问,有的擅长体力技能,有的爱好花草虫鱼,有的喜爱读书,有的厌倦书本。顺“天命”而行的人才教育之道,就应该提供多种土壤和营养,让不同人、不同天性中的“善”天然成长。这样,人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违背人的天性去进行教育,就是“逾矩”,就是不知天命的表现。可是今天,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在假设他们孩子是能做学问者,都去鼓励孩子考大学,全然不顾他们是否真的具有做高深学问的天赋、是否对学问具有真正的兴趣爱好,导致那些即使考上了一流大学的学生也感觉不到真正的幸福[7]。但是,大学既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学生,就应该根据他们的兴趣个性和已有基础对他们进行学术训练,要求他们以真诚的态度进行学问思辨,以致博学笃行,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和找回那个在基础教育阶段被扭曲和抛弃的真正的自己。
二、“爱人之仁”与大学教育中的以人为本
“仁”,在儒家“三达德”道德体系中,是一种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与实践。当人明知解惑之后,怎样去对待那些知识道理呢?这就靠“仁”。作为儒家道德文化核心的“仁”,早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中就已出现。据《左传》与《国语》记载,“仁”的主要涵义是德行[8-9]。到春秋战国时期,“仁”就变成以一套完整的以“博爱”和“爱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如果说“知”更多地是阐释天、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仁”,主要是从人自身出发而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出的道德要求。“爱人之仁”落实到当代我国大学建设之中,也可以生成多重意义。
(一)仁者人也,“仁”是对人的价值与教育意义的肯定
孟子继孔子的学说曰:“仁者也,人也。”(《孟子·尽心》),意思是“仁”和“人”是同一个人概念。这也就意味着“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人从根本上就具有“仁”的品德,或者说,人就是“仁”的代名词[10]。而具体的“仁”,则是“爱、善、美、诚”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总和。所以,当孔孟将“仁”定义为人的时候,就肯定了人具有完美天性的不变价值。孔孟关于人“仁”的这一规定性,远远超了之前关于“仁”的理解,也为“仁者爱人”的具体道德提了依据。“仁者人也”,将人规定为一种善和美好的存在,从而肯定和赞美了人的意义[11]。这一点,落实到大学教育中来,是提醒教育者:正因人具有一切美好的天性,所以培养一流人才的教育才有可能。大学教育的過程应该是引导学生去发现学生自身卓越性、从而构造每一个个人生活的幸福与意义的过程。追求卓越的大学教育,应该是一种提供优质土壤并进行精心耕耘与培育、使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追求与实现自己卓越天性的教育。理想的大学教育,不仅要求珍视本科教育中每一位个体,也要求重视作为整体的大学教育各个层次,尤其是本科教育层次。从现实中我们可看到,越是重视本科生的教育,便越为有可能成为一流的本科教育。美国大学中的本科生学院,其受重视程度往往超过研究生学院。
(二)仁者爱人,“仁”是由亲及远的博爱之心
“仁者爱人”中的仁,与“仁者人也”中的“仁”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是指一种具体品行。正因为人是一种有尊严的美好存在,所以具有仁之品德的人就应该去爱人。人的这种爱人之心乃出于天性,所以,人对人的爱,是由爱亲近的人开始的。“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悌是对自己亲人本能和习惯性的爱,这是人理应做到的,否则就不能成为人。但仅爱自己的亲近之人,这是不够的,还要“泛爱众”,达到“民兴于仁”。孔子的这种由近而疏的仁爱之道,紧紧抓住了人性心理亘古不变的道理,符合人的心理轨迹,是人道精神的高度自觉,也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高度省视。在大学教育中,学生在脱离父母来到大学之后,最亲近的人就是大学的老师,所以他们应该懂得尊师重道的道理。对于师生关系而言,“仁道”或“人道”就是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可是,反观当下大学教育,这种仁爱之道的师生关系很少真正存在。首先,学生对教师缺少应有的尊敬。一些大学课堂上,教师在讲台上上课,学生在座位上有的看手机,有的睡觉;有的学生除了考试之外从来不到课,到了考试时,则要求任课教师透题,如果考试成绩不好,就给教师差评。教公共课的教师尤其难以得到学生的尊敬。其次,一些教师对本科学生缺少应有的关爱。大学的教师往往承受着很重的科研压力,所以容易疏忽对本科生的教育。他们基本上叫不出本科學生的名字,更没有对他们学术和生活作出应有的要求与训练。
大学教育中的“仁”,不仅仅是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师之间相互尊重与关爱,它还期待学生关心整个人类,成为人类精英,使他们不仅成为专业方面的、而且也在人类社会精神方面的引领者。这样,学生就不能只对身边的老师同学行“仁”,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社会有点类似于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理想社会的形成,有赖于每一个人的仁心与仁德,有赖于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而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而言,他们的仁爱也许只停留在对他所接触到的有限的个体身上,而对于普遍“泛爱众”的“仁”则难以达到。去唤醒公众沉睡的灵魂,并能以博爱之心关爱亲者以外的社会与他人,这是大学教育中师生都应承担的重大社会责任[12](P176-179)。因为其“一流”地位,大学师生们成为身兼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不仅自己要成为公众的榜样,而且要凭借自己的一流地位去影响和改造公共社会,引领社会走向理想的“大同”或“共同体”。
(三)克己复礼为仁,“仁”是保障人才成长的规范礼仪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在这里说的是,人只有通过一定的礼仪规范约束自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才能达到天下的美好。这一点对我国当下大学教育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礼是一套道德规范,有必要通过一些庄重的仪式来表达和强化它。目前,我们的大学确实对本科生有许多的规范与要求,但大多只停留在“学生手册”等纸面上,对这些规范的贯彻,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克己复礼”之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将这些条规通过礼仪的形式表达出来。如: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都要足够庄重肃穆,可以从学生角度出发,将“开学典礼”改成“入学典礼”,因为“开学”是站在学校角度讲的,不足引发学生共鸣;增加一些与知识追求活动相关的仪式,如读书节,学术节;增加本科三年级典礼(大学教育一般在三年级进入专业教育,前两年以通识教育为主)等。仪式所产生的庄重感,仪式上学生们的誓言,仪式所催化的青年豪情与热血,对学生的信仰的建立与养成,对学生终身价值观的培养与确立,都有着莫大的影响。当然,礼仪的建立,要以人的真实而合理的心理情感为基础。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是指要恪守不损人利己的礼节。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学校规章制度的设立,一定要符合“仁”的原则,制订者自己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就不能要求学生去做。以“仁”的规范去对待学生,才能培养出具有仁德的一流学生。
三、“不惧之勇”与大学教育中的求真有为
“勇者不惧”,是在“不惑之知”与“爱人之仁”基础上所具备的态度与处世实践原则。具备知识与美德的人,可以勇敢面对并克服来自自我的和外界的困难。这种品德就是“不惧之勇”。将这一道德品质落实到大学教育中来,可生成以下意义。
(一)自强不息,“勇”是不畏困难积极进取的努力与胆量
孔子继承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的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和发奋图强的思想:“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说的是有道义者应当务实而敏于行动,感正义之事就要立刻行动起来。孔子颠沛流离十几年,坚持传播心中的正义,还遇到生死考验的时候也不放弃其君子风度。如一次,鲁国阳虎掠夺和残害了匡人,而孔子因为与阳虎相貌相像而遭匡人的围困。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孔子不仅没有退缩畏惧,反而安慰随行弟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意思是,天都不能丧杀斯文之人,其他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孔子的大无畏精神由此略见一斑。在当代的大学教育中,“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主要体现在对学问真理的追求之中。大学一直信奉“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中立价值[13],而追求真理之道充满艰辛并永无止境,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些年轻生命肩负高强度科研与教学的双重负担,一些科学家从事如地质考察与化学实验之类充满危险的科研工作,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他们英才早逝。人文与社会学科中,为追求与坚持真理而牺牲生命的学者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乔姆斯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14]还是朱里安·本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12](P120),都将真正的知识分子看成是敢于持有异议者,即勇于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说出真相,谴责当权者的罪行,呼吁公平正义以及对穷人和受苦者的关怀。这当然要冒着引起当局恼怒的危险。”[15]大学教育,需要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大无畏勇气。
(二)知耻而后勇,“勇”是诚恳务实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气魄
羞耻感和荣辱心,这本是人的天性,但时刻保持这种天性,在犯错后诚恳地承认自己的不足与错误,却需要勇气。这再一次表达了教育的意义乃是引导学生去“发现自己”。人本来的天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之后,如果没有教育的帮助及自身的努力,就容易丢失与扭曲。孔子强调对“知耻”天性的保护。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意思是诚实地承认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这才是知识的真谛。孔子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知过改过,这也需要勇气。大学教育中,特别需要教育参与者的“知耻”品格。从招生录取开始,明明知道光靠考试难以选拔优秀大学生,但为什么不能废除高考执行完全的自主选拔?大部分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人情难却”,招生者可能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不公正不公平之事。其实,“人情”用于利益与权利争夺的时候,就是一种不诚实不知耻的表现。有些大学也存在一些歪风:学生进入大学以后,时有考试舞弊,论文剽窃甚至代写;教师为职称为名利去跑论文、跑课题,拿到政府科研经费之后不做真实研究,而是以几篇几乎引不起任何反响的论文去应付政府、应付专家审查;甚至完全不做任何科研而以全部剽竊的外国成果骗取国家经费。这些,全然颠倒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荣辱观,抹灭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羞耻感。在这样的“恬不知耻”的学术环境中,怎能期待学生成为社会的精英呢?
“君子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也。”(《孟子·离蒌》),说的是人的生命有限,要具有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原则,坚决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舍弃那些不能做的事情,才能集中精力去做自己有能力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孔子倡导中庸,但知道“中庸之道”难以为之,就提出了“狷者”和“狂者”的概念:“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狂者是期待有所为而积极进取者,而狷者是坚守道义、洁身自好的“有所不为”者。相对于“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时更加困难,更加需要勇气与力量。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学生不为考试而舞弊,教师不为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而找人,专家不为金钱而讲座,学校不为评估而作假,资源控制部门不以项目为诱饵,大学不屈从外在权威,不理会外在诱惑;不追逐外在功名利禄。在这样的舍弃下来从事大学教育,那就离真正的一流大学不远了。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道德价值是孤立的。知、仁、勇三者不但具有各自的范畴,而且在逻辑上前后连贯,在结构上圆融共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达”是“通达”的意思,“德”是知、仁、勇三大美德。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仅知、仁、勇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交通,而且三者也是人返回其天性的通达,通过这种通达,人会重新获得潜藏于人性之中的美德。大学教育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帮助学生发现并彰显自身的知、仁、勇的美德。为此,教师要成为知、仁、勇的榜样,学校要建立有利于学生知、仁、勇品格成长的制度,校园要形成知、仁、勇德性养成的文化。
参考文献
[1] 焦循. 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4:88-89.
[2] 陈晓芬,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19.
[3] Karl Theodor Jaspers.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M].London:Peter Owen Ltd,1965:32.
[4] 陈赞.中庸的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65.
[5] 李静,译注.中庸全集[M].北京:天地出版社,2017:56-60.
[6] 叶澜.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教育精神与智慧[J].教育研究,2018(06):2-7.
[7] 胡弼成,姚云龙.父母素养提升:新时代家齐国治的必修工程[J].当代教育论坛,2019(02):1-14.
[8] 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36-138.
[9] 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7-59.
[10] 蒋伯潜.四书新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21.
[11] 王青.先秦思想文化论札[M].北京:中华书局,2007:178.
[12] Benda Julien.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M].Beacon Press,1955:176-179.
[13] Newmane J.H.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 Indiana:University of Nofre Dame Press,1982:68.
[14] Noam Chomsky.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J].The Y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67(02):98.
[15] 高晓清.大学的文化诉求与创新使命[J].大学教育科学,2013(02):10.
(责任编辑 陈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