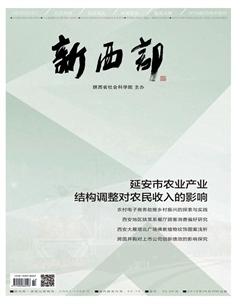宋教坊舞乐、宫廷雅乐中“引舞”及“舞头”的概念内涵分析
朱彦雷



【摘 要】 本文对宋教坊舞乐、宫廷雅乐文、舞二舞中的“引舞”及“舞头”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分析。研究发现,“引舞”和“舞头”并非是两种不同的职司或脚色。“舞头”是从时空前后的角度对某种“引舞”所定义的说法。教坊舞乐中,“舞头”就是舞乐开头部分上场的舞者,具备“引队”功能,又可称其为“引舞”。在雅乐文、武二舞中“舞头”就是位于八佾舞郎前方执旗帜的“引舞”。本文还证明了宋绍兴十三年郊祭时文、武二舞所遵循应该就是北宋政和三年所修订的制度。
【关键词】宋代教坊舞乐;引舞;舞头;礼乐制度
一、引言
宋代教坊舞乐、宫廷雅乐文、武二舞中都有“引舞”、“舞头”等说法,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古杂剧中的“戏头”始于古代舞蹈中的“舞头”,并认为“引舞,亦谓之引舞头”,[1]对杂剧脚色的形成做了重要的贡獻。近世学者对此进行了新的研究并更正了王国维先生关于“引舞始于唐”的观点,同时认为“舞头”和“引舞”,是不同的脚色,功能时有重合, [2]并对“舞末”和“副末”也进行了分析。[3]而笔者认为“舞头”是从时空前后的角度上对某种“引舞”所定义的一种说法,二者并非完全两种不同的职司或脚色,在界限上,“舞头”一般都是“引舞”,而“引舞”却并非全是“舞头”。先从教坊舞乐中的“舞头”进行分析。
二、教坊俗乐中的“舞头”
在宋朝之前,唐代宫廷教坊舞队中,就有“首”和“尾”的提法,基本上同宋代“舞头”和“舞末”概念类似,崔令钦《教坊记》[4]有:
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场,惟搊弹家弥月乃成。至戏日,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没三郎。”令宜春院人为首尾,搊弹家在行间,令学其举手也。
上述史料中,宜春院内人歌舞技艺要远远高于来自平民的“搊弹家”,为了培训,唐玄宗令宜春院内人作为舞队的行首和行尾,并将“搊弹家”置于其行间以学习内人们的舞蹈姿势。在空间位置上,宜春院内人居于舞队的前后,其作用在于令“搊弹家”,“学其举手”,如果称位于队首舞者的为“舞头”的话,那位于队尾的舞人就相应的称之为“舞末”了,同书[5]还有:
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尤者为首尾。首既引队,众所属目,故须能者,乐将阕,稍稍失队,余二十许人舞,曲终谓之合杀,尤要快健,所以更须能者也。
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就缦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开元时期创制的“圣寿乐”是大型舞乐,其中有很多叠次,并且在不同叠次其舞蹈表演风格也不相同。从第一叠舞者着“缦衫”“藏绣窠”,到第二叠“抽去笼衫”“文绣炳焕”,多重叠次,不同的演出风格,就从时间序列上对演出效果提出了要求。因此在舞乐开始阶段,因“众所属目”,必须“故须能者”,选择其中舞蹈技艺优秀的,而且“首既引队”,点明舞“首”为“引舞”的可能性;而曲终时,因“尤要快健”,所以“更须能者”。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导致“必择尤者为首尾”,这符合观众对于多叠次的大型舞乐的观赏心理,同时也符合大型舞乐的组织规律,用技艺精湛的舞者负责开头的暖场及结尾的高潮。而“乐将阕,稍稍失队”,说明在第一叠舞曲将要结束之时,舞“首”完成舞蹈动作后,缓缓离场,实现其“引队”功能,然后“余二十许人舞”。这样首先上场的舞“首”和之后舞队就在时间上串了起来,作为大型舞乐的有机构成部分,舞“首”的舞蹈与之后舞队的舞蹈在节次逻辑上具有天然衔接性,这应该是“首既引队”具有的实际意义。如果从时间上去考察整个圣寿乐的演出,把最先演出的舞“首”称之为“舞头”,把最后演出的舞“尾”称为“舞末”,从“首既引队”的功能描述上称“舞头”为“引舞”,应该是符合演出实际的。
上述史料中的“首”与“尾”,分别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与舞乐的“头”和“末”联系了起来。关于“舞头”,唐代诗人王建在其《宫词》中有“一时起立吹箫管,得宠人来满殿迎。整顿衣裳皆著却,舞头当拍第三声。”[6]描述的正是“得宠人来”时歌妓匆忙迎接的场景,而“舞头当拍”,正值“整顿衣裳皆著却”之时,也恰说明乐曲刚开始不久,这又在时间上将“舞头”跟舞乐的开头联系起来,“舞头”就是舞乐开头上场的演出者。
再看宋代教坊舞乐中的“舞末”,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的记载:[7]
舞者入场,至歇拍,续一人入场,对舞数拍,前舞者退,独后舞者终其曲,谓之舞末。
后舞者终其曲,称为“舞末”,这也是在时间上将“舞末”同舞乐结尾联系起来,“舞末”就是舞乐结尾的演出者。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圣节”条中有[8]:
第一盏,筚篥起《万岁梁州》曲破,齐汝贤。舞头豪俊迈。舞尾范宗茂。
其中,“舞尾”就是“舞末”。既然“舞末”是舞乐结尾部分的演出者,那么与其对应的“舞头”,也应该同唐代一样,是舞乐开头的演出者。这都是从演出时间先后的顺序上对乐舞开头以及结尾的舞者定义的说法,而宋宫廷雅乐文、舞二舞中的“舞头”则又有不同。
三、宫廷雅乐文、武二舞中的“引舞”与“舞头”
再,宋代用于郊庙奉祀以及大朝会的宫廷雅乐的文、舞二舞中也有“舞头”和“引舞”的说法。有的学者则认为“引舞”和“舞头”在宋代都是专门设置的职司或者制度,[9]研究者们多引述《宋史》中的如下内容作为支撑的依据:
乐工、舞师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给。其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诸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10]
上述史料中有“引舞”,“色长”,“文武舞头”等说法,似乎在郊庙奉祭和大朝会的文、武二舞中,“引舞”和“舞头”是独立的职司,由不同人员担任,事实果真如此么?
上述记载的是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郊祭太社、太稷、九宫时招募乐工的情况。从北宋立朝到南宋灭国,用于郊庙祭祀和大朝会宴乐的文、武二舞的礼仪规范经历过多次修订,基本都集中在北宋,修订内容包括礼仪用乐、宫悬器具、衣冠执物、舞蹈动作等细节,人员配备上变化较小。南宋在仪礼用乐制度上基本上遵循的是北宋旧例。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11]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仪礼开始恢复。根据《宋史》在政和三年之前,[12]文、武二舞只有“引舞”和“舞郎”,并没有“舞头”,而政和三年修订的礼仪中增加了“引舞头”和“引舞人”的说法。绍兴十三年的“文武舞头”应该是沿袭政和三年的说法,并且政和三年还分别在舞队前方增设了两名舞色长,同时武舞中执铎的两人改为执单铎、双铎各两人,“引舞”人数比之前也增加了两人,而衣冠服色制度也與前代不同。据《宋史》,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议礼局上奏并被诏许颁行的“亲祠二舞之制(大朝会同)”的记载:[13]
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
文舞分立于表之左右,各四佾。
引文舞二人,执纛在前,东西相向。舞色长二人,在执纛之前,分东西。
若武舞则在执旌之前。
引武舞,执旌二人,鼗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于宫架之东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后。
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
(大朝会:引文舞头及文舞郎并进贤冠、黄鸾衫、银褐裙、绿□裆、革带、乌皮履;引武舞头及武舞郎并平巾帻、绯鸾衫、黄画甲身,紫□裆、豹文大口裤、起梁带,乌皮鞲。)(笔者按:该条在史书中属于小字部分)
引武舞人,武弁、绯绣鸾衫、抹额、红锦臂鞲、白绢裤、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同。
至于新添加的“舞头”(引舞头)的人数配备、职责以及是否可兼任,都不明确。鉴于文、武二舞的“舞郎”、“引舞”、“舞色长”均为左右对称布局,“舞头”人数应该为偶数,至少为两人。为了便于分析,暂且认为文、武“舞头”人数各为两人,并且根据是否由内部人员兼任分成两种情况,制成表1如下:
南宋祭祀礼乐制度多遵循“先朝之旧”,上述史料说明在此次祭祀中,二舞八佾的“舞郎”一共128名,而“引头”又是史料没有提及的说法,涉及“引”和“头”应该就是“引舞”和“舞头”,二者一共24名,则“舞郎”、“引舞”以及“舞头”的总数为152名。根据表1,政和三年以前总人数是150名,因此不可能是政和三年之前的制度,而政和三年(不兼)情况下,扣除色长后“引舞”、“舞头”和“舞郎”总人数为156名,也不可能是这种情况。因此,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郊祭所遵循的只能是政和三年修订的制度,并且“舞头”并非另设,而是由内部人员兼任。
政和三年史料中文、武二舞均有舞色长、引舞(引某舞)、引舞头(引某舞头)以及舞郎等说法;同时,武舞还有引武舞人的说法,而文舞则没有引文舞人的说法。而对于舞色长,则有:
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令赴寺教习。”[15]
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16]
可见“舞色长”是大晟府或者教坊中专设的职官,其“深知舞仪”,可以负责“教习”,并且舞色长跟引舞头的衣冠服色的规定并不相同,引舞头不可能由舞色长兼任。从政和三年的制度中扣除舞色长,则剩下的人员根据所执之物,将引舞分成执旗帜(执纛或执旌)以及执乐器(鼗,双铎,单铎,铙,持金錞,奏金錞,钲,相,雅)两类,并和舞郎一同制成人员数目分布表2,根据职司名称和是否有服色规定的情况制成表3。
比较表2和表3,发现二者可以完美对应起来,政和三年制度中的人员数目以及衣冠服色都已明确,之前困惑的概念层次及包含关系也已明晰。所谓的引舞头(“舞头”)就是“引舞”中执旗帜的人员,而引舞人就是“引舞”中的执乐器的人员,而引舞头和引舞人是从手执器物的不同为了区分而引入的。
整理《隋书》“音乐中”、[17]《唐六典》“太乐署”、[18]《宋史》[19]以及《宋会要辑稿》“乐三”[20]中关于文、武二舞中“引舞”与“舞郎”的衣冠服色制度异同情况,制成表4。
通过表4可以看出,由隋到宋,引舞头(“舞头”)和引舞人的衣冠服色多有变化,两者时同,时不同,北宋就有至少两次变化。在以衣冠服色来表征品级高低的古代社会,这种反复现象也正说明了二者并不存在品级上的差别,也就是说引舞头(“舞头”)中的“头”与“引舞”当中具有组织、管理职能的职官并不想干,引舞头(“舞头”)并非是“引舞”的“头”。而二舞中执旗帜的引舞头(“舞头”)的衣冠服色同“舞郎”却一直都是相同的,“舞头”同“舞郎”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或许可从两者在场上相对位置得到印证。
据政和三年的史料,所谓“宫架”是用于悬挂或者摆放乐器(一般钟、磬等)的架子,在大祭祀礼仪中一般在四个方向上横、纵布置若干编钟、编磬以及其他礼乐用器,形成一个口字型的区域。“表”即舞表,为宫架南北中轴线上的标旗,一共四个,彼此相距四步,用于文、武二舞各种规范舞蹈动作的场上位置指引。
据政和三年的史料,武舞时,“舞郎”似乎置于全部“引舞”(执旌者以及执乐器者)的后方,这条记录本身自相矛盾。原因是的“引舞”位于宫架之东西,也就是口字型宫架左、右两条南北竖边上,呈南北方向的左、右两列纵队,手执器具以引导舞形,其位置是固定的。而八佾之舞是在口字型宫架的中间区域排演,执器具的“引舞”在空间上应该是在左、右两边夹着“舞郎”,而不应是在“舞郎”的前面。另,据宋元丰二年(1079年)详定朝会大乐的奏请,执乐器的“引舞”与“舞郎”是明确的“夹引”关系,史料如下[21]: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
再据《隋书》“音乐志”有:[22]
武弁,朱褠衣,乌皮履。三十二人,执戈,龙楯。三十二人执戚,龟。二人执旍,居前。二人执鼗,二人执铎,二人执铙,二人执錞。四人执弓矢,四人执殳,四人执戟,四人执矛。自旍已下夹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
可见,隋代时执乐器的“引舞”同“舞郎”位置关系同样也是“夹引”,由此,笔者认为政和三年所修订的文、武二舞礼仪中,手执乐器的“引舞”(引舞人)同八佾“舞郎”的空间关系仍然是在左右两边“夹引”。在宋代实际郊祭和大朝会礼仪进行过程中,文舞表演结束后,通常直接更换衣冠和手执器物后再重新上场进行武舞的表演。考虑到二舞共用舞表和酂缀,因此,扣除执乐器的“引舞”后,文、武二舞的空间位置应该完全相同。文舞中由于没有执乐器的“引舞”,执旗帜的“引舞”同“舞郎”是“执纛在前”的关系,二者相对密切,武舞应该也一样,增加了执乐器的“引舞”后也应该不会影响这种关系,这与前面衣冠服色分析是相应的。
史料内容之所以产生自相矛盾,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古代汉语是表意的语言,二舞人员的空间布置早已是礼官们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事实,史料上如此说,并不会因语言形式逻辑的上的矛盾而引起古人对其理解的差别。第二,史料整理和翻版刻印引起的错误,其中“执旌二人,鼗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于宫架之东西,北向,北上”或许为小字,与大朝会条格式一致。
基于以上分析,政和三年修订的用于皇帝亲祠和大朝会的文、舞二舞的人员数量、衣冠服色、场上位置等礼仪制度都已完全确定,将二舞的“引舞”、“舞郎”以及“舞色长”的空间位置情况制成图1。
图1中,四周的两重虚线框代表宫架,执乐器的“引舞”分立在宫架的东、西两边,四个舞“表”位于宫架南北中轴线上,“舞郎”分立舞表左、右,每边各四佾,总共八佾。舞色长位于执旗帜的“引舞”前方。执旗帜的“引舞”(“舞头”)位于八佾舞队的前方。结合前面历代礼仪及其修订中“舞头”和“舞郎”在衣冠服色规定上的一致性以及场上位置前后的密切关系,可以得出,所谓“舞头”(引舞头)中“头”并非是“引舞”的“头”,而应该是由于在空间位置上位于八佾“舞郎”前头而引出的说法,这种说法恰好在武舞时,与同为“引舞”的执乐器者(引舞人)在概念界限上进行了互不包含的明确划分。
有宋一代,文、武二舞中的“舞头”、“引舞”以及“舞郎”等说法在概念的界限上并非很严格,有的时候甚至相互包含,现将《宋史》以及《宋会要辑稿》中的几个说法的及对应和包含关系制成表5。
从表5可以看出,“舞郎”的始终包含着“八佾”舞者,但有时还包含着执旗帜者;而“引舞”始终包括着执乐器者,但有时又将执旗帜者包含在内。政和三年文、武二舞的人员配置中引舞人、引舞头(“舞头”)以及“舞郎”的概念是较为明晰的,三者互不包含,但如此近似的说法仍存在将引舞人完全等同于“引舞”的可能性。而执旗帜者或被“引舞”包含,或被“舞郎”包含,被“引舞”包含,说明执旗帜者和执乐器者一样,因有“引”的功能而被划归为一类;被“舞郎”包含,则说明其本身就属于舞者中的一员,是在八佾舞队之外,空间上位于前头的挥旗“振作”以导舞的舞者。结合图1,“舞头”应该就是在空间位置上对位于八佾舞队前方的执旗帜的“引舞”所定义的说法。
四、结论
本文对宋教坊舞乐、宫廷雅乐中“引舞”、“舞头”以及“舞末”等说法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整理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在宋宫廷的教坊多叠次大型舞乐中,“舞头”是首先上场并负责大型舞乐开头部分演出的舞者,并具备“引队”功能;而“舞末”是最后下场并负责大型舞乐结尾部分演出的舞者。通常“舞头”和“舞末”是由舞蹈表演技艺更为精湛的艺人充当。
2、在宋宫廷雅乐的文、武二舞中,“舞头”又称“引舞头”,是手执旗帜(纛或旌)的“引舞”,因位置在“舞郎”的前方,而被称为“舞头”。在武舞时,“舞头”与八佾舞队左右两边执乐器的“引舞”共同引导舞队的演出。
3、“舞头”和“引舞”并非是两种不同的职司或脚色,“舞头”是从时空先后的角度对某种“引舞”所定义的另一种称呼。在界限上,“舞头”一般都是“引舞”,而“引舞”却并非全是“舞头”。
4、证明了《宋史》“乐五”内所记录的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郊祭时文、武二舞所遵循的应该就是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修订的制度。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59.
[2][3] 黎国韬. 舞头与引舞补说[J].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2(01)43-46.
[4][5] 崔令钦. 教坊记(外三种)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12-13.
[6] 尹占华. 王建诗集校注[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480.
[7]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220.
[8] 周密. 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 2007.25.
[9] 延保全.引戏色及其文物图像小考[J].中华戏曲,2009(02)33-43.
[10][11][12][13][14][15][16][19][21]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3032.1977: 2939.1977: 2937-3363.1977: 3015-3016.1977: 3032. 1977: 3030.1977: 3358.1977: 2937-3363.1977: 2975.
[17][22]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華书局, 1982.343-344.
[18] 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92.402-404.
[20]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