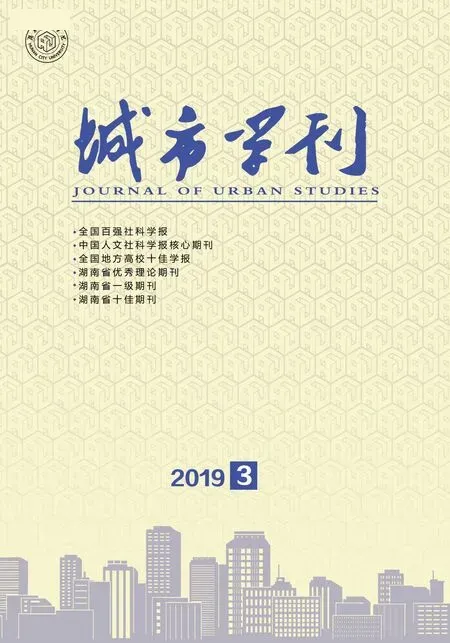19世纪英国城市工业社区的兴起及其影响
欧阳萍
19世纪英国城市工业社区的兴起及其影响
欧阳萍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19世纪的英国号称“世界工厂”,但这一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由于当时政府采取对经济和社会不干预的态度,一些开明企业家开始为其雇佣的工人修建有良好住房且带有教堂、商店和学校等公共建筑的工业社区。工业社区的建设不仅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留存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建筑风格,而且成为此后英国以至欧洲城市社区规划的重要范本。
工业社区;开明企业家;城市规划
19世纪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创造了所谓“伟大的维多利亚繁荣”,[1]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工人阶级居住环境恶劣,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英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工人住房等问题袖手旁观,19世纪一些开明企业家开始为其工厂和企业中的工人修建有质量良好的住房且建设有教堂、商店和学校等公共建筑的工业社区。这些工业社区在住房条件、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英国工人阶级的居住状况
(一)自由放任的指导思想
城市史学家芒福德曾提出:19世纪城市发展的“政治法则”就是相信通过不受约束的逐利行为能达到全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预先注定的协调和谐,有一个世俗的名字,叫自由竞争,或叫放任政策”。[2]自由放任政策确实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当中,个人主义思想使得政府在城市社会管理中严重缺位,最终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度恶劣的城市。
自由放任主义源自法语的“laissez-faire”,意为“让它去,听之任之”,强调政府不干涉经济活动,让企业家和商人自由生产和贸易。18世纪后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尽管工商业者“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但“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3]在亚当·斯密之后,其追随者进一步阐述了自由放任原则,强调通过自由竞争有效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制订有利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法规、维护国内社会秩序和在国际上捍卫英国的工业国家地位——一言以蔽之,应实现政府最小化。
19世纪的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城市下层贫民住房短缺的问题,但是政府“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虽然不能说是软弱无力的,至少也是轻描淡写的”。[4]原因之一是住房建筑成本过高,超出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付能力,因此建筑商不愿意为工人阶级修建和提供住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的干预才有可能刺激工人阶级住房的建设。但是,由于自由放任思想对政府作为的限制,“住房供给的巨大失败几乎一直持续下去。”[4]
(二)极度拥挤的住房状况
当时城市住房最大的问题就是极度拥挤。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来说,他们的时代是“大城市的时代”,[5]因此他们从偏远的乡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然而,这些城市在住房供应方面远远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新来的移民,就像这些人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住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城市环境中一样。恩格斯曾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考察了城市工人的居住环境:“在1840年,5 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 294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 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6]1848年,就连议会议员也注意到“没有什么比伯明翰市、伦敦市以及我国其他任何城市中更糟糕的情况了。在这样悲惨的境地,人们拥挤成一团——不分年龄和性别,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儿子,兄弟和姐妹,陌生的和熟悉的,生病的和健康的,快要死的和已经死的——以一种如此拥挤的、即使是真正的野兽也将会反抗的状态。”[7]就连原本用于储藏东西的地下室也挤满了人:在前工业化时代“地下被认为只适合做地窖或者地牢;但是现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相结合,建筑或者其他行业都充满了独创性,他发明了将地窖和地牢合二为一的地下居室。”[8]
(三)脏乱不堪的居住环境
拥挤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居住环境的脏乱。工业时期有很多城市实际上是由农村飞速发展起来的,一夜之间工厂、仓库林立,但基本上没有基础的排污和供水等设施,导致城市环境脏乱不堪。根据1845年不列颠大城市区域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曼彻斯特的一些地区,7 000多名住户只有33个厕所,在阿什顿区(Ashton)50个家庭也只能共用两个厕所,而厕所的极度匮乏几乎成为当时所有大城市的共同显著特征,即便首都伦敦也是如此。[9]在供水方面,“各个自来水公司供水不足和间歇性……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卫生问题”。[10]许多工人家庭被迫到公共井里取水饮用,但是这些井水“尽管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谈论,但结论都是一样的:一位医生写道‘我每次取一些城镇井水在夏季烈日下放置几小时后,几乎没有哪一次没有看到它变得腐臭不堪’……一位卫生官员直接宣称:伦敦那些浅井里的水集合了所有最坏的特征——它们就是一个巨大粪肥池的排放口。”[10]
拥挤、脏乱的居住环境对工人阶级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使城市的死亡率远高于乡村。19世纪统计学家威廉·法尔曾经比较过1838-1844年英国各地的死亡率,注意到尽管“萨里郡(Surrey)的人口要远远超过曼彻斯特,但在这7年当中曼彻斯特有16 000人死亡,超过了萨里郡的死亡人数……萨里郡有23 523名5岁以下的幼童,其中夭折的有7 364人;而在曼彻斯特5岁以下的幼童是21 152名,但其夭折数为20 726人……在利物浦的情况不会比曼彻斯特好多少。”[11]究其缘由,法尔认为不同阶级之所以呈现差异极为明显的死亡率,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人们的居住环境的差异。[11]
二、英国城市工业社区的建设
恶劣的住房条件导致城市的死亡率上升,也严重影响到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企业家开始考虑为工人提供质量良好的住房。在社会管理中政府缺位的情况下,“19世纪成为慈善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12]1857年,一位社会慈善家宣称:“一个城市的道德状况依赖于这个城市的物质状况:食物、水、空气及其居民的住房;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如此,但令人恐惧的是,在一种还没有估量出来、也许无法估量出来的程度上必定如此。”[13]于是,许多慈善家以改善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和道德水平为己任,致力于为工人提供质量较好的住房,甚至是修建兼有教堂、商店、学校和图书馆等公共建筑的工业社区。
在工业社区的建设方面,比较早且比较知名的当属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00-1810年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建立的协和村,他为其管理的工厂工人建造了住房、音乐厅和其他建筑。这一实践对此后许多英国企业家都有深远的影响。从1800年到一战前夕,英国企业家或是为其工厂里的在职工人或是为其公司因退休、年老和伤残等需要救助的工人修建了30多个工业社区,其中规模较大的社区见表1。
(一)索尔泰尔工业社区
1853年,纺织厂厂主提图斯·索尔特选择距布莱特福德市西北部3英里外的一块地,为其工人建设了居住社区。索尔特说:“我将会竭尽所能地避免因空气和水被污染而带来的麻烦……在给国家提供一个示范居住区这件事上,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14]修建索尔泰尔社区前后历时十余年,共建有850栋房子,可居住4 500人,规划异常规整,22条街道严格地按照几何学平面设计法而分布。所有的房子都有煤气和水,厕所、煤储藏室和火炉的灰炕被安置在后院。除此之外,萨尔特还修建了一些公共建筑如教堂、医院、图书馆和俱乐部。为了保证清洁卫生,社区里还建有公共浴池和洗衣房,装备了当时较先进的洗衣机、绞干机和热气储藏间。这里交通便利,环境良好,与紧邻的布莱特福德市那种狭窄、肮脏的状况形成天壤之别,“成为全国知名的模范城镇(Model town)”,[15]对以后的工人社区建设有较大影响。当时的人对索尔泰尔社区给予高度评价:“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个人的企业如此勇敢地开始一项如此伟大的计划”。[15]

表1 1800-1914年英国部分工业社区一览表
(二)伯恩维尔工业社区
1879年,伯明翰巧克力制造商乔治·吉百利在距伯明翰市中心4英里之遥的乡间建设了新的厂房,并且在附近修建了20栋住房以供工人居住。到1893年,这个被称为“伯恩维尔”的社区扩展到120英亩,到1900年时发展到330英亩,有313套住房;到20世纪初这里有1 110套住房已建好或正在建,居住人口达5 500人。[16]吉百利强调:“应改善大量给工人的不卫生和不充足的食宿,为工人提供一些室外活动,给他们提供机会耕种土地,做自然、健康的消遣。”[14]因此,伯恩维尔社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公共空间。总面积的1/10被保留作为公共活动空间,每英亩土地上修建6栋房子,房子依地形整齐地建在一起。吉百利规定房子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它所属土地的四分之一,这样每家住房都能够拥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菜园、花坛和果树,因此有人指出:“在伯恩维尔,没有什么被允许阻碍空气的自由流动和阳光最大限度的照射”。[16]这里的道路、铁路和水路交通都比较方便,还有商店、学校、艺术厅、公园、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建筑。
(三)阳光港工业社区
在19世纪企业家为工人建设的模范社区中,最有影响的或许是肥皂生产商威廉·利华修建的阳光港。1887年,威廉·利华在柴郡(Cheshire)的威勒尔市购买了56英亩土地,其中24英亩土地用于工厂扩建,32英亩用于为其雇佣的工人修建住宅区,根据其工厂最畅销的商品“阳光牌”肥皂而命名为“阳光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威廉·利华和建筑师们根据阳光港社区不平整的地形和社区布局,将住宅按照街道规划分为不同的公园街区。1907年,在这个社区居住的居民有3 600人,其中在工厂里工作的人超过3 000人。阳光港不断扩张:1889年,这里有28栋住房,1897年增加到238栋,1904年则是600栋,到1909年又发展到720栋住房。[17]此外,阳光港建设了教堂、艺术馆、社区医院、音乐厅、体育馆和露天游泳池等一系列公共建筑和便利设施,以鼓励社区的文化活动、体育活动以及其他社团组织活动的发展。利华曾经自豪地说:“在社会组织和教育机构以及相应的公共建筑方面,没有哪个社区比阳光港取得的成就更大。”[18]
三、英国城市工业社区的影响
(一)工业社区改善了工人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
19世纪英国工业社区的建设极大改善了社区工人的居住条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20世纪上半叶以前最佳住房的标准。当时大多数社区住房宽敞,一改以前几家人挤在一间房间的状况,有的社区每户家庭都有三至四间卧室,并且配有厨房、客厅和屋前花园。社区中房屋之间注意间距,以便拥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有的社区如阳光港的大多数住房都配备有独立的浴室,这被视为“一种非同寻常的奢侈享受”。[18]此外,几乎所有工业社区都建有广场、商店、教堂和体育馆等一系列完备的公共设施,为工人提供了教育、娱乐和休闲的场所,提高了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同时,工业社区住房的租金也能够为大多数工人所接受,通常相当于当地工人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相对较为合理。
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直观表现之一是社区居民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较低的死亡率。以阳光港为例,1900到190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死亡率为16‰,其中人口超过50 000人的76个城市平均死亡率为16.2‰,人口为20 000~50 000人的142个中等城市平均死亡率为14.7‰,而阳光港的年均死亡率仅为9‰,甚至比绝大多数乡村地区的死亡率还要低。[19]其他工业社区的死亡率也较低,1914-1919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死亡率是14.9‰,伯明翰市是13.7‰,而伯恩维尔的人口死亡率仅为7.7‰;这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婴儿死亡率是97‰,伯明翰的婴儿死亡率是101‰,而伯恩维尔则仅为51‰。[16]
(二)工业社区留存了维多利亚时期独特的建筑风格
修建工业社区的很多企业家都亲自参与社区的开发设计,并且力图使社区保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例如,威廉·利华就亲自参与设计,并聘请了当时30多位著名的建筑师进行规划和设计,使得阳光港的工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形成了今天独特的混合式风格。这里每一个街区的住宅都是由不同的建筑师设计的。阳光港没有同样设计的两个街区,建筑风格多种多样,有佛兰德式风格、荷兰风格,甚至还有两所住宅就是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故居之仿制建筑。原材料从木材、砾石到沙子、水泥,颜色多彩,同时又追求社区整体的一致性,同一个街区刷同样的颜色,用木牌划分同组建筑,体现建筑之美。阳光港将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慈善行为与乡村郊区的可视性传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该社区一方面为工人阶级提供舒适宽敞的住房,另一方面又具有花园郊区的建筑审美价值。阳光港现保存有约900栋二级法令保护建筑物①,并在1978年被宣布为文物遗产保护区。
(三)工业社区推动了英国田园城市运动的发展,成为欧洲城市规划的重要范本
1898年,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在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理念,强调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20]提倡建设兼有城市和乡村之优点的理想城市。19世纪大多数工业社区的设计思想都与田园城市理念不谋而合:霍华德强调田园城市应以一个大花园为中心,以林荫大道向外辐射到各街区,而大多数工业社区都建有规划齐整的花园和林荫道;霍华德提出应保持田园城市的低密度居住率,而工业社区的住宅或是半独立的,或是分散为每组四到六间房;田园城市理论强调乡村的绿色景观和城市的便利居住条件,而工业社区的建筑风格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绿地和风景构成社区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霍华德在构思田园城市规划时就曾参观过阳光港等社区,这些社区的建设为其田园城市理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发。正因如此,英国遗产协会曾经指出,“阳光港可以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工人社区范例,也是田园城市运动的先驱。”[21]由此可见,工业社区在建设规划中既考虑为工人阶级提供舒适宽敞的住宅,同时又注重社区的整体布局和风景设计,在城市社区规划中将实用性的社会目标和景观性的建筑目标结合起来,对19和20世纪的英国城市规划产生了积极影响。索尔泰尔、伯恩维尔和阳光港等工业社区规划方案都曾被展出于不列颠皇家建筑协会组织的城镇规划会议,在1910年城镇规划会议上这些社区被描述为“最早的独立田园社区之一,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城市规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
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然而,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状况不仅使疾病横行、治安混乱,而且难以为工商业发展提供大量健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开明企业家开始关注工人居住条件,自发兴建工业社区。这些社区或许存在一些设计问题,且真正受益者也仅仅是工人阶级中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但是,企业家修建的工业社区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住宅状况,留存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建筑风格,并且推动了田园城市运动的发展,成为此后英国乃至欧洲城市社区规划的重要范本。
注释:
①法令保护建筑物(Listed Building)是指具有特殊建筑价值或历史价值的、被专门列入政府保护法令清单的建筑物,分为一级保护建筑物和二级保护建筑物。未经政府部门许可,法令保护建筑物不能被拆除、扩建或改建。
[1] FRANC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54.
[2]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466-467.
[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7.
[4] 彼得·马赛厄斯, 悉尼·波拉德.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8卷[M]. 王宏伟, 等,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559, 560.
[5] ROBERT VAUGHAN. The age of great cities, or, modern civilization viewed in its relation to intelligence, morals, religion [M]. London: Jackson and Walford, 1843:57.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08.
[7] Public health bill-Adjourned debate[DB/OL]. (1848-05-08) [2018-7-20]. http://www.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 1848/may/08/ public-health-bill-adjourned-debate#column_777, /.
[8] 帕特里克·格迪斯. 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M]. 李浩,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65.
[9] Great Britain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Populous Districts. Secon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Populous Districts [M].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45: 61.
[10] HENRY JEPHSON. The sanitary evolution of London[M].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7: 105.
[11] WILLIAM FARR. Vital statistics: A memorial volume of selections from the reports and writings[M]. London: Offices of the Sanitary Institute, 1885:159, 166.
[12] JUSTIN DAVIS SMITH,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ntary secto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14.
[13] CHARLES KINSLEY. The works of charles kinsley, Volume XVIII: Sanitary and social lectures and essays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0: 191.
[14] 伊恩·布兰德尼. 有信仰的资本: 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M]. 以诺,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34, 119.
[15] R BALGARNIE. Sir titus salt, baronet: His life and its lessons [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77: 220, 123.
[16] A G GARDINER. Life of george cadbury [M].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23:147, 149, 155.
[17] DAVID J JEREMY. The enlightened paternalist in action: William Hesketh Lever at port sunlight before 1914 [J]. Business History, 2012,(33) 1: 60-63.
[18] EDWARD HUBBARD, MICHAEL SHIPPOBOTTOM. A guide to port sunlight village[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8, 44, 39, 67.
[19] W L GEORGE. Labour and housing at port sunlight[M]. London: Alston Rivers, Limited, 1909: 152.
[20] 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M]. 金经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6.
[21] Port Sunlight. 424WH Column [DB/OL]. (2005-03-08) [2018-07-30]. https://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 405/cmhansrd/vo050308/halltext/50308h04.htm.
The Rise of British Industrial Villages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OUYANG 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In 19th century Britain was regarded a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bu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hous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was extremely bad. As fac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stood by, some enlightened entrepreneurs began to build houses, even to construct industrial villages with churches, shops and schools for the working class.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villages improv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preserved the Victorian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urban planning of 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industrial villages; enlightened entrepreneurs; urban planning
2018-07-22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YBA164)
欧阳萍(1979-),女,湖南湘潭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城市管理研究
TU 982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9.03.011
2096-059X(2019)03–0061–05
(责任编校:贺常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