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回家
古欣
麦家走进酒店顶层的餐厅,准备接受采访。他告诫自己,这次,一定不要谈伤害,不要谈痛苦,不要谈离别。不久前,《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里,记者写道:在采访中,他提的最多的一个词是痛苦,一共提了35次,此外提了20次孤独,14次伤害和11次忍受。七年前,在另一次采访中,麦家则提了10次伤害。
童年伤害确实成就了他,但类似的话这几年说多了,麦家觉得挺没意思。他希望可以多聊聊文学本身。实际上,也许麦家没意识到,这次采访里他提了很多次家庭。
“麦家老师辛苦了。” 记者对他寒暄。“不辛苦,写小说才是真正辛苦的。” 他向椅背靠去,神态疲倦透着放松,整个人像刚赢了一仗。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在新书《人生海海》里,麦家写了一个被侮辱的英雄。说是英雄,因为主人公有一套纯金打造的手术刀,这套刀为他在抗日战场、国共战场和朝鲜战场上扬名立身,同村的人敬他为“上校”。说是被侮辱,是因为“上校”在村里还有另一个外号:“太监”。
上校这个人物的原型,来自麦家记忆中一个远远的背影。那是小学五年级,村里的老庙要拆,学校组织麦家他们把庙里面的砖头、木头搬下来造新校舍。回来的路上,他们遇见一个邻村的人挑着大粪经过。大家七嘴八舌说开,有人說,这人是个光棍。还有人说,这个人在战场上受伤,下面出了问题。这个印象变成一枚钉子,牢牢钉在麦家的记忆里。
想象就此延展。麦家设想,这个故事应该既和国家、又和个人、又跟村里的谣言缠在一起。他想写一个人走进世俗人情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和乡村的风貌。这之前,麦家的故事大多发生在701,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情报机构。

麦家。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故事围绕着上校身上一道刺青展开:朝鲜战争后,上校因为没人知道的原因被发落回村。最开始,有人说他在部队时受了伤,成了“太监”;等到了“文革”,造反派又“亲眼”看见,上校肚皮上文着“鸡奸犯”。后来又有新说法:上校既没毛病,也不是鸡奸犯,但却跟日本女人好过。于是上校又以汉奸的罪名被逮捕。
上校是一个被时代损害过的人,这样的人麦家写过很多。在那些故事里,他们因为天赋被某个集体或某项使命选中去解决别人束手无策的难题,却在面对日常生活时,比普通人更加执拗、脆弱,最终毁于日常。
《解密》里的容金珍是数学天才,因为丢掉了工作的笔记本发疯。《暗算》里的黄依依是冯诺依曼都赏识的科学家,却为爱情饱受羞辱;敏锐的听觉成就了瞎子阿炳,同时也断送了他……
麦家将这样的人概括为“弱的天才”。他着迷地描摹他们,并分析自己为什么会写所谓的强人、超人、英雄。麦家的童年过得不幸福,写作被他视为逃离与治疗的途径。他说,“我的写作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我一个被童年困住的人,在试图逃离童年。要逃离这个村庄,必须要有英雄气质。”而人物身上的缺陷,麦家认为来自他的家庭。
他说,“我的写作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我一个被童年困住的人,在试图逃离童年。要逃离这个村庄,必须要有英雄气质。”而人物身上的缺陷,麦家认为来自他的家庭。
《解密》中的容金珍,是麦家为自己捏的第一个英雄。麦家将自我毫不保留地融进去。“(容金珍)他那么孤僻,内心那么执着,一个冥顽不化的人,内心高度独立,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这是三十年前我向往的人物。那个时代容金珍就是最完美,他可以与世隔绝,但依然屹立于世,彻底地征服别人,最后也征服了自己,毁了自己……”
说到容金珍,麦家依然动容。创作《解密》时麦家还年轻,容金珍封闭的内心,与世界的紧张关系,都带有麦家的影子。那时他为了写作可以自我放逐,远离家乡,甚至一个人跑到遥远的西藏。
与容金珍相比,上校多了一份灿烂与烟火气,麦家想在这个人物身上展现生命的力量与色彩。麦家向记者强调,现在自己不同了。“家庭美满给了你保护,成功给了你自信。” 体现在作品里,他决定让自己的英雄从封闭的701走回广袤的乡村。
好朋友、坏朋友
麦家的童年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爸爸是反革命、右派,爷爷是地主,外公是基督徒。地富反坏右,他家占了一大半。上学后,他因为出身不好受歧视。冬天天冷,他坐靠窗位置,风把雪花刮到脖子里,他起身想关窗,被老师嘲笑,你头上戴着两顶黑帽子还怕冷啊?
同学骂麦家的父亲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四类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麦家堵在同学家门口,打算捍卫父亲的尊严。父亲赶来了,麦家扑向他,哭诉委屈,父亲却当着众人面,二话不说,两个大耳刮子下去,顿时鼻血喷涌,流进麦家的嘴巴,流过胸前,一直流到裤裆。
麦家委屈,却不解释,只把这口气憋着,从此心里疏远了父亲。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母亲说他成了“洞里猫”,整日一个人窝在角落,不说话也不爱出门。即使出门,也是耷着脑袋,挨着墙根走路。
“我们的家庭被社会抛弃了。”没人跟麦家玩,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朋友——日记。所有心事,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赌气,都倾吐到日记本里,他还记得第一篇日记里自己赌誓,以后也再不喊父亲“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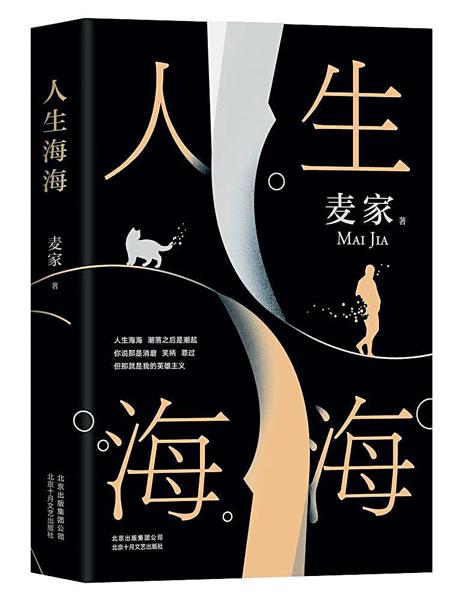
麦家新作《人生海海》。
那时候麦家常常失眠,南方的木头老屋,有很深的屋檐,很大的窗户。夜晚月光透过屋檐,钻进窗户,朦朦胧胧中,就有一只大鸟披着月光而来,把他叼走。这个梦,麦家做了五六年。他想逃离村庄,逃离不断给他屈辱的地方。他幻想一个英雄,带他离开。
十七岁,这个英雄来了。他去医院,碰上解放军工程学院组织招生体检。在医院门口一棵小树下,他把树荫让给了一个刚从医院走出来,长得像马克思的大胡子。对方问他,你是不是也来体检的?这人是招生官,正为招不满学生发愁。就这样,麦家被看中了。
麦家和60多个同籍学生被军车拉到福州附近的山里,天越来越黑了,车还在山路上,坐在车里麦家很兴奋,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学无线电情报专业,但已被神秘感吊足了胃口。那是他第一次坐军车,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家被甩在身后,却也一直跟着他。进校的每个人要交代家里情况,大家都趴在床头柜上写,只有麦家走开,躲到了学校活动室。他为自己的家感到难为情,别人在的情况下没法动笔。那份坦白信,麦家写了两天,三页纸。他的同学大多写一页纸。
大学时隔壁宿舍的哥们也有个日记本,麦家发现后,就有心跟人家交朋友。熟了以后,对方告诉他,自己的本子里写的不是日记,是小说。麦家也试着写小说,开始没感觉,后来他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整本书都是一个男孩喋喋不休地在说话。“我的日记不也差不多吗?”麦家心想。仿照麦田,他写了处女作《私人笔记本》。从此,除了日记,麦家又交了一个新朋友,小说。
1987年的春天,麦家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南京的朋友、作家鲁羊家里看到了博尔赫斯的书,感觉就像一个水滴落入了水里。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写的不就是破解密码的故事吗?那恰巧是麦家有亲身体会的,军校毕业后,他曾在情报单位工作了八个月。
鲁羊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被麦家借走了,一借就是几年,从麦家去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一直到从军艺毕业。毕业离开军艺的前一晚,麦家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决定写一个大东西。也许是博尔赫斯,也许过去在情报单位的经历给他启发。总之,在这个夜晚,密码的故事潜入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对《解密》最初的想法。
但麦家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为此付出十一年的时间。因为题材涉密,当时几乎没人写,麦家只得自己摸索,投稿、退稿、修改、重写,几次麦家都想把它搁下,但几次又忍不住拿起,到终稿总共修改了17遍。这期间,麦家频繁地调动工作,迁居,最后落脚到成都的一家电视台做编剧,不用坐班,有大量时间写作。
麦家的精力也从日记转到小说。成年后,他越来越觉得写日记对自己不好,日记里自己总是牢骚满腹,大都是负能量。他想戒掉。孩子出生是一个外力,麦家对自己下决心,“你现在都是父亲,为人父了,你要告别过去的自己,把这扇门关掉。”
坏朋友戒了,日子只剩下小说。在成都,麦家有一帮热爱文学的朋友,他们以作家洁尘、何大草的家为据点,常常聚会。麦家话不多,腼腆,对文学十分虔诚。他说,“小说里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是不是都用对了,这很重要。” 这句话让当时常常跟麦家聚会的何小竹印象深刻。
躲猫猫
十一年前,麦家从成都回到杭州。他曾发愿要远离家乡、父亲、受伤的童年,但亲历汶川大地震让他彻底改变想法。地震之后,麦家决定搬回杭州,方便周末回富阳照顾父母。但父亲那时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认不出他的儿子了。
那时也是麦家事业上狂飙期。先是2008年,他接连拿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茅盾文学奖。再到2009年《风声》改编成同名电影大火,找上门来邀他写书写剧本的人络绎不绝。
他被裹进时代的节奏,2009年到2011年,连着写了上下卷的《风语》和《刀尖》,一共四本书。最后一次见父亲时,他对父亲说,等我写完稿子再回来看你。让他感到滑稽又悲哀的是,直到父亲葬礼那段日子,他还在赶稿,最后十天,麦家边哭着边把《刀尖》的结尾赶出来。
苏童至今记得,伦敦一个幽暗房间里麦家的背影。那是2012年,他和麦家应邀去伦敦参加活动。他去麦家房间串门,看见麦家坐在没有光线的一侧,一动不动,甚至不刷手机,就那么干坐着。
苏童问他,你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干什么?不出去走走?麦家说,出去干什么?我跟伦敦又不熟。
那正是麦家最消沉的日子,父亲的离世是一个打击,自己的作品质量也不如意。他中断了之前那种有点荒唐的写作生活,形容自己进入了冬眠,什么也不写,每天就看书、健身、侍弄自己的院子。
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麦家对自己的院子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每棵树,每块石头都亲自拉进去。麦家有三兄弟,他喜欢把三兄弟喊上一块干活。有次,他哥忍不住对他说,做你手下一棵树太难过了。
“因为我老是把它移来移去,这次把它移到这里,过了一年觉得这棵树在这看得不顺眼,我又把它移到旁边。”
整整过了三年,麦家才重新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人生海海》。这一次,他严格调控自己的速度,每天八点半在电脑前坐下来,写到两点,只写一千字,又修改,最后留下来的,也就五百字。
两千字是个红线,一超过,他就要怀疑速度,怀疑自己的感觉。“就像一棵树长得太快,我就觉得它质地比较松。”小说初稿写完是去年8月21日,彻底完稿是今年3月3日。写完以后,麦家又改了七遍。他觉得好作品都是改出来的,写作上最大的才华是耐心。
苏童听说麦家新书是“与父亲的和解之书”,以为麦家写的是个自传体小说,“读着读着发现是半自传,我以为是半自传。后来读着读着发现是仿自传。最后发现什么都不是,就是个小说。”
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父亲走了,自己的心有一个角是破损的,写《人生海海》有一个目的是想弥补这个角。但弥补也好,和解也好,不一定要直接写, “真正直接去写,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真正写的话,像泼妇骂街,越骂越怒。作家跟自己也会躲貓猫,躲得越好,解决问题功效越大。”在新小说里,麦家把“我”躲在上校后面。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读到小说的结尾,感觉挺吃惊。麦家的小说过去给他的印象一直是硬到底,他没想到,这本小说里,麦家放松了。“他用归家、爱(来处理结尾),用爱来和解。”
说起过去的伤害,麦家现在认为,“夸大了,肯定是夸大了。”他甚至会用自己的阅历,开导坐在自己对面的年轻人:“有问题也是没问题,年轻的时候过不去。我到了今天回头看自己的过去,我的生命里有很多问题,从原生家庭,包括性格的养成,包括爱上文学,但其实最后所有的问题都会变成你的财富,它有两面性。”
只是他依然不能完全告别。他自己也有些疑惑,本来,他想通过这本书告别童年的阴影,告别过去的写作。但写完之后,麦家觉得,其实跟过去好像还是藕断丝连的。好在,他现在有妻子、孩子、院子、兄弟,还有文学,这些都让麦家感到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