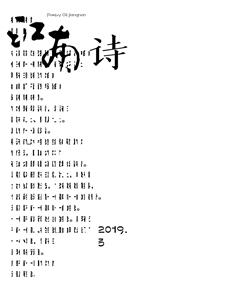蛙皮的湿润,缘于海水
主持人语:
王自亮与伤水经历相似,过从甚密,对诗歌都有着炽热的情感,由王自亮来执笔伤水的诗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伤水浸淫诗歌三十余年,近年来的写作愈发可观。本文回顾了他们因诗歌的相识,伤水的写作历程以及对他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因素:超现实主义和大海,对他诗歌的优劣都进行了恰当而客观的评论。(江离)
一
一直以来,很想写一写伤水,写出这个诗人的精神、骨骼和气息来。坦白地说,既出于对汉语诗歌的新期待,也缘于道义和友情。诗人和画家一样,需要刻画肖像,尤其是精神肖像。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命笔写伤水的“人与诗”,虽然会有力不从心之感。一则因为认知毕竟有限度,二则,我与他之间没有太多“距离”,反而会有一些妨碍。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就是这个伤水,曾经以“阿黎”这个名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5年前在杭州,我与伤水一起接待吕德安和于坚。当吕德安向于坚介绍“这是伤水”,他俩握了握手,可入席时伤水对于坚说:“记得八十年代和你通信的阿黎吗?我就是阿黎”,他们便重新握手,那肯定是紧紧地。于坚每次出门只带他新版的一本诗集,那次便签上“赠阿黎”给多年前的诗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以至于于坚把这次相遇写进他的《朝苏记》一书。这也难怪,“伤水”是2001年才诞生的名字。伤水与海子等人也多次通信,只是这些书信保管不妥,被老鼠当做点心吃了。那时的伤水如刚出鞘的钢刀,结实、锋利、耀眼,充满活力,写出了“海殇”系列诗歌,尤其是那首《关于大奏鼓由来的构想》,让人着实吃惊。其中的血性、刚毅与紧迫的节奏,令我难以忘怀。
1982年初,我從杭州大学毕业到台州行政公署工作,住在行署一个很大的院子里,因为是单身汉,被安置在一个木结构的单间。人一上楼,楼梯就吱嘎吱嘎的响,只要来人老早就会听到。记得1984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有人敲门,来了一个与我个头差不多的年轻人,自报山门,原来是台州师专中文系的学生,名叫苏明泉,也就是后来的“伤水”。当时我略有惊异,发现这个人长得颇为奇特:圆圆的脸,眼睛同我一样小,却炯炯有神,额头很像被一束光照耀着的船首。我们很快就进入自由交谈状态,不需要任何繁文缛礼,也不必有任何铺垫。长久以来,伤水的赤诚、爽直、激越,还有他对诗歌的无比热爱,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从第一天开始,我与他就无所不谈,从此开始了我们漫长的友情。
师专毕业之后,伤水教过书,做过对台贸易公司“琉泰”的副总经理,后来当上了县外贸局长,最后“下海”经商了。多年来他担任苏泊尔集团公司的老总,期间写出了诗作《卖锅者言》。他与我另一个共同爱好是喜欢读张五常,想必是《卖橘者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诗歌写作,对他来说,有时是暗河,有时是明流,始终伴随着他,不曾须臾离开。就伤水而言,写诗与经商是必要的两手,甚至是互文关系。与他交谈,要习惯于话题的转换,从穆旦、艾青、冯至到美国文学的“垮掉一代”,从危机管理、财务分析到“北回归线”、“非非主义”,从居住厦门的种种好处到苏东坡的一言一行,你都得跟上。伤水写诗,与他的生活并行不悖,这使他能将两者互为印证和发明。有时候,伤水不去区分诗歌与日常,人性与科技,文学批评与商业计划书、财务报表。对于这些事物,他是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激昂,同样的不顾一切。
伤水一直游走与商业与诗歌之间,于他而言,很难说这两者何为重要。诗歌写作需要敏锐、精确性和技艺,而商业需要想象力、预见与洞察。也许在他看来,一份商业计划书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应该具备诗人的前瞻与疯狂。在他看来,诗人首先是人,其次是诗人,再次是诗歌写作这门手艺本身,最后才是写作所能抵达的目标。伤水与我一样,从来没有把诗歌创作视作生命的全部。须知,诗歌并非高于一切的事物,真理、悲悯和爱,还有自由意志才是。
二
他的诗歌中,有一种特别的劲道,扩展的力量。由于个性、经历和阅读,以及文学上所接受的影响,伤水诗歌中显示了某种决绝和彻底性。他似乎洞悉人性的秘密,富有语言和意志上的征服感,而且与海洋有着确切的亲缘关系,就像他的宗族和名字。这一点基本上路人皆知,从外表到内心。伤水的诗是无所顾忌的,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一种本质的优雅。从语言的角度看,他也是喜爱延展、叙述和戏剧性,注重自由表达和语义学上的原生态,体现了广阔的陌生化。
到目前为止,他分量最重的诗歌可能是那首《逝》。那是对死亡的一种直接感知,一种不可回避的注视,甚至还对“死亡”动手动脚,想探个究竟。刀、躯体、鱼干,祖父的话,斧头、饥饿、疼痛,黑暗的抽屉,这一切于世间存在过的,并没有因为死亡的洗劫而丧失意义,而那些感慨、修辞和异端,却风一样地“从我身上吹走”,“活着就是失去”,而且目睹一部分山水开始“在我体内腐烂”。
伤水的诗歌,有时充满了“暴力”,对另一些有价值的事物,也就显得更温柔了,保持一种由衷的敬意,他的《玉环城》就是明证。那座有着贵妃名称的海岛城镇——玉环,伤水的故乡,无处不在地潜藏着戏剧性,令人惊奇的生活场景,诱惑、抵御与绝望,死亡的气息,狂暴的场面,使我们体验到了一种“现代变形记”。他把一座海岛城镇与身体、时间和事件置于耦合状态,显然有后现代意味,但基本情感却十分现代。这是一种混成,多声部唱法。不管怎样,是这座奇异、激荡和未知的城镇,让我们的诗人着迷。《玉环城》证实了伤水处理复杂题材的能力:戏剧性、奇异感和如歌的咏叹,操纵自如。
伤水的诗歌,有很多想象力和语言方面的“意外”,比如那首《盗冰者》,要去天山盗冰,就很了不起了,何况这块冰很神秘,被阳光所包围,蓝天所笼罩,取冰的时候,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细节:手指夹取的地方,会很快变薄,而且纹印会成为罪证。他还写到了“时光的警察”。最终的结局是,冰还没有回来,“我就融化在路上”。这里“冰”成了“我”,冰和我一同进入虚无。
而超现实主义是伤水诗歌的本质——场景和主体的变换,无意识的揭示,现实世界与虚幻情景的并置,以及元诗歌的实践,都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这一类诗歌有《你说的王红公,原来就是肯尼斯·雷克斯洛斯》(以下简称《王红公》)《元宵夜,鲤城,与自亮兄、依民兄观看梨园戏〈朱文太平钱〉》《黑》《弑马》《灰白》等等,有的堪称杰作。它们的出现,为伤水进入一流诗人的行列,提供了稳固的基石。比如上述那首《王红公》,就令人击节赞叹——
你第三次赞赏这个书房/我知道它的缺乏 几张诱惑的交椅/比如田纳西的坛子 比如望海之礁/或者马鞍 风雪的膝盖/我们能搬迁波涛吗 漂流木 网和锚/七大洲的爱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攀登/马蹄过处 蚂蚁抵角 蜜蜂含香/“你可以和它们交谈终日”/谈及蛙皮的湿润 神性人性和兽性/出处像户外的群山一样纠结/无需从纵横中抽出指南 心灵在地图上旅行/没必要为认错“桑莲法界”而大喊罪过/好像举报了整个世界/你轻微的下手 就足见力度/随手关闭车门 远在唐朝的李杜 嘭然心跳/我说出你的“在” 超越了体验/爱情和死亡 正如“山脉宁静地流进大海”/你历数罗斯克 奥尔森 施耐德 赖特 默温/当我揪出罗伯特·勃莱/你已经在六百公里之外
作为这首诗写作起因和结果的“证人”,也许我可以写一首与之呼应的“本事诗”,甚至可以不费力气地诠释每一个句子和重要的词语,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伤水这首诗的特质、语气和超现实意味,语流汹涌之际的“两岸风景”,以及几个精神层面多声部的呈现与交织,都足够突出。诗中的人物、引语和事件,经友人相聚时一个不经意的表示,或一个美国诗人名字的引发,“随物赋形,不择地而出”,蕴藉又巧妙,自然而精准,不掉书袋,不显斧凿。所有意象与场景都置于诗人的控制之中,交织、嵌合与彼此穿越,体现了力与美的糅合。诗人余刚甚至认为,迄今为止伤水的诗歌创作以《王红公》为标识与界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足见这首诗的重要价值。
这首诗歌带领我们进入超现实奇境,却不曾乞灵于艾吕雅们宣称的梦幻术、自动写作,还有韩愈式的奇崛之道。那些属于作者个人经验的交往细节,巧妙地嵌入到整个诗歌内部,成为朝向精神新路标的索引。最后一句更是妙不可言:“你已经在六百公里之外”,既制造了时空漂移之感,又一狠心把读者的思绪“拽”回到出发点。在这首诗中,戏剧性与叙述元素不少,都被串联在一个中心线索上:诗歌与人性,时间与“不断超出自身的存在者”。如果以海德格尔式的词汇来概括,那就是“亲在”(Dasein),或曰“此在”。
三
无疑,伤水拥有一个大海。这个海,既是伤水的词库,也是他人格的自我投射。我们看到的伤水之海,游动着令人讶异的鱼群,它们有着闻所未闻的名称,升起了海妖和受伤的牛,而岸边是沉重而飞扬的生活,夹杂咸腥,却绝对真实。一般而言,我们的诗人总是要注视那只永恒之船——这情景,使我们想起了聂鲁达和惠特曼,那张野牛皮似的海,船长、罗盘与和黑色礁石。激荡之海,也是多面具之海。他的《鳗鲡》《鮟鱇》《苏眉》和《海妖》,特别是早些年的“海殇”系列诗歌,能从原始性的海转换成人性之海,进而是生活与生命之海,最终抵达“存在”之海。伤水的那首《别用你的盐腌掉你的手掌》,融大海、语言、性和身体于一体,将海水的蛊惑和伤害,提升到性命攸关的地步,同时领受了一种“咬牙切齿的幸福”。海和人的多面性,昭然若揭。
最近几年,伤水的大海更为庞杂,也更为纯粹。庞杂是因为生活的扩展、精神疆域的拓宽,包括诗人所面对的人事更迭、势力角逐与精神迷惘,特别是超越与回归的双向运动。而纯粹,则是伤水一种朝向源头探寻语言与事实的努力。一度时间生命力受挫之后,个体精神渐趋澄澈的迹象,昭示了伤水大病初愈般的新生喜悦。对于伤水来说,此刻的大海不再是一味“接纳”的辽阔场域,而是反顾、清洗与更新的巨型运动体。
在谈及大海与诗人的关系时,伤水曾对笔者说过这么一番话:“海洋的区域特征对我的影响,仅仅是对其多面性认识的加固。比如,我出生地浙江玉环岛面临的东海,它的面貌是浑浊、嶙峋的,而移居的厦门岛海洋面貌是绚丽、温顺的;从‘观光角度,厦门适合;但从生存和海洋本质上看,老家的海才是海。厦门的海,是一种对比物,让我更认识到海的本质、生活的本质、人生的本质”。
这正如我在《狂暴的边界》自序中说的:“总体上‘大海已经逐渐消失,取代它的,是更为汹涌的日常生活。……应该赋予诗歌以海的形式与力度”。也许,改写大海是我们的共同抱负。如何“改写”?罗伯特·勃莱说:“恪守诗的的训诫包括研究艺术,历经坎坷和保持蛙皮的湿润”,伤水是一个很好的践行者。写到这里,我很想赠他一句诗:“如雾起时,海水打湿了蛙皮/语言纹样,航海图上洋流的标识”。
伤水的《我曾长久地盯着海面》《偶然相联》《那脑壳里的斧凿声》《画鱼》《一幅鱼骨演绎我余生》《不要在盐里叫出咸》,就是将“自我”植入大海与船坞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与海的更多关联。他的《航海者》《熟悉的事物:台风》《在柘木汇看见两张硕大的船木椅子》,既直接触及与海洋相关的人事,更通过大海的象征系统,投射人的灵魂与内心状态:反抗,妥协,挣扎,搏动。那首《读王自亮兄的<寻访定海西码头,未果,转向布罗茨基的布赖顿礁岩>》,何止是大海不安与变化之表现,更是诗歌、情义与精神的析出。
伤水的《方言》,指示了一条从闽南经平阳抵达玉环岛的精神迁徙图,也是那一支方言的源流指南。可以看到,他这个族群所操持的方言,其语汇、发音与语法都浸泡了海水。中古汉语的大海“变形记”,足可追寻。在眺望“岸”和“爱人”的过程中,结晶了与生命—死亡—存在须臾不可分离的盐。这就是伤水的疼痛、焦虑与绝望(他简直是个“疼痛诗人”!)。反之亦然:伤水写出了他的兴奋、飞扬与期待。
对此,伤水有足够的认知与发现。弗洛斯特80岁生日时,当时一流评论家特里林说弗洛斯特诗学主题是“恐惧”,尽管弗罗斯特采用的材料是身边琐事和乡土语境,诗意的精神元素却是“人类的恐惧”。当时惊世駭俗,现已是定论。伤水曾对我这样说,“联想到前几年我分行的‘心情日记,我处理的诗意核心无疑是悲伤,乃至绝望。我不敢能表现‘全人类的悲伤,至少我命令自己真实地表现出阶段性个我的悲伤和绝望;若能通过个我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悲伤,为这个年代写下遗言,当是使命性的愿望。当然,这也是一种‘抵抗,对现实的物质化、娱乐化和精神的沙漠化的一种抵抗,正如勒内夏尔的‘溺水者的呼吸,即是对形成大面积的‘单向度的人(美籍犹太裔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言)的微弱的诗性抵抗。而在日记式写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苍凉,或许:疼痛+无奈=苍凉”。
请细读伤水的这首诗——
我不敢轻易入座。
摩挲它们,用我的双手。这从水中捞回 的十指,
已经无法再痛。那些食指粗的黑洞,
钉子从波涛里拔走:失去阳物的阴道, 是骨对肉的负债,是我欠下的风暴
爱是无法填满的
海洋无法比船板漂得更远
有一种呼啸是静默。有一种聆听不用 耳朵。
我的心太小,装不下整海的灾难。
这双手可以,它的索取、放弃,还有紧 攥的倔强。
我又错了一次!总在关键时刻
是滞重的船木,在挽留我的手掌——
波涛。波涛咽下的船帮。波涛吐出的龙 骨。波涛反刍的桅杆。
那么让人绝望的希望!
——《在柘木汇看见两张硕大的船木椅子》
伤水的笔名,据他说的意思是“将水击伤”,因为他写过同题诗歌。不过我宁可相信,是水将他击伤。对于大海,他以诗歌来祭奠,而非复仇。
四
很难将伤水归入那一类诗人,甚至很难定义伤水的诗歌到底属于“先锋”还是“后锋”,尤其在“先锋诗歌”和现代、后现代遭到极大误解的今天,在相当程度上被扭曲的软语-细雨“江南”。伤水也不是什么“海洋诗人”,这是我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抗拒的称呼。
在伤水的《收到地狱来信》中,我们见证了来自《神曲·地狱》的反抗与决绝,却用了很多反讽的口吻。《在任何一节都可以结束的诗》中,生命状态与诗歌写作特点互为交织,呈现了异质同构的效应。《失忆症颂》与《抑郁症颂》一样,都是作者以病痛与身体感受力为张本,自嘲中有反讽,体验里隐藏对生死的极端体验,对拯救之可能的思索。伤水写林和靖、苏东坡和李叔同,是与众不同的。除了以物见人的传统写法之外,更多采用了情境式对话。通过这些人物的诗词、书法、行迹、事物和言辞,借助于身世同情与精神拥抱而直接沟通。这些对话和移情,使得诗人与历史人物在诗歌中合一。《关于弘一法师》则是伤水诗歌写作的另类,戏剧性的对白、旁白和情境植入,打破了诗歌、电影与戏剧的边界,令人印象深刻。
在《家谱》里,叙述者是迥异于往昔的伤水,对“家谱”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载体,以亲身经历与体验,特别是家族人物的真实生活状态、错综复杂的关系,借助于姓名由来、行迹记载和精神肖像的刻画,对家谱的本质做了具体检视,结尾得出的结论,如此令人惊异:
但一个人变成一个村庄是确凿的/家谱不容置疑,它是没有血性的永远的孤证/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孤证/这没有功效的家族花名册,架屋叠床、枝复脉繁/一个名字在里头,一滴水在河流
至于写埃兹拉·庞德、莎乐美、伊夫·博纳富瓦、罗伯特·佩恩·沃伦、瓦雷里诸人的诗歌,可以看作伤水对精神源头和诗歌教父们的礼敬,也可以当作他对自己诗歌底色的一个交代。诗人兼水手的盖瑞·施耐德,则是他现实榜样。《我的身体就是一座火车站》《书籍整理工》《他们一转身就成为人群》《出租伤水》《轮回》《失踪》《搀扶》 ,是他与现实发生关系,包括龃龉、冲突、和解与盘算等方面的提纯或呈现。或裁其一段,或取其一勺,足见诗人的性情、思想与情绪,其中的愤怒、郁闷和欢快,跃然纸上。
伤水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深受洪迪先生的影响,从思想到人格,从知识体系到思维模式,更重要的是:智慧。从台州出发的诗人、小说家,无一不受洪迪的影响。作为一个思想者、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今年88岁高龄的洪迪先生,被伤水视为“精神父亲”,有时直接以“父亲”相称,可见几十年來他们之间精神上结成的纽带是如何深刻与坚韧。就我所知,他们交谈的母题是多样的,从生命—存在—宇宙直到诗艺—眼光—才具,甚至涉及到商业、物质与历史。在思想与语言的对流中,洪迪先生与伤水会彼此达到新一轮的精神满足,诗与思的对应、匹配与嵌合,以及人生的“大欢喜”。
按照洪迪先生的诗歌理论,诗美时空演化动力可以分为七类:意动型、情动型、象动型、形动型、韵动型、语动型,以及较为均衡的综合动力型。伤水的诗歌从动力学上看,总体属于“语动型”见长的综合动力型。之所以说“语动型见长”,是他对语言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知,并有运用之敏感性和能力。说综合型,说明他有均衡和综合能力,何止一二招术、三五技艺,简直是百变其身,令人莫测。我愿意引用伤水的这首诗作为例证——
雪就要飞遍全身
像血,我割开任何地方都有鲜红流出
另一种飞行是鸟,在被替代之前
它飞出了千山万水
看过、临幸过,在重要处叫唤过
仿佛刻下一个标志
我就站在所有转折的地方
等待一声鸟鸣, 从体内点一盏灯
被纸拥抱的字
挣脱了纸
那在潦草的天空
拼凑成的句子,我不曾写出
一切都那么随意,我躺下一身疼痛
我的五脏六腑充满含义
越过作废的千山万水
我飞临哪里,哪里就有刷新的天地
——《一只鸟废除了千山万水》
伤水的诗歌优势甚多,其中一个值得激赏之处,就是“稳准狠”。问题当然也是,如果不稳不准,狠就变成了“用力过猛”。这个问题在我和他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还有一个不足,就是伤水某些诗歌过于直截,某些诗歌又流于漫不经心,给我以一种良莠不齐的感觉。也许这些都与他的优势联系在一起:心性如潮汐,自然有漫溢之害;产量增长过高,就会有顺手拈来之弊。还有,随机写作有两面性,既能造成意外的惊喜,也可能带来的一些麻烦:经营不够,语言芜杂,成色不足。这需要伤水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在总体风格与基调未曾改变的前提下,伤水的诗学探索出现了两种变化,即:在貌似随意的呈现过程中,以短制见长的巨量写作方式中,体现运思的精微和深邃;与此同时,在自我揭示甚至自嘲式反讽之际,体现世界失去重心后碎片化存在的严苛与无奈。对伤水来说,这些转变尚未彻底完成,但我们有理由期待早日实现。
伤水还是那个伤水,但表现力更为多样而沉稳,遮蔽与澄明交互出现。而语言也因为焦灼、病痛与喜悦的交互作用,而更为沉郁、深厚和内敛,仿佛一个国家从工业革命阶段的扩张,转为后工业时代所寻求的结构与价值。不排除伤水在写作过程中寻求宣泄之快意,但他对内在激情和精粹之作的珍视,却是变化的实质所在。因而,伤水将变得更为彻底,也更有力。
伤水说,“一只鸟废除了千山万水”。而我想说:另一只鸟再现了千山万水。鸟的宿命是飞,被穷尽的天空才是它的边界。诗人的自由天性,不可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