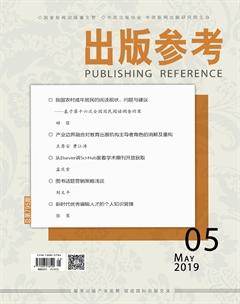黄觉民:集教育家编辑家于一身的一代名编
范军 陈兰枝
摘 要:集学者、教育家、编辑家于一身的黄觉民在抗战时期主编《教育杂志》四年之久。在艰难困苦中他坚守期刊岗位,极力倡导战时教育期刊的大众传播导向,以教育学者的专业眼光,引导杂志持续深入地关注战时教育议题,精心编织杂志的战时话语体系,深拓杂志的国际视野,使战时《教育杂志》既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又成为凝聚教育界人士进行“文化抗战”的重要媒介力量。
关键词:编辑家 教育家 黄觉民 《教育杂志》 议题设置 编辑思想
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集学者、教育家、编辑出版家于一身的大有人在,陆费逵、舒新城、蒋维乔、庄俞、夏丏尊、叶圣陶、范源濂等都是。而说到黄觉民人们不免有些陌生,其实就其在编辑出版活动的实力与贡献,他也应该是可以列入上面那串名单中的。其编辑思想、才干与劳绩,主要体现在抗战时期主编《教育杂志》。这是一位不应被人遗忘的一代名编,其编辑思想与实践经验都值得好好总结。
《教育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的,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办刊宗旨。它是民国教育期刊史上刊期最长、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期刊。抗战时期,该杂志两度休刊,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间(1937-1941)却成为极少仍然坚持定期出版发行,并影响颇大的教育刊物。全面抗战的前期,黄觉民担任《教育杂志》主编,他怀抱“教育救国”思想,将教育期刊作为“文化抗战”阵地,以专业教育学者的眼光审视战时教育,设置战时教育议题,编织战时教育话语体系,其战时教育期刊的议题设置策略和编辑思想对于当代教育期刊的编辑出版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学者型名编辑黄觉民与战时名刊《教育杂志》
黄觉民 (1898-1956),福建省闽侯县人,菲律宾大学教育学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是我国近代少有的获得哥仑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专家证书的教育心理学家。[1]1933年留美归国的黄觉民接受上海大夏大学聘请,担任该校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教授,并兼任心理学系主任;193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审员;1936年7月,开始担任《教育杂志》主编。
黄觉民是《教育杂志》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教育专业背景的主编。从1927年起,他即在《大厦周刊》《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等刊物上发表《国学管窥》《中国最近教育之进展》《中国学校制度的研究》等论文而在教育学界崭露头角。又因黄觉民与欧元怀、鲁继曾等著名教育学者一样,均是苦学出身的专家学者,在教育界颇负盛名。留美归国不久,黄觉民即被《申报》等报刊媒体推举为“全沪十大教育领袖”之一[2]。1935年《教育杂志》开设“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栏目,邀请国内教育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从事摘编和翻译工作,黄觉民又同吴俊升、许恪士、陈选善、张耀翔、廖世承、何清儒、邰爽秋、马宗荣等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及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一同入选,这无疑是《教育杂志》这一当时全国最为权威的教育专业杂志对其专业成就的认可。
同何炳松、杜亚泉、茅盾等商务同人一样,进入商务的黄觉民一直坚持学术研究与著述,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从1934年到1941年黄觉民共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论著及摘要等122篇,同时还在《东方杂志》、《教育通讯》(汉口)等刊物上发表对于教育问题的见解。在商务期间黄觉民独撰、编译的教育专业图书较多,主要有《教育通论》《德国公民教育》《实验教育学》《美国教育名著六十种》《教育心理学》等,编研结合,相互促进。
黄觉民也是《教育杂志》主编中教育实践经历最为丰富的一位,在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之前他曾担任中小学教师、训育主任及校长①,对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情况十分熟悉和了解。早在青少年时期黄觉民就深受“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影响,立志投身教育事业。留美归国后又曾担任大学教授,因其美国一流教育学院毕业的教育背景②,在教育文化学界拥有深厚的校友及学者专家资源。
全面抗战时期,黄觉民怀抱“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的坚定信念,带领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同人,依靠自身所学和丰富广博的文化教育界资源,苦心经营《教育杂志》,使之成为战时教育问题的研讨平台和教育界信息沟通的纽带。其间,杂志不仅没有因出版地不停变化、纸张短缺、交通阻隔等不利因素而衰落或停刊,反而因其鲜明的战时教育特色和别出心裁的“抗战以来高等教育专号”“抗战四周年纪念号”等专号的策划而成为战时教育期刊界的翘楚,在团结抗战及战时民众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和推动作用。这与主编本人的“教育救国”信念是分不开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方杂志》社长兼主编郑允恭叛国投敌,充当伪亚洲文协主席。郑还唆使日本官员诱逼黄觉民出任伪东亚文协教育处处长。[3]遭到断然拒绝。后来,黄觉民经澳门潜回重庆。由此可见黄觉民坚定的爱国信念与“文化抗战”的决心。
1942年黄觉民被派往成都担任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经理,同时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和金陵大学等几所高校担任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福建担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黄觉民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福建省教育工会副主席等职。1951年黄觉民回上海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直至1956年病逝。
二、黄觉民的战时议题设置策略
既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又具深厚教育理论素养的黄觉民对于战时教育问题有着深切的关心和深刻的思考。在黄觉民的主持之下,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杂志》对许多战时教育问题的探讨深入而持久,不仅体现了该杂志的专业性,更彰显了杂志作为媒介在战时教育舆论方面的引领地位。作为教育专家型主编,黄觉民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与学术影响力,亲自参与期刊议题的设置,从而引领教育,影响社会。
1.利用专家“在场”性引导杂志持续关注战时教育议题
黄觉民因其教育专家兼专业杂志主编身份,活跃于当时的教育界与出版界,以其专业的眼光审视教育现状与教育问题,通常能敏锐地关注到教育领域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并依托刊物平台,给予持续的关注。例如抗战时期,许多民众因为战事流离失所,学生更因此辍学、失学,为此,有专家提出民众“补习教育”问题。《教育杂志》1937年第1期便发表了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的,题为《民众補习教育实施的困难及其救济》的文章,介绍实施民众补习教育的困难和办法。
1937年2月4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为“中华职教社开专家会议讨论补习教育各问题专家蔡元培等均出席”。这则消息提到的出席者有蔡元培、王云五、欧元怀、陈鹤琴、何炳松、潘公展、陶百川、黄觉民、刘湛恩、吴蕴初等教育界著名专家、校长以及企业界代表三十余人[4],黄觉民亦位列其中。他敏锐地发现抗战时期有关“补习教育”的议题将会是未来一段时期教育行政当局与教育专家关注的重要战时教育问题。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三年间,《教育杂志》对“补习教育”给予了持续、深入的关注和探讨。
1937年2月,《教育杂志》发表题为《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后的民众补充读物》的文章,作者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顾良杰。第4期《教育杂志》原文转发《教育部令各省推行补习教育》的文件。但对于战时教育问题,黄觉民往往不满足于政策出台前的探讨与政策文件的刊布,而会引导教育各界对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调研和检讨。因此,之后《教育杂志》又围绕这一问题持续刊登了程时煃③、何清儒、沈光烈等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学者的系列调研性文章和后续政府文件。这些文章和文件包括:《职业补习教育的趋势和江西省实施的现状》《如何实施职业补习教育》《职业补习教育教材的编制》《战时职业补习教育的趋势及需要》及《推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等。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钟灵秀的文章《三年来我国实施民众补习教育扫除文盲的总检讨》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至此,距国民政府教育部下文要求各省实施补习教育正好三年。
三年间,黄觉民主持下的《教育杂志》将补习教育从社会到政府,从政策酝酿到具体实施的经过展现得清晰、深入而又全面,更显露出专家型期刊主编既侧重教育理论探讨又注重实践成效的议题设置策略。实际上战时教育期刊的议题设置,既需要尊重教育规律,又需要考量议题的现实价值,判断其能否服务抗战,真正起到教育民众、团结民众抗日的作用。
2.亲自撰文设置议题引发教育界关注和讨论
作为教育学者和知名教育杂志主编,黄觉民对许多战时的宏观及微观教育问题的思考非常深入。在战火纷飞、交通阻断的抗战岁月,常规教育教研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非常态时空背景之下,黄觉民经常亲自撰文阐述战时教育主张,主动设置议题,以引起教育专家和政府教育行政当局的讨论和关注,并期望某些作者的主张能获得教育行政部门采纳。在全面抗战之前,《教育杂志》编者往往先设置议题,然后通过函告征文的方式形成专题或者专号,极少有主编能像黄觉民一样先行撰文抛出议题,然后引导论者围绕主编的主张继续深化、衍生、拓展,然后组织专题或专号。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依托刊物舆论平台,与教育界人士直接对话,这无疑是黄觉民的又一个性鲜明的议题设置策略。
全面抗战伊始到《教育杂志》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的1941年,围绕各类抗战教育问题,黄觉民在《教育杂志》上共发文6篇,每篇篇幅均在5000字以上,分别为:《从战时校舍问题说到改革学校制度》《改变学校办学以解决战时战后的教育困难问题》《战时课程问题》《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问题》《战时战后学校改变办法的再检讨》与《改进大后方的教育刍议》。其中,《从战时校舍问题说到改革学校制度》《改变学校办学以解决战时战后的教育困难问题》两文发表后,黄觉民亲自将文章寄给包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及陈礼江、高觉敷等在内的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专家,邀请他们参与讨论。两个月后,黄觉民将汇集陈立夫、张伯谨、周尚、钟鲁斋、富伯宁、吴同等15位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专家的讨论文章以“战时战后函授自修问题的讨论”为专题在1938年第4期上刊发。为解答专题中各位论者对其文章观点及所提方案的质疑,他又撰写了《战时战后学校改变办法的再检讨》一文予以回应。依此思路,黄觉民由《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问题》一文策划了“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专号”(1939年第3期)。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黄觉民不仅深谙议题设置的规律与技巧,而且以教育专家的专业眼光与敏锐的洞察力,精准地挑选议题讨论的角度与参与者,娴熟地控制议题提出与推进的过程,从而达到使议题引起广泛关注,并将议题推向纵深的传播目的。他深知,设置什么议题很重要,这些议题如何表达同样不可忽视。
《战时课程问题》《改进大后方的教育诌议》两文虽然没有最终形成专题或者专号,却引发了诸多论者的持续思考与回应。例如《战时课程问题》发表后,《教育杂志》又发表了《抗战时期小学课程及教材之研究》《战时课程编制的问题及方法》《战时小学课程如何改变》《关于整理大学课程的几句话》等由吴鼎、钟鲁斋等课程专家撰写的文章,深入研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战时教材、课程以及实施的具体问题。1939年第7期的《教育杂志》刊发了《教育部令设战时课程》的通知,由此可见《教育杂志》议题设置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三、黄觉民的战时教育期刊编辑思想
1.倡导战时教育期刊的大众传播导向
作为留美归国的知名教育专家,黄觉民并没有将《教育杂志》的受众限定在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文化精英的狭窄范围内。黄觉民接任主编后不仅主张《教育杂志》受众的多元化、大众化,更倡导期刊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大众化。全面抗战前后,为团结民众进行“文化抗戰”这一期刊编辑思想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1937年第3期的“编者余谈”中,黄觉民提出:“本志对于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的文章,向来十分欢迎,不过为适合大多读者的程度与需要不得不力求‘大众化……我们相信,高深专门的文章,不一定就要用高深的文字来写,如果以浅显的文字写出来,可以更加明了,更加生动,希望惠稿的作家们以后多多注意这点,俾使自己的研究心得及意见,得便利地传达于全体读者。”这是黄觉民对于传播内容语言呈现方式“大众化”的要求。在全面抗战时期,黄觉民对于期刊内容语言与呈现方式大众化的推动更为着力。
1941年,《教育杂志》推出了两期专号,分别为“抗战以来高等教育专号”和“抗战四周年纪念号”。这两期专号中文章的行文方式并不受教育专业期刊研究论文格式化、程式化风格的限制。有些文中甚至出现了关于西迁高校师生精神状态及高校所在地环境风貌的叙述,使得这两期专号连普通中学生及略通文墨的普通大众都能看懂。由此,读者知晓了高校师生受尽迁徙、轰炸等苦难仍然坚持“教育救国”的感人历程,从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全面抗战时期,黄觉民深感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尤为重视教育期刊传播内容的大众化。为发动教育界人士开展民众教育,“使他们帮忙政府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5],黄觉民不仅要求杂志广为征集民众教育稿件,同时还策划设置“战时补充教材”[6]栏目,精心编选各类助于激发普通民众抗战斗志、深入了解抗战策略的“教材”,并配发按语,指导教师和学生使用。作为教育专业期刊,大胆刊发有关战争战略、战术以及战时金融、国际战局的内容,以“应战时之需”,这不仅可以看作黄觉民战时期刊策划思想的创新之举,更可视为黄觉民对于战时教育期刊传播内容大众化的大胆尝试。在战争的非常态下,黄觉民深知媒介必须更加注重媒介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的大众化,使媒介发挥战斗号召力,才能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奋起抗战。
2.编织战时教育期刊的战时话语体系
1937-1941年,《教育杂志》的议题与内容总是跟随战争的阶段性转化而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战时阶段特征,这是黄觉民期刊话语编辑技巧的杰出体现。自1937年第11、12期他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战时教育问题》和他本人的《从战时校舍问题说到改革学校制度》两篇文章正式开启《教育杂志》的“战时”话语体系建构以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间,《教育杂志》有关战时教育的各类论著、通讯均由“战时”“抗战建国”和“抗战以来”三个带有鲜明战时特色的关键词予以统领,呈现出明晰的战时阶段脉络和鲜明的战时期刊编辑话语特色。
经统计,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文章标题中含有“战时”“抗战建国”和“抗战以来”三个关键词的文章分别为88篇、13篇和72篇。根据战争的阶段性发展,杂志在内容组织和话语编织上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主动设置倾向。1938年带有“战时”关键词的文章由1937年的7篇迅速增长到47篇,可以看出,杂志已经快速而正式地开启了战时话语体系。从1938年上半年到1939年,“抗战建国”一词在《教育杂志》上开始出现并快速增长则是对国民政府1938年4月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回应。1939年标题中含有“战时”一词的文章有23篇,较上年出现明显的回落,这是《教育杂志》的战时教育话语从全面抗战伊始的紧急、嘈杂、多元逐渐向理性和有序演进的标志。1938年下半年以后,《教育杂志》关注的议题已经从初期的“教育方针”“战时学校制度变革”“战时课程”等重大紧急的问题,转向“师范教育”“师范院校创设”等常规但具有国防意义的类别教育问题。1940年具有战时特色的文章不多,这与全面抗战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是对应的。这一年中,该杂志开始关注经过迁徙、流离逐步稳定下来的各类学校的常规教育教学问题。此外,当年的刊物上也刊发了大量来自上海孤岛、华北、东北沦陷区以及大后方的,反映各地各级各类教育实况、现状的文章。进入1941年,经过对前两年战时教育现状、实况的梳理和思考,在黄觉民的主导之下,杂志先后推出了“抗战以来高等教育专号”和“抗战四周年纪念号”,两期专号中95%以上的文章均被冠以“抗战以来”的时间定语,又因作者多为各知名高校校长及各省教育厅厅长,这两期专号一时在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杂志主编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传播活动的发起者,也是传播活动的组织者,因此,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7]。作为《教育杂志》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和灵魂,在黄觉民的精心组织和编排之下,四年间《教育杂志》的每篇文章之间、每期刊物之间独立自为的封闭性被“打破”,转而以一个新系统的结构要素的形式出现。这样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制约性就使刊物形成信息的交换,从而输出更有意义的信息,释放整体大于部分的意蕴和能量。[8]战时《教育杂志》正是通过这一战时话语体系较好地呈现了整个教育领域的生态和舆论场域。
3.深拓战时教育期刊的国际视野
多年的海外求学经历使黄觉民主持下的《教育杂志》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全面抗战时期的黄觉民一直坚持将中国的战时教育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这一视角不仅让内迁的高校师生和其他教育界人士摆脱信息的闭塞,了解世界各国的教育动态,更能让他们知晓同样处于战争阴影之下的欧洲各国的教育应对策略,从而坚定“文化抗战”的信心。
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社跟随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不断辗转迁移,但《教育杂志》的“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栏目不仅没有停办,反而增强作者阵容,尽量实现内容与“战时有密切关系”的编辑方针,以求深拓期刊的国际视野。诸如《英国战时教师和学生须知》《战时疏散学童后分区的教育补救法》《战时教育中之深谋远虑》《英国战时撤退学童计划》《英国对于战时教育措施之筹划》《纳粹摧残大学教育的实况》等来自世界各国的最新战时教育研究成果与信息资讯,为战时教育学术研究和战时教育应对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宽广的国际视野。
此外,为使教育界人士了解国内外的战争形势,也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在“战时补充教材”栏目中,主编黄觉民积极组织并编选了来自外国媒介或由外国记者撰写又或由日本问题专家分析撰写的有关日本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局的文章。经统计,在38篇“战时补充教材”中这类文章有:《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墩开会经过》、《晋察冀三省边区政府的实况》(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采写)、《日本的军事胜利得到了些什么?》(英国丘吉尔首相的广播词)以及《日本现金已尽》《日本侵华的损失》《日本经济的崩溃》等,共计8篇,占所有“战时补充教材”所选篇目的21.1%。由此可见刊物主编拓展期刊国际视野的用心。这些文章的编发和传播,对于阻断因战事不断变化而导致的漫天“小道消息”,向內迁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通报战局进展,鼓舞他们的文化抗战士气是极为重要的。[9]
全面抗战时期,黄觉民还充分挖掘《教育杂志》的期刊内容资源,根据杂志的专号内容编撰《战时教育》《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等图书,这些图书后成为战时各级师范院校教材和战时学生报考高校的“升学指导用书”,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早在民国时期,黄觉民就颇有“融合出版”思想。此外,黄觉民在画刊编辑出版领域也体现出惊人的编辑和发行推广才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曾创办综合性彩色摄影画报《东方画刊》,主编兼发行人初为史谷光。1939年4月起,黄觉民开始担任该刊编辑和发行人。在他主导下,《东方画刊》“将全民族在大时代前所表现的精神及其一切活动,用真实的写影尽量反映出来,兼收关于新知识及调剂奋斗生活的材料,中英文对照说明,全部用影写版印,精美绝伦”[10]。《东方画刊》尤为重视编发反映华北、西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专题摄影报道,宣传抗战。同时担任《教育杂志》主编的黄觉民更在《教育杂志》上用整版的篇幅大力推广《东方画刊》。短短两三年时间,《东方画刊》就成为与《良友》《今日中国》《大地》等画刊一样销行国内外的知名画刊。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黄觉民曾担任教育行政官员后又到大学从教,加之其主要的期刊出版经历主要集中于全面抗战的几年间,相关的资料留存较少,其编辑出版思想和实践一直备受忽视。但无论是从其编辑出版能力,在期刊出版方面的成就,还是从学识和出版人的责任担当等方面来看,黄觉民都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民国出版人物。
注释:
①1934年第4期《教育杂志》“编者余谈”中曾介绍黄觉民历任中学生青年会会长、义务学校校长、福州村光小学校长、青年会中学训育主任、厦门云梯中学校长、菲律宾华侨中学训育主任和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系主任。
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学院,中国近代众多教育学家都是该院毕业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幼教之父陈鹤琴、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以及郭秉文、杨荫榆、林茂生、欧元怀等近代著名教育专家都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或在该学院有过求学或访学经历。
③程时煃,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民国时期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大夏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1][3]福建江夏黄氏源流研究会.福建黄氏世谱·人物篇[M].香港:中华国际出版社,2005:112.
[2]黄觉民演讲心理学应用法今日下午四时在青年会[N].申报,1931-12-31.
[4]中华职教社开专家会议讨论补习教育各问题专家蔡元培等均出席[N].申报,1937-02-04.
[5][6]教育杂志社.编者余谈[J].教育杂志,1937(9-10):142-143.
[7]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128.
[8]李频.期刊策划导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0-91.
[9]吴永贵,黄河清.抗戰责任与期刊岗位——孙寒冰与他主编的《文摘》杂志[J].中国编辑,2015(4):72-76.
[10]韩丛耀,赵迎新.中国影像史(第7卷)[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383.
(作者范军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陈兰枝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教师教育论坛》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