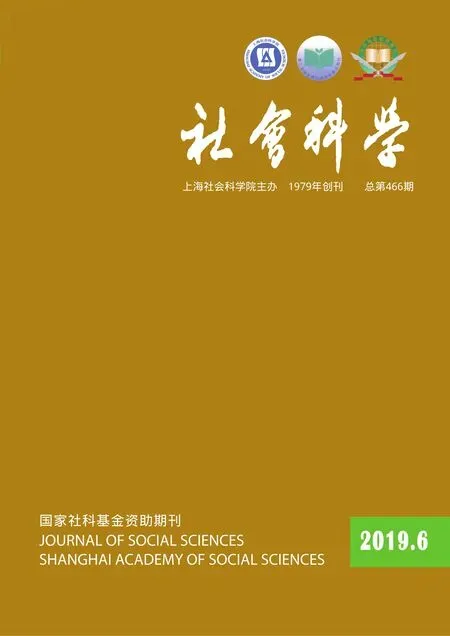动态时间和静态时间的“分”与“合”*
——基于时间理论的当代论争与古代方案的考察
陈群志
一、引 言
许多学者认为,“动态时间”(dynamic time)与“静态时间”(static time)的严格“二分”预设完全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例如,米勒(F.D. Miller)指出,亚里士多德隐性地区分了时间的动态系列与静态系列,虽然他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时间观的差别所在。[注]cf. F. Miller, “Aristotle on the Reality of Time”, Archive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56, 1974, pp.143-147.在此基础上,克雷茨曼(N. Kretzmann)进一步揭示,亚里士多德像麦克塔加(J.E. McTaggart,1866—1925)[注]cf. J.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Mind 17, 1908, pp.457-474.区分A系列(A series)和B系列(B series)那样,已明确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时间类型,并用以解释时间本性的疑难问题。[注]cf. N. Kretzmann, “Aristotle on the Instant of Change (II)”,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s 50, 1976, pp.91-114.但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静态时间观与动态时间观问题》一文中,笔者专门探究了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中是否明确区分了“动态”与“静态”两种类型的问题,并提出了几点看法:
第一,古代时间观念中没有一种清晰的动静二分化的观点,古人无意于此;第二,我们虽然能够将当代英美时间哲学二元区分的来源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本没有持如此区分;第三,依索拉布吉(R. Sorabji)的看法,麦克塔加和分析哲学学派的动静时间区分应该溯源于扬布里柯(Iamblichus of Chalcis,约245—约325),[注]cf. R. Sorabji, Time, Creation and the Continuum: Theories in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ndon: Duckworth, 1983, p.51.在该文中,笔者认同了这个解释,并对此给予了简要说明。[注]陈群志:《亚里士多德的静态时间观与动态时间观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9期。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化,笔者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两种时间系列的区分是否合理?因此,原来探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就不得不再加补充:首先,“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的当代区分与论争在前文中并没有给予具体阐明,还需详述事实;其次,“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的二分对立既然受到质疑,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古代重新寻找原初方案;再者,笔者近来认为,扬布里柯虽然表面上看似区分了“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但究其实质却依然是“合一”的,而非“二分”的。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本文将在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两种时间观的当代之“分”与古代之“合”的联系与区别,阐述方式也随之采用了倒叙追问。
二、当代论争:从A-理论家和B-理论家到麦克塔加
在当代的时间哲学学说中,英美分析哲学家们特别注重区分A-理论(A-theories)与B-理论(B-theories)的构建和探究。[注]cf. C. Williams, “The Metaphysics of A- and B-time”,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6, 1996, pp.371-381; B.V. Nunn, “Differences Between A- and B-time”, Philosophical Inquiry 22, 2000, pp.103-114; L.N. Oaklander,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taphysics of A- and B-Tim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6, 2001, pp.23-36; J. Parsons, “A-theory for B-theorists”, i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2, 2002, pp.1-20.前者注重从时间生成(temporal becoming)角度入手,相当于一种“动态时间”的描述;后者注重从时间关系(temporal relation)着眼,相当于一种“静态时间”的解释。[注]cf. L.N. Oaklander, “The Problem of Time and Change”, Stoa 1, 1998, pp.85-109.两种思路虽然相互之间存在争论,但基本都认同要区分时间观的不同论证。换言之,如果要清楚地认知时间,就需要首先对时间进行“动态”(A系列)和“静态”(B系列)之“分”,然后再执持其中一个立场。
根据笔者的详细考察,A-理论家所持的基本观点是:(1)他们认同麦克塔加对A系列与变化的论证,在此基础上,他们坚持认为变化只有A系列才能说明,B系列是无法说明变化的。[注]cf. G. Schlesinger, Aspects of Time, New York: Hackett Publishing Co., Inc, 1980,pp.23-25; W.L. Craig, The Tensed Theory of Time, Dordrecht: Kluwer, 2000, pp.169-217.(2)他们对A系列的论证诉诸于时态语句和非时态语句的关系问题,以此试图把B系列的表达还原成A系列的语言。如“L在M之先”就能还原为“L是过去而M是现在”或“L是现在而M是将来”之类。[注]cf. C.D. Broad, An Examination of McTaggart’s Philosophy,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264-81,288-317; R. Gale, “Tensed Statements”,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2, 1962, pp.53-59.(3)他们反驳麦克塔加的主要看法来源于两项:A系列不存在无穷倒退的问题和A系列是一种良性循环。[注]陈群志:《麦克塔加与分析哲学学派的时间理论之争》,《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B-理论家所持的基本观点是:(1)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不是去论证A系列是否会造成矛盾,而是认为A系列是主观系列,并不能真正代表时间的本质,时间的本质只有通过B系列这种客观系列才能得以说明。[注]cf. B. Russell,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in The Monist 25, 1915, pp.212-133; H. Mellor, Real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92-102; K. Sneddon, Time,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p.44-46.(2)变化唯有B系列能够给予解释,虽然罗素的论证显得弱势了些,因而遭到了麦克塔加的反对,但其他的B-理论家从“事件”和“事物”的区分来反驳B系列无法说明变化的论证,倒不失为一种强势的辩护。[注]cf. A.N. Prior, “Changes in Events and Changes in Things”, in Papers on Time and Ten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14; K. Sneddon, Time, p.48.(3)他们认为B系列自身就足以构成时间,此中并不需要A系列作为基础,并且主观的A系列必须奠基于作为客观的B系列,换句话说,A系列只是B系列所形成的一种主观结果而已,我们也可以将A系列的表达转换成B系列的语言。[注]陈群志:《麦克塔加与分析哲学学派的时间理论之争》,第84—86页。罗素就说:“如果B接续着A,我们就可以说A在B之先;与之类似B在A之后。这纯粹是语言的定义。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先和在后的关系是在客体与客体之间被给予的关系,而不是任何方式地蕴含着过去和现在。”“当一个事件相比于全部现在而言是在先的就被称为是过去,并且当一个事件相比与全部现在而言是在后的就被称为是将来。”[注]B. Russell,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Monist 25, 1915, pp.212-233.
如此看来,A-理论家和B-理论家虽然都反对麦克塔加所持的“时间是非实在的”时间观,但他们内部却又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差异来源于对麦克塔加的部分赞同和部分反对。从部分赞同的方面看,两者都坚持区分两个时间系列,并且A-理论家同意麦克塔加所言的B系列无法说明时间,B-理论家同意麦克塔加所论的A系列无法成立。从部分反对的方面看,A-理论家认为A系列不存在矛盾,时间的非实在性看法显然错误,B-理论家则指出B系列才能说明时间,它是实在的,由此麦克塔加的结论亦不正确。
经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A-理论家的论证,如果只是基于一种反驳麦克塔加时间观的内在理路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其根本问题恰恰就在于接受了时间的动态系列(A系列)与静态系列(B系列)之“分”,并采取了部分赞同和部分反对的策略。其赞同的方面如前所述,自不待言,其反对的方面则侧重于藉由语言与时态分析来解决问题,进而无法真正进入到把时间作为“原初给予物”来理解,因此也就无法把握时间的本质。简单地说,如果仅仅通过对英语的语言与时态分析就能清楚地认识时间的本质,那么英美哲学家如何来范限其他语言的描述呢?比如:汉语语法并没有像英语那样的时态问题,难道就不能说明动态时间了么?[注]cf. François Jullien, Du“temps”: Elements d’une Philosophie du Vivre, Paris: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01, pp.15-31.同样的疑难,在B-理论家那里也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B-理论家对麦克塔加时间观的反驳没有A-理论家那么来得有力,同时,他们对A-理论的反对也显得相对薄弱,如果只是从是否“客观”来进行辩驳很难具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将英语语言中的时态语句转换成非时态语句,就势必如此。因为A-理论家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将非时态语句转换成时态语句,这很容易做到。因此,B-理论家时间观的自洽性问题困难重重。
直至今日,双方依然争论不休,没有定论,这种情况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实际上,时间本无如此“思心自设”的截然不同的动静之分,而只有古人常言的永恒和流逝之别。这里,本文无意于去解决A-理论或B-理论所涵的复杂问题,也无意于调和两者之间的门户之争,而只想着眼于追述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之“分”与“合”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渊源。显然,当代动态时间观(A-理论)与静态时间观(B-理论)论争的发起点离不开麦克塔加的理论预设,但这个理论预设是如何出现的呢?
比较清楚的是,为了论证时间的存在是不真实的,麦克塔加预设了时间的“二分”,亦即区分了A系列和B系列这两类时间。前者是动态的,源于事件本身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成变化;后者是静态的,基于在先和在后的固定关系,如2017年和2018年,一个在先,一个在后,不能同时出现。[注]cf. J.E. McTaggart, “The Unreality of Time”, Mind 17, 1908, pp.457-458.不仅如此,麦克塔加论证,A系列和B系列都无法构成时间,它们之间也不可融通。然则,时间系列的“二分”只是一种智巧的抽象游戏和语词诡辩,以此来论证时间的实在性或非实在性,都缺乏真正的理论根据。只因时间本身兼具流动和静定的双重特征,这种特征并非通过对动态系列或静态系列或二者的否定就能否定。[注][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4页。
因此,从当代时间哲学的A-理论与B-理论的论争来看,静态时间与动态时间的“二分对立”虽说能够从某些方面进行合理解释,但它们的原初目的都是想应对麦克塔加所提出的难题。然而,解决难题的方式却又建立在一种“床上加床,屋上加屋”的基础上,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更多的解释困境。笔者觉得,既然动静之“分”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回到古代的方案,看看古人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走进时间内部的新启发。
三、古代方案:从扬布里柯到亚里士多德
特尔斯基(P. Turetzky)指出:“麦克塔加问题的提出源自于否决扬布里柯有关两种时间观之形而上学方案的需要。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在先和在后,并把时间与计数联系在一起,此预示了B系列的解释;他也研究了现在,此预示了A系列的解释。”[注]P. Turetzky,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18.
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和扬布里柯的时间学说“似乎”是麦克塔加进行“二分”的理论来源。笔者同意特尔斯基观点中的一部分,即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哲学具有某种类似于“动态时间”或“静态时间”的形式,但我认为他并没有严格区分,也没有进行分别论证。[注]陈群志:《亚里士多德的静态时间观与动态时间观问题》,第88页。如果我们把当代论争中的时间形式溯源到亚里士多德,并认为他“预示”了麦克塔加意义上的两种时间观,实际上没有绝对的证据。更何况,倘若依今天的立场溯源的话,两系时间术语的区分恐怕不仅能够追述到亚里士多德,而且能够追述到柏拉图,甚至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
再者,根据索拉布吉的考察,虽然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里柯恐怕是古代最先对时间作出静态与动态两系区分的人,[注]cf. R. Sorabji, Time, Creation and the Continuum: Theories in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p.44.但是麦克塔加很有可能并不清楚扬布里柯关于时间的论述,又从何去说“麦克塔加问题的提出源自于否决扬布里柯有关两种时间观之形而上学方案的需要”呢。更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扬布里柯的形而上学区分,与其说是一种动静之“分”,不如说是一种动静之“合”。而且,这种动静之“合”一方面可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另一方面也能追述到普罗提诺和柏拉图这个思想脉络。
因此,笔者虽然不同意特尔斯基的观点,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提示出了与麦克塔加的“二分”预设相关的古代解释方案(不是作为理论来源)。我们相信,对这些古代方案的重新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麦克塔加及其后继者(A-理论家和B-理论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的困境,尤其是关于动静时间观的截然对立。下面让我们用倒追的方式从扬布里柯、普罗提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第一,根据当代学者的探研,扬布里柯的确将“时间”区分成了居于理智世界(the intelligible world)的“静态时间”和居于感觉世界(the sensible world)的“动态时间”。不过,在他看来,“静态时间”因其属于理智世界,亦即柏拉图所谓的理型世界(the realm of the Forms or Ideas),是一种高位时间或上层时间(higher time);“动态时间”因其属于感觉世界,亦即柏拉图意义上的殊相世界(the realm of appearances),则是低位时间或下层时间(lower time)。[注]cf. P. Turetzky, Time, pp.51-52.并且,低位时间或下层时间“分有”高位时间或上层时间,永恒不变的理智世界与恒常变化的感觉世界虽然有不同的分属区域,但它们之间是可以传递的,两种时间相遇在“现在”。如图1所示:
图中有两条线:一条直向延伸的水平线和一条恒定倾斜的V形线。水平线居于理型世界的下层边界(the lower bound),V形线居于殊相世界的上层边界(the upper bound)。水平线上的T1和T2表示在现在T3之“先”(Earlier)的部分,T4和T5表示在现在T3之“后”(Later)的部分,而V形线上的T1、T3、T5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其中,水平直线上的现在点T3意味着时间不断地从“先”向“后”位移,与此相关,V形线则意味着时间从将来(T5)经现在(T3)再到过去(T1)的不断运动。[注]有关这种“先”“后”与“现在”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有一段解释:“我们说‘先’和‘后’,就是说该事物达到预定状态的时间和‘现在’之间有一段距离,而‘现在’是过去和将来之间的限,因此,既然‘现在’是在时间里的,那么‘先’和‘后’也是在时间里的,因为‘现在’在什么里,和‘现在’之间的距离也就应在什么里。(但是‘先’在过去的时间里和在将来的时间里用法相反: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把离‘现在’较远的叫做‘先’,把离‘现在’较近的叫做‘后’;而在将来的时间里,我们则把离‘现在’较近的叫做‘先’,把离‘现在’较远的叫做‘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5页。)由此可以得知,V形线的顶部持续沿着水平线从先向后运动,在其交汇处(T3)表示存在着一个固定轴“现在”将时间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作为水平的且不断向右延伸的恒常存在部分和作为倾斜的且不断向左变化的持续生成部分。两个部分在恒常的“现在”点处传递,图1可以解释“静态时间”为何能够拆散为“动态时间”。
依扬布里柯,“静态时间”(水平线)是不变的和永恒的真正时间,是第一时间;“动态时间”(V形线)是变化的和流动的虚设时间,是第二时间。第一时间支配和衍生着第二时间,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传递着两种真实存在的“现在”,理型世界的“现在”是静态的和永恒的,传递其恒常性和实在性给殊相世界的“现在”,而殊相世界的“现在”是流变的和生成的。[注]有关扬布里柯的时间观表述,遗留至今的各种残篇及评注可参见J. M. Dillon, ed., trans. & comm., Iamblichi Chalcidensis: In Platonis Dialogos Commentariorum Fragmenta, E.J. Brill: Leiden, 1973, pp.173-183.乍一看,扬布里柯好似真的像麦克塔加那样把时间分成两类:基于先后关系的静态系列(第一时间)和基于将来、现在和过去关系的动态系列(第二时间)。但实际上,扬布里柯并没有将时间进行“二分”,而是一种“合一”的形而上学描述。这种描述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当然更应当追溯到学派内部的前贤普罗提诺。
第二,扬布里柯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我们讨论他的时间学说,最好将其置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进行衡定,才算合乎情理。普罗提诺自然居于核心地位,扬布里柯的时间观实际上就是批判地继承他的观点而来的。在一篇题为《时间与永恒》(《九章集》第3卷第7章)的文章中,普罗提诺首先随顺柏拉图而表明,时间与永恒是完全不同的,永恒具有永远持续的本性,而时间则属于生成变化的领域。[注][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永恒的事物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它源于太一,指向太一,居于其中而构成统一的整体。[注][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第327页。我们知道,普罗提诺提出了具有一体化的三本体说:第一本体即太一,它超越一切存在与一切思想,生成一切他物,自身却保持不变;第二本体即理智,它源于太一,凝思太一,是太一的表达和活动,它是永恒的精神现实,是真实的普遍存在;第三本体即灵魂,它是从太一经由理智而流溢出来的,是理智的表达和活动。[注][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下册,第543-596页。灵魂又分两层,第一层高级灵魂的本性独立于世界,不直接作用于世界,它直接依赖于理智;第二层低级灵魂与世界的躯体相结合,朝向感觉的现象世界,在它之中有众多个体灵魂,以此而扩充到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注][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第563-564、657-659页。时间就是内在于灵魂之中的,灵魂摹仿理智世界创造出感觉世界,因而产生一种运动,这种运动首先在于灵魂把自身内嵌在时间中,以时间来替代永恒,如此一来,一切生成物都是在时间之中的存在者。[注][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第338页。
由此可见,普罗提诺把灵魂分为两部分:居于上层的部分指向理智,居于下层的部分通过流溢形成变化的世界,时间就与此变化一同运动。灵魂虽说来源于不变且统一的永恒,但其活动产生了时间,时间是永恒的显相存在,它不会像永恒那样是没有分隔的统一体,而是不断运动的,其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它不是完全无限的整体,而是连续无限的顺序;不是完全作为现在是的整体,而总是将来是,将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形成。”[注][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第339页。职是之故,普罗提诺认为,既然灵魂在宇宙中无处不在,那么时间也必然无处不在,它是具有实体性的和真实的事物。
笔者认为,作为后继者的扬布里柯的时间学说虽然源自于普罗提诺,但二者却有着重要区别。对普罗提诺而言,理智世界控制着感觉世界,变化只能在感觉世界里有效。扬布里柯则认为,理智世界虽然控制着感觉世界,但这种控制是缘于其自身内在的动静传递,因此,时间不是内在于灵魂的,而是从理智世界向感觉世界过渡的本体,是一种实现原则。就静的一面看,时间属于理智世界,是永恒的,就动的一面看,它又是时间得以呈现的原因,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在这两种时间的转化中进行的。
第三,扬布里柯的这种时间学说,根据他自己的陈述,应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家和哲学家阿契塔(Archytas)。不过,历史上真实的阿契塔与柏拉图是同时代的人,这比扬布里柯所提到的阿契塔生活时间要早,因此我们只能追溯到一个伪阿契塔(Pseudo-Archytas)。[注]cf. J.J.A. Mooij, Time and Mind: The History of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Leiden·Boston: Brill, 2005, p.62.在这个伪阿契塔看来,“现在”虽然具有不同的内容,但其却分有着相同的“形式”,这就像前面图1所说的“静态时间”与“动态时间”的传递。实则,伪阿契塔和扬布里柯有关“现在”的观点很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注]cf. S. Sambursky and S. Pines, The Concept of Time in Late Neoplatonism, Jerusalem: The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71, pp.12-17.按照他的说法,“现在”一方面作为时间的潜在分开者,是过去时间的终点和将来时间的起点,另一方面,它又是时间的连结关键,是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的合一者。而且,作为合一者的“现在”(犹如理型世界的现在)是同一的,作为分开者的“现在”(犹如殊相世界的现在)是有差别的。[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32页。
显然,亚里士多德重点研究了“现在”,在他看来,没有时间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时间,时间因“现在”才得以连续,也因“现在”才得以划分。[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26—127页。在此意义上,变化必然与时间相连,一切变化都有快慢之分,一切运动都有先后之别。当我们说“在先”或“在后”的时候,即是说此事物达到预定时间与“现在”还有着一定的距离,至于距离的多少并不重要,而得知“现在”是过去和将来的界限才最重要。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似乎已使用着麦克塔加预设的A系列和B系列术语。
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在《物理学》第4章第10—14节中,亚里士多德用了非常多的“过去”、“现在”、“将来”和“在先”、“在后”这样的时间术语。[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121—122页。这也是特尔斯基之所以认为亚里士多德预设了A系列(动态时间)和B系列(静态时间)的原因。然而,就像笔者已在另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持有两种时间观,但他并没有分别对待,更无意于严格区分。[注]陈群志:《亚里士多德的静态时间观与动态时间观问题》,第88页。与时间的动静二分相对照来看,他的时间观更多的是一种动静合一论。只是与扬布里柯的动静合一相比,亚里士多德所言的“静态时间”反而是建立在“动态时间”之上的。
综上所述,古代方案与当代论争完全不一样。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源于麦克塔加的两种时间系列的区分,接受了把时间进行“动态”与“静态”二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古代,无论是扬布里柯,或是从其再回溯到普罗提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间问题的探究都是按照“合一”的方式进行的。笔者认为,如果跳出当代分析哲学的这种侧重于语言时态的分析走向,我们会更加认可古代哲学中有关时间问题的解释。不管怎样,时间始终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事实本身,胡塞尔将其称之为“原初的时间域”[注][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0页。,这个“时间域”显然只能是动静合一的。
结 语
麦克塔加虽然在形式上好像接续了扬布里柯的区分,也同样把时间区分为“静态时间”(B系列)和“动态时间”(A系列),但他的模型却完全没有扬布里柯式的形而上学设定,而只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进行了主观客观的二分划界。因此,在麦克塔加那里,“静态时间”因其具有恒定不变的客观性反而不能代表时间的本质,动态时间因其不断变化的主观性反而能够体现时间的本质。我们可以说,麦克塔加将扬布里柯的时间学说进行了“砍头”,去掉了作为时间大脑的永恒的理智成分,而彰显了感觉世界的绝对权威性。更重要的是,他接着论证了时间的非实在性,不管是“静态时间”抑或是“动态时间”都是非真实存在的。换言之,他不仅仅进行了“砍头”,同时也进行了“割尾”。这样的话,整个的时间的存在性都受到了否定。在麦克塔加之后的一百多年内,英美分析哲学学派的时间讨论大体都在此范围内进行,或辩护之,或反驳之。[注]L.N. Oaklander(e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vol. 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1-232.
如今看来,早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扬布里柯那里,就已经将时间区分为两种形态:“静态时间”和“动态时间”。只是这种区分的实质并非从主观客观(A系列B系列、A-理论B-理论)角度来进行,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时间作为从理智世界向感觉世界过渡的本体)层面给出的。职是之故,“静态时间”只存在于理智世界,它是不可分离的真实时间,具有稳定的永恒的理智秩序;“动态时间”则存在于变化和运动世界,它是可分离的衍生时间,具有流动的变化的生成秩序。其中,“静态时间”与“动态时间”是奠基与被奠基的相合关系。扬布里柯认为,这两种时间都是实在的,因为理智世界与感觉世界虽然有不同的分属区域,但它们之间可以通过实在存在的“现在”来传递。
如果我们再倒转过来(回到亚里士多德)进行理解的话,麦克塔加以及A-理论家与B-理论家所争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能直接看出其中涵摄亚里士多德的痕迹。总的说来,整个西方哲学中有关时间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柏拉图《蒂迈欧》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所给出的范限。无论是扬布里柯给出的肯定的解读,还是麦克塔加给出的否定的解读,都可视为是基于前贤的思想资源而来的。如果说,怀特海认为整个欧洲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注脚”[注][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页。,那么也不妨说,都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一系列注脚”。当然,如怀特海所言,“注脚”并不是说学者们摘取了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而是指所讨论的范围依然是散见于其著作中的基本观念,时间理论在西方古今的走向亦是如此。
总之,在本文讨论中,我们采用了一种逆序的方式,亦即从当代英美哲学时间观中的论争问题追溯到麦克塔加,再从麦克塔加追溯到古代的扬布里柯,并由扬布里柯溯源于普罗提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路走来,笔者实际上只想解决一个疑惑:时间能否区分为“静态”与“动态”两种类型?依今天全面科学化、智能化的时代来看,似乎这种区分更能把具体问题探索清楚,时间哲学也能有一个讨论的“共同模式”或“典型范本”。在现行的学术话语体系下,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划定区域的“窄而深”之研究,当然有其合理性,也能自圆其说。可是,对于涉及人类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等多重视域的时间研究,行之有理并不一定行之有效。因此,我们不得不向前回溯,在当代动静之“分”的背后找到时间原本相“合”的古代根据。
——《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基于国际理论家的视角》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