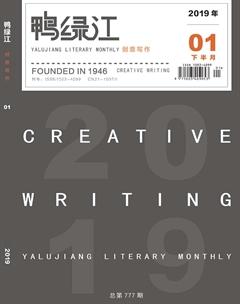与故宫对话
叶君 张诗淇
在浮躁、功利之气弥漫的时代,为故宫修复文物不仅是一件日常工作,也是一种人生修养。这些匠人们身怀绝技,专注敬业,一件器物的修复也是一种文明的传递。《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工匠之心记录工匠精神,创意独特、语态轻快、叙事平易、清新自然,赢得年轻观众的追捧,为纪录片开辟了传播新空间。
为什么选《我在故宫修文物》?其实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它体现了纪录片在今年发展的两个标志:第一是新媒体传播,第二是品牌。2005年徐欢做了一部十二集的《故宫》纪录片,那是中国纪录片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到《故宫100》,做出那么多小体量碎片化很精致的作品,再到出现《我在故宫修文物》,把品牌做了一个延展。在这个过程中,给纪录片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启示。这个作品给纪录片带来的启示对中国纪录片领域非常重要。
其實这个片子最早在电视播出,收视率并不是很高。我想说的是,需要找到新的观众群,找到知音。以往的纪录片不是不好,而是讲话方式有点陈旧,因为纪录片还没有找到最准确的传播方式。这个片子给人的启示非常重大,我也要向年轻的团队学习,让纪录片年轻起来,不能一张嘴就是五千年,很高兴看到这个片子,也祝贺他们给中国纪录片带来的启示。
——张同道
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经验是做研究,这个也是清影工作室的长项,每次做纪录片之前,先做调研,做研究,做一个非常周密的研究报告,发现它的价值和意义。现在的纪录片换了年轻人的视角去看世界,过去我们担心小孩拍这些匠人,他是不是能够很好地去沟通、共鸣和理解,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是可以的。
过去我们拍纪录片的时候,带着一种道德怜悯的状态,说这些人比谁都苦,比谁都惨,其实《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创作者反而发掘了这些工匠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会作为粉丝去对着这些工匠,跟这个有特别重要的关系,这是一种表现好人好事和英雄模范等题材的很重要的观念转变,这可能也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尹鸿
张诗淇:不同于以往的故宫题材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拍摄对不同类别文物的修复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讲述,您是出于什么考量选取了这样的切入口?
叶君:之前我接触过故宫的很多东西,2011年我做了《故宫100》,又接触了一个我国香港作者的书《我的家在紫禁城》,这个“我的家”就有一个“我”的概念。当时取这个纪录片的名字时写了很多题目,写满了一张纸,团队就一起商量,最后确定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名字。
张诗淇:之前您提到,早在2010年,主创团队就开始关注故宫的匠人群体,有着十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四个月的集中拍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田野调查报告的内容吗?这对您拍纪录片有着何种启发和灵感?
叶君:这个调查不是我做的,是制片人带着学生做的。他们大概在故宫里面待了三四十天,跟着各个工艺组,什么捣糨糊的啊,在木器组做鱼鳔胶的啊。我当时不在,我在做《故宫100》。我自己拍纪录片的灵感其实都不是来自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我看得比较少。我看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学科,比如《红与黑》《水浒传》《红楼梦》、唐诗宋词,我的灵感都会和这些有关联。在这些作品中,你看到的世界重新分解,又在重新组合。
张诗淇:就《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方式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麻花式的构建了多条故事线交叉叙事的复合结构,并且运用了一种平民的视角,您是如何制定这个叙事策略的?
叶君:其实这个叙事策略是拍完之后,剪辑时发现的。拍的时候我们跟着十几个工艺组在拍,这个时候其实相当于挖矿,你预测这个地方有矿,就先挖,挖完之后再筛,筛完之后可能这些矿还要重新组合成合金。我们就是在重新创造的时候发现,也许用《水浒传》的结构是最好的。当时素材有三万多个镜头,剪辑对于人的阅读理解能力要求又比较高。比如说你剪辑青铜器那部分,你要懂工艺,还要对干事的工匠赋予文学色彩,去阅读理解他的世界,进入他的世界,看看他在意什么东西。
张诗淇:回顾《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的走红,您认为新媒体场域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什么助推作用?如何做到纪录片在新媒体这个场域中发挥更大的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您认为纪录片应该怎样兼顾它的人文性和趣味性?
叶君:我平时喜欢看人类文明史,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就会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比如从最早的纸张到电影的出现,再从电影到电视,再从电视跨到手机,无非就是换个瓶子来装酒。
很简单,质量做好并且与观众的接受度串联起来,就可以。人类历史上很多东西发明出来后,最初都是小众人才能享受到,随着技术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这是很好的。我从来不会去想人文性、艺术性、趣味性的问题。这就好比你问足球运动员为什么躲过两人而射门,他也说不出为什么。
张诗淇:《我在故宫修文物》从播出到现在也两年多了,现在的您再回头看这部作品,有什么遗憾或者认为可以更加完善的地方?您理想中的音乐效果是什么样?
叶君:不用再回头看,我自己剪完之后都知道有很多遗憾。像镜头、音乐、节奏、整体的感觉,这些全有漏洞。很多镜头都是不经看的。音乐最开始找人做了,做出来的实在没法听,后来也没有用到片子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人家一听说是在做故宫题材的,他就把音乐做成“荆轲刺秦王”那种感觉。
后来我一直在找音乐,想要一些现代感的音乐,这可能也和个人审美与爱好有关系。比如有一些电子音乐、游戏里面的音乐,在现代感的节奏中融入了古典的成分。比如说像敲一个大陶瓷缸的声音,或者木质的弹拨类乐器这种感觉的音乐,你能感觉到是某种材质的乐器的弹奏,但节奏又是比较有现代感。基本上按照这种感觉去寻找的,也能够和主题比较贴近。
张诗淇:那您觉得中国的文化产品应当怎样走向世界?
叶君:就像足球一样,多踢国际比赛,踢多了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中国足球一踢就知道世界排名才八十几。要多参与国际交流,知道自己在世界文明的位置。但是也很难,因为现在很多人宁可不做事,也不愿意犯错,这几年的气氛就是这样的。要走向世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张诗淇:结合您从业的经验和感受,您能分享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吗?您心目中优秀的纪录片是怎样的?
叶君:资本的风险这几年很明显,可能也与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心态有关系,老在想弯道超车,那别人为什么不弯道超车?这就是中国的资本环境,本来应该有自然生长的空间,但人们都是在非常快地套取利润。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好莱坞平均制作周期是871天,放在中国就不太可能。最近都在说,才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影视的资本热潮就消退了,这还只是资本和商业的环境。目光放在整个生产线上,就会发现各个位置上的人专业度都不够,他们都来不及去专业。
之前看过一段话,其实不仅可以形容纪录片,也同样可以用来衡量各种内容生产。拿作家作比,四流的作家只是简单或肤浅地图解现实,不过供人消遣和休闲罢了,反腐败小说、美女文学、新写实主义等,大多在这个境界;三流的作家,透过现实已窥视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子,像莫言、贾平凹、陈忠实、余华、阿来等作家已超越这一境界,正在向人本身进军;二流作家,直抵丰富、复杂、多维的人性,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探索,许多小说为什么没有生命力,就因为他们还处在时代和现实的包围中,还没有冲进历史和文化内核;一流的作家,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不仅穿透现实、历史和人性本身,而且关怀人类存在的意义,像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海明威等人,无不是这种境界。就纪录片来说,总体就是争取做到专业性和大众性的平衡吧。
(叶君,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张诗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