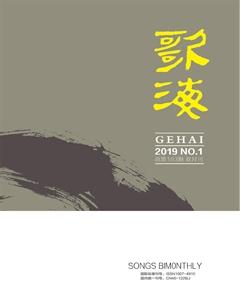叙事方式与新诗意的阐发
黄莹 何敏慧
[摘 要]作为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体验,诗意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渐渐失落,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世俗生活中的情感体验——“新诗意”。新诗意的出现源于人类文明的高度成熟和社会生活中庞杂的信息量,个人意识和理性思维越来越发达的人类开始从现世生活中寻求意义感。诗意凭借语言敞开,新诗意凭借叙事阐发。叙事通过对事件序列的协调,开拓出广阔的表达空间,延伸出多维度的诗意空间。正是叙事这种对“异质”事物极强的容纳性,使其成为新诗意最重要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诗意;新诗意;叙事;广西苗族歌谣;鲍勃迪伦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曾经引起了人们对诗意的无限想象和解读。如今技术的发展在日益消解着神性的存在,诗意作为一种蕴含着神性的、丰盈的存在方式和体验感受也日益稀缺。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世俗生活的日渐精致化,社会生活成为自然景观的一部分,衍生出一种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新的体验感受。
海德格尔认为“歌给予神人一体关系的基础以证据,歌见证着神圣者”①。人类因心灵的颤动而歌,由此抒发了神人一体的诗意,可见歌与诗意之间存在着一种古老而微妙的联系。也许海德格尔所说的“歌”和我们今日之“歌”稍有偏差,但诗与歌同根同缘是我们探讨诗意承载的应有之义。所以本文将以广西苗族民间歌谣和鲍勃迪伦的歌曲为例,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中,追溯苗族民间歌谣对诗意的不同表达。并以此为线索,探讨鲍勃迪伦歌词中是以何种表达方式来承载人们立足于世俗生活的新的体验感受,由此厘清这种新的体验感受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表达方式及其意义。
一、 从诗意到新诗意
(一) 古典诗意
诗意,这个词的内涵是广阔而又具有多种阐释性的。提起诗意,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诗歌。海德格尔曾提出过“诗歌”的两种涵义:“一般而言的诗歌,适合于世界文学中全部诗歌的诗歌概念。但是‘诗歌也可以意味着:那种别具一格的诗歌,其标志是,只有它才命运地与我们相关涉,因为它诗意地表达出我们本身,诗意地表达出我们处身于其中的命运。”②与这两种诗歌涵义相对,诗意也有两种涵义。狭义上,诗意可以作为一种文学话语,指的是文本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意境;而从美学上说,詩意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体验。本文对诗意和新诗意的探讨都指的是后者。
如果追本溯源探讨诗意的源起,我们会发现诗意最初是一种纯朴的生存感受和存在方式。维柯在《新科学》中通过对“诗性逻辑”的讨论,追溯了原始的诗意的起源。他认为诗意源于原始人类盛大的想象力,对原始人而言,他们的感觉先于理智,他们是用感觉来解释世界。所以诗意最初指的是原始人通过强大的想象力赋予世界的一种神性。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那句著名的诗——“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中的“诗意地栖居”意思是说: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撼。①也就是说,所谓的诗意,指的是人类在永恒的自然面前的一种惊颤,是神性世界折射出的一种光晕。丁来先在《诗意人类学》中指出:“当宇宙深处的综合性神秘透过神秘的媒介传达到我们的内心时……就会激起一种超常的、隐秘的体验,让我们感受到生存无以名状的扩展……这种生存感受或体验,我们经常将其称为‘诗意。”②
追溯诗意的源起和发展可以发现,诗意的内涵总是与神性的、永恒的感觉相关联。如果说这世界巨大的神秘是一块掷入水中的石头,诗意就是那块石头激起的层层涟漪。这主要是因为人类文明形成伊始,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粗糙的、感性的、脆弱的,同时也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人类在这世界上的生存境况愈是脆弱,就愈是渴望永恒和神性的存在。而在这世界的构造和纹理慢慢明晰后,诗意仍然作为人类返回物之本源时而体会到的一种澄明的、宁静的感受,以及精神“返乡”时所抵达的清明的、空旷的境地。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神性和永恒渐渐被科学技术所消解,当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智,诗意的立足点也就渐渐被抽离,诗意的内涵被架空,成为一个“过剩”而又“稀缺”的虚无的词语。
(二)新诗意
诗意在现代社会的日渐缺失是人们越来越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不再依仗想象来解释世界,曾经对这世界朦胧模糊的感觉变成了光天化日下无法更改的事实。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生活的节奏趋于高速和碎片化,这极大地缩短了人们感受世界的时间,人们内在的自我的感受越来越少,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人们对神性、永恒的希望,从而转入一种对现世生活的关注。为强调这种转变,笔者将以往的诗意定义为古典诗意,把转变后的诗意定义为新诗意。
现实生活何以能阐发新诗意呢?现代社会是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社会都不同的存在。这是一个“上帝死了”的时代。理性思维的发展使人类赋予了这个世界不可变更的逻辑,原始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和强大的想象力在现代人身上只留下了凝固的知识。然而,这也是一个人类文明高度成熟的时代。社会中各种规则、无数关系的相互交叉、集合衍生出了新的“自然景观”。现代社会本身除了具有众所皆知的契约性,还具有被契约性所遮蔽了的丛林性,在现代社会充满了野性与规则的龃龉和妥协。如果说古典诗意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原始人类对世界的“不可知”,那么新诗意的产生则是由于这种复杂的人类社会群体的“不可知”。但并不是说新诗意与古典诗意是南辕北辙的。《诗意人类学》中指出诗意的阐发有三个层次,分别是:感性层次、有限精神层次、超验层次。③而古典诗意一般指的是诗意的超验层次,也就是说这种高层次的诗意存在是超出人类有限的生活经验的,是对神性的感应和召唤。而我们现在提出的新诗意其实可以认为是诗意的有限精神层次,这一层次的诗意以凸显人为根本的精神,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赞美人的力量和生活。
“你向神灵诉说,但你们全都忘了一点:初生果实往往不属于终有一死的人,而是属于诸神的。唯当果实变得更平凡粗俗,更习以为常,它才归终有一死的人所有。”④荷尔德林的这句话也许能解释新诗意之于人类的意义。新诗意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入世的诗意,立足于世俗化的现实生活的,注重现实的呈现,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获取诗意。如果说古典诗意是一种澄明的敞开,是返回人类本源时感受到的一种“清明的空旷”,那么新诗意强调的则是一种可触摸的真实感,一种对现实生活切实的体验,一种对社会生活本源的追求和努力。
那么,古典诗意和新诗意作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感受,是如何借助歌这一媒介阐发的呢?诗意的阐发与文本的表达方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微妙联系?——这是笔者接下来要论述的内容。
二、 古典诗意与新诗意的表达方式
(一)语言与表达方式
诗意作为一种审美的存在方式在文本中的抒发很大程度上要借助语言。语言是人类切近存在物本质时由人的类比思维产生的符号,是存在物的一个对照,所以语言的存在是解蔽的。语言让存在者敞开,处于一种无蔽的状态。海德格尔认为这样一种对遥远之物的道说便是宽泛意义上的诗。诗将遮蔽、隐匿的事物显示出来,使人到达一种澄明的敞开域,诗意境界的抵达可能会借助语言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基础的语文教育中,叙事和抒情常被认为是一种并列的表达方式,叙事侧重叙述事件,抒情旨在抒发情感。但事实上,在诗歌借助语言表达阐发诗意的过程中,叙事和抒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傅修延在《中国叙事学》中认为“叙事”是一个卷入因素与涉及层面更多的能指,“抒情”实际上附丽于“叙事”之中,两者之间为“毛”与“皮”的关系。在诗歌表达中,叙事和抒情往往都是共时性地存在着,只不过或隐或现,各有侧重。赵毅衡教授的“广义叙事学”的构想给出了叙事的两点定义:一是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二是此符号链可以被另一主体理解为具有事件和意义的向度。叙事作为一个多层面的能指,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不仅在传统的叙事文本中发挥作用,对诗意的阐发也起着重要作用。
接下来,笔者将以苗族民间歌谣和鲍勃迪伦的歌词为例,探讨叙事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诗意的阐发。
(二)叙事对古典诗意的阐发——广西苗族民间歌谣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皆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光潜认为文学起源于“诗乐舞”,而周作人认为“歌谣原是方言的诗”。所以我们可以从民间歌谣这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中追溯诗意的阐发与表达方式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究叙事何以能成为新诗意的重要表达方式。
在廣西苗族民间歌谣中,对世界的建构往往是叙事为主抒情为辅,对现世生活的关注则是抒情为主叙事为辅。苗族民间歌谣从曲调上划分,有古歌、酒歌、果哈调、呼勾调、开声歌、山歌拉木歌、季节歌、迎客调、哭嫁歌等数十种,从内容上划分有古歌、仪式歌、劳动歌、时政歌、酒歌、情歌、谜语歌等。其中苗族的古歌是指苗族古代先民歌唱宇宙诞生、物种起源、开天辟地、民族大迁移等为主要内容的歌谣,苗族古歌往往借助宏大叙事的方式,表现出原始人民用强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感受力解释这个世界的智慧。比如在苗族古歌《顶洛田勾》中就叙述了世界产生的过程,其中有一段写到:
枕海阳生一蔸大枫树,
根须拖到阁埃阳,
树梢长到天上,
大北风吹倒了大枫树,
树根翻到山槽底,
树干横在山坡上。
树根浸在水里给石膏鱼 蛋,
树梢又发芽了。
树干的蛀虫变成两只蝴蝶,
蝴蝶飞进岩洞里生了五个蛋。
有一个蛋养出月亮,
有一个蛋养出太阳,
有一个蛋寡去了,
有一个蛋生个又毒又丑的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羊卡。
用红水染的一个蛋生出顶洛,
顶洛五万年不死。
矮岭做他的凳子,
高山做他的吃饭桌。
他戴的帽子是有刺的花做的。
他讨了三个老婆:
一个是寨上的,
一个是水头的,
一个是海上的。
《顶洛田勾》的这一段叙述了太阳和月亮的产生,为后面七个太阳的诞生做铺垫。从单纯文本上来说,这段歌谣是淳朴而粗糙的,我们很难感受得到这段歌谣与文学意义上的诗意有何联系。但是这段歌谣表现的是一种“万物有灵”的意识,苗族先民以淳朴的生命意识和强大的感受力赋予了万物生命,在他们眼里天地万物都是有灵的,就连日月也是可以孕育出来的。先民的这种世界观显然是由自身推及到世界的建构,这种神人同构的世界观其实就是维柯《新科学》中提及的“诗性智慧”的一部分。在《新科学》中,维柯认为“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①。维柯把这种原始人因为对世界朦胧的认识而产生的类比思维称为“诗性逻辑”。而在苗族古歌的叙事中,神人同构的意识其实就是来自这种诗性逻辑的延伸。当原始人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切时,“在无知中把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②,而叙事的表达则承载了原始人类对世界的逻辑。他们通过叙事的表达方式,将自身存在的逻辑类比到世间万物,于是便出现了古歌中人格化的“太阳”“月亮”等。也就是说,在苗族古歌中,苗族先民用叙事的方式建构起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种“认知”很大程度上不是“事实”,而是他们的意识——对神性的渴望和对永恒的追求。所以苗族先民通过叙事阐发的诗意其实是“古典诗意”,是苗族先民在建构他们意识中的世界时感受到的精神的圆满和宁静。
然而苗族歌谣中的劳动歌、酒歌等与现世生产活动紧密联系的歌谣,却主要以抒情的为主,即使有叙事,也是为抒情而服务。也就是说,在涉及世俗生活时,苗族先民习惯通过抒情的方式表现人们的主观感受。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日常生产生活劳动中,直抒胸臆的歌谣有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比如苗族拉木歌《拉山》中反复出现的“嘿呷辣麻,嘿呷辣麻!”就是拉山时候的号子声。另一方面,在农耕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简单淳朴,个人意识也越来越发达。而抒情作为个人意识的直接产物便成为人们表达主观看法的主要载体。
从苗族民间歌谣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可见,在最初的文学样式中,通常会通过叙事承载原始人的“诗性逻辑”,从而阐发古典诗意。但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往往通过抒情来抒发。
(三)叙事对新诗意的阐发——鲍勃迪伦作品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古典诗意渐渐失落,新诗意应运而生。向内的抒情是建立在主观感受上的,然而新诗意却是立足于纷繁复杂的世俗生活的,这就要求与之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可以开拓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在现代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下,事态与事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比直接的抒情更具张力。由此,叙事成为新诗意表达的重要手段。
2016年10月13日,美国音乐家鲍勃迪伦以民谣歌手和摇滚歌手的身份获得了2016年度诺贝尔奖,瑞典学院给他的颁奖词为:“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鲍勃迪伦以一个歌手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诗意作为一种审美存在方式,其阐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歌曲作为一种古老的方式,更是阐发诗意的一种重要方式。抛开鲍勃迪伦歌曲的旋律的音乐性不说,他的歌词不管是从文本表现形式还是语言内容来看,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笔者将通过对鲍勃迪伦歌词的分析,解读“新的诗意表达”,并由此探究新诗意与叙事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阐发的。
鲍勃·迪伦(Bob Dylan) 于1941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希宾(Ribbing)镇。迪伦前期的作品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1962年,美国黑人民权斗争从南方扩散至全国,迪伦创作了《答案在风中飘》;1963年,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影响下创作的《大雨将至》成为美国民谣史上的经典之作;1963年8月,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前的民权运动大游行上,迪伦用一首《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表明了他的立场;1964年,他用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反抗一切旧制度传统;1965年,在新专辑《回到根源》中,迪伦甚至将政治、宗教、人生、爱情等多个题材都融合到歌曲中。直到1966年,双唱片专辑《美女如云》的出版,标志着鲍勃迪伦成为民谣复兴运动的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张专辑起,鲍勃迪伦歌词中抒情诗词的连贯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丰富内涵的意象的叙事。
通过对鲍勃迪伦音乐发展的梳理可以发现,鲍勃迪伦的音乐发展始终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历史相缠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黑人民权斗争到古巴导弹危机,从对旧制度的反抗到引领美国青年思潮的转变,鲍勃迪伦的作品一直都是立足于社会现实,于现实的纷纷扰扰中寻求存在的意义。鲍勃迪伦的歌词中是具有诗意的。但这种诗意并非古典诗意,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新诗意。鲍勃迪伦歌词中表现的诗意不再具有神性的色彩,而是撕裂的、残缺的、灰暗的,即使在这些残缺中也存在着对完满的追求,然而这种完满已经不再带着神性的色彩。鲍勃迪伦的摇滚乐歌词的核心内容,就是号召人们反抗压抑人性自由的美国社会,鼓励人们自由地享受世俗生活的欢乐和爱欲。60年代的美国社会是一个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物化”,人的心灵在现代社会过度成熟的制度文明框架中负重前行,所以鲍勃迪伦的歌词对人的心灵的解放是很有必要,而且极具现实性的。
在鲍勃迪伦的作品中,不乏抒情性的作品。但是其真正深刻的、具有新诗意的作品,更多地是借助了叙事的表达方式。1963年创作的《大雨将至》被认为是暗讽古巴导弹危机而做。在这首歌的歌词中,鲍勃迪伦放弃了以往的那种连贯的一气呵成的抒情方式,通过叙事来营造出诡异恐惧的情节。但与传统的叙事方式不同,鲍勃迪伦在叙事中加入了形形色色的意象,这些意象割裂了叙事原有的连贯性和序列性,使得整首歌词的叙事衍生出多层的含义。比如在歌词的第一节:
喂,你到哪儿去了,我的蓝眼睛的儿子?
喂,你到哪儿去了,我亲爱的年轻人?
我在那十二座烟雨迷蒙的山脚下迷了路
我连滚带爬地走过六条高速公路
我走进了一片悲伤的森林
我走出森林又遇到了一打死亡之海
我走过一万里路,却总是走不出坟墓
那猛烈的、呼啸的、急骤的、疯狂的、
那瓢泼般的大雨将要来临
《大雨将至》的第一节通过叙事描写了一个迷路的年轻人。但是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的意象——山脚、高速公路、森林、死亡之海、坟墓,却是匪夷所思的。这些互不兼容的意象通过叙事共同营造了一种大雨将至、黑云压城的氛围,这是抒情所不能达到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認为这是因为鲍勃迪伦受到了现代诗歌的影响,将民歌与现代诗歌结合在一起。现代诗的影响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更直接的转变源于新诗意的阐发对于表达方式的要求。如前文所说,新诗意是一种立足于世俗生活的审美方式,而世俗生活的庞杂、纷繁、残缺很难直接通过抒情的方式表现出来。欧阳江河在《叙事性诗学的源起和倾向》中提出,“抗议作为一个诗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为它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①。与抒情相比,叙事更能容纳“异质”性的事物的敞开,通过对事件的叙述引申出多维度的涵义,从而表现出一种历史纵深感和现实穿透力——而这即是新诗意的核心所在。
三、新诗意与叙事的相互作用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见,叙事与诗意的相互作用可以总结为这三个阶段:最初,原始人类凭借其丰盛而强大的想象力和感受力,用语言把这大千世界表现出来,通过叙事赋予了世界“诗性逻辑”。而当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日渐明晰之后,阐发神性和永恒的“古典诗意”渐渐隐没在抒情的表达中。现在“新诗意”的表达又需重新借助叙事的表达使其与社会现实相关联。所以追寻叙事与诗意表达的脉络,可以发现叙事自始至终都作为一条或隐或现的线索,支撑着诗意的阐发。
但是原始人类阐发诗性智慧的叙事与阐发新诗意的叙事有所不同。首先,表达“古典诗意”的叙事往往是过去时态,表达新诗意的叙事则往往是现在进行的时态。中文的表达对时态的要求没有这么明确,但是叙事让笔者在上文阐发叙事与古典诗意的关系时,引用了《顶洛田勾》中关于太阳和月亮的产生过程的内容。其实不仅是《顶洛田勾》,在苗族其他古歌中也有相似内容。
新诗意是现代社会语境下的立足于现世生活的一种审美感受。它是妥协的诗意,放弃对永恒的渴望而转向现世的刹那芳华。但同时,它又是真实可感的诗意,在世俗的龃龉和对立中产生意义感,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新诗意将对神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人的力量的关注。新诗意的出现说明人类不仅是从实际操作中脱离了上帝,而且潜意识深处也放弃对神性的渴望,将对神的依赖感转移到人自身,从自身的生活、人类的生存中获取满足感和意义感。
综合上文分析可知,在广西苗族民间歌谣中,人们通过叙事抒发以对神性和永恒的追求为特征的古典诗意,以此构建出原始人意识中的世界,但是对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歌谣中多采取抒情的方式。而在鲍勃迪伦的歌词中,则以叙事的方式来承载一种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新诗意。其实不管是新诗意还是诗意,都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和感受体验而存在,叙事的过程其实是使其“及物”的过程。叙事让诗意与现实的事物相关联,使得人的感受更切近“物之本质”。
新诗意借助叙事而“及物”,通过文本叙事达到一种敞开的状态。如果说古典诗意凭借语言而敞开,那么新诗意则是凭借叙事而敞开。叙事凭借对事件序列的协调,开拓出广阔的表达空间,延伸出多维度的诗意空间。特别是在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个人化的抒情在混沌的事态前显得太过单薄,难以蕴含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叙事对新诗意阐发的关键在于,叙事是通过故事的厚重来间接抒发现代人不可名状的感情。换句话说,现代人特殊的精神体验很难再通过抒情这种直接的意识转换来表现出来,而需要将其揉碎在事态的起承转合中,才能感受到那转瞬即逝的“光晕”。
荷尔德林在后期曾经作过一句有名的诗:这并非稀罕之事/犹如那晚餐时分/鸣响的钟/为落雪的覆盖而走了调。语言是解蔽的,然而也是遮蔽的。也许所有表达方式之于古典诗意或新诗意都只是那纷纷的落雪,但如果那落雪的覆盖可以产生另一种不同的灵韵,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参考文献:
[1]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丁来先.诗意人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 〔意〕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 陳日红.广西苗族歌谣研究——以融水苗族歌谣为中心[D].暨南大学,2014.
[5] 孙基林.“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诗学的源起与倾向[J].山东社会科学,2013(8).
[6] 张福海.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D].山东师范大学,2011.
[7] 夏斯翔.文学诗意初探:从发生起源到要素解读[D].华中师范大学,2014.
[8] 魏天无.从抒情性到叙事性:诗歌“知识型构”的转换[J].同济大学学报,2011(5).
[9] 陆修远.鲍勃迪伦摇滚艺术价值探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D].浙江师范大学,2010.
[10] 顾祖钊.论文学语言的诗意逻辑[J].文艺理论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