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星星
安德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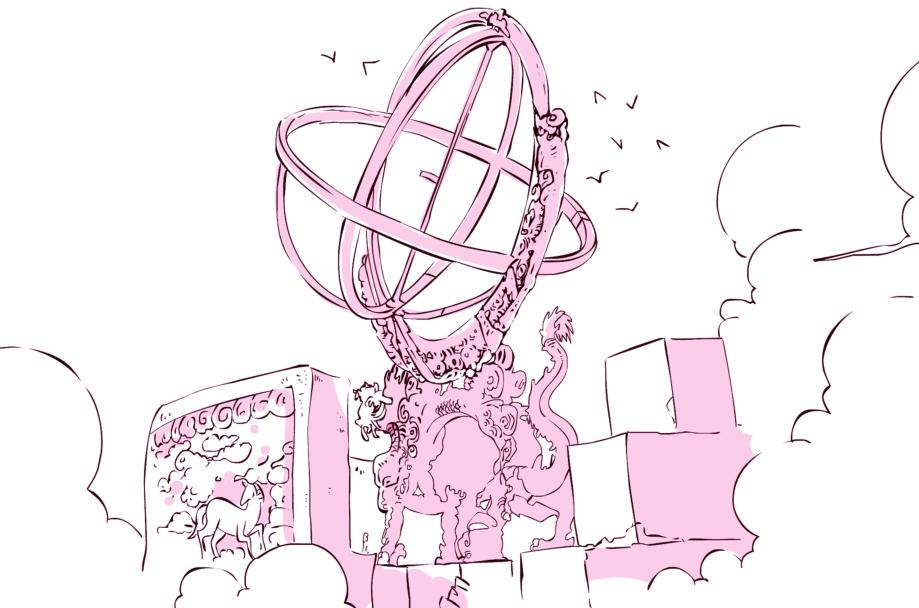
第四节车厢 精奥异人
一
明朝和清朝遗留下来的老北京城,本由平面呈“凸”字形的内、外两城所组成,开有“内九外七”共16座城门。如今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及德胜门箭楼尚存,其他城门均不复存在,只保留了原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标志。但在这16座老城门之外,还多出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这三个听起来也像是城门名称的地名混杂其间。明清时期,老北京城的城门不是简单的出入通道,而是设计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每座城门,均由城楼、箭楼及连接二者的瓮城所组成,瓮城之中,形成封闭的空间,敌军一旦闯入,即被“瓮中捉鳖”。
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都不具备上述设施,它们只是在清朝灭亡之后,为了交通方便,交通部门陆续在老城墙上开辟的通道而已。复兴门和建国门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当时,建国门名叫启明门。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之下,1945年11月9日,政府将这个城门改名为建国门。
如今的建国门地区,霓虹灯闪烁着现代气派,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动着都市的繁华。然而,在建国门地铁站的西南角,却矗立着一座略显神秘的建筑——古观象台。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东侧还保留着一座高台。这里距CBD中央商务区很近,脚步匆匆的都市白领们天天路过这里,不经意的回眸间他们总能瞥见这个景点,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院子的用途,更不会知道它里面都有些什么。
其实,这里就是中国古代的皇室派专人夜观星象的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在元朝被称为司天台,到明清时则被称作钦天监。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最终被定名为古观象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二
时光回转到1713年6月,明安图在钦天监毕业,被留在钦天监的时宪科担任五官正这一职务。这相当于现在的留校任教,多么让人羡慕啊!
钦天监,官署名,是我国古代的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由于历法关系农时,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因此钦天监正的地位十分重要。秦、汉至南朝,太常所属有太史令掌天时星历。隋秘书省所属有太史曹,炀帝改曹为监。唐初,改太史监为太史局,属秘书省。乾元元年(758年),改称司天台。五代与宋初称司天监。
公元1279年,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在如今的建国门地铁站的西南角这个位置建造了司天台,用于观测星象。这个司天台也就是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的钦天监。钦天监的正殿名为紫微殿,在中国的传统中,紫微星为帝星。郭守敬当时在司天台的贡献,是得到了忽必烈的授权,派出大批人马在全国二十七个不同地理位置进行太阳升落时间的观测,史称“四海测验”,由此整理出测定不同地域“真太阳时”的技术,亦得出回归年为365.2425天的精确数字,这与现行天文历法完全一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后来他基于此废除了漏洞百出的旧历法,推出了无比精确的《授时历》,比同样精度的全球现行《格里高利历》(即阳历)早推出三百多年。
明代沿用的历法计算方式误差较大,不利于王朝的统治。恰在此时,传教士带来了新历法。明初设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后改称钦天监,有监正、监副等官,有西洋传教士参加工作,任务仍然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明朝官方的历法《大统历》基本上就是对郭守敬《授时历》的翻版,只做了很小的改动。明朝末年,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西洋传教士开始与中国皇家密切接触。来自西方的天文学、数学被引入钦天监的工作,东西方天文学开始交汇、融合。在玄学领域,对东西方交流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传教士有两位,一位是清朝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他把《易经》带到了欧洲并疯狂宣传,其中的阴阳二进制思想启发了数学家莱布尼茨,后来他发明了计算机的雏形。另一位则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他竟然加入了中国皇家的钦天监,成为跨越明、清两代的钦天监最高长官。汤若望于1622年进入中国传教,他有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明朝的钦天监推算日食时间失败,崇祯皇帝命令官员徐光启重修历法。徐光启在1630年调汤若望进京,协助制定《崇祯历书》。汤若望虽是外国人,但因他掌握了天文计算的独特技能,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钦天监。

1644年,多爾衮率清军攻占北京城,中国面临改朝换代。汤若望身为钦天监的老大,挺身而出上书请求保护钦天监,获得清政府的同意,钦天监在一片风雨飘摇中保留下来,汤若望也因此成为跨越明、清两代的国家首席天文官。他作为外国人,免不了被很多保守派的中国本土势力所嫉恨。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杨光先的官员带头设计陷害汤若望,给他定了死罪。全国的传教士亦都被押至北京接受审讯,大祸临头。结果在审判的最后关头,北京城突然发了一场蹊跷的强烈地震,妖气逼人。这场地震把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吓坏了,她马上出面干预,汤若望这才得以死里逃生,但是钦天监仍被重创,几名中国官员被处死,数十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汤若望不久后也病死了,就葬在另一位知名传教士利玛窦的墓旁边。杨光先的势力接管了钦天监,并试图恢复旧历,但他们学艺不精,制造出来的东西漏洞百出,贻笑大方。杨光先实际上是鳌拜的人。康熙皇帝成年以后,对鳌拜十分不满,立马从钦天监下手追查。康熙找到汤若望生前的助理——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让他与杨光先现场比试天文知识与技术。结果毫无悬念,杨光先被南怀仁完美击败。康熙罢免了杨光先,以南怀仁为首的西洋传教士重回钦天监管理政务,中国的天文学亦因此得到继续发展。南怀仁在康熙的授命下,为钦天监建造了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等大量精密仪器。
钦天监的最高长官是监正,监正有两种,一是不懂科学、挂名食禄的人,一是精通天文专业的,是实际上的业务负责人;其次为监副。钦天监下分时宪科、天文科、漏刻科和回回科等四科。近代,钟表传到中国以后,“漏刻”逐渐不用了。因此,漏刻科后来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回回科研究的是元明时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天文历法,但因为不切合中国实际,而且当时其内容已经陈旧,所以在1657年回回科就被撤销了。时宪科主要负责编订每年颁发一次的历书《时宪书》和研究“日月交食”。时宪科的最高长官是五官正,五官正共四人,满族二人,蒙古族二人。五官正的工作,除去日常工作外,还要把用汉文写的《时宪书》翻译成满文和蒙文,以便向满族和蒙古族颁发,供人们使用。此外,時宪科还有春、夏、中、秋、冬官正各1人,秋官正,汉族1人;五官司书,汉族1人;博士,满族1人,汉族2人,蒙古族2人。
钦大监是清政府专门管理和研究天文历法的中央机构,也是培养天文历法人才的学校。这里是天文历法人才荟萃的地方,其中有著名的中国天文历法家,也有掌握近代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在那里任职。这里收藏着丰富的天文历法以及数学等图书和资料,还设有当时国家级水平的各种天文仪器。这些为明安图在从事天文历法的学习和研究时,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料和观测仪器,他还可以直接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近代科学知识。
这种环境对明安图的学习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明安图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把书本知识和对天象的实地观测结合起来,进行了学习和研究,使自己的学业日有所进。当时人们称道明安图的学识——“精奥异人”。
三
明安图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八年,一直在钦天监任职。他热心于本职工作,认真观测天象和编制《时宪书》,使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与日俱增。在天文历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明安图回到家就会跟家人一起,动手做蒙古族的美食。这一天,明安图想起了蒙古族的独特食品——炒米。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蒙古族的日常饮食中也日渐增多,最常见的是面条和烙饼,还有用面粉加馅制成的别具特色的蒙古包子、蒙古馅饼及蒙古糕点等。贤惠的妻子一听明安图在念叨炒米,便放下手中的活儿,起身亲自去给他做炒米去了。
愉快的家庭生活,家人的全力支持,给明安图的工作很大支持,他可以全心投入工作,这为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帮助。
明安图在钦天监任职整整51个春秋。其间,前47年里他一直担任钦天监时宪科的五官正。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他已经68岁了,由于赴新疆测绘任务的需要,他才被破格提升为钦天监的监正,全面执掌钦天监的工作。此后,他仅当了为时5年的钦天监最高长官,就因为健康状况离职了。
当年明安图是在钦天监时宪科里任职。他所担任的五官正一职,工作内容是非常繁重和复杂的。明安图以勤奋的工作态度、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技艺,几十年如一日,年复一年地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如同小时候,天天听着额吉唱蒙古族的民歌,也不会觉得厌烦一样。工作之余,明安图也会唱额吉教他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调节自己的生活。朦胧中,明安图仿佛又听见了额吉在哼唱那首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情的长调民歌《富饶辽阔的大草原》,歌声悠扬,婉转动听,明安图就是在额吉的歌声中慢慢长大的,额吉的歌声也是明安图的精神食粮,给他力量。
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的美称。蒙古族的民歌可分为长调和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东部的牧区以及阴山以北的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能很好地反映出草原的辽阔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据考证,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历史相当悠久。短调民歌主要在内蒙古的西部、南部的半农半牧区流行,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
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的内蒙古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在晚年被提升为监正的五年当中,明安图作为一名精通专业技术的长官,除了负责钦天监的全面工作之外,其所从事的科学技术活动,大体仍是他任五官正时的那些工作内容。
明安图经常性的本职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参与一年一度刊出的《时宪书》的编制工作
《时宪书》是一种历书,俗称黄历,也叫皇历。其中着重记录有关天文历法和农时节气的内容,这些对指导生产特别是农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书中有宣扬皇恩浩荡及封建道德等忠君思想,还有宣传迷信的“宜忌”“宜迎”等内容,如某日忌出行、某日宜祭祀、某日某时在何方迎财神或喜神等。当时,皇帝是非常重视《时宪书》的制定工作的。钦天监首先要把制定出来的《时宪书》样书呈给皇帝审批。经过皇帝审批之后,正式定稿印刷,然后将正式出版的《时宪书》颁行全国。

明安图从事这项工作的最早记载,是在《大清康熙六十一年时宪法》上,有“食员外郎俸五官正明安图”的字样。在这以前的《时宪书》上都没有他的署名。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钦天监任职的最初几年,即奉命参加了编写《律历渊源》一书,似乎在那段时间里他还没有参与编制《时宪书》的工作。其后,在历年的《时宪书》上,几乎都有他的署名,直至他离开钦天监那年所编成的《大清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时宪书》上,也还有他的名字。可见编制《时宪书》一事,是他一生当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二、参与汇制题本的工作
明安图要经常把他们观测到的各种天文现象的结果汇制成题本进呈给朝廷。这也是他经常性的业务活动的内容。在这些题本中,除进呈上述《时宪书》样式的题本之外,大量是预报“日月食”或“观候事”的题本。这类题本上呈的次数很多,有时进呈之频,一年之中竟是月连月,甚至一月之内日连日。这项工作既是琐碎的,又是科学性很强的,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错误。要做好它,非勤奋精明之人,是难以胜任的。就预报日月食来说,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能够把这种预报作得准确无误,确实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当时君主专制的环境下,要担负着很大的风险。
雍正七年正月十七日(公元1729年2月14日),发生了月食。在这次月食发生之前,在明安图的主持下,他们共同进呈了两次预报月食的题本。在题本中,预报了这次月食在北京地区的初亏和复圆的时刻,同时绘制了在北京地区月食的起复方位图像,还预报了在各省月食初亏先后的不同时刻。可见要准确地预报一次月食,其中涉及许多科学性和技术性的问题,这都是要花费很多精力的。明安图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准确地预报日、月食以及其他一些天文现象的。由于他技术纯熟和工作细心谨慎,几十年中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错误,大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钦天监呈请清政府编制《日躔表》《月离表》二表。《日躔表》和《月离表》是关于太阳运行(日躔)和月亮运行(月离)的天文表。一般所说的日躔、月离都是指日月在黄白道上的位置。钦天监建议由西洋人戴进贤、徐懋德负责挑选熟练人员,详加校定整理。戴进贤不久编出了《日躔月离表》。这个表只有钦天监监正戴进贤、钦副徐懋德和明安图三个人能够使用。戴进贤的《日躔月离表》之所以只有上述三个人能够使用,其他人都不懂,最主要的原因是该表没有解释说明推算的方法,因此1737年5月,原任史部员外郎的顾琮再次向清政府提请修改《日躔月离表》和《历象考成》一书,并推荐戴进贤为总裁,徐懋德、明安图为副总裁,这项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三、参与将《时宪书》翻译成蒙古文的工作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所制定的《时宪书》是面向全国的,除了汉文版之外,还要翻印成几种民族文字的版本,颁发到少数民族地区。明安图出身于蒙古族,将《时宪书》翻译成蒙古文的任务,就成为他责无旁贷的一件事。由于明安图对这项翻译工作做得出色,乾隆皇帝曾赐他“翻译进士出身”的荣誉。
明安图一生的时光和精力,几乎全部都是在钦天监里度过和耗尽的。其间虽然有几次奉命调出参与编书和测绘地图,在这些方面所做出的成绩甚至超越了他的本职工作,但那些工作对他来讲毕竟是暂时性的工作。
明安图常年在钦天监里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本职工作,是一名勤于本职工作的天文官。虽然关于他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不见记载,但从实践角度上看,他在天文歷法方面所从事的活动,确实为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贡献了力量,他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