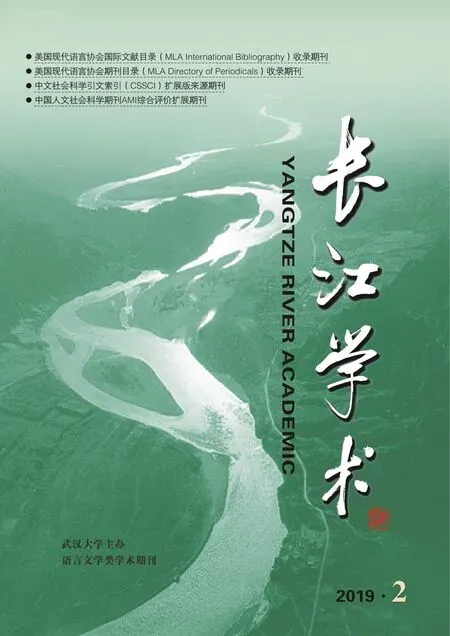现代“拟古主义者”:再论“旧派诗人”与其继承者
——论《现代“拟古主义者”:1900—1937中国诗词传统的延续和创新》
〔澳〕寇志明著 卢 姗译
(1.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 悉尼 NSW 2052;2.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现代“拟古主义者”:1900—1937中国诗词传统的延续和创新》(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1900—1937)(哈佛东亚中心2013年版)的杰出之处在于:以百科全书式的广度及深度,对20世纪有关清末民初旧体诗写作的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以往时代,一个学者想取得这样的学术成果需要耗费毕生的精力,而吴盛青在她的第一本著作中就做到了。
这部专著并没有墨守成规地套用学术界流行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恰恰相反,它极富创造性和生命力。它的价值远远大于向其他人文领域的学者们展示西方文学理论对于中文文本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挑战了20世纪的普遍观点: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和倡导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旧体诗便失去了它原本的地位和意义。
吴盛青研究的是在20世纪初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夕这个时间段里,词和诗的新变化。她关注的时间段是民国时期,这恰好与我在《微妙的革命》中所关注的时间段互为补充。我在《微妙的革命》中重点介绍的是清末民初(1860—1919年间),被当时的批评家所看好的那些旧体诗作。我研究旧体诗的出发点其实是探讨鲁迅的前人们作诗时循旧和创新程度究竟孰轻孰重。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想法渐渐变得相对次要,因为我发现,通过旧体诗作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相反,吴盛青的研究似乎更加针对胡适(1891—1962)和陈独秀(1879—1942)两位提出的带有宿命论意味的观点:奄奄一息的旧体诗是不能完全表达这个日新月异又复杂多变的世界的;从本质上来说,旧体诗总跟声名狼藉的满清王朝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她还在序言中提到:我假定一个“现代拟古”的紧张关系,以突出现代文化结构矛盾和对立的性质,但同时也凸显了它们彼此之间互相融合与改造的能力。
以“现代拟古主义者”的角度看待问题是一种辩证思考,不考虑现代性批评范畴的特殊性,不照搬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在这个看似矛盾却又互相依赖的结构中,我把“传统”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领域,借此探索“现代主义者”和“拟古主义者”之间动态的互相作用和对峙冲突。更确切地讲,在高度美学化的形式和实践中去实现“传统”的意义。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文学形式和文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别出心裁的创新。当然,这里的“现代”是一种描述范畴和批评工具,更是一种文学价值的彰显,而并非论证的目的。(第9页)
换句话来讲,吴盛青试图将我们带出传统和现代的二分主义,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为什么她选择使用“拟古”这个术语,或者为什么叫诗人为“拟古主义者”?我认为,他们的创作理念是符合当时中国诗歌主流的,而当时挑战旧体的新诗只不过是一个末流,日本学者仓田贞美将其形容为“既成诗坛”。在周策纵看来,只有新诗的支持者才将新诗的“胜利”视为文学史上积极和进步的行为。我认为,吴盛青的解读中最大的潜在失误是:她质疑胡适和陈独秀创造的文学“等级”,这个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恰恰默认了等级本身的历史存在。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使其更具有法理性。但是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一代人文学者对文学史认知的集体记忆。
吴盛青认为,20世纪初期旧体诗的创作为诗人们提供了文本和社会空间。这个空间让诗人们反思文学主体性、文学想象以及文体创新,从而使得诗人们能够重新确立集体认同感,并且加深文化记忆。这些观点固然不错,但我认为,旧体诗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加权威的文化话语权,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这样的话语权显得愈发重要。当然,其中也不能排除民族主义和精英文化主义的影响。
这本著作由三部分构成,每部分又细化为两个子部分。全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某些部分还有主题性的考量。第一部分讲的是“诗之哀”(或许称“失之诗”更为妥当),考察的是作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的古体诗。第一章关于词的论述主要围绕着庚子事变展开:八国联军镇压义和拳运动,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任由北京落入洋人手中。她对这个历史事件所触发的系列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鹏运(1848—1904)和朱祖谋(1857—1931)这两位重要词人身上。凭借精湛的翻译功底,吴盛青将书中所有的古典诗词都做了中英双语对照,并通过细腻而又深入的讨论,向我们展现了“比兴寄托”这个传统的写作手法是如何让一个貌似浅白的爱情悲剧拥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意蕴,进而成为岌岌可危的国族尊严和行将就木的文化的时代寓言的。(第57页)
第二章名为“激进的拟古主义:陈三立对文化危机的回应”。此章从晚清诗人被笼罩在强大的传统阴影之下这个事实说开去。诗界革命(如黄遵宪)和同光派(陈三立、郑孝胥等)创作的诗,挑战了形式上的制约和所谓谬误,尤其当涉及新的西方文学命题的时候(第110—111页)。这是一种尝试,它们向日益僵化的旧体诗注入了一定的新的活力。在我看来,这一主张或许适用于对诗界革命的分析,对于“同光体”诗人却不一定适用。我认为,同光体诗人的创新意义在于主题上而不是形式上,虽然也不乏例外。他们利用传统语汇来构筑形象,埋设隐喻,并用传统的文学形式对其加以呈现。吴盛青接下来的论证似乎也都是在继续印证这个观点,譬如接下来这一段分析就颇有洞见:
陈三立最喜爱用“劫灰”这一意象,这个意象的原始概念缘于佛教,指的是毁灭人世间的烈火熄灭后的余烬。“劫灰”是中国诗歌中的一个常见意象,但是在这里,我们得以窥见陈三立对于当时惨淡的文化现状颇为悲观的态度。陈三立写道:“嫦娥犹弄山河影,未辨层层是劫灰。”劫灰落下,一层一层地交覆铺叠着无尽山河,这苍劲的画面看似具有无限张力,实则饱含失落惆怅。“劫灰”在这里,其实指的是经年累月的战争和骚乱侵蚀下,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同时也可以看做诗人精神痛苦的主观映像。关于王国维的殒殁,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对此,陈寅恪一语道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如此而言,其评论可能也适用于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的遭遇。巨大的社会变革颠覆了传统的文人价值体系,陈三立不得不接受中国没落的事实。但他坚持用文雅的诗歌语言、修辞和形式进行创作,以体现其儒家的道德意识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懈追求。理想的幻灭、危机的意识以及各种充斥着的充满张力悖论的学术理念,都使他的诗作中的抒情变得更加强烈深刻。(第129页)
陈三立通过传统的语言和艺术形式,向当时的读书人很好地传达了这种不安、痛苦以及对传统秩序消亡的忧惧。所以,胡适的反对派、留学哈佛后回国的胡先骕(1894—1968)等人,把陈三立看做中国20世纪头30年里最伟大的诗人。
吴盛青对中国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了解甚深,因此会不自觉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到了晚清宋诗又主宰了诗坛这一观念(第114页)。在《微妙的革命》中,我曾经质疑过这个观点,我认为晚清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时期,许多流派时而相互冲突,时而又彼此重叠,就像拟古派和中晚唐诗派,但总体来说,并未形成一方独大的局面。吴盛青在著作中强调宋诗的哲理性和智识性。这些特性十分契合19世纪知识界十分流行的实用主义趋势,包括经世致用的理念,以及可以体现新的自我身分和社会典范的道德观念。(第115页)
相较而言,唐诗大胆张扬、丰富多样的意象,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吉川幸次郎曾将唐诗比作红酒,宋词比作茶(第117页)。吴盛青认为,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严峻形势,势必要求知识分子们面对现实时持有无比严肃的态度,于是乎,宋诗顺应时代重新成为主流。其他的一些当代学者也秉承此观点。但在我眼中却并非如此,我认为当时诗坛呈现的是百家争鸣般的盛景。我怀疑他们同那些鼓吹白话文胜利的人一样,或多或少受到了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晚清诗歌编选者的影响。这些学者包括陈衍(1856—1937)、钱基博(1887—1957)、钱仲联(又名钱萼孙,1908—2003)以及钱钟书(1910—1998)。与此同时,从吴的行文中也可以感受到该学术脉络的影响。
钱仲联几乎是单枪匹马在中国大陆开拓了清诗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十年里,学界对陈三立以及晚清诗歌的学术研究兴趣日益高涨。因此这本书也囊括了中国本土最近的学术成果。(第 114页,注 19)
通过这种学术路径,该书展现了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并在专业领域中得以脱颖而出。但是更准确地讲,钱仲联的成就是重建和复兴了晚清诗歌的研究。他的学生,比如马亚中和魏中林继承了这一传统。我曾希望可以挑战这个主流观点,但他们依然支持并不断强化这个观点。
陈三立的诗作《晓抵九江作》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在一艘满是酣睡旅客的船上,唯独诗人是清醒的。有趣的是,吴盛青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借用了鲁迅的“被一众酣睡者所环绕”这一经典形象进行印证。这个形象,生动而又深刻地表现了晚清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景象。
“沉睡者”的形象在晚晴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在陈三立写完该诗的十年后,王国维用“鼾声四起斗离离”来形容自身的孤独。鲁迅著名的比喻:“铁屋”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和“许多熟睡的人们”,也早已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而陈三立早在鲁迅之前就已经创造了“沉睡者”的形象。这并不是要轻描淡写鲁迅的创造性,而是为了说明“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晚清时期是十分流行的。(第141—142页)
正如他的前行者和后继者一样,鲁迅确实接续了这个传统。吴盛青与我在各自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形象,在合适的人笔下,便会成为文学创作改进的工具。
《现代拟古主义者》第二部分讲的是“知性的诱惑”。开头便提到城市里诗社、词社逐渐出现并繁荣起来的现象。社员们用优雅的古体诗歌形式进行创作,化解动荡的社会秩序带来的内心不安,这样的表达方式内敛却也不失风流。而且,通过这样的形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系上了充满创造力的文化纽带。
现代中国文学史给清末民初的旧体诗简单粗暴地贴上了“阻碍社会进步”的标签,却忽略了旧诗创作的重要社交功能。第四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讲述了陈衍的诗词生涯。
陈衍是陈三立和郑孝胥的文坛诗友,他参与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加入了同光体圈子。通过梳理陈衍的诗歌编选和教学工作,吴盛青论述了他从旧式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巨大转变。(第221页)陈衍著名的《石遗室诗话》曾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和杜亚泉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除此之外,他还编纂了《近代诗钞》。陈衍在国学方面的成就无人能出其右,他也曾在许多当时看来较为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任教,其中包括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大)、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他编著的文学选集和文学批评,提升了同光体与新儒学家的学术地位,郑孝胥就是一个例子。郑后来担任了伪满洲国总理,以新儒家学说(譬如“王道”)来支持溥仪而掩饰日本人的所作所为。陈衍在得知此事后,遂断绝和郑孝胥的友谊关系,并将其作品从他所编的《近代诗钞》中删除。
吴盛青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学场域的概念,分析了陈衍是如何利用文选编者(例如他编纂的《近代诗钞》191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在台北再版)和大学教授的角色,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声望,从而继续影响如梁启超和钱钟书等后来的知识分子的。这一切都表明,陈衍是识时务者,与陈三立不同,他能够顺势而为,适应新的时代。与此同时,却也让人不禁质疑他所坚持的立场,比如“诗歌应当是独立无私的”这一观点暗暗契合了当时很多“新诗”倡导者的心态。(第224页)
吴盛青告诉读者,陈衍坚信修养诗性的前提是与世隔绝。他认为唯有如此,自己的情感才能找到恰到好处的抒发方式。她继续说:“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精髓就在于个体的表现力和独特性”,可是“‘清’、‘寒’、‘瘦’是旧时审美的常用词汇。”(第242页)如此,如果陈衍只是在新的时势下简单地强调和倡导这种旧的审美形式,那么他的“现代性”是从哪里来的呢?(第242页)相比而言,陈三立并不像诗界革命那样通过使用新词,也不像新诗那样使用自由诗体,而是通过新概念的表述方法和对诗歌进行重新定义设法达到“不俗”。(第243页)如同王国维,陈三立是在寻找一个形而上的艺术领域来应对传统语意系统的瓦解。(第243页)换言之,陈三立的审美观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尽管他最终可能拒绝了融入现代社会。然而,陈衍的现代性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不确定的,尽管他很顺利地融入了现代社会。这一对比,我们明显看得到诗歌创作为何在首位而批评总次之。
在第三部分“以古时之火点燃现代火炬:在时光中旅行的诗歌”中,吴盛青通过介绍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性理论,分析了女诗人作品中男性声音的使用和性别角色的扮演,比如喜欢异性装扮的秋瑾,还介绍了南社年轻的革命男诗人周实(1885—1911)创作时用的女性声音。(第267—276页)
在之后的第五章中,她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一位令人刮目相看、不落俗套的女词人——吕碧城(1883—1943)。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她就曾环游世界并提倡保护动物权益。而在此之前,她基本上被学术界所忽视。(第268页)
吕碧城出生于山西太原的一个士大夫家庭,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12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早在吕碧城9岁时就议定婚约的当地望族汪氏,在吕家遭遇变故后连忙退婚。家道中落后,吕碧城不得不离开家乡,只身奔赴天津。
凭借着一封阐述女子教育观点的信件,吕碧城得到了天津《大公报》的创办者、主编英华(又名英敛之)的赏识,成为该报的第一位女编辑,并开始发表诗作,从此在文坛初露头角。
吴盛青翻译了吕碧城1904年创作的《满江红》上阕,并评论道:“吕鼓励妇女扮演新公民的角色,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并直言女子解放当为民族复兴之第一要务。”
尽管吕碧城对秋瑾的牺牲倍感痛惜,但是她并不赞同秋瑾在政治方面的极端主义和排满立场。与她交往的社会名士中,不乏在事业方面给予她许多帮助的才子和高官,但她却选择终身未婚。
1920年,37岁的她前往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与美术,同时兼任上海数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两年后,吕碧城学成归国,翻译了《美国通史》和其他一些作品。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并在瑞士蒙特勒旅居了一段时间(1928—1933),用文言文为上海多家报纸和杂志撰写游记。吴盛青评论道:“她对帝国主义、社会不公以及种族歧视等问题都有极为深刻的见解。”(第285页)上海及其它大都市的读者对此类作品甚是喜爱,而作为如此现代化的女性,吕却在1930年代仍然使用文言文进行创作。对此,吴盛青在字里行间似乎表露了些许的诧异。(第289页)1929年,吕碧城代表中国在日内瓦参加了国际动物保护会议,1930年皈依佛门,并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翻译了大量佛经。
众多文豪对她的词赞赏有加。她父亲的友人樊增祥认为她的词能与李清照相媲美,钱钟书更是把她看作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第288页)她早期的作品弥漫着深邃的思乡之情,后期则转向歌颂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瑰丽奇景,所谓“向山的灵魂致敬”。(第309页)至此,她“摒弃了将女性当成玩物的描写方式”,(第315页)而注意在作品中强调女性作者身份。(第310页)在“文化时空的翻译”这一节中,吴盛青展示了吕碧城如何利用“怀古”来描绘欧洲和中国的名胜古迹,并且在具有强烈阳刚意味的文本空间中注入女性的细腻情感。(第316页)
吴盛青将吕碧城描写欧洲风景的词,拿来与康有为(1858—1927)和汪精卫(1883—1944)二人的词作对比,例如描写罗马遗迹的一篇,吴评论道:
康有为的诗境磅礴大气,充满了男性阳刚的雄心壮志,而吕碧城的词则围绕着自我和人世沧桑的周旋而展开,充满了女性的阴柔之美,不再像传统词那样仅仅表达男性的壮志难酬和感慨时光飞逝。(第322页)
引用的例子说明了他们的差异,但这是否也体现了豪放派和婉约派固有的传统差异?如果真是如此,抛开主题和背景,这些词又能有多少现代意味?事实上,在吕碧城同样以忆古罗马为主题的另一篇词作中,写到“十二世纪时,成吉思汗统一欧亚,罗马属焉”。吴盛青在其中察觉到一丝准文化霸权的气息。(第320页)吕作为诗人,其特别之处便在于能够运用传统譬喻的联想来描述异国场景,以及她拒绝将传统视为男性主导的话语,(第331页)从而在传统文体中引入新的性别视角。早期中国的留洋诗人们习惯用诗的形式记录见闻,吕没有遵循这一传统,而是特意选择用词来描写西方景象。吴盛青总结道:“吕碧城的词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汇的空间,在她的词中,传统中国文化与欧洲名山大川相互融合,此外,她还构筑了新的性别关系,这或许就是她作品最大的成就。”(第331页)很遗憾之前的文学史家们并没有给予吕应有的关注,而吴盛青著作的贡献之一便是重新发现了吕碧城。
第六章“炯炯赤蔷靡:古文形式与翻译”是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在其中,吴盛青探讨了中国诗人如何利用传统的形式来翻译西方诗歌(我认为他们拿捏得比较成功),创作了大量在当时很受欢迎的旧体诗,但这种尝试却因为后来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不幸中断。我想,这是因为国文课程并不包括这种用古文翻译的外国诗歌,新文化的权威者,拥护者们以及文选编辑们也将它们排除在经典之外。吴盛青告诉我们:“我对流行观点持反对态度,我认为不能单纯地将外国文本的归化翻译看做是不准确的翻译,而是应该先考虑到目标和现实操作的难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潜在的文学创新。文化内涵会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挪用和转化,原文和译文的差距之间也能迸发出新的火花。”(第335页)
在分析苏曼殊(1884—1918)翻译伯恩斯和拜伦的作品时,吴盛青意识到他使用了Roman Jakobson所谓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进行游移。与直接使用比喻不同的是,苏运用了“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手法,而“有的学者认为隐喻(metaphor)和“兴”的使用是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根本差异所在”。(第336页)
换言之,苏曼殊利用了吴盛青所说的“归化”方法,将诗歌原文的意思译成了中国古典诗歌。苏在翻译时更关注诗体的结构和语言的流畅性。(第339页)而离我们时代更近的其他译者,则更关注词义翻译的准确性。比如,把苏曼殊和袁可嘉(1921—2008)分别翻译的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作品进行对比,吴盛青观察到:“袁可嘉的白话文翻译,在意思和句子结构方面都十分接近英文原文。而这种印象的产生也是因为现代白话文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欧洲语言的句法和语体。”(第339页)因此当鲁迅呼吁改变汉语以使其表意更加准确的时候,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汉语已经开始改变了。
但鲁迅只是在翻译现代文学理论时提到准确性的要求,而苏曼殊则是在翻译诗歌;理论和实践终归有所差别。我们来比较伯恩斯1794年所写的一首歌第一节的两个不同版本的译文:
O My Luve’s like a red,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袁可嘉的翻译版本为:
啊,我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
它在六月里开出;
啊,我爱人像一支乐曲,
它美妙地演奏起来。
苏曼殊的翻译为:
炯炯赤蔷靡,
首夏初发苞。
恻恻清商曲,
眇音何远姚。
比起袁可嘉的译文,苏曼殊的译文更加精致和优美,袁可嘉的译文中直言不讳的部分在苏曼殊的译文中表现得更为朦胧。袁可嘉将“My Luve”翻译成“我爱人”,而苏曼殊用“赤蔷靡”和“清商曲”指代她,而在第二和第三节中,也只是用“美”来指代她。
我认为对于能够理解旧体诗的人来说,苏曼殊的译文比起袁可嘉的译文来说,更能够传达伯恩斯的诗意。吴盛青提到,“苏曼殊以及其他译者特意尝试将原文中的异国情调归化入古文形式。”(第340页)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归化”吗?对此我表示怀疑,我认为他们只是想用他们认为是“真正的诗歌”形式来呈现外文诗。
苏曼殊的译文使用了古代歌谣的形式来呈现伯恩斯苏格兰民间英语的效果,并且还原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意(袁可嘉的版本则并没有这样做)。至少这种诗意对于当时读者来说是,或许当代一些读者也能有共鸣。国学大师章太炎是苏曼殊的导师和伯乐,因此,吴盛青猜测章太炎或许对苏曼殊的翻译有潜在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章太炎校订、修饰过苏的翻译,并且有意添加了一些不必要的生僻典故来卖弄学问。然而我认为这里的“生僻典故”更像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策略,用以表现特定的文学和历史的差别。(第343页)
此处我同意吴盛青对于拟古主义的判断。这就是章太炎的一贯风格,而这种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早期(1907—1908)的创作。之后吴盛青又提到了苏曼殊翻译的拜伦的作品:在1908年的2月和3月份,苏沉浸在拜伦的诗歌中。(第350页)1908年1月和2月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刊载于《河南》第二期和第三期,其中拜伦便是作为中心人物出现的。《河南》第二期的卷首插画是苏曼殊的画作,题名为“洛阳白马寺”。
这样的时间巧合说明苏曼殊也可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或者两人有所合作——鲁迅关注拜伦的人生经历而苏曼殊则侧重于作品。接下来,吴盛青加以进一步的有力论证:我暂且认为,这种独特的翻译方式挑战了人们过去对于翻译的常规理解。过去,在不平等的文化结构中,翻译仅仅被看作两种文化中更为强势的那方单向的作用。这种独特的翻译方式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语言相互冲突和协调的例证。(第345页)
接着,吴盛青又提到了另外二人的作品来说明这种归化翻译并不是个案。其中一位是《圣经》的译者吴经熊(又名John C.H.Wu,1899—1986),他对《圣经》中的诗篇《圣咏集》(1948年完成)的精湛翻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引起强烈共鸣的中国化的上帝形象。(第346页)而另一位是东南大学教授李思纯(1893—1960),他的一系列西方现代诗歌译作以及其它出现在《学衡》中的作品也是如此。
这些译作包括文言译作的诗歌,有波德莱尔(Baudelaire)、保尔·魏尔伦(PaulVerlaine)以及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的作品。可惜的是论述都太简短,也缺乏例证。吴盛青此时笔锋一转,继续讨论苏曼殊,但却在结尾时调整了论断:“虽然这些旧体诗形式的英文诗歌译文为中国传统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不得不承认,古典文言和诗歌形式对于现代性的承载力是有限的。”(第348页)对此,我感到些许失望。其有限的地方在哪里,论证又在哪里?这本著作原本是论据充分的,但在这里却没有进行论证,而是突兀地下判断。所以,我无法不怀疑这是由于上一代“固定的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该章的后一部分“翻译抒情的亲密”主要讲到了拜伦和西方浪漫主义对苏曼殊的影响,苏曼殊有时被称为“中国的拜伦”。吴盛青告诉我们,“苏曼殊跟拜伦的相似之处,并不在于政治热情或革命功绩,而在于强烈的情感和对爱的表达。”(第352页)她引用东京大学学者藤井省三的话:鲁迅认为拜伦是在寻求个人自由,而苏曼殊在拜伦身上发现了如何在个人心里找寻内在的爱。(第352页)吴盛青讲道,“苏曼殊在翻译实践中赞扬爱的浪漫以及个体性,在诗歌文化中实现现代化的自我构造……拜伦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上,都为他提供了一个参照对象……苏曼殊借助这个参照对象,并且利用一种拜伦式的张狂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生活和诗境中创造了一个符合新型公众口味的、情感张扬的主体形象。”(第353页)
这确实是那个年代鲜活的文学现象,但我并不确定这是否就是对“现代”的定义。吴盛青写到,苏曼殊利用充满男子气概的第一人称“我”,来称呼他的爱人,这应该也是受到了拜伦和伯恩斯诗歌的影响,并且这一特点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十分突出。因此,我也联想到了1903年春鲁迅所写的《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里鲁迅使用了男性意味十分强烈的第一人称“我”,并在诗的最后一句以坚决而自信的方式进行了双重强调:“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里,他并非对着爱人喃喃私语,而是向着民族的苦难咆哮。就像张向天很久以前指出的一样,这或许也是受到了拜伦的影响,特别是拜伦作为斗士的那一面。
吴盛青将苏曼殊与李白进行比较,认为比起李白的潇洒放荡,苏曼殊的表达则更加直率大胆。(第357页)在吴盛青看来,苏曼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拒绝将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佛教信仰(他本人是佛教徒)凌驾于爱与自我之上——他认为,抒情主体“我”才应是话语权的主导,(第358页)这一点体现了拜伦、伯恩斯和雪莱共同的文化影响。(第359页)苏曼殊以僧侣伶仃的形象“投射自己的孤独寥落、无所归属与飘零感。这种手法表现有出奇的现代感”。(第360页)可是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异化感才能算有真正的现代性。
吴盛青告诉我们苏曼殊最喜爱的是以下的诗句:
袈裟点点疑樱瓣,
半是脂痕半泪痕。
吴盛青观察到,通过“樱花瓣”的奇异形象和“脂痕”与“泪痕”之间转情诗喻和隐喻的使用,诗人将宗教信仰和主观感受之间的冲突无限放大。(第360页)但这个冲突由来已久,自中世纪甚至远古起就已存在。我们能将它和鲁迅的旧体诗句所表达出的现代意义下的畏怖相比吗?
昔闻湘水碧如染,
今闻湘水胭脂痕。
当然,在这里鲁迅是在影射1931年异议分子被肃清,革命烈士法外处决以及国共内战的历史背景。但苏曼殊也同样经历过许多包括戊戌变法、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在内的重大历史性变故,他在日本时曾是中国革命者的知己密友。
苏曼殊早逝于1918年,并“未经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所以他选择以古文来翻译、写作很可能是受时代所限,并非有意识的选择”。(第363—364页)
但在吴盛青的书中并没有呈现他如何选择这个过程,而是直接给出了他选择的结果。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她观察到苏曼殊(据说为中国读者写过一本梵文语法)视梵文文学为最上,中国文学次之,西方文学最末,并解释道:
他对西方文学的偏见似乎与他对浪漫主义的痴迷相矛盾,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这应该是一种策略和心理反应。他反对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对等的文化、政治以及科技实力较量。在西方科技面前,古国文明显得力不从心。苏曼殊虽看不惯西方霸权主义,但依旧积极地吸收其文化精髓,参与考量外来文化影响力的优劣。(第364页)
苏曼殊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政治和科技不对等的交流体系,以及古老文明的生存局限性的批判,与鲁迅早期(1907—1908年)在日本写的文言论文几乎如出一辙。他拒绝西方霸权,但积极吸收其文化精髓的做法也与鲁迅早期的论文和1934年所写的《拿来主义》里的观点非常相似。因此,我认为增田涉提出的苏曼殊与鲁迅两个人相互影响这一说法可能性很大,并且这些观念在当时文化圈中是极为流行的。
本书最后提到的是以哈佛大学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的门生吴宓(1894—1978)为中心的“学衡派”,其中包括郭斌龢(1900—1987)、柳诒征(1880—1956)和胡先骕(1894—1968)。这是一群接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力求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共同点。
尽管他们在评论中国时,经常引用20世纪初“国粹派”的思想,但他们的方法路径却体现了世界主义和英美思维模式的影响。就像吴盛青评论的:“吊诡的是,正是在西方思想和模式的影响下,这批知识分子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欣赏和利用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遗产。”(第366页)
在“克制的意志”这一部分中,吴盛青集中探讨了吴宓的翻译。主要是他所翻译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的诗歌,以及吴宓如何“利用翻译的手段来实现对文化和现代性的批判”。(第336页)在哈佛留学期间(1918—1921年),吴宓主修了维多利亚诗歌,他十分欣赏拜伦、罗塞蒂和阿诺德的作品。吴盛青详细分析了他翻译的罗塞蒂的诗歌《思忆》,这首诗记叙的是一位女性临死前对爱人的钟情诉说。
吴宓将诗歌翻译成了五言古诗,“从而将婉转柔弱的哀伤发挥到淋漓尽致”。(第368页)吴宓认为,中国的古诗和英文的十四行诗相似,所以用古诗进行翻译,是最佳的选择。对此,吴盛青似乎并不反对,尽管吴宓“将罗塞蒂的诗境汉化并且极大程度上缓和了原诗的宗教色彩”。(第369页)
比起其他四位译者(难道四位当时都能算是“拟古主义”者?)的古体诗译文,吴盛青更加看好吴宓的译作。她并没有引用其他译者的译文,却强调了吴宓在语言方面对性别歧视的谨慎处理,以及对宗教和性别的关系、爱和政治寓言的关系的有趣探讨。(第371页)吴盛青还提到,其他译者笔下的女性形象都饱受相思折磨,十分谦卑,这样一来无法很好地传达宗教和爱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这样的紧张和冲突,在罗塞蒂诗歌中至关重要。白璧德称之为控制生理冲动从而成为更清高的自己的“克制的意志”或者“内在的抑制”,(第371页)这里我猜想吴宓是对儒家名言“克己复礼”的一个回应。
接着,吴盛青简单地提到了吴宓翻译的阿诺德的《安魂曲》,这首诗记叙的是一位女贵族的殒殁,全诗基调十分忧郁。吴盛青评论说,“这首诗通过负面情绪的荒芜力量,让人对现代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第373页)吴宓认为阿诺德是“浪漫主义忧郁情结的典型人物。他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一心投入诗作中,并坚守自己的立场”,(第374页)就像历史上的屈原。在她看来,吴宓和阿诺德惺惺相惜,在那个令人迷失而无信仰的转型年代,诗歌成为现代世界新的宗教信仰。在阿诺德的挽歌中和他隐藏在讽喻之下的痛苦中,吴宓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而我也十分同意吴盛青的观点。留洋归国的吴宓拥有更广阔的世界视野,能够更好地欣赏阿诺德的诗作。而他的导师白璧德相对偏狭,白璧德不认同阿诺德“诗歌终将取代哲学和宗教”的观点,并认为这是阿诺德“有问题的一面”。(第374页)然而,阿诺德和白璧德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宓,促使他清醒地面对传统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及其瓦解。(第375页)对于这些问题,清末年间的旧派诗人和鲁迅同样倾注了许多心力。
“阮玲玉自杀”事件后,吴宓为她写了一首悼亡诗,风格就与其译诗中的某篇一致。诗中用了“落花”的意象,而这个意象,王国维在自尽前也曾借用过。(第375页)有趣的是,当时吴宓解释道:“惟予诗除现代全世界知识阶级之痛苦外,兼表示此危乱贫弱文物凋残之中国之人所特具之感情。”(第375页)他又进一步解释道:“安诺德之诗之佳处,即在其能兼取古学浪漫二派之长,以奇美真挚之感情思想,纳于完整精炼之格律艺术之中。”(第376页)换言之,他翻译的内容也正是他自己所想表达的(而对此我认为有时也适用于鲁迅)。吴盛青对此评论道:“在中西文化冲突对立时,文体形式和拟古主义的选择背后的意蕴不容小觑。西方文化在被精心摘选之后,所留下来的部分成了文人们的依靠和灵感源泉。”(第377页)
吴宓和他的同事们宣称不过问政事,而是潜心追求更高的文化价值。吴盛青留意到这个说法:“充满了矛盾和权力冲突,浸没在民国的文化和政治的纷乱中。”(第377页)她总结道:“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吴宓译作的文化作用,他用中国古典文化这一形式引入和塑造西方文化,巧妙地将古典文化融入新时代,展现出了现代文化内在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第 378—379 页)
在本章结尾,吴盛青引用了吴宓翻译的安德烈·舍尼埃的L’invention(《发明》)其中一句:“用新来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Sur des pensers nouveaux faisons des vers antiques)在我看来,这句翻译胜于原文,而且除了硬要加骚体助词“兮”之外几乎感受不到“拟古主义”的气息。
综上所述,虽然我对题目中“拟古”的使用以及书中提到的某些“拟古”诗人作品的理解持一定的保留意见,但总体上来看,这本书是一部学术杰作。作者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从晚清诗人开始分析,到托多洛夫,然后又回到潘重规和钱钟书。吴盛青的见解深入透彻,翻译准确可靠,评论也恰到好处,没有任何学究气和沉闷感。她的阐述富有逻辑性,而且尊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文笔也流畅易懂。简言之,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部作品都是中国近、现代古典诗歌研究成果的翘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