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在此的雷耶斯
徐兆正
雷耶斯:那么,我是谁?
此处大海止息,土地伊始。雨落入惨白的城市,携带浊泥的河水滚流着,岸边的湿地盈满潮水。
《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一书的叙述,始于诗人雷耶斯从巴西回到他阔别十六年的祖国葡萄牙。在一九一九年,他迁徙至里约热内卢并定居于此;十六年后,诗人搭载“高地桥梁”号倏忽而归,那是一九三五年底,欧洲的情形不容乐观,那是安东尼奥·萨拉查建立第二共和国后的第三年。翌年,这个国家便卷入西班牙内战,而德军撕毁了《凡尔赛条约》进驻莱茵兰,意大利攻占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反观雷耶斯的个人情形,正如他当初去国态度之决绝,此刻他回到里斯本概也并非出于怀乡的原因。即将抵达港口的船渡始终是适合小说开始的场景,但在这里,对从阿尔坎达拉港口走下船舱的雷耶斯来说,却多少显得不明不白。他为何重回里斯本,不见说起。事实上整部小说亦复如此,作者萨拉马戈以诗人的回归起始,但也似乎就到此为止,类乎一种戛然而止的叙事:雷耶斯甫一抵达里斯本,他的命运便被定格在了悬置的瞬间。

《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 葡] 萨拉马戈著黄 茜译作家出版社2018 年版

若澤·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
置身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雷耶斯找不到可以展开的道路,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他暂居布拉冈萨旅馆,断断续续写了几首聊表心迹的诗,反复涂抹修改。(例如:“像神祇一样活着,缄默而安静,除了观看无所作为。”)写诗之余,他又同酒店的服务员丽迪亚暗生情愫,且接连爱上了两位女性。更多时候,雷耶斯就像夜游神一样在里斯本的迷宫里闲逛,从迷迭香大街出发,或者选择木厂大街,或者选择雷默拉勒斯大街,行经军械库大街,七月二十四日大街,好望角大街,耶稣受难像大街……直到走得双腿意识到疲倦。并无一条被预先照亮的道路,如同科斯托拉尼·德若笔下的夜神科尔内尔,抑或是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因为事业与爱情的受阻,漫无目的的散步是文本中唯一的行动。正因为此,雷耶斯早已不是本雅明指认的存在于十九世纪巴黎的“城市闲逛者”,与爱伦·坡故事中的侦探亦无多少相同之处。用作者的话讲,这是“因为世界与里斯本笼罩在雾气之中,叫人分不清东西南北,而这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向下倾斜”。
在战争的阴影尚未被雷耶斯感知以前,他还曾因不知如何生活而祈求众神让他无所祈求,但紧接着,当战争逐步逼近国境,“生活于他而言已经悬置,充满问题的同时也充满期待”。雷耶斯开始准时阅读当地的报纸,并且将动态告知于他的听众:两位坐在公园里的老人。这实在是文人的哑剧,但除此以外,人们还能要求这个“一半是享乐主义者,一半是禁欲主义者”的异教徒诗人做什么?如果说公园里的那两个充耳不闻的老人是葡萄牙公众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之交喑哑的缩影,那么雷耶斯的迷惘所倒映的,则是他被抛入的年代里葡萄牙的迷惘。他想要知道自己是谁,如同深陷泥潭的葡萄牙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发生于雷耶斯返回里斯本那一时间段的另一件事,是葡萄牙的另一位伟大诗人佩索阿刚刚殁世。因此,提及雷耶斯当时的生存环境,也就不能不提到他在寂寞日子里唯一的消遣—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最初返回里斯本的动机之一如今变作了他生存的全部激情—等候佩索阿灵魂的造访。
这次会面直到小说行进至六分之一的篇幅时才不疾不徐地发生。不过,两人在夜晚的会面同样平淡如水。佩索阿告诉雷耶斯,自己的灵魂还可以在世上逗留九个月,他给出的理由是:“在我们出生以前,人们不能看见我们,却每天都在想着我们,在我们死去之后人们不能再看到我们,而每天都多忘记我们一些,除了特殊情形之外,九个月恰好足够一次彻底的遗忘。”同佩索阿的会面也许让两个人的寂寞都有所缓解,而雷耶斯也确实在佩索阿的灵魂身旁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九个月。然而所有这一切深夜里的促膝长谈都无助于清除雷耶斯的困惑。他不仅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重新开始生活,甚至也不了解自己是谁。在小说结尾,当佩索阿告知雷耶斯两人不能再次见面,因为他的时间到了,雷耶斯也站起身来,穿上外套,同佩索阿一起走进坟墓。诚如萨拉马戈所说,“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一辈子从来没弄明白他到底是谁”,这一点对于雷耶斯也是如此:他同样经历了不知道、想要了解但终究一无所获的旅程。
普鲁斯特曾经指出这是人生最苦涩的事情:“现实随着我们所用以取代它的有条理的认识不断地增加和严密化,而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现实就是,确实存在着我们到死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极大危险,我指的是真正的生活,是被最后揭示出来、被弄清面目的生活。”最苦涩的,莫过于在骑上灰色马以前,仍未澄清生活的本来相貌,亦认不得自己的面目。雷耶斯显然是带着这种遗憾离开人世的。我们还应该记得,在归来的轮船上,他曾经以阅读那本《迷宫的上帝》作为消遣,并且暗自玩味那个名叫赫伯特·奎因的作者的名字:“Quem,请注意,Quain,Quem,由于某人在‘高地桥梁号上识得了他而不再籍籍无名的作者,如今,若那里有的是唯一的副本,竟或连这一本也遗失了,我们则更有理由问:Quem(谁)?”雷耶斯由Quain联想至Quem大概并非是玩一种文字游戏,更有可能的是后面这个词早已横亘在他心头许久,于是他才会念着Quain的名字,却发出了Quem的读音。我们不无理由相信,他也注定想到了下面这一点:“那么,我是谁?”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
从小说情节来看,《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讲的就是这一件事:雷耶斯在佩索阿逝世以后横越大西洋回到故土,在陪伴佩索阿走过人生最后的九个月之后,与他一同归于忘川。
谁是雷耶斯?
“认识你自己”被苏格拉底视为个人在智识上的最高使命。这是雷耶斯的未竟之功,可对于他想要了解的真相,身为作者的萨拉马戈与作为读者的我们终究还是知道:雷耶斯是佩索阿异名体系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一。在一九三五年给蒙特罗的信中,佩索阿如此介绍雷耶斯:里卡尔多·雷耶斯“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波尔图,是个医生,现居于巴西……(他)从一九一九年开始就住在巴西。到了那里,他立刻就放弃了原国籍,因为他是个君主主义者。通过在学校里的培训,他成为一个拉丁语专家,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成为一个半专业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在相貌特征上,(他的)“个子矮了点儿,但也不是那么矮,要壮实很多,但为人精明……(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在写作风格上,雷耶斯受贺拉斯影响颇深,以短诗与颂歌见长,尽管在佩索阿看来他的语言由于过分追求纯粹而变得单调。除了思想观念的部分,这大概就是我们如今能够获取的全部信息。雷耶斯是佩索阿在一九一四年之后偶然创造的异名人物,也是佩索阿唯一没有规定死亡时间的异名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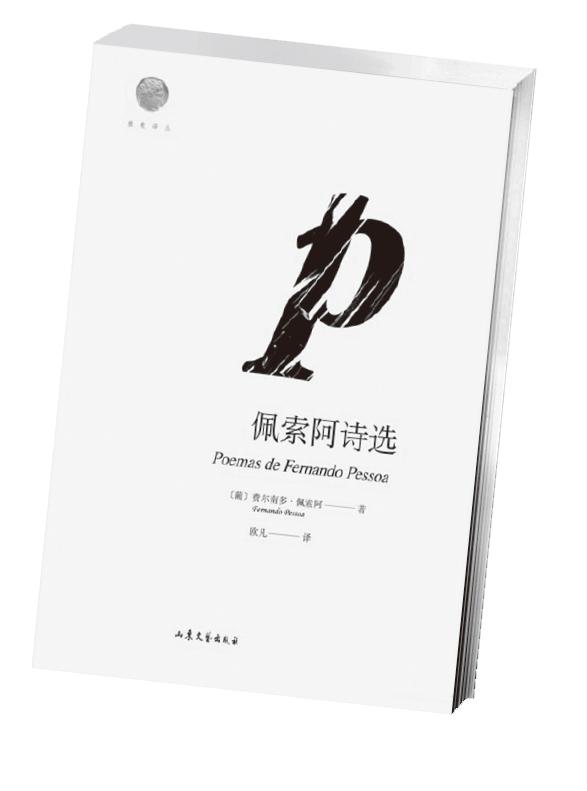
《佩索阿诗选》[ 葡] 佩索阿著欧 凡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

《惶然錄》[ 葡] 佩索阿著韩少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年版
异名与笔名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但仅就异名拥有独立的生平行止这一点而言,两者的差异显然更大。谈论佩索阿一生的诗学成就,无可回避他所创造的这种异名写作方式。同样是在给蒙特罗的信中,佩索阿罕见地谈到了这种特殊写作的精神起源:“从幼儿时代起,我就总喜欢幻想在我的周围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幻想出一些从来不曾有过的朋友、人物。自从我意识到我之为我的时候起,我就从精神上需要一些非现实的,有形象,有个性,有行为,有身世的人物”,“异名的精神起源存在于我对人格分类和伪装怀着的持续而根本的倾向”。进一步说,通过创造出一批体现自身性格因素抑或径直处于“本我”层面上的异名,随着他们自由地展开各自的生活和交际,佩索阿也就创造出了另一重世界。这个世界诞生于想象的分裂的夜晚,佩索阿同他们争辩、交流与对话,这正如现实世界是未曾分裂的白天,而佩索阿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里斯本的小职员,日常生活乏善可陈。从这一点来看,异名写作似乎就是佩索阿自我创制的一种生活方式,即用想象的夜晚去制衡那现实的白天。
尤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一诗学创造甚至已然预示于佩索阿的名字(Fernando António Nogueira de Seabra Pessoa)之中。在葡萄牙语里“pessoa”意指人,而这个词源出于拉丁语的“persona”,有演剧角色佩戴的面具之意。不过,偏重于面具的伪装意味,仍然无法真正凸显异名的特质,仿佛它终归是佩索阿在文学形式上别出心裁之举。然而在佩索阿看来,与其说异名是作者戴上了面具登上舞台,还不如说他就是“另一个人”,这也是异名(heterónimo)在葡萄牙语里的原义。理解这一点,有赖于我们对不同异名人物进行详尽的理解,包括他们的生平经历、昔日交游、文学创作以及思想观念。帕斯在为《佩索阿选集》撰写的序言中有一语说得极好,他说:“异名者的真实性取决于他们的诗学连续性,他们身世的逼真。他们是必要的造物,不然佩索阿也不会穷尽一生创造他们,与他们相处;如今要紧的不是他们对于他们的作者是重要的,而是他们对我们也同样重要。佩索阿,他们的第一读者,从未质疑过他们的真实性。”将以上诸部分合而观之,我们得到的便是异名的本质因素,亦即他们的诗学连续性。
佩索阿创造了七十二个异名,他们就像七十二个人一样,有的写短诗,有的写颂歌,有的从事批评翻译活动,而所有这些异名人物创作出来的作品,在图书馆都被归入“佩索阿”名下。埃德温·霍尼格在《自决之书》的英译本前言里有云:“他的抒情诗天赋创造出了各种有血有肉的生动角色,这些角色有助于调整他那错乱的个性,并且给予他的艺术一个存在的理由,而若非如此,他的艺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理由。”某种程度上,异名蕴藉的可能性不仅仅指涉了艺术的可能性,也具有将艺术擢升为本体论的含义,使之成为诗人存在的理由;反过来看,若果佩索阿处决掉其中一个,也就意味着他丧失掉一种展开生活的方式—尽管佩索阿展开生活的途径过于奇怪,即通过泯灭自我来创获他者,以此将一己感受的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因此,当佩索阿几乎为所有异名都安排好一生(唯独遗漏了雷耶斯)时,这其实也是一种既绝望又清醒的隐喻。

《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收入博尔赫斯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版
在小说《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中,萨拉马戈从佩索阿手中接过了雷耶斯这个人物形象,并且转瞬就让他去阅读赫伯特·奎因创作的《迷宫的上帝》,熟知博尔赫斯的读者恐怕难免莞尔一笑,因为赫伯特·奎因同样是博尔赫斯杜撰出来的人物(见《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收入《小径分岔的花园》)。于是,当在返回故土船上的雷耶斯读到那本《迷宫的上帝》时,便形同开启了两种并不存在之物的对话—那个从未在此的人面对着一本从未在此的书—因而是虚构的虚构(这也是萨拉马戈这本小说的特质)。但萨拉马戈之所以在佩索阿的七十二个异名人物里,选中雷耶斯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却并非与雷耶斯个人的诗学连续性有关,亦不是出于他思想观念里斯多葛主义的倾向,而是如上所述,即雷耶斯是佩索阿唯一没有处决掉的异名:佩索阿从未搞清楚自己是谁,固然是萨拉马戈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之一,更关键的地方,却是佩索阿在生前未尝规定异名者雷耶斯的死亡时间。由是,这个个体才被他的命运攫住,吊在空中,而他的命运便是虚构本身。在我看来,这是此书叙事得以展开的根本前提。
悬置,或虚构之虚构
在这部小说里存在着两种悬置。首先是作为主人公的雷耶斯在生存状态上的悬置:无所适从。他好像热衷于在这重回的故土上散步,尽管这种散步已然出离波德莱尔对瞬时之美有所发现的命题。就像小说里偶然提到的那一句“这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向下倾斜”,我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种关乎时代现实的象征,个体在街道上迷路,猶如葡萄牙在其时的政治状况里没有出路一般。个体情形在这里亦是社会状况的倒影。雷耶斯正是被抛于这样的年代与这样的国家。被抛是一种被动的悬置,是根基被挖去之后对一切不确定状态的承受,同时也是在怀疑之雾中看待城市的风景。此外,雷耶斯在生存状态上的悬置也生发主动的一面,那就是“我是谁”的追问:“要为自己的肖像赋予新的实质,要能够把双手放在脸上而认出自己,将一只手放在另一只之上并相互紧握,这是我,我在这儿。”
在主动这一面,悬置已然接近于胡塞尔的看法。后者重新启用了早期怀疑主义者的一个概念“epoche”(中止判断),亦即凭借着相对性的自觉,将一切关乎外部现实的独断看法存而不论,悬置起来,借此从作为事实的现实世界进入到作为本质的纯粹意识世界。雷耶斯同样关注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仅仅存在于他的意向性中。两相来看,他的被抛状态未尝不可能是他对自身倒映的葡萄牙的悬置。通过对充满确定性的对象(报刊新闻、公众意见、领袖讲话、“一个城市的低吟,六百万人的叹息,渺远的叫喊”)的怀疑,自我肖像的实质或许有可能重新向雷耶斯展开—尽管他对此不无怀疑,而这种怀疑最终又在一种感伤的预感下被证实,譬如他曾在“高地桥梁”号上默念Quain或Quem的名字,也许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了某些事情。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意义上的悬置,实则源于一个虚构者对虚构的感知。
其次是第二种悬置,亦即萨拉马戈对于小说的线性叙事采取了通盘悬置(或曰放弃)的策略。这样做的主要后果,就是令此书显示出以诗来写作一部小说的野心,它类似于马拉美或福楼拜曾有的狂想,萨翁在书中也有此示意:“旅者攀上那无休无止的长梯,看起来要到达第一层楼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是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以不分行的形式书写对话,将迅疾的讲述让渡为迟缓的显示,同时增大文本层面的编织密度。若果将小说的叙事一分为推动叙事的与阻碍叙事的两方面而论,那么它的叙事动力就是隐而不彰的谜题(“那么,我是谁”),而它那犹如里斯本街道一般的叙事阻力则注定使读者迷失其中,或径直从语言的长梯上坠落。可是反过来讲,以如此激进的姿态显示,恰恰合乎了所显示对象的本质,亦即我们早已知晓而唯独雷耶斯毫不知情的事:他仅仅是佩索阿的一个异名人物,并不真实存在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难于转述萨拉马戈这部小说的情节,归根结底是由于它过分贴近激情匮乏而戏剧性丧失的生活。我们阅读这部小说,仿佛也就是在阅读我们日复一日的庸常:雷耶斯每日的闲逛与逗留都没有目的,恰似我们的生活也缺乏任何终极目的一样,呈示为一条直指虚无的射线。
雷耶斯的命运早已被虚构判决为虚构,但作为读者,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依然会为了共情而选择相信,这便是小说显得格外动人的原因。正是在这里,萨拉马戈更为有力也颇为动人地重新估价了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他让这个问题通过文本虚构而具有了可以思辨的形体,由此将其从文论的泥潭与飞旋的术语中拯救出来。读者像是围观世间戏剧的神灵一样,津津有味、当然也不乏同情地注目雷耶斯继续在里斯本街道的阴影里踟蹰。他早已不在,所有人都知道,唯独他不知情。他不知情,或者他还在怀疑自己是否知情,甚或是他已经知情却又不愿相信。当佩索阿在一九三五年规定了雷耶斯早于他一年出生的这个事实后,尽管后者早已被判决为虚构,其命运的圆环却并未真正闭合,诚如詹姆斯·伍德所说:是萨拉马戈的叙事令“它变成了一个感人的追查,目标是弄清楚何谓真实的自我”。在这场追查里,追查的对象是一个注定得不到答案的斯芬克斯之问,但也腋集了后现代文本所能提供的所有细微感情。依我看,它远比技术上的元小说游戏动人得多。
面对这本写于一九八四年的小说,任何轻易的置评恐怕都将失之得当。因为萨拉马戈对虚构文体理解的深化,对元小说内涵的移置,已然使得元小说除了要承担叙事的形式职责以外,还要内化为一种并非确定的主体的精神象征。作为读者的我们只能尝试着指认它是什么,以此避免将它归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类。虚构是雷耶斯被给定的命运,叙事则进一步地将这种命运导向了自我同一性在现代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境遇之中。此书的题辞之一来自于佩索阿的一段话,他说:“若对我说如此描写并不存在的人是荒谬的,我要回答我亦没有里斯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或这个写作的我,或任何臆想之地存在的证据。”这不再是巴门尼德的意思,也早已超越了休谟的怀疑,而似乎更像是普特南关于“缸中之脑”的设计—我们如何相信自己?包括相信自己的存在,相信我们并非是那被虚构出来的人物?—雷耶斯的忧郁令人恻隐。
二○一九年四月二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