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上山
李庆西
一
老话说“逼上梁山”,但《水浒传》里真正被逼无奈上山落草的就那几个,林冲、杨志、鲁智深、武松,之前史进也算得一个。史进因暗通少华山“贼人”被官府追杀,乡里已无容身之地。且说起初还不肯落草—“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史进跟朱武那伙人喝酒吃肉称兄道弟,却不愿和光同尘混迹其间,可见上山为盗是莫大的污名。当然,被逼上梁山的还有宋江。那些人里边,宋江上山的道路最为艰难曲折。
自第二十一回杀阎婆惜之后,宋江就开始了流亡生涯—辗转柴进、孔太公庄院和花荣的清风寨,终究被青州官军捕获。幸赖清风山燕顺等人搭救,逃过一劫。继而又有秦明、黄信归顺,几股人马合成一伙,宋江俨然已是这帮人的老大。面对官军征剿,宋江决定带领弟兄们去梁山泊投奔晁盖。可是转而又生变故,途中遇上投送家书的石勇,说是宋太公已殁,宋江便撇下众人回家奔丧去了。
宋江跟王伦、林冲不一样,不是从柴进庄院直奔梁山,而是几番迂回,绕了老大一个圈子才上山入伙。书中不厌其烦叙述这些,用以揭示其无地彷徨的心路历程。前脚刚迈出去后脚就退回来了,这个世界只要给他一点点念想,他绝不肯出离社会去啸聚山林草泽。
宋太公其实没死,赶上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以为杀惜之事不再被追究,便让宋清写信将宋江骗回家来。宋太公最担心这儿子成了绿林匪贼—“我又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可没想到,宋江回家当晚,宋家庄就被官军围了。宋江被押往县里,又解送州府,脊杖、刺配自然免不了。宋太公花钱买通官员,给宋江发配到鱼米之乡的江州。临行前,老父谆谆嘱咐:“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作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果然,差人押解宋江路过梁山泊时,他们就被劫持到山上。晁盖亟劝宋江入伙,宋江坚决不干,非要去江州服刑。他说:“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这话说得有些尴尬,先前青州一段,好像成了迷途羔羊。
初到江州宋江没吃多少苦头,牢城管制不严,况且有戴宗照应。但想半生虚掷,又被黥面发配到这里,自是无比郁闷。“潜伏爪牙忍受”,亦实在难以忍受,浔阳楼题反诗竟惹大祸,被通判黄文炳检举下狱。梁山方面得知宋江罹此厄难,伪造蔡京文书使将宋江押送东京,打算途中截人,可惜此计又被黄文炳识破。这下几乎进了鬼门关,江州蔡九知府决意就地斩决。接下去便是梁山泊好汉劫法场,上演大闹江州一幕,将宋江从鬼门关里拽了回来。

梁山泊好汉闹江州,明刊杨定见序本第四十回插图
闹江州又灭了无为军,这是梁山泊第一次攻掠州府的军事行动。事情搞大了,这回宋江顾不得“不忠不孝”的污名,终于跟着晁盖回梁山泊,算是正式入伙。这是小说第四十一回叙说的事情,从杀惜到此已整整二十回,除去叙说武松的“武十回”,其余十个章回基本上就是叙述宋江从流亡到上山的整个过程,其间一波三折,情节跌宕起伏。对宋江来说,上山落草只是人生下下策,无路可走的无奈之举。
二
上山落草不一定是无路可走的选择,往往亦是不安分的生命躁動。白衣秀士王伦科场失意即游走江湖,由柴进赍助银两,便去梁山泊拉起了队伍(据林冲说最早是杜迁“得到这里”)。既然不能进入赵宋王朝体制,王伦郁闷苦闷之中决然投袂而起。
晁盖、吴用等人投奔梁山泊可另作一说,虽说逃避官军缉捕,起因却是劫生辰纲一事。那是他们主动出击,以江湖手段“取不义之财”,不能说是被人家逼的。这种团伙劫掠的营生,即使未留有后手,跑路之后啸聚山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像宋江去江州途中遇上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张横那些人,原本就在江湖上从事打劫勾当,说到上山落草不用大费周章。梁山一百零八人中,这类角色不在少数。
从王伦到晁盖,意味着江湖社会从秘密状态转向公然对抗官府的造反行为。体制溃败无疑给出“揭竿而起”的合法性,那些被历史教科书称之“农民起义”的武装暴动历朝历代都有,却不一定都是农民起义。其中既有英雄失路之绝地反抗,亦不乏热血青年咸与造反,更有趁火打劫混吃混喝的一干闲汉。可是,从《水浒传》描述的情形来看,造反绝不是因为民不聊生,书中不曾出现饿殍遍野的景况,反倒是处处呈现一派《清明上河图》的繁胜画境。不必说大名府和东京那些大都市,即如孟州、蓟州、江州之类三四线城镇,甚或清风寨那种小地方,亦是民丰物阜的气象。小说演示的矛盾冲突主要在于体制内部,一切因官场弊恶而起,林冲、杨志们的走投无路并非反映民生疾苦,那些个体的厄难之所以被放大,是因为天下没有说理之处。在上是高俅、蔡京一班佞幸把持朝政,在下是郑屠、牛二、西门庆那些“破落户”祸乱市井,以致从上到下纲常颠倒,贤良受屈,也就是聚焦于古人所谓“贤”与“不肖”之对立。显然,小说家的叙事目标在于政治伦理方面的拨乱反正。
宋江不愿上山落草,是尚未感受到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他的厄运是从杀惜开始,阃内之事没有道理可讲,杀人乃因招文袋内私通梁山的证据,这是他的“原罪”。作为帝国基层政府的县衙吏员,宋江处世练达,在当地人情社会乃至江湖上口碑极佳。他恪守儒家纲常,又深明江湖大义,其内心早已将扶危拯溺的江湖规则与所谓仁义忠恕的圣人教谕融为一体。之所以不惮风险私放晁盖一伙,不是他生有反骨,只是觉得这样做符合道义。道义也是硬道理。宋江是极有理性之人,掩护晁盖是不得已,却不至于自己也蹿入山林。浔阳楼题反诗是他内心偶尔的躁动,他不能不意识到现实的荒谬,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真正跌入了那个无处讲理的黑洞,真正身陷囹圄之后,才终于转向体制的对立面。
梁山一百零八人中来自体制内的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多数是被俘或投诚的军官,计有秦明、黄信、李云、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凌振、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十七人,从书里描述的情形看,这些人转变立场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深切感受到官家体制之暗昧。另外,花荣、雷横、朱仝、孙立、孙新等人,本身与江湖人士关系密切,投身绿林亦是机缘凑巧。当然,还有走投无路的林冲、杨志、鲁智深、武松,邓飞、孟康那几位,还有被赚上山来的徐宁(朱仝也算是被赚上山的一个)。这名单中还要添上施恩、戴宗、李逵、杨雄、裴宣、蔡福、蔡庆那些人,作为押狱、孔目和牢卒,他们原本亦是体制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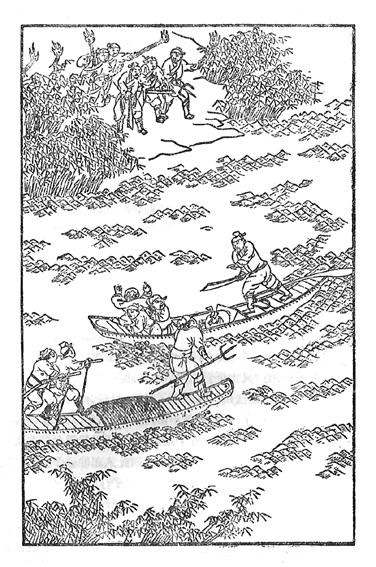
浔阳江上宋江几乎吃了张横的“板刀面”,明刊杨定见序本第三十七回插图
大批体制内人物反水,几乎都在一念之间,只是秦明在瓦砾场上有过一节踯躅。说起来谁也没有宋江的转变来得困难。
三
从流亡江湖到上山入伙,宋江这一路险象环生,可谓九死一生。去往花荣清风寨路上,他被清风山燕顺一伙逮住,差点被掏出心肝做了醒酒酸辣汤。离开了清风寨又落到老奸巨猾的刘高手里,押在囚车里要解往青州。解铃系铃都是燕顺那伙人,这是江州之前的生死场。后来发戍途中更是步步惊心,揭阳岭上被李立用蒙汗药麻翻,进了镇子又让穆氏兄弟追杀,浔阳江上几乎吃了张横的“板刀面”。在江州,题反诗惹下杀身之祸,如果不是最后被押上法场,又被梁山众人救出,他还不至于上山。
他何苦于此?他内心的苦楚有谁可知?古人做小说多用白描手法,主要以外在的形态、动作来描述人物,由事件发生的情节、细节推及内心世界—这既不像西洋小说那样擅用内心独白直抒人物心理活动,也不具有戏曲唱词那种自我倾诉功能,这就未能使读者直接窥见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写法不能说尽是缺点,“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抑或自有含蓄之妙。显然,宋江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更在文本之外的衍生和扩展,亦即由阅读感受所生成的无形的文本。你可以说那是推测和想象。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书中内文说是“巳牌前后”,应是上午),那是一幅横尸遍野的空廓画面,感觉中清寂的马蹄声似乎由远而近,亦自传递出悲凉之中的百感交集。字里行间不见他是怎么想的,可内心必是翻江倒海。
梁山一百零八人中没有人比宋江遭受更多厄难。卢俊义也算大难不死,却没有宋江这般内心纠结,卢氏是被吴用的计谋绝了后路,更被妻子和管家所抛弃,人生之转圜不暇多想。可是,宋江的心思不只是“飘蓬江海谩嗟吁”,身处江湖之远却忧庙堂之君,只是忠良之辈都成了山林草寇,心中靳固不移的伦理纲常比照现实全是悖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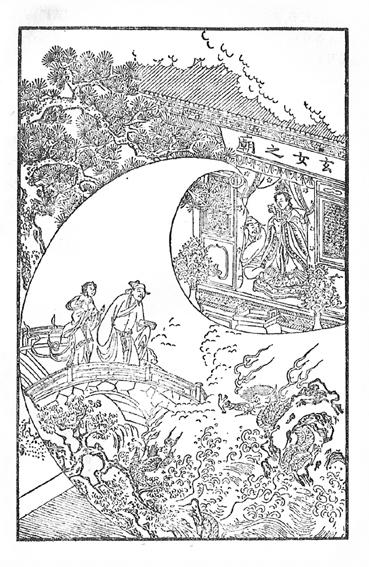
宋江还道村受三卷天书,明刊杨定见序本第四十二回插图

呼保义宋江,明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东奔西窜的流亡生涯有着太多的苦涩与辛酸,对宋江而言,这是一番自我救赎的历程。尽管已是几近崩塌的纠结,但书中几乎不让宋江的内心活动形之于色(浔阳楼醉酒之际是一个例外),这是着意要塑造其老成练达的老大风范。于是,只有四处辗转的一路颠踬,看上去只是一个犹豫和延宕的过程。是困扰,亦是淬砺,如此方谓玉汝于成,这样的人物内心有着足够的坚韧,其信念亦足够坚强。
这个江湖上众望所归的人物,竟迟迟不肯与道上的弟兄们把臂入林,无疑是存有价值认同的差异。当然,他不是缺乏男子汉勇气,也不能说他是多么舍不得那种刀笔小吏的庸碌人生。宋江必然想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背后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造反纳入合法化的叙事轨辙。正如娜拉走后怎样,宋江的问题是,上得梁山之后,他能做什么?其实,他还来不及想好,就被命运裹挟而去。
直至小说第四十二回,宋江于还道村受三卷天书,这才使他解除了那个心结,困扰已久的合法性问题总算得以澄清。九天玄女给出的“替天行道”四字,无疑是一个解决方案—“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正是这几句话,将梁山泊的江湖道义与古代圣贤制定的伦理纲常捏合到一处,使针对官场浊流的造反行为有了“替天行道”的合法性。
四
书中有一个缺省的情节常被人忽略,就是宋江并未将玄女天书一事禀告晁盖。宋江在还道村口被梁山众人接着,也不曾跟任何人说起玄女庙内的梦境。当然,天机不可泄露,玄女娘娘叮嘱过,三卷天书“只可与天机星(吴用)同观,其他皆不可见”。

晁盖曾头市中箭身亡,明刊杨定见序本第六十回插图
宋江上山后坐了第二把交椅,晁盖依然是山寨老大,但在某種意义上晁盖已是局外人。作为行动指归的“替天行道”方案并未提交领导层讨论,宋江的方针是只做不说。或者,只是在招纳官军将领时作此申明:权借水泊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云云。如俘获彭玘、呼延灼、关胜,赚得徐宁上山,他都说过这番话。直到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排座次后,梁山顶上才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晁、宋二人都是庄院主出身,都有“仗义疏财”的美誉,可是在江湖上宋江的名声要大得多,在山寨内部也更有影响力。书中一再出现这样的场景,那些好汉见得宋江,听说“及时雨”和“呼保义”的大名,忙不迭俯身跪拜。对于晁盖,则完全没有这等发自肺腑的敬意。小说家这样处理,似乎在二人之间埋下了某种罅隙,但书中偏偏不写两位首领有何抵牾(不能说没有丝毫分歧,如闻时迁祝家店偷鸡,便是各有掂量),维护着一种和衷共济的团结气氛。但从实际情形看,宋江颇有行事之便。
从宋江上山到晁盖曾头市中箭身亡(小说第四十二回至六十回),书中几乎没有叙述他们二人相处的情形。其间插入了若干游离山寨的叙事单元,如李逵沂水之行,石秀杀嫂和杨雄的故事,解珍解宝入狱和获救,雷横打死白秀英和朱仝误失小衙内,李逵打死殷天锡,戴宗李逵蓟州寻找公孙胜,时迁盗甲和智赚徐宁等诸多关目。这些章节之间,又接连穿插宋江指挥的多次军事行动,先后有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州解救柴进,击败呼延灼又攻打青州,大闹华山救出史进鲁智深,芒砀山收服樊瑞一伙。这一系列征战晁盖都不在场。宋江上山以后,晁盖就没有什么戏码了,唯一出场是攻打曾头市那次,可是一上阵就挂了。不消说,这些正是小说家扬宋抑晁的春秋笔法。
过去有一种意见,有谓宋江上山后蓄意架空晁盖云云,将小说叙事旨意视为宋江本人的手段,实为牵强之说。宋江旨在以江湖道义重述儒家仁义忠恕,哪里会施出这等手段?从水浒故事的起源和衍变来看,宋江的地位不容置疑。水浒元故事显然与史籍中“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的记载相关,而晁盖的名字根本不见于史传。其实,早先在水浒故事雏形的《宣和遗事》里边,宋江就是梁山泊寨主,晁盖则在玄女天书的三十六人名单中,那些人统属宋江麾下。天书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再看现存几部元杂剧水浒戏,晁盖作为亡故的寨主只是被提及,而并未出场,可能在元剧时期就被摘除了。到了《水浒传》这儿,三十六人扩展到一百零八人,晁盖却不在其中,小说家是有意将他处理成过渡性人物。在《水浒传》成书之前的水浒叙事中,晁盖原本就没有多少故事,故而被整合到书中这个人物只能作为陪衬角色。
晁盖弥留之际,当众吩咐宋江:“若那(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不啻剥夺了宋江继位的合法性。后来卢俊义捉得史文恭,宋江要让卢氏坐头把交椅,很难说是存心谦让,还是不得已的表态。当然,以宋大哥的威望,兄弟们不可能另择他人。
五

《癸辛杂识》〔宋〕周密撰 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97 年版
水浒人物中,宋江的身份很特别。作为郓城县一名衙吏,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又好习枪棒拳脚。他在乡下有庄院,又在江湖上广结人缘,且年逾三旬不置家室(阎婆惜并非妻室)。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行事方式,不像是要安安稳稳过小日子。想想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那个著名的排比句:“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如果一直排下来,则有宋江举于庄院和抄事房,在小说家看来,排到跟前就该是他了。纵观历朝历代,多半是像他这样苦其心志的乡镇青年主导历史走向。
小说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有一处介绍耐人寻味。济州府干吏何涛来郓城县捉拿晁盖等人,先找当天值日押司,正巧在县衙对面的茶坊碰见宋江,书里说:“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作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蹊跷的是,宋江排行第三,却不见说上边两个哥哥,只提及弟弟宋清。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太史公笔下汉高祖刘邦隐晦的排行。《史记·高祖本纪》避刘邦名讳,单称字“季”,乃暗指刘邦排行第三。司马贞《史记索隐》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则季亦是名也。”故元人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曲干脆以“刘三”直呼高祖。这宋江被命名排行第三,不知是否比附那个伟大的刘三。有意思的是,征方腊归来,小说里也专门写了宋江还乡的一幕。
然而,宋江毕竟不是刘邦,他要做的是摧陷廓清,而不是改朝换代。南宋龚开(圣与)所作三十六人赞序,被认为是关于宋江的早期传说。赞序中第一个说的就是宋江,有谓:“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讳忌。”(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不知为什么,宋江的传说一经流行就定下了“不假称王”的基调。以江湖身份干预国家政治生活,俨然保乂王家的“不二心之臣”,这恐怕是当日士人所构想的一种角色。
宋江之造反,不同于陈胜吴广,更不像刘邦那样自立基业,而是打算在原有的王权框架内除弊兴利。
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刘邦,面临“天下苦秦久矣”之局,改朝换代自是必然之势。《水浒传》描述的社会状况则完全不同(那几乎就是一个丰裕社会),忧患一小半来自夷狄,更多的是来自当朝奸佞—冠屦倒施,纲纪废弛,意味着最大的社会问题在于缺乏公平与正义。所以在宋江看来,重要的是如何“去邪归正”,调整体制内的各种关系,而不是打碎旧政权再另起炉灶。
按书中描写,梁山军事力量屡压官军,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要推翻赵宋王朝似乎不在话下,至少亦足以建立一个地广人稠的割据政权。当然,这样推演完全脱离了历史背景,北宋政权不曾面对如此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更未亡于内乱。小说如此夸大山寨实力,显然是为了创造梁山泊与朝廷对话的可能性,亦在于强调宋江之忠义与不二之心。第八十回中,梁山泊击溃十路节度使进剿,还捉了高俅本人,由此展现宋江以德报怨的宽厚襟懷,表明与朝廷合作的诚意。忠义堂筵席上出现了燕青与高太尉厮扑争交的一幕,则是将绿林与官家置于同一平台的政治隐喻。这种意念性叙事是针对历史或然性的另一种推演。北宋末年何曾出现宋江这样的人物,小说塑造这样一个颇具王者风范却并不觊觎王位的造反者,实是表达改良政治的构想。如此设事,亦乃宋元以后士人反省历史的一种认识。
早年在咸阳,刘邦目睹秦始皇出巡的威仪场面,不由叹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在会稽,项羽直视车上那个远去的背影,忍不住要说:“彼可取而代也!”太史公放眼艽野荒陬的风雨雷霆,刘项之辈放言彼可代之,实是一种初始化的英雄史观。
在江城,在浔阳楼上,宋江眺望夕阳西沉,感恨伤怀之际在粉壁上写下被认为是要谋反的诗句:“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是表白什么?说是谋反并无根据,黄巢绝非他心目中的英雄,宋江蔑视那种成事不足的揭竿而起。日后上了梁山,他的目标是以江湖道义矫正伦纪纲常,补苴体制之罅漏,而自始至终可见“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卓绝之迹。小说借此表达了一种特别的英雄史观。
六
小说第六十回,晁盖死后,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一大关目。宋江的目标是要将江湖道义投射于“辅国安民”的政治轨辙,具体说来就是走招安路线。之前,闹华山那回,为赚取御赐金铃吊挂,梁山众人将奉旨降香的太尉宿元景劫到少华山,宋江想起玄女娘娘有言“遇宿重重喜”,趁机向宿太尉传递了等候朝廷招安的意愿(第五十九回)。作为当朝主抚派大臣,宿太尉日后对促成招抚梁山泊起到了重要作用。至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后,招安终于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寄希望于高俅促成此事不啻与虎谋皮。从山林走向廊庙是一个颇为艰难的过程,不仅御前一班奸佞竭力阻扰,梁山内部亦是阻力重重,此中曲折不遑细述。
大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水浒的讨论产生了诸多话题,对招安一事更是多有訾议。批评者究诘所谓“投降主义”,自然是基于一种预置的主题论,即《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让梁山好汉皈依朝廷,无疑篡改了造反者的正义叙事。早先,金圣叹腰斩水浒,是因为招安乃使强盗从良,这又翻了个个儿,成了英雄失节。一反一正,都完全固着于“汉贼不两立”的历史经验。
其实,这部大书既非描述农民起义,也不是一部具有史实依据的历史小说(不说别的,宋江事略见诸史书只是一鳞半爪,其他梁山人物更是于史无征)。而且,它不能说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其叙事逻辑完全出于超越历史经验的某种构想。
说起来招安的名声确实不大好,这不仅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按民间常理也是一种“认怂”。江湖上讲究恩仇快意,革命斗争是你死我活,梁山好汉如此自毁前程确实让人心意难平。按小说描述,招安的结局最终是一出悲剧—梁山泊的江湖道义不仅未能改变官方的政治腐败,为朝廷攘外安内南北征战之后,到头来宋江、卢俊义还是死于奸佞之手。单就这个悲剧事况而言,其叙事逻辑倒是未能摆脱“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经验。
可是,如果不走招安道路,这故事就很难往下写了。既然,梁山泊实力如此强大,加之道义优胜,取代大宋王朝自是势在必然。真要按李逵所说,宋大哥做皇帝,卢员外做丞相,岂不成了毫无依凭的悬空叙事,那就太过离奇。其实,后人续貂的《水浒后传》就是相似的思路,不过那是去海外谋取王业,而非在国人悉知的朝代序列中强行加塞,倒也无甚大碍。其实,如果真正要显示梁山泊的反抗与斗争精神,自然也有合乎经验和逻辑的写法。那就是让这个江湖武装团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且又死心与朝廷硬磕,或因内部分化而出现变故,最后被官军剿灭,也算是虽败犹荣。当然,那就不是《水浒传》了。
梁山泊叙事(尤其是作为“小水浒”的个人叙事)固然具有反抗意义,但这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究其指归,整个作品的主旨,乃挣扎于愤懑与无奈之局,找寻出路而已。反抗只是一个方面,反抗之后如何,才是最终的命意。小说家采撷林林总总的江湖叙事而结撰成书,更多是着眼于救赎之义—梁山泊的救赎,宋江自身的救赎,乃至王权体制的救赎。当然,小说并不能给出光明而稳妥的道路,只是从“伏魔殿”扃闭的殿门被打开,儒家政治伦理根基开始动摇之际,个人或江湖群体的反抗叙事便有了重新定义的可能,按书中所述,亦即试图以治国平天下的名义找到出路。
所谓“替天行道”,首先是获得以江湖地位干预国家政治的话语权,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想象。书中搬出九天玄女,以神道设教,是在君权王权之上确立良知与道义的地位。
七
毫无疑问,按通常文学批评标准,宋江是《水浒传》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其性格承载最为丰富,既有厚度,也有深度。但不可否认,这个人物并不讨人喜欢。不仅是由于招安的缘故(招安沦为悲剧有些自作自受的味道,亦且缺乏悲壯感),更有性格原因。
明刊容与堂本有李卓吾评骘梁山人物优劣,认为宋江“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确实有些猥琐相。另外,也有“长厚似伪”的问题,鲁迅对《三国演义》的刘备就有这样的批评,宋江亦大抵如此,尤其是一再要让位卢俊义,难免给人做秀的感觉。不过最主要的是,他缺乏英雄人物的果敢、威猛气质,而且作为山寨统帅,偏生武艺又不出众。这样说好像纯然出于孩童的游戏趣味和判断标准。其实,这恰恰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对于《水浒传》这样内涵复杂的作品,早期阅读的理解程度和喜恶倾向是否会形成审美心理上滞留长久的片面印象(据笔者有限经验,大多数人初次阅读《水浒传》是在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江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天子身边那班奸佞依然一个不少,征方腊归来被朝廷打发去楚州做个无所事事的安抚使,多少有些嘲弄意味。旧小说中被人崇敬的英雄,不是豪迈爽直的勇武之辈,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厉害角色,宋江却不然。其一生忍辱负重,终竟未成大业,梁山泊由辉煌到寂灭只瞬息而已。
可是宋江认了,他早有盘算,上山就是为了下山。
二○一九年一月七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