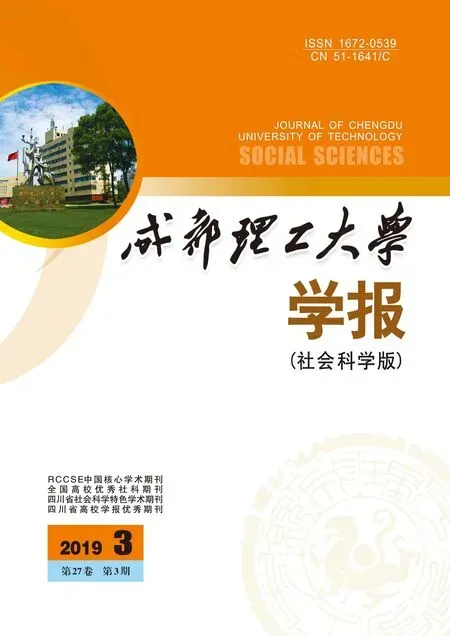文史对话:《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新历史性
李 静, 何 敏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1731)
一、引言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哥大史》)是由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当代美国多位知名汉学家共同编纂的一部西方视角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于200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西方汉学界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的经典读本。
《哥大史》的问世有其深刻的意义。第一,《哥大史》弥补了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的空白。它不是对中国文学经典的编译,而是“为中国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主题建立一个诠释体系的尝试”[1]Ⅲ,这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门。第二,虽然“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美国的学生”[2],但通过审视异质文化看待中国文学的视角,可促进中国学者看待中国文学史思维的变化。“撰写文学史是一次远游,不仅是去到异于当下的历史时间中的远游,更是去到异于已有文学史的叙事空间中的远游”[3]128,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深入到西方视角看待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史,实则也是一次“远游”。第三,《哥大史》突破了传统中国文学史编纂方法的常规。如,传统的中国文学史按照朝代的时间分期进行编写,《哥大史》采用的却是朝代与主题相结合的编纂方式,“希望在一个全景式的年代框架下,进行主题式的探索”[1]Ⅷ。这样的方法能够让更多的边缘文学发声,给予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可能性。《哥大史》的编纂工作历经十年,即1990—2000年,正处于新历史主义思潮兴起的大背景下,其编纂思想也受其影响。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理论学派,“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观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4]23,以其先锋姿态尝试实现对旧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不赞同旧历史主义以统一的历史背景来规约文本,也不赞同俄国形式主义一直以来把文学当作自律自足的个体的批评方法,它认为历史与文本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相互对话。其代表人物有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正如格林布莱特反复强调,新历史主义“没有单一的研究方法,统一的图景,也没有详尽的,被定义的文化诗学”[5]19。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新历史主义内部各个理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新历史主义呈现如下特点:(1)打破了文学与历史的二元对立,强调史中有文,即历史的虚构性;文中有史,即文学也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文化具有了文本的特征”[6]385。(2)认为历史是人为建构的,这种建构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的操控,即“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3)“一切文本(文字文本与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7]51,同时文本又参与历史的建构,即“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分析《哥大史》中的新历史性,认为《哥大史》将文本概念延伸到文化与社会历史背景,研究对象十分广泛,这与新历史主义把文化看作可被解读的对象之观念不谋而合。《哥大史》解读中国文学史,在对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读时,洞察到了产生这些文本及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让历史与文本互文。更重要的是,哥大史对于边缘文学的关注重新建构了中国文学史的面貌,为其又补上一块拼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这体现了《哥大史》文本的历史性。《哥大史》虽尽量展示中国文学史的原貌,但具体要解读哪些时期,哪些作家,哪些文学,哪些社会背景,其中的选择背后必定暗含一种话语,中国学界对于这部文学史的接受,也暗示了当前中国学界研究视角的转向,这展现了《哥大史》历史的文本性。将文本概念泛化,细读文化,是实现文史对话的前提,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两者无法截然分开,在这样的视角下,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建构也就实现了相互对话的效果。
二、广义的文本对象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将研究对象从原本的书面文本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广泛的社会存在,主张超越文学研究,注重文化研究。维瑟尔(H. Adam Veeser)曾对新历史主义进行尝试性地总结,其中一点便是“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没有不同”[6]384。正如孔凡娟所言,“新历史主义又把文本泛化,把历史、文化也当作各种不同的文本来对待,它们是不同于文学文本的非文学文本(社会性文本)”[8]182。《哥大史》广义的文本对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它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包括语言、宗教、民族和阶层关系等,并探究了这些关系内部的文化因素;第二,它把文学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文本进行解读。
(一)作为文本的社会历史关系
《哥大史》不囿于传统中国文学史中对文学文本的节选与解读,研究对象十分宽泛。语言文字、思想与宗教的关系、精英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他们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在《哥大史》的解读范围之中。第一章的《语言与文字》,就对作为中国文学基础的汉语汉字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一章详尽地阐述了作为汉字的文言与作为汉语的白话的区别,虽然“中国文学在语言学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区别。但这二者之间的边界很模糊,因为它们相互借鉴”[1]27。中国文学可大体分为文言文本与白话文本,《哥大史》作为一部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梳理的著作,对形成中国文学的这两大类文本进行探究无可厚非。但它对没有发展为文学传统的地区性白话也进行了探讨,则可见其雄心——《哥大史》不仅要展现语言文字所反映出来的文学传统,更要解读其内在的文化传统。《哥大史》呈现了这一事实,即在古代中国文学格局中,没有史诗,神话类文学极少,并认为形成这一文化格局的重要原因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字优于言语。文言文本在文字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比如,官方白话作为一种言语,即便得以进入文学文本系统,在古代中国文学书写的地位还是逊于文言文本。再比如,从形式上说,白话文本中夹杂了大量文言,文言文本却几乎不含白话杂质;从时间上说,白话写作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兴起的,没有文言文写作那样拥有那么悠久的传统。从《哥大史》如何解读文言与白话可以看出,《哥大史》不仅限于对文学传统的呈现,它更偏重于解读其内在的文化要素。
(二)作为文本的社会历史背景
《哥大史》把社会历史背景当作文本,注重对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进行解读。其在介绍文学文类时,几乎每一章都要对其萌芽、发展、巅峰以及消亡或融合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阐释。由于其基于文类划分的编排方式,在部分章节出现重复解释乃至分歧。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以文学作品节选为主,而《哥大史》注重文本解读。其在引言中坦言:“中国文学史中的大部分还是基本上以翻译和节录为主,解读只占很小的位置”[1]Ⅲ,所以其写作目的必定将文学文本的解读放在首位,且解读的角度注重社会历史背景。《哥大史》把产生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当作其研究对象,这一定位招致美国学界的批判。“缺乏连续性和整体性,有些章节甚至自相矛盾,或者相互重复,而这些漏洞都没有被总编辑注意到或做出处理。因此,这本书变得好像不是一部‘文学史’,而是一部‘论文集’。”[9]2对于这样的批评,梅维恒在《引言》部分进行了回应,“我并不坚持观点的绝对一致性,我坚持的只是论据的严格组织”[1]Ⅷ。所以,梅维恒在意的不是对文学现象的呈现,而是对这一特定文学现象背后复杂文化因素的挖掘和解读。梅维恒应能预见到缺乏整体性这一问题,但是他也坚持,若是要对社会历史原因进行解读,“一些观点或者诠释上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个观点都揭示了这一复杂多面问题的一个或者多个层面”[1]Ⅷ。如果《哥大史》不是将文本对象扩大到社会历史背景这一广义层面,美国学界或许对这本中国文学史不会有那么尖锐的批判,但也会因此失去它最大的特色。
综上,可以看到,《哥大史》的文本对象已超越文学文本,注重非文学文本。超越文本细读,注重文化细读。这体现了《哥大史》文本对象的广义性,也是新历史性的表征。赋予文化以文本的特点,这既是新历史主义的起点,也是《哥大史》的起点。
三、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看到了文本与其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也主张文本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的建构。不是像旧历史主义那样,抛却文本的特殊性,认为文本只是对历史背景的被动反应。新历史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文本的历史性,即文本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是“它们本身会再次成为对其他文本进行阐释的中介”[7]51,参与社会历史的建构。因此,在新历史主义批评中,文学与历史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其注重的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动态交流。《哥大史》的视野“从其发轫期到当今的中国文学史全景”[1]Ⅳ,每一章在论述某一文类时,必谈到其时代背景。梅维恒认为,“文学不是自在自为之物,而是社会政治的力量和文化事实之无尽序列的产物”[1]Ⅴ。这一编纂思想贯穿全书,是以每一章的论述都不免谈到其时代背景,包括政治力量、经济实力、技术发展、文化氛围等。更为重要的是,《哥大史》关注了边缘文学,如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等,这对于还原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参与了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
(一)贴近历史背景
正如新历史主义对于文学的理解一样,《哥大史》“将中国文学视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存在”[1]Ⅴ,不停地阐述社会历史背景对文学的影响。导论部分就先行讲述了中国社会“文人文化”的起源对中国文学风貌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巨大思想内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才在中国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文”以及“文人”何以在中国古代备受推崇?《哥大史》把文学和政治联系到一起,从文与仕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在中国古代,精通文章写作的知识分子能够出仕,成为很多人开启政治生涯的不二选择,这一传统从汉时甚至更早朝代就有了。受此影响,文学形式和内容为政治所塑造。形式上,文学类型大多与政治活动有关;内容上,强调“文以载道”,即文章的社会责任。很明显,《哥大史》认为文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更具体的例子也体现在第16章《宋词》中。第16章的编纂者傅君励从政治经济以及技术发展等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宋朝在政治上完成了中央集权,但同时受到北方两个外族的威胁,政治改革多发;在技术上,印刷术兴起;在社会阶层上,士大夫阶层崛起,“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为宋朝的诗歌发展烙上了直接的印记”[1]340。这些例子再次印证了梅维恒所说的“文学不是自在自为之物”,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纯粹美学(为艺术而艺术)发展缓慢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哥大史》看到了这些文学文本身上的时代烙印。
(二)还原历史背景
《哥大史》文本的历史性不仅体现在它把文学看作社会历史的产物,更体现在它还原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参与建构了中国文学史。旧历史主义的叙事是宏大的,这掩盖了主流话语之后的声音。长久以来,我们把历史看作连续的、唯一且权威的存在。但是,新历史主义试图发掘宏大历史背后的边缘话语,认为历史是“小写的”“复数的”。《哥大史》的编纂思想跟新历史主义一样,把中国文学史看作“小写的”“复数的”历史,而不是粗暴地按照朝代进行定性。“书中对长久以来被轻视或者忽视、但是对深度理解中国文学十分重要的一些方面作了特别的强调”[1]Ⅷ。它按照年代与主题相结合的编纂方式也让其得以重新审视未被主流文学史注重的边缘文学,对“边边角角”的挖掘与重视解构了主流文学史的权威。《哥大史》在第七编单独开出一编对边缘文学进行梳理,这是极其罕见的,充分显示了《哥大史》挖掘边缘文学,参与中国文学史建构的决心。在最后几章中,《哥大史》探讨了民间文学以及周边文学,论述了很多中国文学史都不曾提及的精英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少数民族的文学和口头文学,甚至还专门探讨了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
《哥大史》第一次给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书写开辟了篇章,“中国文学研究中另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是对女性文学及其地位的再诠释”[1]15。《哥大史》单独为文学中的女性开辟了一章,在“口头文学”一章中也出现了她们的身影。白安妮编纂的“文学中的女性”这一章比较全面,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数是男性权力的附属,如反映在部分《诗经》《史记》中的女性形象比较负面,《水浒传》中对受虐女性的暴力描写更加触目惊心。白安妮对这一事实并没有回避,但也强调了女性形象建构的另外一面。即在南方楚地,“女性是精神和肉体的完美体现,是不可企及的愿望的概念化之对象”[1]200,这在《红楼梦》中达到顶峰,其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哥大史》对于中国古代女性形象的历史还原比较全面。在这章中,也涉及了女性作家的自我书写,不被主流文学史看重的女性作家作品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重视,女性文学历史得以重新建构。《哥大史》正是在对文化边角的挖掘之中重构了中国文学史的面貌,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
《哥大史》看到了文学被社会历史建构,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必定染上浓厚的时代气息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哥大史》通过对边缘文学的解读与挖掘参与了社会历史的建构,实现了文与史的动态交流,他们相互建构,在此过程中得以进行对话。
四、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的文本性是新历史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即历史是主观人为建构出来的历史,但这种建构背后隐藏的实则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历史是一种建构,“不管这样的历史如何真实,背后总有编写者的目的,总有更大的意识形态语境”[6]387。 因此,透过文本我们能窥见被选择文本对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以上我们已经说到《哥大史》挖掘了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如女性文学、民间文学等,为中国文学史本来的面貌又补上一块拼图。这样的选取方式必然体现了《哥大史》背后的意识形态,有对中国文学的重视,有对女性文学的关注。反言之,《哥大史》时隔15年才得以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视角的转变。《哥大史》对于文章主题的编排和选择体现了怎样的意识形态?中国学界对于《哥大史》的接受又体现了怎样的研究风向?
《哥大史》的编写以及出版是在21世纪初,中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背景下展开的。正如序言中谈及编纂背景所言,“越来越多的东亚裔美国公民开始对自己原民族文化遗产感兴趣,许多人希望能够读到一部全面而且目标多元的中国文学史”[1]Ⅶ。无疑,在中美文化交流日渐火热的背景下,《哥大史》的出版是国学热下的产物,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10]154。《哥大史》实现了对传统中国文学史编纂体例与内容上的双重突破:在内容上,《哥大史》最后几章中谈到朝鲜、日本和越南对中国的接受,这是从前的中国文学史未曾涉及过的话题,给海外学者了解这部巨著提供了契机。在体例上,按照西方的文类划分法,将中国文学按照诗歌、小说、戏剧等进行划分,便于西方读者接受。据梅维恒所言,这本书的初衷是“为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出版的,但它的受众也包括在美国读书的、想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其他学生”[2]。这部书实现了这个初衷,宇文所安评价它“全面呈现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为读者了解广大而又复杂的中国文学世界提供了最佳门径”[2]。中美文化的频繁交流让更多人注意到东方这座文化宝库,无论是华裔还是外国人,都有了解中华文化愿望,这让《哥大史》的出版成为必然。
《哥大史》在中国学界的接受反映出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转向,其试图在西方人眼中找到一些自己未曾发现,或者说未曾重视的边缘文学。2016年,《哥大史》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从2001年到2016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哥大史》因何隔了15年才从西方传到东方?这背后一则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海外视角的关注,以及想要通过异域视角,从不同方位了解中国文学的强烈愿景。二则,《哥大史》的重新发现与另外一部巨著《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史》)的发行不无关系。《剑史》英文版于2010年出版,时隔3年便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作为一部由海外汉学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巨著《哥大史》当然会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三则,《哥大史》与《剑史》都涉及中国学者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以女性文学为例,图1~3是在CSSCI与北大核心数据库中以“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

图1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图书学术发展趋势曲线

图2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期刊学术发展趋势曲线

图3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学术论文学术发展趋势曲线
根据数据可看出,我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日渐关注。图书发行在2014年之前虽然有波动,但不甚明显。2014年是一个分界线,出现一个高峰,虽然2015年、2016年有所下降,但在2017年开始回暖。期刊论文从2005年开始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并在2010年井喷,此后的年份比较稳定。关于此主题的学位论文也在2005年之后开始猛增,到2015年的十年间一直居高不下。总的来说,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的关注度在2005年后持续增长,是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两本来自西方的中国文学史,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热门话题进行了探讨,因而广受欢迎。《哥大史》虽时隔15年,却最终在中国得到翻译与出版,这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转向。
《哥大史》尽量做到还原中国文学史本来面貌,但跟任何书面记录一样,是一种主观书写,是编纂者对客观事实的再加工。如在对张爱玲和鲁迅的取舍中,梅维恒个人就比较偏爱鲁迅,给予了他很大篇幅,对于张爱玲只是简单提及。《哥大史》对于主题的确定和文章的选择,体现了其历史的文本性,也体现了它背后的意识形态。中国对《哥大史》的接受也体现了内在的意识转变,即中国学者对研究中国文学视角的转变。《哥大史》是主观与客观的交汇,落脚点既在文学,又在历史,文学与历史相互建构,再次展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动与交流。
五、意义与局限
“文化模子的不同,必然引起文学表现的歧异。”[11]3《哥大史》是美国汉学界的集体编撰成果,编者来自美国知名汉学机构,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之大成。美国汉学家生长于异域的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学者有不同的学术传统,因此,《哥大史》必然呈现出“他者”风貌,具有鲜明的美国汉学特色。在当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国家文化战略大背景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有如下意义:
第一,《哥大史》的出版便于西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20世纪中期,美国成为世界汉学重镇,60年代出现了三本华裔学者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为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述》(1961)、赖明的《中国文学史》(1964)以及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1966),但它们都只概述了部分作者感兴趣的章节,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学史的全貌。《哥大史》是美国汉学界第一部完备的中国文学史巨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文化,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契机,帮助他们深入到异质文化中“远游”。
第二,《哥大史》在游览中国文学史这幅宏大画卷时,深入到历史与文学的边缘,为中国文学史补上了新的拼图,如女性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周边文学等,是对还原中国文学史真实面貌的有益尝试。同时,它又给予了中国学界和中国读者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性,是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的有益补充,“颇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他者视角,亦是中国学界与海外汉学往来相长的一件幸事”[12]2。
第三,《哥大史》消解了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即文学具有了权威性,可以当作还原历史的材料,历史具有了虚构性,可以作为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哥大史》作为对中国文学史的记录,可以当作文学文本进行解读,从中看到编纂者的偏好,看到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同时,它也可作为还原中国文学史的有效材料,把我们的目光延伸到边缘文学上。这一特点帮助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了文学与历史的对话。
当然,《哥大史》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被诟病最多的即“缺乏整体性”,这与它基于文类分类的编写体例有很大关系。每一章的撰写者确实都是非常优秀的汉学家,也正因为如此,不可避免,对同一个文学现象的阐释会出现多样化,有些观点甚至针锋相对,也无怪美国汉学界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次,虽然梅维恒尝试尽量做到全面,《哥大史》的主观性依然较强,这不利于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全貌。如梅维恒个人比较偏爱鲁迅,这直接影响到对鲁迅介绍的篇幅占比。最后,《哥大史》的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如第六编,它将注疏、批评和解释作为独立文类,这十分勉强。在十四章介绍完唐诗后,紧接着十五章介绍词,十六章介绍宋词,元曲与元诗也是单独成章,显得有些混乱。
文学史本是来自西方的学术术语,从属于西方的知识体系。文学史的书写是将对中国的文学史料以“文学史”之名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寻求其内在联系,本质上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学史料纳入西方的现代术语。仔细考察《哥大史》中汉学家的书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不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增益关系,而是文学史本身与书写者立场的引力结合。中国文学史的整个起转承合发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上,有其完整的系统与内在逻辑;而汉学家的文学史构建立足于西方的学术话语系统与文学传统,其学术背景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并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
虽有种种不足之处,然瑕不掩瑜,不管是对海外读者,还是对中国读者,《哥大史》带来了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的可能。它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了文学与历史的对话。汉学家们突破国别文学的界限,将中国文学投射进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中加以探究,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范畴之内进行文本比较和分析。他们延伸了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在21世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于推动中西文学交流有着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