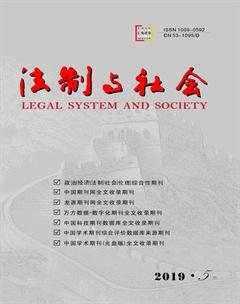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挑战与前景
摘 要 当前印太地区的安全图景显现出高度不确定和潜在张力。战后以美国为首的以扩大威慑和遏制的具体保障为基础双边同盟网络现在正逐步让位于构建更加多样化的阵营和联盟,以管理日益复杂的一系列区域安全问题。多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已成为这种合作的两种日益突出的形式。即便在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小多边主义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依旧吸引了体系中对多边主义持保守态度的行为体。然而,该地区的小多边主义的发展仍不充分。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此机制的看法也不明确,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意图和作用仍需要重新定义和澄清,当然,这与“印太”以及“小多边主义”仍然是一个在构建中的概念有关。我们要认识到,“印太”概念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所构建的专有名词,中国的发展和利益决定了要对“小多边机制”构建提出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并采取理智和有效的行动,更好的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 亚洲权力网络 小多边解决方案 三边主义 辐辏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强化与中国的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YJCGJW012)。
作者简介:岳小颖,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亚太安全研究。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5.165
一、问题的提出
有效管理印太地区安全业已成为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最迫切需要。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如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的安全困境以及大国博弈和权力变迁的广泛战略影响非常明显。移民、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恐怖主义、贩毒、网络犯罪、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关注并影响其国内政策议程。如今印太,这个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政策的不确定性,构筑了更加复杂和潜在紧张的战略格局。这种战略图景由于战后美国的同盟和非结盟的合作伙伴的变化而日趋复杂化。战后美国构筑的“轴心—轮辐”同盟体系针对特定威胁和议题形成了更广泛的安全联盟。当前,东北亚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传统上不结盟的行为体如印度,包括东盟各成员国正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的印太地区探索与推进和其他各国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俄罗斯也希望在亚洲不断发展的战略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区域安全合作与竞争共同加强的背景下,两个趋势值得关注。首先,在未来印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中,中国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各种问题和危机的处理中,該地区的海洋国家,比如美日澳印与中国进行合作或竞争的程度,将决定该地区未来最终形成何种具体的区域安全秩序。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不仅体现在有效化解朝核危机、南中国海问题,而且彼此的合作程度是避免地区性冲突和战争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当前中美之间的多种分歧,使实现这些目标最终并不一定形成“共同安全”模式,也不一定构成中美两国关于区域危机管理的妥协,很多关键区域反而会成为冲突的爆发点。
第二个趋势是自1951年9月《旧金山条约》签订以来,美国战后双边安全同盟体系已经开始演变为一个不那么层次分明以及更具柔性为基础安全协作。冷战期间这个亚太同盟网络的独立成员国在五角大楼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指导下通力合作以遏制中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导致美国同盟体系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冷战后朝鲜对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可信度的强烈挑战,该战略依赖于对手的“理性”的传统假设,以确保将地区危机升级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朝方激烈的言辞,比如威胁要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使华盛顿和纽约遭受核袭击,将首尔和大部分韩国吞没在“火海”中。它确实在该地区引入了一种核边缘政策的政治因素。与之相对,美国的措辞和军事姿态亦复如是。2018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下,高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转圜。由于美朝在解除制裁与弃核步骤上分歧仍存,美朝首脑会晤后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美韩军演,以及国际社会并未解除的对朝制裁,这给美朝关系前景蒙上了阴影,日韩两个美国盟也面临地区安全的复杂挑战。2019年2月,美朝领导人在越南举行会晤,美朝在今后能否进一步建立互信,使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取得进一步突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其次,第二个因素主要源于第一个因素,即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国安全议程变得多样化,而且彼此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与韩国相比,日本似乎更多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在没有美国协调的情况下,日韩两国也难以达成实质性的双边合作。韩国现任政府明显倾向于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处理与对朝关系。作为一个位于亚洲的“西方”国家,即便澳大利亚不面临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现任政府依旧与其前任政府一样担忧,担心在中国实力日益上升之际,战略上和文化上被“强大而有力”的美国朋友抛弃。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认为另外两个盟友菲律宾和泰国的政治精英挑战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和程序,国内的政治趋势产生了社会混乱并破坏了民主。后来,随着印太地区大国权力斗争和均势产生的微妙变化,尽管面临着美国传统安全保障可能会丧失的危险,菲泰都与中国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几乎没有解决泰国和菲律宾对美国外交政策越来越体现出孤立主义倾向的担忧,东南亚也被排在美议事日程的后边。
印太地区保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免受外部国家威胁以及有效管理大国竞争带来的影响等传统安全议题显然增加,其紧迫性也在加剧。 这使美国及其盟友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特朗普政府公然蔑视气候变化政治、削减支持粮食援助的预算、减少国际卫生项目的资金等,都突显了传统地缘政治在其政策议程中的核心地位。2017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简要论及其他新出现的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和网络空间威胁。然而,它在更广泛的美国本土安全背景下这样论述,也与特朗普经常宣传的“美国优先”姿态一致。此外,《国家安全战略》只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形势做出简要表述,将其视为“自由或者压迫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表现,并通过加强与盟国以及新的安全合作伙伴的防务关系得到最好的解决。
《国家安全战略》还强调美国需要通过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和重振双边贸易安排(将其置于泛区域经济和外交工具之前)和“促增长”来支撑其作为印太大国的经济增长。它设想美国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一个致力于自由市场的国家网络,并保护其免受破坏其主权的力量的侵蚀。在这个非常广泛的框架内,这种方法很可能包含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政策工具,多种形式的安全网络去解决上述议题。各种形式的多边主义,特别是小多边主义,现在正在与传统的旧金山体系的形势在印太地区的秩序建设中形成竞争。了解这些安全组群是什么并评估其有效性,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地区的多边安全政治。 所以本文致力讨论的问题是,各种形式的多边主义,特别是小多边安全合作特点是什么?与多边安全合作的异同是什么?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国应如何应对?
二、核心概念的厘定
首先将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简要的界定。多边主义“就其定义来说,主要是指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这些原则是规定合适的行动的,并不考虑在任何特定事件下各方特殊的利益或者战略紧急情况。多边主义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组成的国家团体的政策,还在于它是在调整这些国家间关系的一定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协调活动。 作为一种社会性安排,多边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协调性行为活动实现共同利益。约翰·鲁杰认为,多边主义在制度性方面主要具备三个特征。第一个是“不可分割性”。多边主义的参与国在相关事务上把自身视作总体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意适用于每个国家的原则,并用于知道自身的决策和行为,国家之间通过协调性行动来共同追求最大化利益,从总体上而不是仅考虑自身或局部来权衡国际交往的利弊得失。 第二个是“普遍性行为原则”。每个国家行为体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而遵循的行为原则可以被理解为包含国际规则、国际规范以及决策程序等要素,每个国家行为体在一定行为原则的指导下,协调行动,最大程度地平等参与。 第三个是“互惠的扩散”必须发挥作用。在以多边主义为原则的国际规制框架下,“成员国总是预期所达成的协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总体上带来大致相等的收益,取得秩序性的联合收益,而不是在互动过程中以抵偿的方式寻求收益”。
与之相对,小多边主义是一种范围更小的(通常是三个或四个国家)在限定的时间内处理、解决特定的威胁、突发事件或安全议题方面分享相同的利益。目前学术界尚未就如何在国际安全背景下精确定义“小多边主义”达成共识。迈尔斯·卡勒认为,冷战后时代,当较大的集团变得过于笨拙或者与国内政治利益产生分歧时,“规模较大”的集体行动的形式之外开始出现多边机制内的“较小规模”、更為非正式的集体行动形式。布拉德·格劳瑟曼和斯考特·施耐德将其界定为“经过修正的多边主义的变体”,致力于增加合作参与方之间合作能力和可能性的“小多边的解决方案”。 维克多·查认为,小多边安全合作的三个主要特征是:1.相对于多边安全集团,参与者数量较少;2.这种安全群体具有临时性的特点,由于没有制度遗产,会临时形成和解散;3.关注的重点是传统安全议题。
双边主义、三边主义和四边主义是由多边或者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国家行为体的数量来定义的。双边主义是两个国家在给予对方优先待遇的基础上合作,根据共同利益实现排他性的独有收益。 这种合作可以体现在正式条约中,也可以非正式地进行,这取决于要解决的共同威胁或共享的安全利益。三边主义处于双边关系和更广泛的多伙伴安排之间,使其成为最小的多边主义形式。 四边主义涉及四个国家之间的对话和不间断的实质性合作合作(例如军事演习或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等行动)。四边主义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联系在一起,例如那些分享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去制衡实际的或潜在的敌对力量。
三、作为多边安全变体的小多边主义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东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等多边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但并未实现其目标。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地区论坛(ARF)和2005年东亚峰会(EAS)的成立,该地区开展了更加全面的多边安全对话。不过,ARF和EAS都没有满足一个可行的集体安全机构的三个先决条件。例如,如果在尊重普遍的行为原则和追求国家自身利益二者选一的话,国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如果各国认为他们在区域或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几乎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就无法指望他们通过互惠的扩散来实现“漫长的角力”,或者以战略克制的方式去遵守组织原则。
在战后的欧洲,过去破碎的历史和大战的遗产加强了地区领导人建立旨在保障欧洲经济繁荣和集体安全的多边规范和制度的动力。与之相对,亚洲国家并没有相应的历史经验。许多亚洲的主权国家是战后非殖民化进程加速的产物,许多领土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摩擦造成了深刻的安全困境。正如约翰·鲁杰观察到的那样,大国均势以及双边同盟体系是亚洲安全政治的主要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将小多边主义视为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多边主义的有用变体。然而,小多边主义的可行性取决于,在将旧金山体系转变为更加具有流动性和复杂性的区域安全网络过程中美国能否变得更加成功。为了验证这一论点的,首先将讨论印太安全背景下的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将考察迄今为止,美国是否成功地将小多边主义作为美国的印太政策工具去应用。
小多边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内在固有的灵活性,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主自愿而非强制性地履行承诺有关。莫斯·纳姆认为,小多边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种“更聪明,更有针对性的途径......让尽可能少的国家能够对特定问题产生最大可能的影响”。 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在没有其他亚洲安全秩序取而代之的情况下,小多边主义的特点和易管理性被视为当今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可行替代方案。作为其诉求的一部分,小多边主义是自愿的而不是契约性的;其任务是具体的而不是全面的; 通常是区域而不是全球; 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 小多边安全对话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加强了现有双边安全同盟的韧性。在美日韩的联合安全磋商和朝鲜核问题上的协调中,美国从中弥合了日韩传统安全议题上的分歧与差异,信任机制得以构建和加强,这一点比较具有说明性。
小多边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与多边机制相比,更小或更精简的安全组群并不一定在管理任何特定安全问题方面都获得成功。必须保证正确的国家行为体参与小多边安全组群,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机会。美国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朝鲜问题和导弹威胁,在协调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实质性努力,但三边协调和监督小组或TCOG(成立于1999年)仍然挣扎于盟国彼此间的多种差异之中。朝鲜不愿采用其谈判伙伴所要求的方式合作,最终机制解体。第二个问题涉及外部国家对小多边机制实际目的的看法。2007年提出的涉及美日澳印四边倡议,以及其领导人不时提出的“民主国家同盟”就是典型的代表。中国认为,所谓“民主国家之弧”只是北约传统遏制战略的衍生物,主要针对中国。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于2018年再次启动,但鉴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其是否会重蹈覆辙或者比原来成功,目前尚不清楚。
在解决具体问题领域时,有学者认为三边主义似乎比亚太地区的其他小多边变体更具适应性。迈克尔格林认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这种积极的三边主义或许会被界定为不同区域秩序之间的中间阶段。 如果它是正确的,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团体需要超越其目前的比较相对适度的职能,比如低调的小多边对话并进行不定期的军事演习。小多边主义要小心谨慎的在大国竞争与“竞争性多边主义”导致的霸权倾向中继续发展。随着时间的演进,在多边论坛协调或谈判对区域安全问题的解决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小多边主义还需要构建可信的声誉,才能成为沟通、协调和解决地区重要安全议题的渠道。
现实主义者认为多边主义在在处理传统安全性议题时稍显被动。那小多边主义应该发如何发挥作用?为了评估印太地区安全政治中的小多边主义当前和未来的可行性,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小多边是否可在不对称的“轴心轮辐”体系与难以应对印太地区的结构变化的多边主义之间架起桥梁,并探讨小多边主义作为秩序建设机制的作用。
四、多边主义与小多边主义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及其盟友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认识到,应寻求一种合适的方式使“辐辏体系”适应印太地区快速变化的战略环境。它们认为,中国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前美国及其地区安全伙伴面临的安全挑战。凭借其贸易和投资效益,“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均势,美国及其盟国显然需要其他政策方法来对冲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转型。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小多边主义和非正式的双边安全伙伴关系都是这一过程的逻辑衍生物,也是恢复旧金山体功能的一种手段。在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吻合的地区,美国选择建立双边“伙伴关系”。美国与新加坡在1990年签署了一份为期15年的谅解备忘录,授权美国海军有新加坡的海军和后勤空中设施的使用权。美印在2005年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国防协议,随后在军售和联合军事演习方面推动了现在的实质性国防关系。越南与美国的安全关系最近加速拉近,美国与和新西兰的重要防务关系得以持续。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在振兴双边同盟与培育新的安全伙伴关系的同时,开始致力于采用小多边方式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尝试。尽管美国的在印太、中东、反恐方面都有战略资源的投放,但美国在印太地区自愿参与各类小多边计划已久可以与其双边防务安排相媲美。这种小多边合作具有灵活性,并直接针对特定的地区威胁和挑战,没有面临诸如|“同盟的牵连”“同盟的抛弃”等传统的集体防御难题。因此,美国领导的小多边同盟作为旧金山体系双边联盟政治的补充开始发展起来。战后的一些国家与美国建立双边安全伙伴关系,为获取结盟的长期安全收益在一些短期议题上顺从美国的要求。然而,随着该地区的权力平衡及其威胁环境发生变化,这些同盟利益或“公共产品”如核威慑保障和国防技术转让的规模和性质都开始变得更加脆弱。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美国第一”,双边同盟日韩需要负担更多费用,日韩对美国延伸的威慑承诺的传统信念目前正在接受考验。 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两个盟友,由于与奥巴马政府在政府治理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一段时期内与美国关系较为紧张。菲泰同作为东盟成员国,都关注反恐、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美国和其他盟友一起解决此类非传统挑战的小多边联盟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项。比如,美日澳印曾经组建“核心小组(Core Group)”,为印太地区受2004年12月地震和海啸影响的国家提供及时的安全援助和灾难救援。
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小多边安全政治中的一些实践为判断它们的效果提供了可以分析的对象。比如2005年启动的美日澳部长级“三边安全对话”(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是对美日、美澳双边同盟从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协议向采用秩序構建的方式应对日益广泛的国际安全威胁的安排的转变。澳日印三国也发起了三边对话以协调海上安全、反恐战略、区域连通性以的集体安全协作。澳日印有决心维护该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继续”,并担心如果彼此不共同协作,中国最终可能会实施符合中国利益的区域安全治理规则。三国合作逐渐制度化,第四届会议讨论了2017年12月在新德里召开,讨论了印太地区安全问题。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洲之行中首次正式提出“开放和自由的印太”概念,美日澳印四国西太平洋海上合作机制磋商启动。同月,四国在菲律宾马尼拉东亚峰会期间宣布重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就亚洲的基本规则秩序、航海与公海上空飞行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连通性、海上安全、朝鲜问题以及不扩散、恐怖主义等七个议题进行探讨。
东盟构建了本地区的诸多安全机制,由于然而由于国家间缺乏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制度规范去构建类似北约的机制框架。东盟地区论坛关于实现“综合安全”的议程尚未实现,东亚峰会作为地区共同体建设的实际角色仍然不甚明晰。地区性多边组织显然无法坚持各成员国平等的“东盟方式”的原则去解决地区棘手的传统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不對称同盟中的较大和较小的盟友在经历比如不对称性的依赖和资源差异,成员间因为安全问题而讨价还价,进而产生的紧张局势时,小多边主义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正如格林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以同盟为中心的三边合作通常不是针对第三方的集体安全安排”。它们政治制度相似,需要避免对手和潜在的敌对霸权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并且对“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有相似的认知,试图通过小多边行动,在一些特定的问题领域,在美国传统盟友与其他新盟友获得的收益之间“取得平衡”。当然,本地区一些较大的地区多边安全集团批评小多边主义仅仅是一种“清谈馆”,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它们的共同目标还尚待考证。在一定意义上讲,它可以作为“辐辏体系”与印太地区尚不完善的多边秩序建设架构之间的桥梁组成部分,但其作用的发挥还需时间检验。需要认识到小多边机制的功能与作用无法与美国现有的同盟体系相提并论。与美国和盟国的安全利益有关的印太地区小多边安全政治至少有两个障碍。该地区的大国权力博弈,可能会使一些小多边安全计划不堪重负。该地区的小多边主义更加强调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的构建和强化,但是小多边合作的持久程度还受美国和盟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对小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等概念进行了界定,结合分析它们运行的战略环境,对其作用与效果进行比较,最后讨论了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小多边主义及其局限性。小多边主义是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一种相对短暂的手段。它是一个本质上较为脆弱的安全协作过程,受其参与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因素以及整个区域战略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有可能越来越受到局限。
在印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图景中,美国将扮演何种角色直接影响该地区地缘政治中任何“小多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当前,特朗普政府试图让盟友与合作伙伴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持续战略参与支付更多费用,并依靠与中国在一些地区性安全议题的合作,实现美国和盟国的利益。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表述以及后来彭斯在巴布亚因几内亚的发言中,可看到,美国依旧会在印太地区维持原有的地缘政治存在,但更多体现出一些单边主义的特点,这会影响印太地区小多边安全政治的未来前景。对印太地区危机管理问题的大国谈判与协调也会影响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效能。美国及其盟友如何有效应对是影响未来印太稳定和平的因素。美国盟友间潜在的分歧、地区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担心安全合作会激怒中国、以及美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需求,使中国无法被排除小多边安全合作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小多边主义视为印太地区秩序建设下一阶段的前奏的预期可能为时过早。
小多边安全合作需要将一些相互对立甚至冲突的安全要素进行平衡,并将此融入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过程中,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此机制的看法也不明确,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意图和作用仍需要重新定义和澄清,当然,这与“印太”以及“小多边主义”仍然是一个在构建中的概念有关。我们要认识到,“印太”概念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所构建的专有名词,中国的发展和利益决定了要对“小多边机制”构建提出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并采取理智和有效的行动,更好的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
注释:
Bishop,J.(2017, April 20).Joint press conference, Australia–Japan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2+2), Tokyo. Retrieved from?http://foreignminister.gov.au/transcripts/Pages/2017/jb_tr_170420b.aspx?w=tb1CaGpkPX%2FlS0K%2Bg9ZKEg%3D%3D, 11 July 2017.
Fitzpatrick,M.(2016).Asia's latent nuclear powers: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delphi Books.Abingdon: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artcher,P., “North Korean missiles can strike Australia and we can t stop them”.Sydney Morning Herald,2017, July 8.
Flores,H., “US forces assisting Philippines in battle to end siege”.The Philippine Star, 2017, June 11.
Tsjeng,H. Z.(2017, May 6).“ Time for ASEAN s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to put traditional security on the agenda”, TheDiplomat.https://thediplomat.com/2017/05/time-for-aseans-defense-ministers-meeting-to-put-traditional-security-on-the-agenda/, 21 February 2018.
White House. (2017, December).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etrieved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 2017-0905.pdf, 21 February 2018, P.45.
Ibid, p.47.
[美]約翰·鲁杰著.多边主义[M].苏长和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381页.
Weber,S.(1991).Multilateralism in NATO: 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1945-19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viii.
Keohane,R. O.(1986).“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0(1),1-27.
Glosserman,B., & Snyder, S. A.(2015).The Japan-South Korea identity clash: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162; Oye,K.(1986).“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In K.Oye (Ed.),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pp.1-24).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20-21.
Cha,V. D.(2003).“The dilemma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Multilateralism versus bilateralism”. In P. F. Diehl & J.Levgold(Eds.),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pp.104-122).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p.116-117.
Tago,A.(2017, August).Multilateralism, bilateralism, and unilateralism in foreign policy.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http://politics.oxfordre.com/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 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449, 27 February 2018.
Kamphausen,R. D.,Park,J. S.,Sahashi,R., & Szalwinski,A.(2018, February).The case for US-ROK-Japan trilateralism: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NBR Special Report No. 70).Seattle,WA: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Campbell,K.,Patel,N., & Singh, V. J.(2011, June 11).The power of balance: America in Asia.Washington,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nas. 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power-of-balance-america-in-iasia, 27 February 2018.
Mearsheimer,J.(1994/1995).“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19(3),5-49.
Ruggie,J. G.(1992).“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3),561-598.
Naim,M.(2009, June 21).“Minilateralism: The magic number to get real international action”,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6/21/minilateralism/, 11 July 2017.
Patrick,S.(2015).The new “new multilateralism”: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t what cost,Global Summitry,1(2),115-134.
Cha,V. D.(2003).“The dilemma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Multilateralism versus bilateralism”, in P. F.Diehl & J.Levgold?(Eds.),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pp.104-122).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117-118.
Green,M. J.(2014).“Strategic Asian triangles”, inS. M.Pekkanen,J.Ravenhill, & R.Foot(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p.758-774).New York,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770.
Tow,W. T., & Limaye,S.(2016).“Whats China got to do with it? US alliances, partnerships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Politics & Policy,8(1),13-18.
Kamphausen,R. D.,Park,J. S.,Sahashi,R., & Szalwinski,A.(2018, February).The case for US-ROK-Japan trilateralism: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NBR Special Report No.70).Seattle,WA: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Government of India. (2017,December 13).4th India-Australia-Japan Trilateral Dialogue.http://mea.gov.in/press-releases.htm dtl/29176/4th_IndiaAustraliaJapan_Trilateral_Dialo gue_December_13_2017, 21 February 2018.
Teo,S., & Singh,B.(Eds.). (2016, February 23).The future of the ADMM/ADMM-Plus and defence diplomacy in the Asia Pacific(Policy Report).Singapore: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