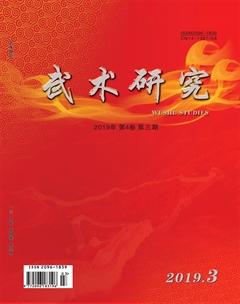仪式理论下壮拳“拳舞”的解构与透视
王晓晨 乔媛媛 孙庆彬 王世景 解少康 王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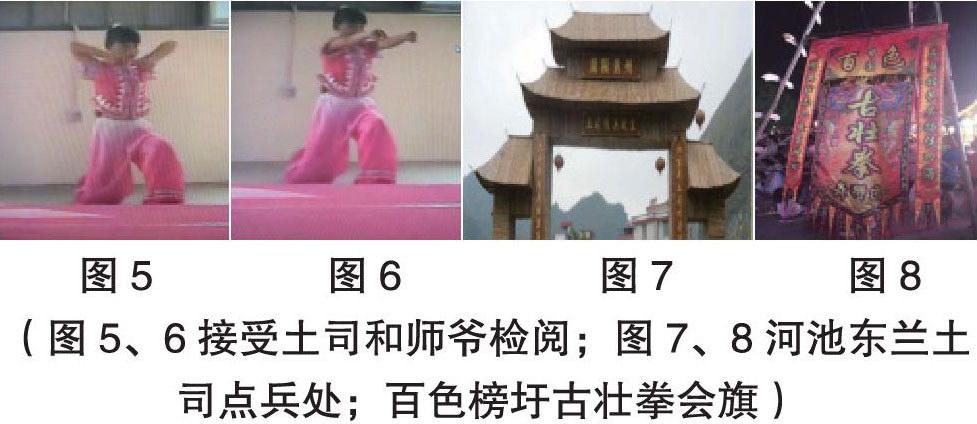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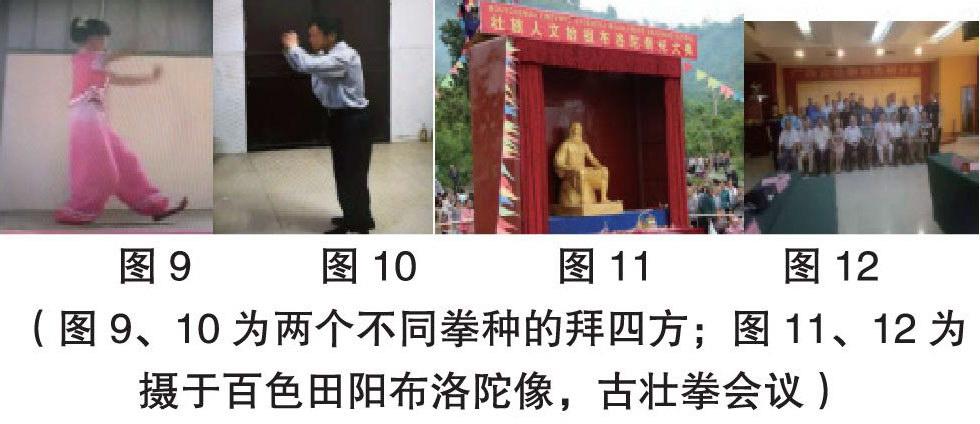
摘要:拳舞以其仪式的文化个性,成为拳种发展中高度程式化与标准化的存在,完整存储了拳种的诸多文化信息。对其解构与透视为全面认识拳种及实现拳种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绝佳视角。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运用仪式的多元理论对壮拳拳舞的基本程序及其象征符号的文化所指进行梳理与寻绎,认为:敬酒于战神侬智高环节不仅反映了壮族宗教信仰中的英雄崇拜而且折射了酒作为壮人人生关键时刻过渡性标志的文化意义;接受土司和师爷检阅环节不仅反映了历史上土司意志在事关土兵生死的壮拳中的体现,而且折射了壮拳的传承路径及师爷与土兵之间的关系;拜四方环节不仅通过礼拜家中已逝老人灵魂反映壮族民间社会的尊老意识而且通过礼拜现场的观众折射了社会道德中的人人平等诉求。
关键词:仪式 壮拳 拳舞 侬智高 土司 师爷 布洛陀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9)3—0059—06
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理性人”到现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从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到主张“理解社会学”的马克斯·韦伯,其学术逻辑主线和落脚点都是围绕“理性”和“行为”而展开。尤其是韦伯基于人会思考和选择,其行为合乎理性的预设,将人的行为分成工具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以及与之相对的传统的行为和感情的行为。并指出行为是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的行为,它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或者体现一定的意义。仪式作为集中展示人类社会行为的文化活动,其整体营造的是非理性场域,而单独考究其作为符号的具体行为又具有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与此同时,仪式又有着“借助永恒不变的和潜藏着的形式、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从而消除了历史和时间”的基本特征。因此,聚思之余,检视与厘清仪式行为的复杂性就成为人们认知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存在的常用视角。
壮拳“拳舞”以其仪式的文化个性,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依循其高度标准化和结构化的传承特征而得以保存至今,这就为研究壮拳拳种文化提供了标本和空间。意即对拳舞中这些裹挟在象征之网中的行为进行分门别类、梳理这些程序和时空的象征意义对认识壮拳的前世与今生提供了独特视角。如此,壮拳拳舞包涵了哪些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又所指哪些方面的文化内涵?分别有着何许功能?等等这些符号学、人类学与文化学的探究与考量对认识壮族武术,尤其是古壮拳的发生发展以及未来走向都至关重要。基于此动机,在精读了囊括壮族历史人文、宗教信仰、民俗艺术等诸多文化内涵的《壮族通史》《壮族文化史》《壮族社会生活史》《壮族图腾考》《壮族民间宗教文化》《布洛陀》《侬智高》《瓦氏夫人》《壮族医学史》《壮族文学史》等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和团队在2015至2017年间多次南下广州南沙,西下百色田阳、苹果榜圩、河池南丹、宜州合寨、云南文山等地对昂拳、傅氏古壮拳、黄氏家拳等“古壮拳”和“土壮拳”进行了田野调查,田野中就“拳舞”中的符号意义与传承人、习练者、广西武术院专家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并对壮拳“拳舞”的历史发展、民风民俗、文物遺存以及集体记忆进行了整理,为本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一手资料。
1壮拳拳舞的仪式抽剥
壮拳是壮族武术的统称,而壮族武术现存拳术套路就有包括“古壮拳”、牛角拳、“土壮拳”、擒功大王拳、山林伏虎等在内的35种之多,梳理发现其中只有一些古老的、最传统的拳种才有拳舞展示;同时发现即便是同一拳种又有着不同拳舞,以昂拳为例,不同地域、不同土司创编的拳舞又有所不同。但做研究总是从特殊中找到一般、从差异中找到共同、从变化中找到规律,意即这些拳舞的程序虽有不同,但聚焦到拳舞仪式中的的最小单位——象征符号又是大同小异的,意即这些象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又是几乎近同的。因此,研究对象选取“古壮拳”“土壮拳”、牛角拳等拳种中共同存在的仪式程序和象征符号作为研究对象来探究壮拳拳舞的文化内涵,从而试图窥探壮拳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与文化。
2壮拳拳舞相同的基本程序:象征符号的出场
“仪式是人们在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沿着“仪式一直被作为宗教的实践和行为来看待”的逻辑,梳理学术史发现,无论是对仪式在原始社会内部作用进行宗教社会学考察的涂尔干,还是对仪式功能进行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更抑或是建立在两位之后的基于“结构一功能”体系建立仪式研究范式的特纳,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认为,“仪式是由一个个象征符号构成的,象征符号与人们的社会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且又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是仪式语境中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而现实中象征符号往往有着能指与所指的双层隐喻,意即看到这种囊括实物或者非实物的举止在内的象征符号总能让人想到另一种事物或意义的符号表达。于是,大的方面壮拳拳舞的基本程序又是这些象征符号出场的基本方式,随着程序的展开,象征符号总是在仪式参与者、观看者的头脑中传达着某些信息、上演着集体记忆、强化着族群认同。
然“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壮拳拳舞作为形成于冷兵器时代,在出征前夕、决死之际的生命之舞符合“人穷必返本”的逻辑,其基本程序依然与壮人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宗亲世故息息相关。综观壮拳拳舞共同的基本程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礼敬战神、拜土司和师爷、拜四方。首先,礼敬战神环节的主要象征符号表现有舞者两肘上架,两手似捧一物,低头目视所捧之物;接着单膝下跪,然后两手上举,仰头虔诚向上看。其次是拜土司和师爷。其象征符号的表现为双臂由上举变为前平举,接着两肘上架,接着再做一次双臂平举。最后是拜四方。其象征符号的主要表现有舞者不慌不忙地匀速依次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腿部是虚步,双手上下挥动作打鼓式;也有的拳种在此环节有差异,比如“土壮拳”直接简化为朝四个方向行作揖礼。
3象征符号的文化所指与意义阐释
“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正如格尔茨的研究取向一样,仪式研究是着眼于民族文化的解释学领域,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深描,而非寻找严谨逻辑中的科学规律。在文化解释中关注的更多是仪式中象征符号所指的器物、制度和精神等层面的文化意义以及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普遍秩序和集体记忆等社会价值和功能。随着仪式研究思路的更迭,尤其是福柯“知识考古”的解释方式出现以后,“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单一行为、器物——包括文字的物态认识,而是意识到在客观自然的本体之中就潜伏着历史的叙事范式和具备了进行重新破译的潜质。”于是仪式研究也就出现了要么不说,要说就聚焦到仪式的细节和技术,或者整段程序的意涵,进而追溯到文化原点的研究范式。
3.1礼敬战神与酒的物语
课题组成员将田野调研中所收集到的拳舞录像视频和资料展示给古壮拳名家刘志岩先生看后,他立刻指出:“这些动作在壮族的刀盾舞中也有,是敬壮王、敬战神的;壮族地区的老土拳的起势中多有这些敬神拜神的动作。”另一位壮族古壮拳师姚磊先生对刘师的观点比较认同,并进一步指出:“双肘上架捧起的器物是壮族大海碗,里面装的酒,敬的是壮族战神天子侬智高。”
3.1.1战神侬智高:宗教信仰中的英雄崇拜
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灵魂观念是整个宗教信仰的源头和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宗教意识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超自然的、不朽的灵魂观念,就不可能有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灵观念,也不会有任何宗教信仰。并认为这种“万物有灵论”是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实物崇拜的逻辑前提。如出一辙,壮族的宗教信仰也是建立在灵魂观念基础之上的,有着“鬼魂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等多重崇拜,神祗较多而且繁杂。比重上以祖先崇拜居多,无论是信仰程度还是信众规模都占有较大比重,然建立在祖先崇拜之上或模拟血亲的英雄崇拜更是影响深远。在远古,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制度下对一些生前强有力的、对氏族部落有贡献的酋长或部落领袖及氏族头人,在死后被人们尊崇为英雄神灵而祭祀的文化传统一直沿袭至今。正如费尔巴哈在其《宗教的本质》中指出“宗教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和意识;宗教乃是对于我之所以为我的思量和承认”一样,壮人民间社会认为这些生前强有力、武功高强之人死后其灵魂依然具有庇护族人的功效,尊崇、祭祀这些祖先为守护神,可以保护氏族和部落。笔者和团队在桂西北调研中发现,当地莫姓壮族崇拜莫一大王,认为其是南丹莫氏土官的祖先,生前力大无穷、文治武功超群,死后被当地壮族作为地方守护神立庙供奉。不一而足,在土官、土司等治理阶层的推动下,这种像“莫一大王”“瓦氏夫人”“韦氏三父子”“岑三爷”等地方性具有同质化的祖先中的精英在数百年的流传中被演化成当地社会最基本和最具有活力的神祗来规范当地现实中的社会秩序,可谓英雄崇拜的深层动因。而作为北宋年间带领壮族南御交趾、北抗朝廷,深切关爱壮人疾苦的民族英雄侬智高更是在民间传说中被神奇化为最大英雄神而崇拜,“在壮族人民的心目中,侬智高既是一个出身神奇的龙种,也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帅,更是壮族人民心目中的依王。”显而易见,英雄崇拜为仪式中的敬壮王、敬战神找到了文化原点。
3.1.2大海碗敬酒:生死语境中的标志之举
关于战争与酒,历史上不仅有着三国时期关羽“云长停盏施英雄,酒尚温时斩华雄”的勇冠三军;而且有着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爱国抱负,更有着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所展示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酬筹,英雄豪迈之气。史实表明,酒在战争中的应用由来已久,而且积累了丰富意涵。然仔细梳理不难发现,酒在战争中的使用往往在关键节点时刻或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转折时刻。饮酒后较之饮酒前,社會角色、精神状态或者重大决定上都有所变迁。无出其右,在壮族酒文化中依然可以找到酒的这种物语现象。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壮族民俗活动,酒往往成为中心物质。特别是“在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性仪式中,壮族经常把酒当做一种标志,用以象征人的生命从一个阶段步入另一个阶段。酒伴随着壮人的出生、婚丧、死亡的各个阶段”。而壮拳拳舞的展示时刻往往在决死格斗之前或者在奔赴战场之际,其仪式场域营造了一种生死难料之际的凝重氛围。因此,大海碗敬酒在向战神表达崇拜和致意之余,更多彰显的是仪式者的决死之心,一种“已报必死之心,当全力一战。苟不幸遭逢失败,祈予庇护,保吾平安,若处困境,翼能获指点迷津”的祈愿。就像法国著名民俗学家范热内普基于仪式的结构分析而发现了仪式的过渡性一样,此段武舞程序中的酒作为象征符号,其意义更多在于“建构一种过渡,为该人进入到新的地位提供一种标志物。这种标志物对此前构成一种区分和隔断,对此后则构成一种新的资格,它代表一种新的生命转换和开端。”因此,海碗敬酒,更是生死语境中的誓师标志。
3.2接受土司和师爷的检阅
当课题组将录像视频呈献给广西壮武研究院院长苏荣舟先生,苏先生认为:此段“拳舞”程序是狼兵出征前接受土司和师爷检阅装备,礼拜土司和师爷的行为,苏先生同时指出此举不但具有激发勇气、热身等作用,而且每个拳舞都有头有尾、土司不同此段拳舞的程序也具有内容不同的特点。
3.2.1土司意志: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圭臬
土司制度是“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对西、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是中央王朝对控制一定地域、掌握一定军事、政治、经济权力的各族首领,通过授给他们不同级别的一定世袭官职,让其缴纳一定贡赋、承担一定义务的办法,把各族地方性军事、政治权力间接纳入中央王朝政权系统内的特殊政治制度。”然正是这样一种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清,清雍正改土归流后逐渐走向衰亡,前后延续近800年的制度,对置身西南地区的壮族族群影响深远。制度理性下,缺乏更多钳制的壮族土司在地方统治中往往走向荒淫无道、穷兵黩武,欺压土民甚至对抗朝廷,这种现实需求中往往为增强其武装力量的壮拳武技及其仪式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空间。从隋唐的羁縻时代到宋元明清的土司时代以及“改土归流”时期,壮族土司的武装力量“土丁、峒丁,无不习战,标、枪、刀、弩、箭、牌等武器,用之甚精,故强武可用。明代之土司土兵中的狼兵,更是‘鸷悍,天下称最,不仅艰苦耐劳、勇敢善战,而且人数众多,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军事诉求上,土兵的作用主要有“讨蛮”“守境土”和“抗交趾、倭寇外侵”等功能。除此之外,各土司之间为争夺地方、人口的统治权而互相争战,土兵又成为土司争霸地方的工具。一言以蔽之,战场厮杀中的你死我活的现实诉求更是将壮拳武技的地位推向了极致。而“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的土司不仅将这些满身武技的土兵视为私有财产,更是在武装其士兵的方法和手段中渗透着其意志,使得土兵的身体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其所属土司的特征和标记。每次出征前,土司都要检阅土兵,而英勇善战、难以辖制的狼兵更是如此。被誉为明代《山海经》的《赤雅·狼兵》中就有:“狼兵鸷悍,天下称最……土官亲行部署乃出,性极贪淫,动不可制,严志明律用之胜,否则败”的记载。访谈中,古壮拳名家唐曲先生对此文化事象进一步补充说:“宁教拳,不教舞。每一个土司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拳舞,归降与道歉的方式之一就是跳拳舞。如果土司接受道歉,就把酒言欢、前嫌尽释;否则就刀兵相见,以死相拼而决出胜负。”不言而喻,跳拳舞乃是维护生存尊严底线的最后一道程序。此时此刻,接受土司检阅装备或授旗,领会土司授意,奋力拼杀中去完成其社会角色应扮演的历史责任。
3.2.2勇猛再造:师爷检阅中的安全眷顾
师爷这一社会角色由来已久,只是在明代以前大都以幕僚、幕宾等而统称,清代以降被世人称为师爷而已。宋元明清以来的壮族土司的治理团队中不乏师爷身影,他们往往受聘于土司,协助办理文案、钱谷、安全、刑名等事务,为土司在激烈的内外竞争中出谋划策、贡献智慧而让其立于不败之地。官职与俸禄上,“师爷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只是受聘于幕主官员的佐治人员,双方宾主相待,实质上是雇佣关系,是聘用的私人顾问或私人秘书。其被聘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私人行为,其报酬主要是由官员从政务专用经费中开支。在用人行政上是辟而不署。”正如“土司学”著名学者成臻铭先生在其《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一书中的研究表明一样,土司的师爷在辅佐土司的过程中,凭借其在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案牍、兵法武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干才能来攫取个人的社会地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其“其效力已至犬马”,深得土司信任。自然而然,壮族土司中无论是文土司还是武土司大都将传授武技、打造武装力量的任务交给其聘任的师爷。著名壮学家梁庭望先生研究指出:“明代桂西壮人,每生下一个男丁,就把他看成未来的‘狼兵。父母称上一块和他分量相等的铁块,用红绸扎好,庄重地挂在孩子床头。待他长到十来岁,便用这块铁打成一把刀,闲时由土官的师爷教其习武。”师爷与土兵在事关生死的壮族武技的传承与承传中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而且视如己出中师爷以其高超的实战能力为土兵营造了安全感。正如戴国斌教授提出的“格拳致知”教育逻辑中土兵将壮拳不仅“扩展为‘身体之拳”、延伸为‘器械之拳而且深入到‘心意之拳”,几近降神附体之地步。因此,临战之际得到师爷对装备的检阅和慰问眷顾,其勇猛再造之效无与伦比。
3.3致敬父老乡亲
笔者和团队在文山广南县、崇左大新、南宁武鸣、百色靖西、河池宜州等地调研中发现众多壮拳传统拳种的拳舞中,有的带有“敬战神、敬壮王”和“接受土司和师爷检阅”等环节,有的却没有,但大多数都有“拜四方”环节,它们的基本程序中象征符号体系内容虽有差异,但传达的都是致敬父老乡亲之意。就此环节的所指,被称为“壮拳第一村”的河池宜州合寨村的传统土壮拳师父韦名旺老先生解释说:“拜四方首先是拜四方神灵,其次是拜观众,感谢众人的捧场。”当进一步追问,“四方神灵指什么神?”时,韦老先生说:“主要是去世的长辈”。
3.3.1娱魂:人伦道德中的尊老意识
壮族的伦理文化中尊重长者、敬爱老人的意识特别浓重。“老人家的话就是宝,老人家的话就是药”是壮乡民间社会的共识。壮族家庭教育中,晚辈要尊敬老人,言语不能顶撞长者是常常听到的劝诫。田野调查中发现,即使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壮族鳏寡老人也同样受到尊重和爱戴,众人善心的逻辑起点似乎不是基于怜悯和恻隐,超越了儒家的“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递进模式,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其实这与壮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活生产模式息息相关。因为“那”是稻作文明的表征,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之一,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实用理性中,经验往往大于一切,而老者就是经验的载体、智慧的象征。被誉为壮族“道德经”的《布洛陀》一书中的布洛陀作为百越民族的创世英雄、壮族的始祖,其形象就是一智慧老者。“千百年来布洛陀诗经和布洛陀故事在我国南方的南盘江流域、红水河流域、连同左右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区广泛流传。每年三月三歌节,壮族百姓都自发到布洛陀故乡田阳敢壮山祭拜布洛陀。”时至今日,广西武鸣县、马山县一带的壮人依然认为家中老人去世后,其留在家中的灵魂和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若活人经常对它们祭祀,它们就会时刻保护家人,不让各种妖魔鬼怪进入家中或危害家人”;贵港一带的壮乡民间“各家各户的厅堂中都摆有神龛,供祭祀去世的老人”,并保留此处不乱堆杂物、不乱挂衣服,不准未满月的产妇走近触摸的禁忌。因此,尊老意识将拳舞“拜四方”环节拜四方神灵的逻辑起点落到了实处。
3.3.2娱人:社会道德中的平等意识
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定性为“家产制官僚社会”,意即由于官方公共财政制度的缺失,而没有形成一套精确而统一的管理机制。然而这并不影响民间社会的有序运行,基于某种相处标准的社会道德在其中功不可没。在壮乡,这种相处标准就是平等意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一样,壮族稻作文明中这种“春耕待插秧,有牛要相帮。挨家轮流种,合力度大忙”最具体最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可谓是平等观念形成的原点。追溯历史,产生于明代的壮族长诗《传扬歌》就是一部通过揭露统治者不平等的剥削行为而祈求平等的叙事诗歌。壮族文化原典《布洛陀诗经》第6篇“唱罕王”中也有“众人平等,不能相欺”的社会道德诉求。不仅如此,形容兄弟同根平等的壮族格言“刀断水不断”,壮族习俗“结老同”“打老庚”等都是建立在“没有地位高低、身份卑贱之分,权利和义务是平等”基础之上的。较之汉族结拜中存在的长幼有序、兄弟有别的“差序格局”,壮族社会的区隔并没有那么清晰可见。这一点,在壮族的丧葬文化中体现的尤其明显。为了减轻死者家庭的负担,壮人发起共渡难关模式,意即“众人前去静忙和慰问时都自发地准备一些布匹、钱物和祭祀用品等物品作为随手礼赠送”,这种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互助互爱的社会伦理习俗至今在壮乡很多地方依然保持良好。在这种一来一往的礼物交换中,“人们将灵魂融于礼物,亦将礼物融于灵魂”,人与物相混融,社会道德与公平契约想混融。礼物交换同时也是人们强化社会公平意识与建构公平秩序的一种“总体呈现体系”。因此,正是壯族社会中这种平等意识才有拳舞中“拜四方”敬观众时的“捧场”之说,因为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场”可以捧也可以不捧。
4结语
功能主义学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分析是在田野事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各个功能在完整的文化体系中所发生的联系和作用,来解释文化的特性。壮拳拳舞虽是一段简短的身体活动程序,但是通过梳理不仅可以管窥到壮人在封建时代生死有命、安全不保的生存危机下所造就的宗教信仰中的英雄崇拜以及临战之际豪饮摔碗酒进而誓死一搏的形象;而且可以审视到羁縻时代、土司时代、改土归流时期峒丁、土兵在峒主、土司的驱使下披坚执锐、东拼西杀的战争生活史;同时又能感受到基于稻作文明实用理性下形成的壮族民间社会文化中的崇老意识与平等意识。不难看出,即使每个壮拳拳舞的基本程序有所差异,但其内蕴的象征符号的文化所指却大同小异。总体折射出壮拳不仅事关壮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性而且与其政治文化、社会道德息息相关的文化个性。这些为壮拳在地方教育资本凝练、区域社会治理参与、文化品牌塑造、体育产业振兴等方面有所作为而实现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打下了基础。回眸历史,壮拳一直是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拳种,然时至今日,其发展、传承、研究呈现出“遥看草色近却无”的境遇。抛砖引玉,希望学界给以批评指正,给壮拳以更多的关注。
——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