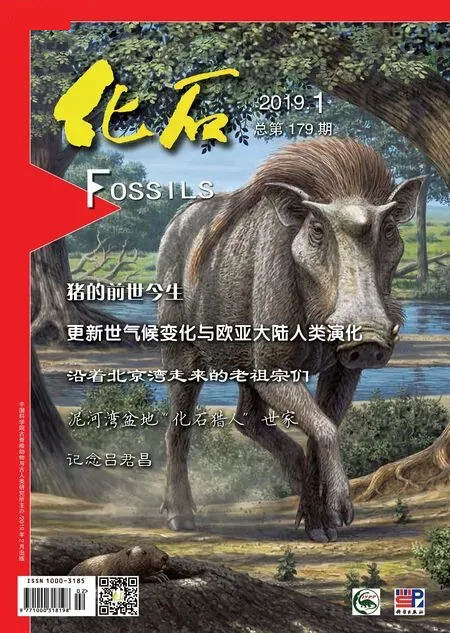华莱士
郭建崴
前文提到,1858年,华莱士的一篇论文催生了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正式问世。可见,在进化论的发展历程中,华莱士是功不可没的。可是如果您上网查查“华莱士”这个名称,竟然在最前面出现的网页和词条里,不是某个时髦鞋子的品牌,就是某个快餐连锁店的广告;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人物,还是某个NBA球星的名字。在科学史上曾经作出过那么重大贡献的一个人物,竟然被人们给淡忘了。
也许,这种淡忘是因为达尔文的光辉对后世过于耀眼,以至于遮蔽了华莱士的身影,正如有些书籍里提到华莱士时的轻描淡写:“英国生物学家,通过对马来群岛动物分布的考察和研究,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写成的论文中,独立地提出了与达尔文经过20多年辛勤研究相一致的结论。”
这话听起来味道怪怪,难道说华莱士脑子里产生进化思想纯靠一时的灵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还原一个当时的真实华莱士。

华莱士,也独立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促使达尔文“提前”发表了他的巨著《物种起源》
出身贫穷,但自强不息
他的全名是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与达尔文出身于富裕之家不同,他于1823年1月8日生于像狄更斯的小说里常常描绘的那样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普通”家庭。他后来在回忆曾经的亚马孙之旅时写道:
如果我父亲稍微有钱一点点,如果我整个的生活稍有不同,那我一定会把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到科学上面去,因此不太可能踏入亚马孙那几乎无人知晓的莽莽丛林中去观察自然,并通过采集标本来谋生。
而在这趟旅行之前,为了生存,华莱士从十几岁起就开始自食其力,当过木匠、检验员和教师。与许多自学成才的人士如出一辙的是,他工作之余的时间大多是泡在公共图书馆里。
奠定后来人生之路的另一个起点是从事土地丈量,这一不需要大学文凭的技能是哥哥教会他的。那是一种野外工作,干活的地方随处可见的植物和昆虫吸引了华莱士。而在兰开斯特工作期间,他结交了一位有着同样爱好的受过很高教育的朋友亨利·贝茨。这位朋友在当地乡间收集的数百种形形色色的甲虫触动了华莱士。从此,他开始了一种新生活,正如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所写:
哪怕在我们很忙的时候,我在星期天还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带上采集箱,走很远的路到山里去,然后采满一整箱财富回家……在这样的时候,我会体会到每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给自然爱好者带来的那种快乐,几乎等同于我后来在亚马孙捕捉到新的蝴蝶品种时体会到的那种快乐。
1844年,一部名为《自然创造史的遗迹》的匿名著作风靡英伦。这部书描述了宇宙的自然历史,把它开始于宇宙诞生那一刻并一直持续到现代的过程称为“自然孕育”。书中认为地球生命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自然万物起源之初,而从创生的自然过程来看,拉马克式的进化成为新物种诞生的动力。英国民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作品,因此它畅销至极,第一版在几天内就销售一空,到了1853年时,已经重印到第10次增订版。在达尔文看来,这本书的内容一般,文字、逻辑都不严谨,许多观点与自己相左,但是达尔文还是既兴奋又恐慌。兴奋的原因是其畅销说明了大众渴望了解蔑视传统与宗教的有关自然界的新观点,这也是他在1844年才向莱伊尔、欧文和约瑟夫·胡克(英国当时的著名植物学家)透露自己进化思想的原因;恐慌的原因是他担心再不及时发表自己观点的话,其他人也许会抢先发表同样观点而使自己失去“首发权”。于是也是在1844年,达尔文还把自己整理出来的那个230页的手稿交给了胡克阅读。不过后来,达尔文还是对《自然创造史的遗迹》评价道:“此书在英国有着极大的贡献,曾经唤起一般人士对于此项问题的注意,废除了成见,以备接收相似的学说。”
对华莱士而言,《自然创造史的遗迹》这本书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进化的思想,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1848年,25岁的华莱士决定成为职业“标本猎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是一个独特的职业,许多从业者游走于乡间原野甚至闯入荒原密林去采集标本,然后卖给博物馆或是有钱的收藏家。而华莱士更是把亚历山大·冯·洪堡和达尔文等博物学家奉为心目中的英雄,立志追随他们的脚步去环球旅行。受作家威廉姆·亨利·爱德华茨撰写的《亚马孙河航行记》的启发,他把巴西选为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贝茨和他一起动身,搭船到达南美洲,而后顺流北上来到位于亚马孙河与里奥内格罗河交汇处的门劳斯城,再分头沿两条河溯源而上。
连绵的阴雨使里奥内格罗河暴涨,华莱士和他的印第安向导划着独木舟进入密林。树木弯弯地贴近河面,森林里多样的生物让华莱士异常振奋,他写道:
我们随处可见,热带植物有更大数量的物种多样性,更多的外形,比温带地区多得多。
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处的野外包含如此之多的地表植物,哪里都无法超越亚马孙流域。
华莱士仔细观察并记录了亚马孙雨林中蝴蝶的形态差异,这与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地雀喙的形态差异可谓是殊途同归。经历着丛林中的快乐和艰苦,在华莱士的大脑里,迟早会想到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此之多的生物物种从何而来?许多物种在外形上如此相像,但在细部却如此多变。与达尔文一样,华莱士因临近物种之间的差异而感到震惊;也和达尔文一样,华莱士开始思索,它们是如何慢慢地发展出了这些不同形态?他写道:
自然史中,没有哪个部分比对动物进行地理分布的研究更加有趣也更有指导意义。相距不到50英里或100英里的地方,经常发现这里有一些种类的鸟类和昆虫,但在另一边却找不到。一定有某种边界控制着每一个物种的分布范围,一定有某种外部的特征来标志彼此不跨越的界线。
历时4年,抗拒着家常便饭般的淋雨以及不时袭来的黄热病和疟疾,华莱士在亚马孙热带雨林里走过了漫漫长路。一路上,他通过向英国的博物馆和收藏家寄售自己采集的标本来换取盘缠。1852年,他包好最后一批收藏品登上回国的航船。
命运多舛,出海3个星期后,这条船在8月6日失火了。
得以逃生的华莱士乘救生艇在海上漂泊了10多天。勉强从火灾里抢救出来的东西,除了手表,就只有一个小锡盒,里面装着几件衬衣和几本画有植物和动物草图的笔记本。他无奈地写道:
我的采集品里有多少罕见和令人惊奇的昆虫,我看着它们的时候曾经产生过多少快乐呀!一次次被疟疾折磨近死的时候,我却爬进了丛林,回报我的是那些从未见过的漂亮动物!有多少地方是欧洲人从未涉足过的,而我自己却踏入进去。如果那些罕见的昆虫和鸟儿还在的话,一定会唤起我多少的回忆!
现在,空空如也,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显示我踏足的那些未知陆地,能够显示我曾经见过的野外景色!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遗憾毫无用处,我尽量少想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只关心实际存在于当下的事情。
华莱士就这样从热带雨林里回到了英国,虽然物质上损失惨重,但是思想上却收获满满——与达尔文一样,他相信相关的物种是从共有的同一祖先分化而来,当然,分化的原因在那时还是一个令他困惑的问题。

达尔文在笔记本里最早画出了进化树草图
8年与3天
亚马孙雨林中4年的历练使华莱士从一个普通的“标本猎人”升华为真正的博物学家。回国途中的火灾磨难也没有消磨他的豪情壮志。他于1854年动身前往新加坡,从此在马来群岛开启了一段跨越8年时间、行程长达约2.3万公里的标本采集与科学研究征程。
虽然季风和疟疾成为困扰他野外研究的最大阻碍,但不懈的努力使他此次的东南亚之旅大获丰收。他总共采集了超过12.5万个甲虫、鸟类以及其它动物标本,其中,包括一种被其命名为“华莱士的金色鸟翼蝴蝶”的蝴蝶在内,有数千种动物是西方人见所未见的。这些标本的大部分都卖给了英国的博物馆和收藏家,其中也有为达尔文采集的许多重要标本。之前,他和达尔文曾见过一次面,在这期间,还通过两次信,交流过关于生物进化的一些认识,他知道达尔文在思考物种起源的问题,但并不知道其具体的过程和细节。
进入马来群岛后不久,华莱士已经确信物种并非不能变异了。1855年,他在现为马来西亚一个州的沙捞越撰写了一篇进化论论文,《论调节新物种引入的法则》,并创立了以其撰写地命名的沙捞越定律。在这个定律中,他把进化描述为长着不同枝干的一棵树,这一观点与达尔文早先在笔记本里画出进化树可谓是异曲同工。而且从此,他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的问题已经是物种如何变化了。
随后的第二年,在结束了位于现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龙目岛的科学考察之后,华莱士发现,西部岛屿上的鸟类等动物很像亚洲的物种,而东部岛屿上的则更像澳大利亚的物种。这条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动物类群隔离开来的界线至今仍被称为“华莱士线”。
两年之后,华莱士在2月份身染疟疾,病倒在特尔纳特岛上。间歇性的高烧让他感到时冷时热,大脑也忽而清晰忽而模糊。某天夜里,高烧中的他想起了曾经读过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当初达尔文读到此书时闪现的念头一样,一个同样的解释在华莱士的脑海里迸发出来:
他突然想到要提出一个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生物会死掉而另一些却活下来?答案很明显,一般来说最适应的就能够活下来!疾病侵来,只有最健康的那些才会躲过或是康复;面对敌人,只有最强壮的、最敏捷的或是最聪明的那些才能打赢或是逃脱;饥荒来临,只有最好的猎手或是消化能力最好的(什么都能吃)才能熬过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接着他推论,所有活着的动植物物种都可能发生变异而产生变种,通过在实际的环境当中清除那些适应能力较弱的变种,最具适应能力的变种就会脱颖而出并得以繁衍,这就是适者生存,其结果是产生新的物种。
我终于找到了长久以来一直在苦苦追寻的自然法则,它可以解决物种起源的问题……我急切地期待自己身体康复,以便立即写出论文提纲。同一天晚上,我就圆满完成了提纲的工作,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晚上认真地写好了论文,以便赶上下一趟邮班寄给达尔文,而下一趟邮班两三天内就将出发。
这就是那“短短3天”的故事,但是如果没有之前对大自然的由衷热情、如饥似渴般接受的知识的储备以及艰苦卓绝甚至是九死一生的野外生涯,灵感从何而来?而这一历程,与长他14岁的达尔文在早他若干年所经历的又是何等地相似。因此,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分别由他们两人独立思考得出,这绝非偶然现象。
华莱士之所以将论文寄给达尔文,是因为他相信达尔文能够理解自己的观点。随论文一起的信件里,华莱士向达尔文提出一个希望:如果赞成这篇论文,请把它转寄给莱伊尔审阅。
4个月后,达尔文于1858年6月18日在自己位于肯特郡道恩村的家里收到了这份非同寻常的邮件,而在同一天达尔文也刚好写出自己准备出版的鸿篇巨著的原稿的摘要。看到自己默默无闻地谨慎准备了20年的理论出现在他人笔下,达尔文即感到震惊又觉得沮丧。
虽然左右为难,但达尔文还是立即将华莱士的论文转寄给了莱伊尔并建议发表。莱伊尔了解达尔文的一些工作,于是与早就读过达尔文有关自然选择手稿的胡克商量了一个出于对达尔文爱护的解决方法,建议两人同时发表论文。最初达尔文担心这么做会让华莱士觉得不公平,不过最终,还是听从了伊莱尔和胡克的安排,在两位“主人公”都不在场的情况下,达尔文的手稿摘要和华莱士的论文于1858年7月1日在林耐学会上被一起宣读,并随后发表在当年的林耐学会学报上。一起发表的还有1857年9月5日达尔文写给哈佛大学的爱沙·葛雷的信,信中讨论了佩利关于上帝存在的著名的设计论,极其谦虚、毫不武断地指出,完全可以把佩利认为按目的设计的东西解释为偶然性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出于对达尔文人格和智慧的折服,更由于达尔文在次年也就是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产生的巨大影响,华莱士对能与达尔文共享荣誉而高兴,而且后来,他总是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反过来,达尔文也把华莱士描写为“慷慨高贵”的人物。
在1862年返回英国之后,华莱士受到一家由科学家组成的秘密俱乐部的热烈欢迎,俱乐部成员包括查尔斯·莱伊尔爵士、约瑟夫·胡克、达尔文以及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此举表明,华莱士已经成为了当时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
后来的50年时间里,他总共撰写了800多篇文章、22部著作。其中包括《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以及在达尔文去世后的1889年出版的《达尔文主义》,他在前面那部书的献辞里写道:“本书献给物种起源的创始者达尔文先生,以表达敬意”。
由于在动植物地理分布研究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华莱士被誉为“生物地理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