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暗藏文学家写史的一颗雄心
江冰
《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是一部让人入戏很慢的长篇小说,我看了三次开头才读进去。上海一个老宅里住着一个上海男人,一晃六十多年,从一九四九年至今。人物很少,视野不大,故事情节亦无传奇,甚至有一种怀旧电影的慢节奏。读最初一百页时,我时常觉得作家王安忆写得太慢了,但我还是被一步一步地拽了进去,迟缓以至黏稠的叙事,天地、环境、心理、评点、抒情均融汇其中。几乎只用逗号句号的一个一个自然段,却深入骨髓地写活了上海。让人掩卷深思,发现王安忆在不大的格局中却暗藏文学家写史的一颗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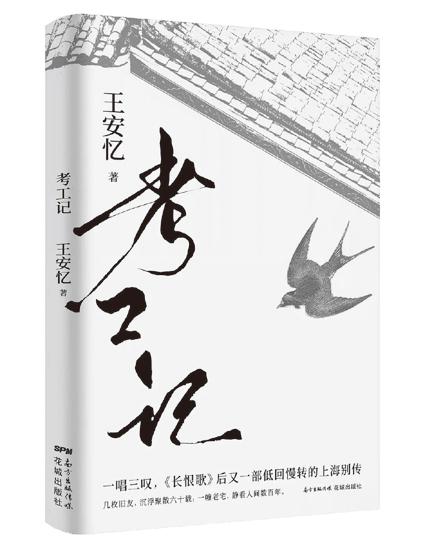
《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2018 年版
作品特有的叙述方式悄然施展魔力
我惊讶于作品特有的叙述方式。王安忆的叙述有如黄昏慵懒散漫的气氛,夕阳一寸一寸地在破旧老宅的墙角移动,迟缓乃至黏滞,仿佛下一秒时钟就要停摆。每个自然段相对匀称,一般只用逗号、句号,少有惊叹号和省略号,基本不用引号和冒号。让人初读时略感沉闷,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上海城市街坊中,颇有些压抑与危险的气氛,犹如浓稠的晨雾包围着你。不急不缓,琐碎日常,仿佛后劲十足的自酿农家米酒,在悠然中渐生效果。
在一种波澜不惊的氛围中,展开长篇小说的叙述。这样一种特有的叙述方式,我在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等作品中已有领略,但长篇小说《考工记》将其推向极致。仔细揣摩不难发现:看似低调内敛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却有内在的张弛与跌宕。比如第二百十五页,主人公乘渡船去大虞家看望因为“文革”而去“避风头”的朋友奚子—
正在渡船上,望着江对岸,他觉得魂仿佛被勾走。大虞,奚子,他,又在一起,就少了朱朱。过去的日子,绰约回到眼前。动乱的年代。尽是丧失,终也有一点可得的。汽笛鸣叫,心跳得厉害,昨天让惊惧攫住,只顾着应付,此时,百般滋味涌上,情何以堪!船头乒乓撞击码头的水泥堤岸,铁链子哗啦啦拖曳,他偏腿上车,跳板在轮下咯楞咯楞轧过,转眼骑在村路上,直向大虞家去。门前的地平撒着谷米,鸡们悠闲地踱步,门里边,两人正在对酌。
可以看到,一个自然段中间人物行动的描写、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夹杂在一起,情与景相融,再跳到码头、骑车、进村的现实环境描写,内部层次清晰,内容丰富而充实。妙在过渡相当自然,而且行文简洁,推进迅捷,省去了不少过渡的词语,甚至连引号都无须使用。这就是王安忆在《考工记》中发挥到极致的一种既简洁又生动灵活的叙述方式。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式的自然景物描写、法国文学中《红与黑》式的心理描写、鸿篇巨制《红楼梦》里家常式的琐碎叙述,似乎都被打碎后重新组合而形成一种属于王安忆特有的叙述方式。她稳居其中,游刃有余,挥洒自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艺术与思想。她轻松地摆脱了古典小说细节繁琐的弱势,有效地获得了一种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节奏,同时也恰到好处地调剂了《考工记》相对迟缓的叙述风格。

《红豆生南国》王安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
值得肯定的还有,在这种自由过渡的叙述中,王安忆为自己争取了一份无限伸张的自由,不尽的寓意与话题的延伸在此达到一个相当舒坦的境界。浅读者可得情绪牵引,深读者可得会心一笑,时代背景悄然隐藏,给予读者一个自我想象的空间。比如,第三章结尾,大虞与主人公对饮畅聊,谈及因为开工厂而因祸得福,人气充斥,让老宅得以保全,“楼上那只靴子总算落到地上”。彼此对话一转,就到了主人公单的向视角:“对面人有点不认识,不是朋友,而是乡下的术师,通天地,知未来。”酒后真言、谈话主题、人物心理、现场氛围参差呈现,一个不少,相得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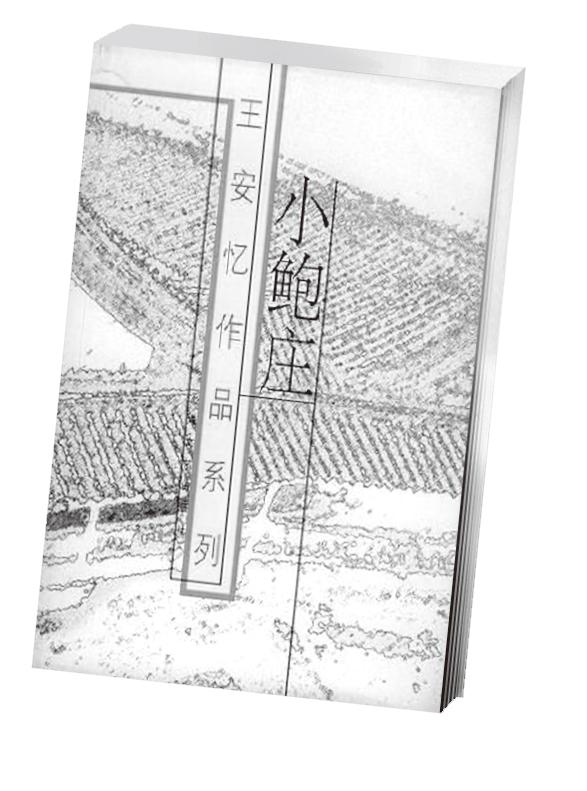
《小鲍庄》王安忆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知晓控制或许是一种大家风范
回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力深厚而持久,从儿童文学出道,到知青作家“雯雯系列”般清新可喜,再到以上海这座城市为舞台,她的小说创作在题材选择上呈现出“大跨度”的特点。她在一九八五年就发表了至今读来依旧深刻凝练的《小鲍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开掘与把握在当时文坛已经出类拔萃,卓越不凡。经过三十多年历练,王安忆显然更加老道。《考工记》呈现的就是她非凡的控制力。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虽然并非气势宏阔、惊涛骇浪,但却显示出一种大器,艺术控制力极高。初读《考工记》,有感于迟缓黏稠的叙述,却慢慢陷落在王安忆特有的艺术叙事魔力之中。当年《小鲍庄》里试图透过现实事物表象揭示文化秘密的努力,慢慢转化为看似风轻云淡,实则暗藏玄机,表面讲日常故事,骨子里却透露时代消息的大家风范。恰恰合了一句古话:看似寻常最奇崛。
控制首先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没有惊人之举,没有异禀之处,甚至连古典式的形象描写都省略,主要抓神态抓态度抓精神。比如,第一章对主人公陈书玉的出场介绍,身份、性格、学历、出境经历,没有一点静止的概述,所有的介绍都在人物命运流动中完成。同时顺畅地牵引出“西厢四小开”,大刀阔斧,点到为止。但四人之间的关系链条却定位准确,惟妙惟肖。各有背景,各有个性,单个平常,合起有气势。“四个人所以结缘,除兴趣爱好相投,更重要的一项,就是经济”。不经意间,王安忆抓住了新中国与旧时代的一个变化纽结:以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划分阶级。出身血统论,阶级成分论,为《考工记》中人物的命运走向设立了牢不可破的“人设”,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再如,主人公對冉太太一往情深,但情感含而不露,藕断丝连,发乎情,止乎礼,王安忆描写克制隐忍,却不由地焕发出动人的魅力。
其次表现在小说创作对时代生活反映的控制上。文学如何反映时代?中国内地五○后六○后作家,包括更早的四○后乃至三○后作家始终纠结这个问题,而文学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感无法卸去,于是,加倍纠结而痛苦。整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作家,尤其是贴时代最近的小说家的焦虑史。在新时期开疆拓土的从维熙、张贤亮、王蒙、高晓声、邓友梅、刘心武、蒋子龙、路遥、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张洁、谌容、方方,等等,莫不焦虑并探索于此。王安忆自然也在这个探索的队列里。我以为,到了《考工记》,王安忆通过恰如其分地把握“控制”,用自己的特殊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小说反映时代的尺度问题。
总结起来,王安忆至少保持了两个距离:不与具体时代过于贴近;不与具体时代的具体事件过于贴近。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注重重现一种时代氛围。而且也避开正面描写,通过作品人物的心理与身体感觉去折射,让读者进入一种虚构的情境,去细心体会具体时代在平常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而生动的变化,一呼一吸之间,一餐一饮之间,有意无意之间,透露出无法言说的时代消息。所谓大时代皱褶中个体小生命的喘息:声声入耳,息息相通,那般自然,那般亲切—或许这就是王安忆“控制”艺术的诀窍与奥秘所在。但,以“诀窍与奥秘”命名它,稍显轻浮,我以为它更是一种态度、一种文学之本分,或者也可以称作文学价值观。

《长恨歌》王安忆著作家出版社2000 年版
先说“大饥饿”,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王安忆通过一幅上海街头景象速写,巧妙地点出饥饿时代的到来:槐树花打尽,野草扒光,厨房熄火,孕妇缺奶;人们举止失度,神情萎靡,唯有一个共同的相貌:动物觅食。走失的猪,厨子的眼,夜晚的钟鸣……描写接近荒诞,但王安忆打住了,笔尖滑向主人公的食欲:猪油一小团搅进米饭,白糖合进大米粥里;别人面黄肌瘦,他却面色红润;进食近乎强迫症,一口气吃下半斤太妃奶糖,所有的想头都被食欲一扫而尽。新时期以来,作家写饥饿大多惨烈,但王安憶却写得诙谐,别有一番灵动,形象地折射时代,却并不正面评价。
再说“文革”。由于进入王安忆自身的体验世界,对“文革”初期的时代氛围的描写相当精彩,同时也十分克制。王安忆将时代巨变巧妙地控制在作品主人公一个人的感觉领域:世风渐渐粗暴,戾气四起,杯弓蛇影,惊惧不安,行为犹豫,走路蛇行, “隐行人”出现;大祸降临之前,最是不安,直到抄家,主人公才缓舒一口气。如此细致地描写特殊时刻的特殊心理状态,足以让后人去体会、去品味一个普通人的生命状态,其说服力当不亚于历史记载。我十分欣赏王安忆在此段惊恐不安气氛的描写之后,似乎不经意地叙述了一段主人公带队下乡的经历,写得温暖而亲切,离开喧嚣城市,乡村的静谧安然唤醒了孩子们心底最本然的情感:与人为善,和谐相处。其中学生失踪一段,最为感人,让读者相信人们心中的真情构成的足以抵抗劫难的人性本然与亘古道义之力量。孩子们的善良质朴与小学女书记的镇定自若可以对照地读,读出什么?—作者没有明说,但我将此也视作王安忆对于时代历史书写的恰当控制:以个体写时代,以文学论历史。
唯有钦佩《考工记》中王安忆的定力与耐心。世间人事了熟于胸,却不动声色,娓娓道来,自有一番见解,自有其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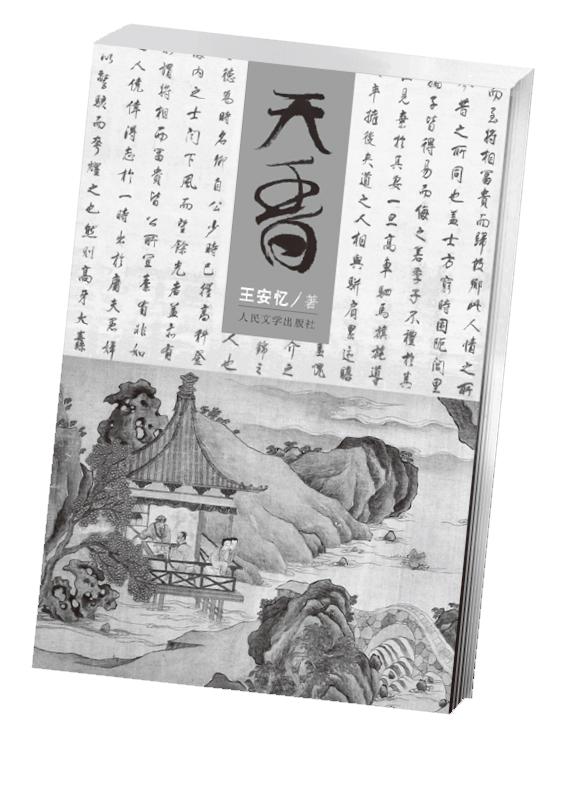
《天香》王安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
低回慢转依然是一部城市的历史
纵观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背景集中于生活地上海,可谓不离不弃唯有上海。《考工记》对上海这座奇迹般崛起的城市也是一往情深,对其城市文化个性以及出现在舞台上的各色人物的叙述无处不在,可以说无不打上上海的烙印。“沪味”在《考工记》中主要不是通过方言、实物、景色来表达,而是间接地通过人物交往的行为特点,悠悠然然地传达出来。比如,第一章中对旧上海“富”与“贵”的评说,“赤脚穿皮鞋,赤膊带领带”的发家史,以及“小开”称谓之意趣,都是深入沪上精神的阐释。再如,第三章陈玉书与姑婆吵架分家一段:一张八仙桌,杯盏灶头之间,琐碎细密争斗,活化出上海人个性的一面。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王安忆的其他作品,对大上海的叙述精彩纷呈,只是《考工记》更加偏重克制含蓄一路。
一部当代史,在一个上海男人的身上风云变幻,没有正面描写,全是鸡零狗碎,但多余小人物在大时代浩荡中的绰约身影,却于生命状态中有一份深刻的洞察。不少精彩处,深得传统小说真传,同时兼得西人视物之深刻。但绝不卖弄,守紧小说家、文学家的本分。

王安忆同名小说改编话剧《长恨歌》海报(2004)
《考工记》又如一面镜子,照出当下文坛中不少写作者的虚妄与做作。此作让我重新审视作者,思考长篇小说格局:并非只有鸿篇巨制一路,小视角、小场面、少人物、少冲突也是一路。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篇幅上出现“小长篇”的趋势。《考工记》显然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可以探究的实践经验。沿着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均出自江南的思路,我再次认定江南才是出真正长篇巨作的福地,阴柔内敛同样适合长篇小说。
上海近百年崛起,沐浴西风,在中国的确独标一格,其影响新锐强大,其标志亦相当明显。即便“文革”时期,上海文雅讲究依旧;即使市场经济潜规则大行之际,上海生意大多敞亮。城市管理,井井有条。我特别赞成来自上海学术界的一种新说法:上海“东方巴黎”之成就并不仅仅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智慧和财富与世界市场接轨,与世界携手共同创造了一个传奇的“上海滩”。
上海的市井生活、城市个性,以及沐浴西风的特点,促使城市在不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殊异的文化传统。书写上海,从十九世纪起就开始形成气候,王安忆后来居上,成就突出。早年以儿童文学和知青文学起步,但很快就在大上海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立足点。从《我爱比尔》到《长恨歌》《天香》,再到《考工记》以及一大批中短篇小说,王安忆确立了对这座城市的书写。毫无疑问,在中国内地都市文学创作中,王安忆雄踞要位,其对中国城市成长的艺术把握与思索,已然托出作家书写城市历史的一颗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