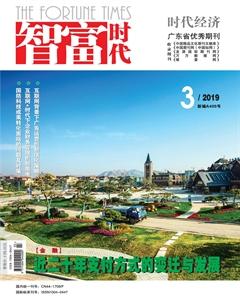论《河童》中对现世的讽刺
马畅
【摘 要】《河童》是芥川龙之介晚年的代表作品,在《河童》这篇小说中无不充斥着他对生命、对人性宗教、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与怀疑。他用怪诞的手法描写了23号精神病患者在河童国的见闻与经历,以河童国的社会形态来讽刺映射日本当时的社会黑暗面。本文将从家庭关系和人类关系、资本主义残忍的剥削压迫,以及宗教死亡的态度这三个角度对《河童》一文中对现实日本的讽刺进行分析。
【关键词】《河童》;现世;讽刺
芥川龙之介作为“新思潮”派的代表。其创作风格与文学内涵在近现代日本作家中也是独树一帜,虽然他在35岁时便早早因现实的幻灭而自行中止了生命,但他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仍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作品。《河童》作为他晚期的代表作,也最能代表其结束生命前的的思想路径和内心状态。这篇文章是作于1927年,之后不久芥川就自杀了。这不禁会使人猜测《河童》中是否蕴藏有他自杀的原因和征兆。《河童》中以日本传说的河童世界为背景,表达他出了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并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厌烦。想逃离,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一、社会关系与战争
河童是日本传说中的一种动物,河童的总体形象就像一个高三四十公分奇丑无比的青黑色猴子。在这些“丑陋低级”的河童的眼中他们是比人类还要高级与聪明的动物。我们人类当作天经地义的正义、人道,河童听了会哈哈大笑。我们觉得荒谬的,他们却当成正经。他们会征求未出生小河童的意见,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他们认为只考虑父母的利益太自私也太可笑。因此小河童可以在出生前向他父亲表示:“我不想出生,因为,首先仅爸爸的遗传性精神病我就受不了,其次我不愿做一个河童”。这是否在讽刺人类父母的生育意愿从来都只是父母的选择,未来孩子的生存环境从不在考虑范围内,人类会面临很多选择却永远无法决定自己是否应该降生于这个世界,我们有选择结束生命的权利,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选择开始生命的权利,如果有,这个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幸的孩童,因父母的不负责与一时冲动而要孩子承受一辈子的痛苦。其次,河童的家庭更是一种互相折磨的存在,并且他们以此为乐、“父母、子女、夫妇、兄弟等等都以互相折磨为生活的唯一乐趣。”在这里,芥川通过河童国的习俗,影射了人类世界的人伦关系。其言外之意是说,人们应该相敬相爱、互相包容,若彼此折磨、迫害,终究会丧失人性而不配为人,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如果人们相互仇视、自相残杀,那与丧失亲情伦理的河童也无异。[1]
芥川还通过河童国和水獭国之间的战争来映射人类之间的战争。不管是什么种族的战争结果往往都是两败俱伤,伤亡惨重,因为错杀了一个水獭这个小事,由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结果是河童的胜利,但他们也牺牲了大量河童,战争不仅在河童间,人类社会中两次世界大战均是小事作为导火索,人类自相残杀,流血牺牲惨重。芥川通过对河童国战争的描写来讽刺人类战争的无情,以及给人类本身带来的伤害。
二、“吃人”的资本主义
处于机器大生产时代的河童国,因机器的高效取代了手工劳动力,机械工业迅猛发展,职工大量被解聘,每年不下四、五万匹河童失业,可是奇怪的是该国却不见罢工的风潮,问及原因,河童资本家噶尔很坦白地说:“这是因为都吃掉了呢”,河童国执行一种“职工屠杀法”,每年解雇的河童都统统被杀掉,肉便作为食物让大家吃掉。大言不惭的说这样还给河童免去了饿死或者自杀这些麻烦。由于屠杀量大,故肉价相当地低落下来了。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芥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同时还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思想的“自然成长”。从形式上讲,作家用狂人讲述的离奇古怪的河童国来观照日本资本社会,实际是提供了一种象征物,一面哈哈镜。[2]资本家的横行霸道,剥削压迫工人阶级。我们对河童国的职工屠宰法愤怒生气,却没有任何的立场来控诉河童国的无情,人类社会比河童国更加殘忍。职工屠宰法中浸透了河童的血。这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狂人怎能不愤慨呢?然而审判官却反唇相讥道:“别开玩笑啦……在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的女儿不也是在当妓女吗?吃职工的肉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不仅河童国的河童已经将此作为稀疏平常的事情,人们不是也没有办法对人类社会的资本家奋起反抗,只能是一味地顺从。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不同的是,芥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 鲁迅先生批判的是封建礼教的“吃人”。[3]两者不同中又有相似。都是“吃人”一个吃的是人的劳动人创造的价值,另一个则是吃的思想。
三、宗教与死亡
《河童》中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是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生活教,生活教的本质就是受苦,活即意味着承受痛苦,因此圣徒斯特林堡、尼采等人在受尽生活之苦后选择信仰生活教,为生活教的教义是“生机勃勃地生活下去”。生活教无视现实中存在的实际困难——生活之苦、病痛之苦、社会丑恶等等[4]芥川龙之介是是信仰基督教的,但他的信仰又十分多元化,对佛教等也颇有涉猎。他信仰宗教追求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肯定这种宗教思想,对宗教还怀有怀疑态度所以他很矛盾,河童中给别人讲经传道,十分圣洁的教会长老,也会偷妻子的钱去买酒喝。这一讽刺,揭露和抨击了河童国宗教的丑恶,也巧妙地讽刺了宗教背后不堪的一面,他极力抗争却又不得不安放自己的思想,这种分裂的他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芥川笔下的河童形象中,最为突出的是诗人特库,这一以“超河童”自居的诗人,芥川倾注了全部感情,在他身上芥川的投影更为明显。诗人特库对于生命与艺术的理解也就是芥川的思考。特库自杀以寻求解脱,他的艺术灵感已经枯竭,他认为他已经没有了价值。失去了艺术生命又对现实社会绝望。诗人的自杀及死后他与亡灵同灵学会会员的对话。也被认为是芥川自己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及对于死后一些问题的担心。“描写陷入艺术与人生的绝境而自杀的特库的同时,联系自己的死发出深刻的感慨。”这是颇有道理的。借这位诗人之口,芥川道出了自己的痛苦、疑惑、矛盾和绝望。[5]我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对于结束生命自己还是可以掌控的。
四、结语
全文采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视角,用人类的视角来对河童国与人类社会进行对比,河童国的种种习惯如孩子出生的权利、家庭的结构等让身为人类的他觉得十分疯狂。当它终于想要回到人类世界的时候,却发现人类社会暗流涌动,也远不如让令他觉得疯狂的河童国透明。他妄想回到河童国并把河童国看做是他的故乡,23号精神病患者替他表达出了对社会的无序的无力,政治与资本制度的残忍的无奈,以及对于信仰与生存的怀疑。同时这也是他对于当时日本社对会大环境的失望与对个人生存意义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孙立春.试论芥川龙之介动物题材小说的寓言行[J].名作欣赏.2010(06).
[2] 鲁杰,王宗.略论《河童》中的审丑艺术[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9).
[3] 陈珍.《河童》与《野火》中的“吃人”意象探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2).
[4] 覃振桃.论芥川龙之介《河童》中的艺术与宗教[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8).
[5] 于丽萍.芥川龙之介及其晚期作品《河童》[J].日本研究,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