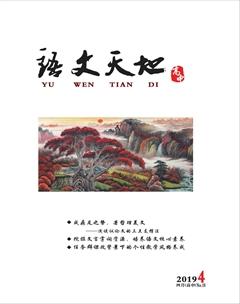从比较中掌握文言知识——以《五人墓碑记》为例
毛雪梅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比较始终能够给思维与理解提供重要帮助,这是因为人们在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进行认知时,均会以比较的方法加以区分,让此事物与彼事物的不同之处显现出来。对于高中阶段的文言文教学来说同样如此,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文言文学习时,便可以针对不同文章特点加以比较,让学生在比较中汲取知识、谋求进步。比如在学习《五人墓碑记》这篇千古名文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文体、内容以及写法几个方面横向比较,有助于学生得到更多的文言知识熏陶。
一、从文体出发的比较
文体是文章的根本,作者在行文之初,首先要考虑的便是文体问题,而读者在接触某篇文章时,亦应首先明确摆在自己面前的是哪种类型的文章。对于文言文来说,其文体特征往往在题目之中便显现出来,像很多文章均以“记”为题,如《小石潭记》《桃花源记》《游褒禅山记》等,本文所举《五人墓碑记》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记”属于一种常见古文文体。基于学生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可以明确“记”这种文体应当归于散文这一大类。
之后则可以将本文与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名篇佳作进行对比,由此探索出《五人墓碑记》的不同手法。比如《小石潭记》重在写景,其间多有清静悲凉之感,作者以小石潭之深幽来比拟自身情怀;《岳陽楼记》以重修岳阳楼为契机来借景抒情,重在人生感悟的抒发,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内涵形象地铺展出来。相比而言,《五人墓碑记》则是利用记人的形式,展现出自己对于生死大命题以及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可谓以记人为表,以议论为里。在这样的比较之后,学生更容易发现“记”这种文体的应用广泛性,既能用于记人记事,也能用于写景抒情,还可以用于说理论证。在学习《五人墓碑记》时,适时适当的比较分析,对不同侧重点的“记”分别指示其特点,会让学生更加全面地理解相关知识内容。
二、以写法为重点的比较
在进行《五人墓碑记》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将相关历史资料展示给学生看。比如在《明史》列传里面,便有周顺昌等人的记述:“佩韦等皆市人,文元则顺昌舆隶也……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傍,题曰‘五人之墓……”学习《五人墓碑记》的同时,把《明史》中的相关段落一并展示出来,会使学生意识到对于同样的内容,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写法,并独立探索不同写法的优势,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与概括。
首先,从文体上进行分析,《五人墓碑记》属于“记”,这在前文已经述及,而《明史》中的相关记载则为“传”。其次,从行文手法上分析,《五人墓碑记》是一边议论一边抒情,而《明史》中的相关列传则是对过程的忠实与客观记录,并不掺杂主观的感情。再者,如果分析描述过程可以发现,《五人墓碑记》是对五人献身精神的颂扬,但《明史》列传则比较冷静。最后,若是对写作手法进行探讨,则《五人墓碑记》的对比手法反复应用值得注意,在对比之下,五人的形象鲜活地展现出来;而《明史》列传的相关描述则比较平淡,特别是对五人就义的过程同样如实记录,符合史传体裁的特征。
三、基于内容的比较
在学习《五人墓碑记》时,重点要基于内容去掌握文言知识,在接受五人的死难过程描述内容以后,对五人之死加以深入研究。比如对于“激于义而死”如何理解?即什么是“激于义”?在思考之后认知:五人之死同现实生活中的病死、因事故而死等是全然不同的,他们死后被尊崇、被安葬,在墓门树立石碑,显现出这五人之死是因难得的正义与义气。他们选择死亡,是重于泰山的。和他们相比,一些生前安富尊荣之人,一旦死去便马上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二者在比较之后,前者因为激于义而死,后者平平凡凡而死,将给学生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另外,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将此五人的表现同一般缙绅的行为加以比较。五人是市井小民,地位不高,家境不好,同时又“素不闻诗书之训”,而那些缙绅则生活优渥,满腹经纶。然而在魏忠贤作乱之际,满腹经纶的缙绅认贼作父,这五个人却可以做到不计生死,奋起反抗。在这样的对比之后,五人激于义而死更显出难能可贵:他们社会阶层不高,也没有学习过高深的文化,却可以将自己内心的朴素忠义观念落实到实践中去。在他们去世之后,其姓名被标于大堤之上,使天下人都能够前去拜祭,可谓虽死犹生,虽死犹荣。这种对比,使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得到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与生死观的熏陶。
事实证明,在学习《五人墓碑记》这篇文章时,若不进行这样的比较,学生便不容易对文本内容有深刻的理解,也无法真正体会文章之中的精神内涵。在内容的比较之后,即使教师不做更多的讲解,学生也将从中感受到作者所欲表达的情感。对于这篇文章是这样,对于其他文言篇章的学习同样如此,教师都应当努力发现内容上的可比较之处,以独特的介入视角启迪学生。
高中时期的文言文教学始终是重点和难点之所在。教学实践证明,教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采取比较法,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使学生更加轻松与深刻地领会文言文的知识精髓,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独立阅读与思考的能力,从而给高中语文课堂带来全新的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