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金色
张佳玮
人人都爱金色。璀璨的,绚烂的,闪亮的——这不,手机都爱出个把香槟金、玫瑰金。当然也有其他金色。比如白金,比如紫金。人类所爱的,还是温暖华贵的暖金色。
哪位问了:金色是黄色吗?不是的。黄色可以是柠檬,是香蕉。但金色不能那么鲜亮。“金无足赤”,金是该有点赤色的。大概是:黄色多一点橙,或琥珀色少一点橙,那就是金色。
为什么要镶金呢?嗯,为了显得有钱呗!
金色可以是东北剥蒜小妹身旁穿貂大哥脖子上晃动的大金链子。东北大哥的大金链子土吗?说明大哥是个实诚人,有钱!
金色也可以是真诚。我们那里早年间,定亲时婆婆要将当年自己当嫁娘时婆婆送的金戒指给媳妇,粗大笨重,喜笑颜开:你看这戒指,够分量吧?真金!不信,我咬给你看,还有牙印呢!
当然,主要是显摆。20世纪初,有化学家为俄罗斯贵族用华丽璀璨的金餐具吃鱼子酱辩护,说别的器具都有味儿,就金子特别稳定,不会影響鱼子酱的味道——按这个逻辑,上好的树脂勺子还没味儿呢,您干吗不用?
所以最初对金色的使用,都逃不脱高贵与奢侈。埃及的金制法老面具,希腊人传说中伊阿宋去寻找的金羊毛,公元前意大利人用的金冠,皆如此。金子是财富,是华贵,是购买力,是一切。
1492年,西班牙占领格拉纳达,阿拉伯人被赶过直布罗陀海峡,同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伊莎贝拉一世与丈夫费迪南二世喜极而泣,认为这无限的财富是上帝的恩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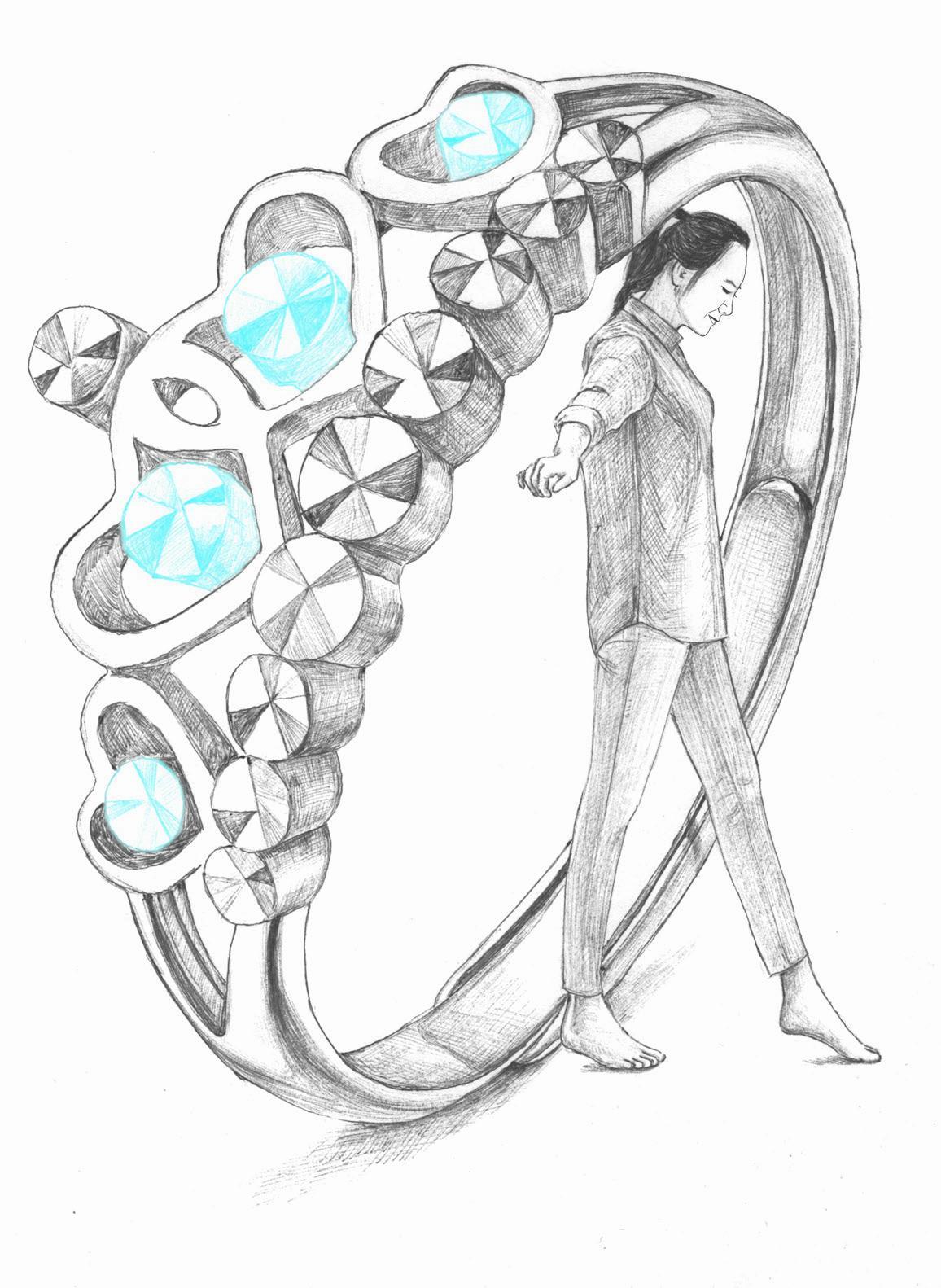
为了酬报上帝,他们修了塞维利亚主教座堂,其中有无数金闪闪的装饰。
17世纪,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喜欢土豪金。当然,那会儿巴黎许多金色装饰不是金子,而是黄铜。
当然,也有人是真的爱金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大师切里尼说,他喜欢金色,“金子很容易加工,而它光芒璀璨的美丽,是无可比拟的”。凡尔赛的设计师之一勒诺特尔先生则认为,金色是漫长冬天里,最让人舒适的颜色。
仔细想想,也是:秋天黄叶满地,是金色的;秋日麦田,是金色的。夕阳是金色的。烛光是金色的。甜白葡萄酒是金色的。蜂蜜是金色的。金色很温暖,又甜蜜,尤其在昏暗之时。
谷崎润一郎先生在《阴翳礼赞》里提过这么个观点: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素来对幽暗阴影有讲究。金色在日光灯下看来,一点都不美。但若阴影昏暗下看来,泥金画与金箔,就有种绚烂的金色光晕,很美。
这么想,还真是。在如今这不愁照明的时代,明亮的日光灯照耀下,北欧人推崇的原木质感、科技爱好者喜欢的暗沉金属,甚至陶瓷与皮革,都显得温润不张扬,而大金链子却容易显得浮华俗气。
但在过往那个照明稀缺、室内经常幽暗、高纬度地区半年都阳光稀缺的时代,金色却在晦暗中荡漾着梦幻的温暖之美呢。
这么想来,在半夜烧烤摊旁的大金链子,的确比在白日T恤上闪耀的大金链子要顺眼得多。奥黛丽·赫本小黑裙上的一点金饰,比梦露一身白衣一头金发要更适合东方审美。
所以,到最后,也许穿金戴银并不是为了炫富,只是骨子里的一点传统东方审美:在一个色调暗沉的季节或环境下,需要些许收获的、甜蜜的、温暖的金色。实际上,切里尼早就说了:真正的金都不那么扎眼,而是温暖如夕阳。而贝尔尼尼更吐槽过路易十四明晃晃的那些太阳王审美,“都是黄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