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古典与修辞
何博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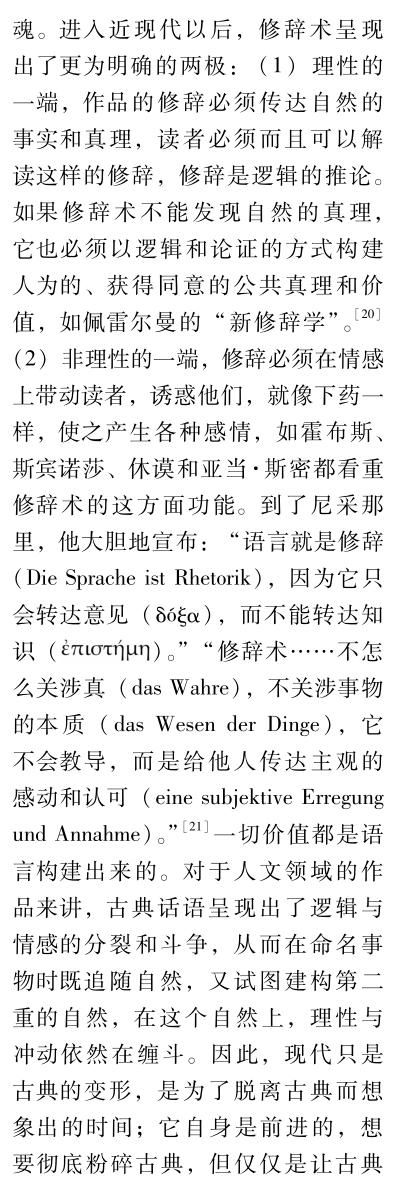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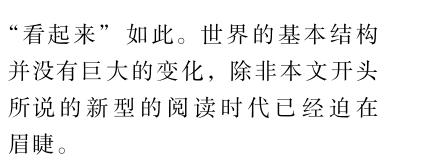
尝试从三个概念入手来谈论读书和治学,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有助于组织起结构和展开如下几个论题:在现代世界,古典没有被遗忘,而是以瓦解和多元的形态,持久地留存;古典式的阅读依然有着它的重要价值;这种阅读是一种阐释和想象的方式;它的对象就是自然或人为的修辞所编织的身体;修辞学研究依然是人文学科的核心之一。
提起读书,有人或许就会想起曼古埃尔(AlbertoManguel)的《阅读史》[1],进而还有他的《夜晚的书斋》[2],有的人总是以近乎偏执的态度收藏陨石般的图书,在有限的空间里陈列出一个不会流浪、比心灵还狭小的宇宙。当然,阅读并不止乎书籍,有人会设想这样的问题:书是阅读的必然对象吗?它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书的世界,阅读是什么样的?它是不是仅限于书?其他可读的东西,甚至是其他载体的书,与纸书又有什么区别?
这些问题在费希尔(StevenRog erFischer)的学术作品《阅读的历史》[3]中都有一定的梳理和解答。在最后一章,他展望了以视觉为中心的未来世界的阅读,阅读成了交流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接受文字图书的活动。也许就像今天,颤抖如落叶的短视频就是让人阅读的未来形式,尽管人们未必能读到什么,但他们可以模仿,这就是影像阅读带来的交互效果。换言之,视频中的人和场景,就是原本作为文字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意义,它们无须再加工,直接从世界中写成;没有过去,没有“古典”;生活就是文本,影像就是书纸,时间在翻页,社会来阅读。由于这样的视频还基本上承受着音乐的策划,这里面又引出另一个问题,阅读也要依赖“听觉”,这不单单是暗示有声书这种形式。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不再仅仅靠视觉来读,还需要“听读”。“抖动的声音”更能控制“目光”,牵制阅读的倾向。[4]与这种新型的阅读相对,可以说,从前的各种阅读都是“古典的”。
对人文学科的工作者来说,他们很难接受没有书本,甚至没有纸卷的世界,至少这样一来,没有哪种东西可以将研究成果物化,让时间凝固,在这个意义上,著作仍然就像古代的石板、雕像、金字塔、庙宇一样厚重,令人生畏。他们需要空间,必须以祭祀的方式管理木乃伊般的典籍,就像克拉克(John WillisClark)《照管图书》[5]里描绘的那些大教堂、修道院中神圣的馆室;前辈的学者装在可以手捧的佛龛里。当然对于另一些相信默克斯基[6]的人来说,存有电子书的膝上电脑更能掌控,更可以满足占有欲和安全感,不至于让自己显得渺小。这样一来,问题就从书的载体转向了其所占有的空间性上。人文学者喜欢这种边界固定的区间,或许可以说,就是执迷于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只有书可以象征它,从而展现理智超越物质和现实的地位。
他们会问出更极端的问题。存不存在沙之书?有没有只属于自己这个群体的文本和知识?他们还会尽可能创作出巨大的难以阅读的东西,即使是在现代社会。除了那些在书架上正襟危坐、卷帙浩繁的学术专著,他们还尝试其他的可能。有一位作家朋友推荐过新出的《灵的编年史》[7],可以相信,这是一本精妙的艺术品,配得上它的价格,尽管一些从右向左排列的汉字令人晕眩,抗拒着视线。其作者也是学者,有心国学,迷恋坚硬的文字,[8]所以才会写出这种不易阅读的小说般的专著。它也许近似《芬尼根守灵夜》《哈扎尔辞典》,甚至是《微暗的火》以及同一作者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两千余页的评注。它们的作者在本质上依然是热衷典籍的古典人,而不像石察卡(V.M.Straka)及其《S.:忒修斯之船》[9]。
这样一来,话题就转向了古典。人文阅读(还有写作)在本质上依然是古典式的:依靠纸质图书,崇尚典籍,建构知识和想象的空间;解读者的作品又被后面的一代代人继续阅读;所有新潮的文本(如果不被遗忘,但即使遗忘也会被发掘)都会被古典化,有的成为经典,经历长时段后化为相对的古籍;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而是时间还没有让它变得那么旧;也因为现代人习惯于将并不长的时间历史化,所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争,不只是在斯威夫特的18世纪,[10]當它终结时,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文化会消亡/继续。对于当代来说,古典拖住了影像视觉占据主导并且有可能“焚书”的未来,让它不至于迅速降临。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典”这个话题在日益发展的今天依然颇为盛行,依然是争议的话题。因为古典是长久存在的阅读方式的源头,一旦阅读,就要从古代开始读起,一本书越古老,就越像夕阳般金黄的琥珀。也许没有哪个人文学者的书房里没有古籍,所有崇尚阅读图书的人都会最终返回古老的著作,无论中西。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并不是看不见的往昔,而是若即若离、下着灰色雨的海岸线,就像这一行延伸的文字。虽然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在《海葡萄》(SeaGrapes)一诗的结尾说,Theclassicscanconsole.Butnotenough,但他本人清楚,没有这种慰藉又是不能生存的:一切在重复,希腊的奥德修斯可以出现在欧洲,也可以在加勒比,在中国;没有奥德修斯,也会有传说中的某个狡猾多情的漂流者;没有荷马,也会有《奥马罗斯》(Omeros)。
当代更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古典的研究。他们的身体是现代的,一旦进入台灯下,影子却是古代的。他们也许目的不同,有的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学,有的试图复活严格的古典学教育和学术体系(如看重小学、文献编纂和校勘,遵循古代或现代的体例和义理逻辑来阐释文本),有的为了研究现代的问题[11],有的出于个人的兴趣,[12]无论是否信仰,有的则将之用于虚构性的创作。
从学术的角度说,进入古典是艰难的,但一旦涉足,虽然如陷泥沼,却又是迷人的。首先在于,它对语言和文字的要求极为严苛。一门语言总是牵扯着其他的语言,就西方古典学来讲,学习希腊语的学者,必须修习拉丁文,而且除了英语之外,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至少要有阅读的能力,因为有庞大而不能忽视的研究文献需要它们作为钥匙。由于希腊文明还流传到了其他的地区和民族,如果加以研究———事实上国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那么比如,流传到亚美尼亚地区,就应该了解这方面的语言;在闪语地区,就不能不学古代叙利亚文,尤其是阿拉伯文,否则会错过阿维森纳这样的大师还有他的巨著《治疗论》。对研究东方文明和亚洲历史的学者,要求就更高,诸如希伯来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藏文、蒙古文、梵文、巴利文,现代语言的俄语、日语、土耳其语等都在学习的范围。这些令人目眩的文字和一些仅凭想象才存在的声音,既是挑战和困扰,又是值得开拓的疆域。这样的文字世界并不亚于徐冰的《天书》,甚至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后者的创作来源。
这样的阅读最为原始,直接要面对古老的文本,有的经历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古典学者和历史学者要亲自收集抄本,校读文字。他们面对的不是人为编制的奇异的文本,比如前面说过的那些;他们不是玄幻作家,玄幻的是自然和人类难以超越的时间。他们观看古典的角度,也许就是低机位的小津式的“榻榻米视角”,或者是锡兰(NuriBilge Ceylan)和贝拉·塔尔(BélaTarr)那种缓慢、冷静和悠远的长镜头,他们的目光就仿佛来自维米尔的《地理学家》和洛威尔(RobertLowell)《收场白》(Epilogue)中考察、检视和记录的眼睛。
但是,有的古典研究者着眼于义理和思想。他们并不看重语言文字,对于古典和现代外语,甚至也没有掌握到精通的程度,基本上依靠标准的译本。有的学者会质疑这样的研究风格,但这其实也是治学的一条路径。王阳明就会这样认为,“大抵训释字义,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奥蕴,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语所能喻。后人多有泥文着相,专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从法华转也”。(《传习录·与黄勉之书》,其二)[13]若不在字句和版本上追求,能得其精义足矣。比如阅读《理想国》,斯灵思(S.R.Slings)典范性的古希腊文的校勘本和勘注[14]是必读的,但如果不能完全进入希腊文,现代语言的译本其实足可传达主要的意义与逻辑,如肖利(PaulShorey)和阿兰·布鲁姆的英译本。对于从分析哲学角度研究古典文本的学者———也是当今最为流行的研究思路———只要在关键概念和字句上不迷失,这就可以把握作品最基本的意图。还有一些學者从戏剧性和文学性入手,他们虽然可以熟练掌握文字,但也不拘泥于此,而是侧重理路和启示。更有些学者对古典持批判和超越的态度,不希望“死人抓住活人”(《资本论》),他们在阅读《理想国》时,会反讽地推荐《国家与革命》,但这并不冲突:古人就是用来摆脱的,直到摆脱者被时间消化。身为“历史天使”的本雅明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恰恰采取了拟古典的方式,消解/弥合既完整又破碎的历史。
无论是哪种进入古典的方式,它所依赖的初步基础都是阅读自然。尽管“古典学”这个概念与历史建构密切相连,而且有着人为创造的过程,[15]但它的根基依然是一种原始的命名思维。就像《旧约·创世记》2:19—20说的亚当命名万物的典故(译文从和合本):“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古人正是在解读自然的语言,倾听世界的声音。所以福柯《词与物》中会说:“在原初的16世纪的历史存在中,语言并非一套任意性的体系(un systèmearbitraire);它置放于世界之上并且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既是因为物本身作为语言,隐藏和宣明了它们的谜(cachentetmanifestentleurénigme),又是因为,词语自行提供给人,就如物被辨认出一样。人们为了认识自然而打开、拼读和阅览的这本书中的巨大的隐喻,正是另一种隐喻传送的可见的、更为深刻的反面,它促使语言存在于世界之上,存在于草木、石头和动物中。”[16]在这个时期,四种相似性(laressemblance)成为知识型(episteme)的建构方法:适合(laconvenance)、仿效(lemulation)、类推(lanalogie)与交感(lasympatheie)。万物如谜语,等待古人的解读,这种魅力促成了林奈和格斯纳(ConradGesner)的命名,衍生出了现代的《塞拉菲尼抄本》(CodexSeraphinianus),涩泽龙彦版的老普林尼,[17]博尔赫斯的《想象的动物》,还有沃尔科特诗中名称不定的加勒比的植物。而如格兰维尔(J.J.Grandville)的奇幻画和克苏鲁神话(CthulhuMythos)则是对自然事物和世界的变形和重塑。
依靠对自然的“阅读”,对万物的命名,人文学科保存住了古典的阅读和幻想的方式。上述这些千奇百怪的作品与严肃的古典学研究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可以大胆地认为耶格尔(W.Jaeger)编订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就是一部解读古典、将片段缀合、使之成为完整却又破碎、合乎自然而具有想象力的艺术品。他也许就像佩雷克(GeorgesPerec)在《人生拼图版》(La Viemoded'emploi)[18]中的做法一样:摸索锯齿,辨认图案,将之拼缀。只不过佩雷克是自己构造图像,切割,分散,让读者拼合。又如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19],既是对古典小说“人名+绰号”的谱系的戏拟,又是学术性的“诗史”,每一个人如同拼图的一块,或构成星座的星点(每个人恰恰就排入了天罡星与地煞星),但它们按照不同的阅读“目光”(如着眼于地域、阶层、政治倾向、团体、代际等)可以构成新的图案、星簇或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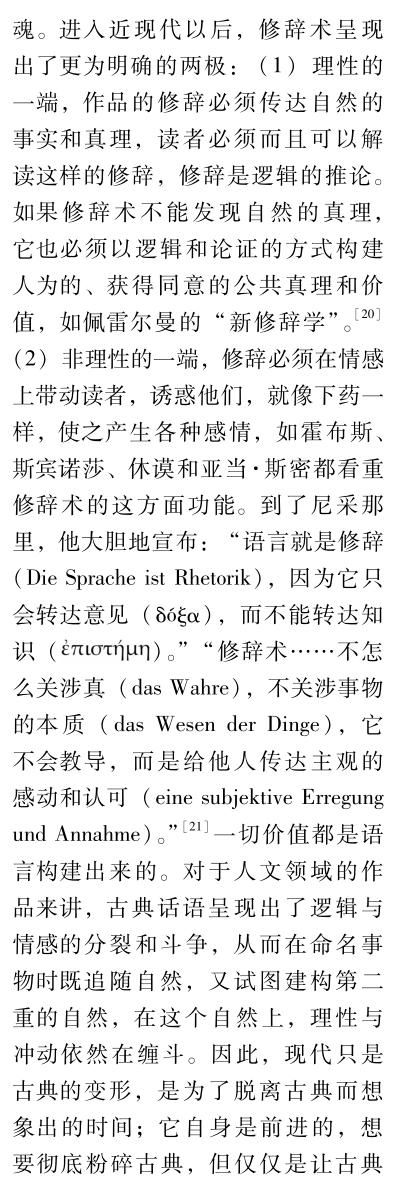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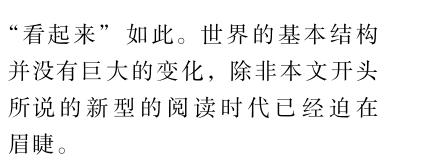
这样,阅读就在应付这两种修辞之间。一方面解读古典的逻辑和对自然价值的证明,另一方面要阐释古典时期涌动的非理性的狂躁;一方面阅读历史中的人如何从理性的角度对自然价值加以否定和超越,考察过去的知识如何被新的思想体系覆盖,修辞的变化就像地层的沉淀,但另一方面,又要勘探其中的裂纹,挖掘和辨认难以整合的残余,就像拉康清醒地将康德和萨德并作一对,也许康德的影子或背面就是萨德。无论承载修辞的文本时代如何,这种阅读的方式是不变的:它探寻修辞,从而走上一条因自身而不断分叉的路,跟随阿里阿德涅线,但没有止境,误入无限的歧途———就像布柯特(JamesWardByrkit)的《彗星来的那一夜》(Coherence,2013);它的读物是一部宏伟的自然百科,或这本书繁衍的后代;它手持一面复制万物的镜子(但也是自然提供的),让自己迷惑,超越自然,最终被自然吸收为一个词。(参见《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
当专业化统治这个世界,很多人文学科获得了承认,但也许失去了活力,如“修辞学”本身,经历了起起伏伏,一旦成为学科之后,被赐予了研究框架和体系,但却丧失了原有的锐劲,海德格尔、尼采、保罗·利科、罗兰·巴特都是它的解救者,但它无须拯救。人文学者似乎不能遗忘无形的“修辞”首先就存在于自然之书,它是人类之书的基础。自然这张宏大的文本具备着各种潜在的辞藻,等待解读和误读,学者们难以离开古典和经典的阅读方式,他们接受专业制度的训练,但也需要对这种制度进行想象性的超越,这完全围绕着修辞展开:深入到不同话语的修辞结构中进行解读;尝试在不同事物、不同学科之间建立灵活的隐喻、换喻、转喻、反讽等关联;用修辞的论证和逻辑进行写作和研究,但又能让完整的框架自行破碎化;掌握命名和概念的生产技术,但又能赋予旧的概念全新的修辞力度;对于材料,用措辞来揭示事实,但在言语上又留出务虚的可能。这样的研究似乎就像本文一样:用车辙或轮胎印迹般的书名号,用这样一份偶然凑成的书单,将读者带向德拉邦特(FrankDarabont)《迷雾》一样的修辞世界:读者一绝望,雾气就散去;而作者就生活在回避自身又重返自己的永恒循环,还有某种吊诡之中,就如这句话:本文没有使用一个“我”字。
注释
[1][加拿大]曼古埃尔.阅读史[M].吴昌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加拿大]曼古埃尔.夜晚的书斋[M].杨传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李瑞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也可以参见罗伯茨(ColinH.Roberts)和斯基特(T. C.Skeat).册子本起源考[M].高峰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美]坦瑟勒(G.ThomasTanselle).分析书志学纲要[M].苏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4]这里似乎可以联系米歇尔·希翁(MichelChion)《声音》中的分析。[法]米歇尔·希翁.声音[M].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尤见第一章第3节的“声音图景”;第六章论声音的力量;第十章论视听的联系。
[5][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照管图书[M].杨传纬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6]作为电子书和数字阅读的崇拜者,贾森·默克斯基也必须用一本“纸质书”的题目来表达惊人的预言,见BurningthePage:TheeBookRevolutionandthe FutureofReading(Sourcebooks,Inc.,2013),中譯本见焚毁书籍[M].韩玉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7]原刊于《收获》(长篇专号,2017年冬卷),见霍香结.灵的编年史:秘密知识的旅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8]他用另一个名字辑成《明清篆刻边款铁笔单刀正书千字文》,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这本书与那一本并不矛盾。
[9]艾布拉姆斯(J.J.Abrams)和道斯特(DougDorst).S.:忒修斯之船[M].颜湘如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仍然不矛盾,导演或监制过《星球大战》《星际迷航》《碟中谍》这些系列,还有《科洛弗档案》《科洛弗道10号》《科洛弗悖论》的艾布拉姆斯必定会构想出这样的吸引视觉的“反图书”。
[10][英]乔纳森·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M].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11]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2]如冯象重译《旧约》,最早像《创世记:传说与译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最新有《圣诗撷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13]也见“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在知道者默而识之,非可以言语穷也。若只牵文泥句,比拟仿像,则所谓心从法华转,非是转法华矣。”(《传习录·答陆原静书》)两句本自《坛经·第七品》:“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14]PlatonisRespublica(Oxford ClassicalTexts),OxfordUniverstiyPress,2003;CriticalNotesonPlatosPoliteia,Brill,2005.
[15]关于古典学的建立和发展,见[德]维拉莫维茨.古典学的历史[M].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M].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6]M.Foucault:LesMotsetles Choses,éditionsGallimard,1966,pp.49—50.见第二章,第四节“物的书写”(LécrituredesChoses),译文为笔者所译。
[17][日]涩泽龙彦.奇想博物志[M].黄怡轶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18][法]乔治·佩雷克.人生拼图版[M].丁雪英,连燕堂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19]不能离开王培军的笺注本,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如《管锥编》并不是没有体系,它的体系是自然的,依附于古代典籍,它的任务就是建立联想,提供更多的可能的读法。另外,作为一部在修辞层面上进行游戏的作品,它研究的对象恰恰就是下面要说的修辞。
[20]ChamPerelman&LucieOlbrechtsTyteca:TheNewRhetoric:ATreatiseonArgumentation,J.Wilkinsonand P.Weaver,trans.,UniversityofNotreDame Press,1969.
[21]F.Nietzsche:NietzscheWerke:KristischeGesamtaugabe,BandII.4,De Gruyter,1995,SS.425—426.这种修辞观影响了德里达、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