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无聊的封面
王霜霜

“神感到无聊,所以创造了人类。亚当因独处而无聊,故而夏娃被创造出来。从那时起,无聊就进入了人类社会。”
——《非此即彼》(Either-Or)克尔凯郭尔
无聊至死。
1972年的初夏,时而暖煦的阳光,温柔的海浪轻抚着西班牙海滨小镇卡斯特尔德费尔斯。此时在当地一座小旅馆里,曾出演过《月亮与六便士》的英国演员乔治·桑德斯吞下了五瓶安眠药,永久地睡去。他留下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世界,我要离开了,因为实在太过无聊…… ”
桑德斯并不是唯一把无聊和死亡连接在一起的人。2010年的《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中,两位心理学家对7500多名伦敦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并追踪,得出结论——越无聊的人越可能早逝,尽管无聊本身并不致命,但预示着身体或心理状况欠佳。
可时至今日,“无聊”成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流行。大言不惭点儿说,成了现代人类的底色。
某商业机构的一份在线调查显示,普通英国人每周有近6小时处在百无聊赖的状态。心理学网站Psychology Today的一篇文章称,美国超过90%的年轻人每天都感到无聊。在中国,有学者对黑龙江省7所高校1668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感到无聊。
无聊究竟是什么,为何人会感到无聊?这个话题如果仅仅用神经递质多巴胺缺乏来解释,那实在是乏味、无趣并且无聊。为了避免这一状况,学者们早已从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对这两个字解构探究,为“无聊”增添了些许趣味。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把无聊分成“简单性无聊”和“存在式无聊”。前者指的是做一件事情很乏味、枯燥,比如参加一场“尬聊”的聚会。后者则引起“个人意义的丢失”,陷入一种虚无感,心如止水,无欲无求,让人相信人生只是一场空。卡夫卡亲身体验过,他在日记中抱怨“似乎我所有的一切都离开了我,并且好像即使一切都回来了还是感到不满足”。
这种让人如此痛苦的“无聊”,并非与生俱来。
18世纪前,英语中还没有“无聊”一词,直到1750年,无聊(bore)第一次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中,“无聊”在很长时间内是身份的象征,是上层社会的特权,只有僧侣和贵族才感到无聊。宫廷画上,贵族们虚无的眼神无不佐证着这一说法。卡尔加里大学教授彼得·图希甚至从大量画作中提炼出“无聊”的套路——双手叉腰,倚靠在桌子上的手肘,哈欠,耷拉的脖子,空无一人。

“ 科学怪人”毕导希望,能把科学最好玩儿的一面展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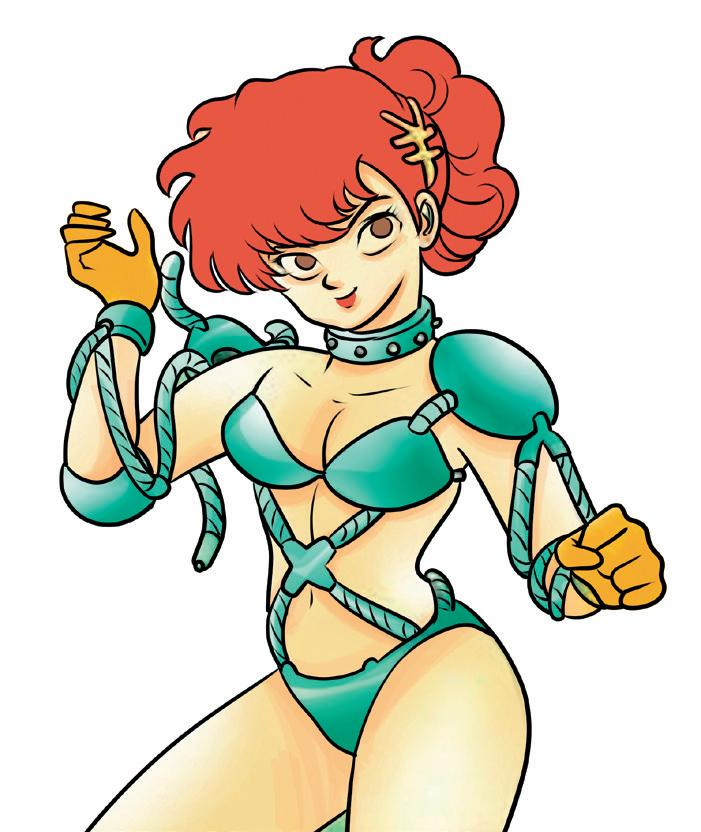
畢导为小游戏“跳一跳”研究出了抛物线大法
在很多建构主义社会学家的眼里,无聊产生于18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产物,“那时发生的社会变化形成了现在的人类”,也就有了无聊。

人称“保定爱迪生”“手工樊少皇”“无用发明家”的耿帅,凭借那些离奇古怪的无用发明、冷峻而略带神经质的表现,成为新一代网红

1月3日,河北省保定市,耿帅制作的铁面具(@视觉中国 图)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帕特里夏·迈耶·史派克对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分析发现,“产生的无聊环比上升”。这个时期恰恰与18世纪工业革命城市的货币经济繁荣并行发展。货币经济和大都会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货币经济中,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价码,按价销售。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写道,“在一个由各种事物和力量构成的巨大的、势无可挡的组织面前,他完全变成了一个齿轮,这个组织逐渐从他手中拿走了与进步、精神性和价值有关的一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们无可避免地对大都市产生厌倦,对事物漠不关心,一切变成了无意义的体验。
而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心价值与意义,希望实现自我意义,可是并不清楚实现何种类型的自我。当面对更多的刺激时,感受到更多的无聊,一方面获得了解放,一方面又成为了奴隶。
对比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无疑称得上加速器,一切似乎在步西方社会的后尘,既包括他们的繁荣,也包含他们的无聊。
文学作品已然体现了这一点。文学博士杨荣在《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写道,王朔在《顽主》《浮出海面》《过把瘾就死》等小说中,塑造了一群游弋于社会边缘的放浪不羁的“顽主”形象。他们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藐视权威和神圣,感受不到人生的理想、激情和追求。而贾平凹的《废都》中,“文化名人”庄之蝶更是一步步地走向心灵虚无。
放下手机,立地成佛。看看身边,地铁上那些刷着手机,呆滞的眼神;五道口程序员“996”的崩溃,雾霾中不可避免的虚无感,无不提醒着——人生无聊。
并非没有人反抗过。《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书中,作者给出的方法是睡觉,可是睡醒以后呢,谁又能睡一辈子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建议,“当无聊来临,将你自己完全投入无聊,让无聊压榨你,淹没你,直到最深处。”可具体方法是什么,没人知道。
既然无处可躲又无力对抗,可否给无聊增加一些有趣——尽管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显得不太搭。本期的封面故事中,我们报道了三个无聊至极的人,看看他们如何与无聊和解并共处。这其中,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村民手工耿用废物制作着各种无用的东西,他希望成为“一个自由、无用且浪漫的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毕导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科学怪人一样,喜欢用科学解释一切无聊的东西,比如大便时如何压水花。还有27岁的王村村,曾经花了三个小时数草莓籽,六个小时数一碗米,并用近两万个气球试图让猪飞起来。对他来说,无聊是一种状态、抽离,更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觉悟”。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无聊的封面。希望这三个看似无聊,实则有趣、自由的灵魂能将我们从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拯救,不求流芳百世,只求像他们一样无聊得浪漫而有趣。共勉。
参考资料:
彼得·图希,《无聊:一种情绪的危险与恩惠》,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拉斯·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齐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杨荣,《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2012
王霜霜

“神感到无聊,所以创造了人类。亚当因独处而无聊,故而夏娃被创造出来。从那时起,无聊就进入了人类社会。”
——《非此即彼》(Either-Or)克尔凯郭尔
无聊至死。
1972年的初夏,时而暖煦的阳光,温柔的海浪轻抚着西班牙海滨小镇卡斯特尔德费尔斯。此时在当地一座小旅馆里,曾出演过《月亮与六便士》的英国演员乔治·桑德斯吞下了五瓶安眠药,永久地睡去。他留下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世界,我要离开了,因为实在太过无聊…… ”
桑德斯并不是唯一把无聊和死亡连接在一起的人。2010年的《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中,两位心理学家对7500多名伦敦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并追踪,得出结论——越无聊的人越可能早逝,尽管无聊本身并不致命,但预示着身体或心理状况欠佳。
可时至今日,“无聊”成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流行。大言不惭点儿说,成了现代人类的底色。
某商业机构的一份在线调查显示,普通英国人每周有近6小时处在百无聊赖的状态。心理学网站Psychology Today的一篇文章称,美国超过90%的年轻人每天都感到无聊。在中国,有学者对黑龙江省7所高校1668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感到无聊。
无聊究竟是什么,为何人会感到无聊?这个话题如果仅仅用神经递质多巴胺缺乏来解释,那实在是乏味、无趣并且无聊。为了避免这一状况,学者们早已从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对这两个字解构探究,为“无聊”增添了些许趣味。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把无聊分成“简单性无聊”和“存在式无聊”。前者指的是做一件事情很乏味、枯燥,比如参加一场“尬聊”的聚会。后者则引起“个人意义的丢失”,陷入一种虚无感,心如止水,无欲无求,让人相信人生只是一场空。卡夫卡亲身体验过,他在日记中抱怨“似乎我所有的一切都離开了我,并且好像即使一切都回来了还是感到不满足”。
这种让人如此痛苦的“无聊”,并非与生俱来。
18世纪前,英语中还没有“无聊”一词,直到1750年,无聊(bore)第一次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中,“无聊”在很长时间内是身份的象征,是上层社会的特权,只有僧侣和贵族才感到无聊。宫廷画上,贵族们虚无的眼神无不佐证着这一说法。卡尔加里大学教授彼得·图希甚至从大量画作中提炼出“无聊”的套路——双手叉腰,倚靠在桌子上的手肘,哈欠,耷拉的脖子,空无一人。

“ 科学怪人”毕导希望,能把科学最好玩儿的一面展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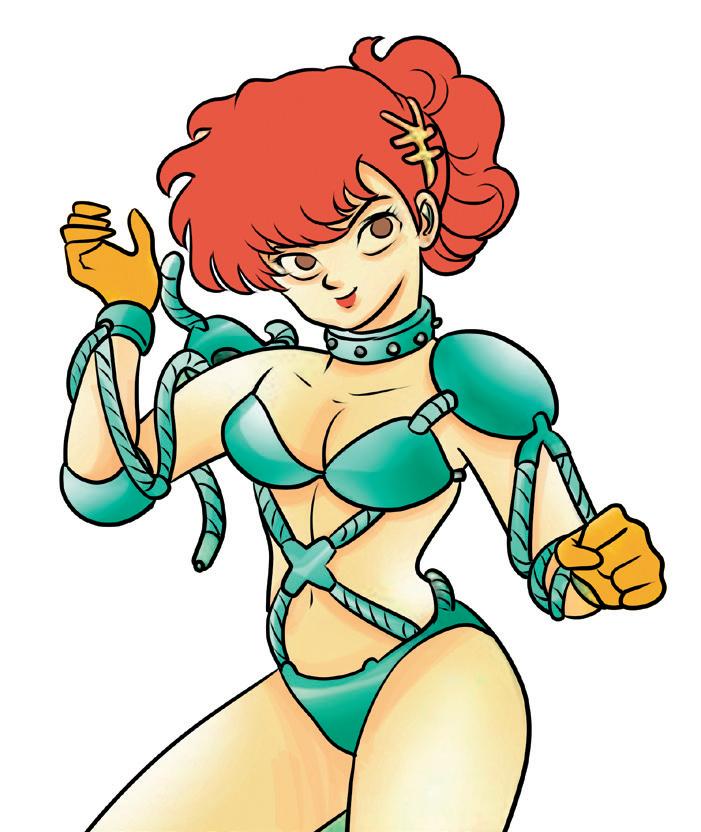
毕导为小游戏“跳一跳”研究出了抛物线大法
在很多建构主义社会学家的眼里,无聊产生于18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产物,“那时发生的社会变化形成了现在的人类”,也就有了无聊。

人称“保定爱迪生”“手工樊少皇”“无用发明家”的耿帅,凭借那些离奇古怪的无用发明、冷峻而略带神经质的表现,成为新一代网红

1月3日,河北省保定市,耿帅制作的铁面具(@视觉中国 图)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帕特里夏·迈耶·史派克对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分析发现,“产生的无聊环比上升”。这个时期恰恰与18世纪工业革命城市的货币经济繁荣并行发展。货币经济和大都会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货币经济中,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价码,按价销售。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写道,“在一个由各种事物和力量构成的巨大的、势无可挡的组织面前,他完全变成了一个齿轮,这个组织逐渐从他手中拿走了与进步、精神性和价值有关的一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们无可避免地对大都市产生厌倦,对事物漠不关心,一切变成了无意义的体验。
而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心价值与意义,希望实现自我意义,可是并不清楚实现何种类型的自我。当面对更多的刺激时,感受到更多的无聊,一方面获得了解放,一方面又成为了奴隶。
对比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无疑称得上加速器,一切似乎在步西方社会的后尘,既包括他们的繁荣,也包含他们的无聊。
文学作品已然体现了这一点。文学博士杨荣在《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写道,王朔在《顽主》《浮出海面》《过把瘾就死》等小说中,塑造了一群游弋于社会边缘的放浪不羁的“顽主”形象。他们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藐视权威和神圣,感受不到人生的理想、激情和追求。而贾平凹的《废都》中,“文化名人”庄之蝶更是一步步地走向心灵虚无。
放下手机,立地成佛。看看身边,地铁上那些刷着手机,呆滞的眼神;五道口程序员“996”的崩溃,雾霾中不可避免的虚无感,无不提醒着——人生无聊。
并非没有人反抗过。《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书中,作者给出的方法是睡觉,可是睡醒以后呢,谁又能睡一辈子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建议,“当无聊来临,将你自己完全投入无聊,让无聊压榨你,淹没你,直到最深处。”可具体方法是什么,没人知道。
既然无处可躲又无力对抗,可否给无聊增加一些有趣——尽管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显得不太搭。本期的封面故事中,我们报道了三个无聊至极的人,看看他们如何与无聊和解并共处。这其中,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村民手工耿用废物制作着各种无用的东西,他希望成为“一个自由、无用且浪漫的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毕导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科学怪人一样,喜欢用科学解释一切无聊的东西,比如大便时如何压水花。还有27岁的王村村,曾经花了三个小时数草莓籽,六个小时数一碗米,并用近两万个气球试图让猪飞起来。对他来说,无聊是一种状态、抽离,更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觉悟”。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无聊的封面。希望这三个看似无聊,实则有趣、自由的灵魂能将我们从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拯救,不求流芳百世,只求像他们一样无聊得浪漫而有趣。共勉。
参考资料:
彼得·图希,《无聊:一种情绪的危险与恩惠》,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拉斯·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齐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杨荣,《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