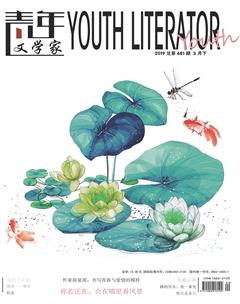王鲁彦的革命叙事
方竹欣
摘 要:20世纪30年代,王鲁彦的革命叙事呈现出如下特点:从经济视角揭示阶级矛盾;民俗盛事的插入赋予了作品浙东地域风味与宏大叙事的感染力;塑造了悲剧青年农民领导者形象——华生;借助幻觉揭示人物心理和农民的悲惨命运,以此控诉剥削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
关键词:王鲁彦;革命叙事;经济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9-0-02
30年代的中华大地正是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受到现实的感染,王鲁彦以昂扬的热情书写这时代的风云激荡的革命图景,一年之内就连续创作了《乡下》和《野火》两部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并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具体体现为:
1.从经济视角揭示阶级矛盾,着力表现经济崩坏下暴露的社会矛盾以及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冲击下难以为继的社会现实。
在《野火》中,除去华生和阿如老板结仇是因碾米风波外,每次农民们和地主、鄉长等人的矛盾升级都是围绕收租、收税等经济问题展开。比如傅青山的手下黑麻子温觉元和阿品哥借收捐调戏秋琴,被华生和阿波哥撞破后痛打一顿,写下服状仓皇逃离;又比如阿如老板在收租时打死了阿曼叔,触发众怒最终促成了乡民们的反抗。在这里,作家注意到了阶级矛盾的激化与经济矛盾密切相关,两个阶级的对立实际上是两个阶级的经济冲突。此外,作品中还体现了农村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冲击下的崩坏,比如阿如老板的碾米店在更先进的轧米船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又比如《乡下》中,阿毛的撑船生意因轮船的出现而难以维持,阿利曾经开着一家布店,经营土布生意,但最终在价格便宜数量又大的洋布侵占市场后被迫关闭布店。当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冲击下逐渐土崩瓦解时,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处境都会变得艰难,这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
2.承续二十年代创作的“乡土风”,在革命叙事中插入风俗描写,赋予了作品独特的浙东地域风情与宏大叙事的感染力。
事实上,江浙并非当时革命中心,革命的激烈程度不如湖广等地,书写恢弘的革命场面通常也不是浙东作家所长,例如楼适夷的《盐场》,巴人的《六横岛》等作品就曾尝试书写宏大的革命场面,但终究因为表现革命的格局限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1]。由此,作家另辟蹊径,并不刻意描绘自己不熟悉的革命场景,而是结合沿海农村的现实情况书写出真正符合浙东特质的“接地气”的革命小说。例如《野火》中对迎神赛会的描写就颇为壮观:喧天的锣鼓,如潮水般涌来的人群,震耳欲聋的鞭炮,惊天的巨旗……不仅赋予了作品鲜明的浙东地域风味,更与怒火燎原的农民起义交相辉映,极大地增强了作品昂扬积极的感染力与震撼力,配合“起义虽败,革命之火永存”的主题思想,《野火》确实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3.深刻洞察了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黑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并借助幻觉揭示人物心理,描写出农民被剥削阶级折磨至疯癫的悲惨命运,反映了农民反抗的迫切性。
《野火》中的傅家桥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层政府和地主乡绅们沆瀣一气,不断地巧立名目、鱼肉乡里,甚至在干旱、瘟疫刚刚肆虐了这片土地后,他们也不让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稍稍缓解,而是继续借着做佛事的名义征收远远超过农民可负担的捐税,而农民只要稍有不满或者略微表露了反抗情绪,关押打骂都只是小惩大诫,就是被打死也不足为奇,他们就像是皮肤上的蚂蝗,不吸干农民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就誓不罢休。同样,在《乡下》中,百姓的生活本已十分艰难,但乡里却苛捐杂税不断,阿毛只是在交税的时候抱怨几句,就立马引起了金生校长等人的不满,他们不但暗地里把阿毛赖以为生的船砸了洞,还诬陷阿毛要杀害乡长,害得阿毛入狱三年。阿毛入狱后,被非人的生活条件和心里不曾平息的怨恨折磨着,又挂念着自己年纪尚轻的儿子,他不甘的怒气,对儿子的愧疚,对朋友的担心一同纠结在心里,以至在恍惚间看见:“一团漆黑的东西向他滚了来,进行得非常迅速,巨大而且生动,像一匹野猪——像一匹熊——像一匹狮子——像一匹象……他越走越近,越近越清楚了。他看见它张着大嘴,露着獠牙,挥动着粗大的尾巴向他奔了过来……”等到这怪物跑进阿毛才看出来,原来它是强生乡长、金生校长、阿坤杀猪屠,而当阿毛在盛怒中要与他们拼命时,才看清那些不过是蜡烛映照下自己的影子。作家借阿毛的幻觉,在虚实交替的意识流动之间,既形象表现出阿毛对强生等人的憎恨,又以幻寓真地揭露出剥削阶级衣冠禽兽的面目,实在是精妙之笔。这些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就像无底深渊一样,这些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就像无底深渊一样,如果说阿毛招致祸事是因为表现了反抗情绪威胁了他们的统治,那三品的结局就更能体现这些剥削者的残忍。三品向来以忍让为处事哲学,从不敢反抗,可是,金生校长等人在诬陷阿毛时也将三品顺带关入了监狱,等到三品从监狱出来后,这些人更是变本加厉,借着迁公墓和修公路等名义敲诈勒索三品,甚至掘了他家的祖屋和祖坟,三品最终被活活气死。就像阿毛说的:“在这样的世上活着做人,岂止像灯蛾一样,越往亮处飞越危险,就是躲在黑角里,也会有不测的灾祸落到头上来。”阿毛的那句“我做不得人了!”华生等人以“我们还能活下去吗”为联合众人的口号分明都是被逼无路后的破釜沉舟,既然是“亡亦死,举大计亦死”,那不如就与这些豺狼虎豹拼个你死我活。在这些作品里,剥削与压迫都是那样血淋淋地触目惊心,难怪《野火》再版之时会引起国民党文化特务机关的警惕而遭删节[2],作家在暴露将农村政权的腐败与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方面确实达到了应有的深度。
4.塑造了在动态发展中成长的悲剧青年农民领导者形象——华生。
华生是作家在《野火》中着力塑造的主人公,他血气方刚,年轻有为,从不屈服。华生最初出场的时候,性格几乎与《乡下》中的阿毛如出一辙,他们都坚信着自己的拳头政治,面对不公平的事情时,第一反应就是打回去,谁怕谁。所以,一开始华生在因为轧米与阿如老板发生冲突时,阿如“举起竹杠对着华生的头顶劈了下去”[3],华生则是“偏过身,用扁担用力一击”,阿如从店里摔出大秤锤来的时候,华生也是毫不示弱将秤锤扔回去,砸碎了阿如的柜台,即便是在面对乡长傅青山的时候,华生也不畏强权,大声回答“打就打,我怕谁”。不过,作家对这种单枪匹马的个体反抗显然是持否定态度,因此阿毛的结局是发疯死亡,那么在《野火》中,华生的形象就不能不有所发展。由于华生和阿如在碾米时的冲突,华生的哥哥葛生被逼着给阿如放鞭炮道歉,华生在得知此事时,瞬间血气上涌,怒发冲冠,第一反应是要拿着锄头去“结果傅阿如那条狗命”[4](正如阿毛当初要拿着斧头去结果仇人一样)。但是在途中被阿波哥拦下,经过阿波哥的劝导,华生慢慢冷静下来,开始从长计议,并暗中以“我们还能活下去吗”为口号联系众人,一步步扩大起义队伍,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动复仇。这时候的华生获得了第一次的成长。后来,阿如在收租的时候打死阿曼叔,面对众人不可遏制的怒火,华生也并未马上行动,而是决定等到第二天一早,开祠堂一并清算阿如、黑麻子等人的恶行。可以看出,华生从冲动鲁莽,信奉拳头政治,成长为领导带领众人进行有策略斗争的领袖,其形象始终处在动态发展之中。既有缺点又有着成长发展的华生体现出了有血有肉的真实性与被解读的丰富性,这样的人物在30年代革命小说中并不多见。此外,作品最后安排了华生被捕,起义失败的悲剧性结局,也反映出作家对现实的进一步把握与思考:封建剥削阶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与他们相比,个体依靠力气的反抗终究会失败(阿毛),联合起来的群体虽有着更大的力量,但和这些根深蒂固的权利网络相比依旧弱小,革命之路究竟该何去何从,作家还在苦苦思索着。可是,与《乡下》暗淡悲伤的风格相比,《野火》的色彩已经明亮了许多,作品最后以“现在是冬天”作为结尾,分明暗示着这严冬过后将迎来春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寓意也为三部曲的第二部《春草》的诞生埋下了伏笔。除了华生外,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形象也可圈可点,例如阴险毒辣、两面三刀的基层统治者(剥削者)傅青山,虽然出场次数不多,却也塑造得颇为传神。
注释:
[1]王嘉良:《王嘉良学术文集 9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第223页。
[2]曾华鹏,蒋明玳编:《王鲁彦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3]鲁彦:《野火》,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4]鲁彦:《野火》,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参考文献:
[1]王嘉良:《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曾华鹏,蒋明玳编:《王鲁彦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