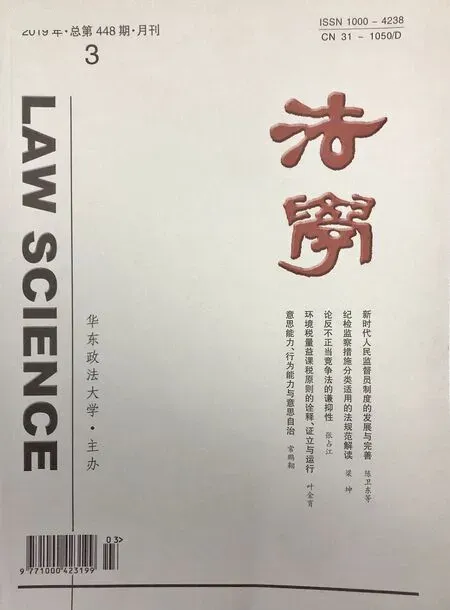意思能力、行为能力与意思自治
●常鹏翱
法律行为〔1〕为简便起见,本文将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能力分别称为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承载意思自治的功能。就我国的民法规范而言,在判断自然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生效与否时,第一道关是行为能力适格,即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无效(《民法总则》第144条),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民法总则》第145条),无需再判断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内容是否违法背俗。显然,行为能力是意思自治的起点,只有行为能力适格,才有必要判断意思表示的品质,并最终落实意思自治。我国民法学理在论述行为能力时往往提及意思能力,即认识和判断自己行为的能力,并将其作为行为能力的基础。〔2〕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229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在此理论框架下,意思能力成为行为能力的起点,无意思能力即无行为能力。这样一来,意思自治的起点就要从行为能力往前推至意思能力。
既然意思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基础,则其完全被行为能力包含,即有行为能力就有意思能力,在行为能力有成型规范体系的现实中,将意思能力单列出来,除了能阐明其与行为能力的逻辑关系,别无实际意义。对此,有学者指出,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并不完全一致,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无意思能力时的法律行为无效,〔3〕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7~68页。这就赋予了意思能力以实践价值,并进一步印证了意思能力是意思自治的起点。问题在于,行为能力只有与意思能力保持一致,方可谓意思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基础,在此前提下又认为二者可以不一致是否自相矛盾。显然,这个问题指向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而要理顺该关系,应从体现意思自治功能的法律行为效力入手,探讨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在行为能力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民法规范中,意思能力能否发挥作用;在这些规范之外,则应探讨意思能力能否或如何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
一、“借壳型”意思自治:行为能力替代意思能力
基于制度功能的比较,意思能力在东亚民法和欧陆民法均不乏身影,它要根据特定人、特定行为进行具体判断。为简便起见,在判断法律行为效力时,类型化的行为能力替代了意思能力,但行为能力实质上表明意思能力的大概率情况,意思能力对行为能力起着支撑作用,由此可以说意思能力借助于行为能力这个“壳”影响了法律行为的效力,这种关系架构即“借壳型”的意思自治。
从根源上看,意思能力对应德语“Willensfaehigkeit”一词,〔4〕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日]新井诚:《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行为能力·不法行为能力》,《法学教室》第144号,第16页。但当代德国民法著述不再提及该术语。日本民法学理和司法实践长期使用这一概念,2017年5月26日修订的《日本民法典》也加以采用。意思能力是一般人正常的意思决定能力,它有两重因素,一是能正确认识自己要做的行为,二是按照该认识妥当地控制自己将要发生的行为。〔5〕同上注,新井诚文,第16页;[日]须永醇:《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法学教室》第103号,第53页。其中,前者指向理解能力,后者指向自主决定能力,缺失任一因素,都表明自然人没有意思能力。有无意思能力需要就具体人和具体行为的情况作个别的和具体的判断;〔6〕同上注,须永醇文,第55页。或者说,意思能力之有无应根据交易的性质以及法律行为中当事人的判断能力进行关联判断,对具体事项作具体判断。〔7〕参见民法改正研究会、[日]加藤雅信:《日本民法典修正案 I 第一编:总则》,朱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237页。实务判断通常采用以下两个标准:一是自然人精神能力程度的各类指标,据此判断其有无相应的辨识力;二是合理的意思决定,即有意思能力的行为人应会作出合理的意思决定,由此推论具体行为未体现出合理的意思决定,故行为人没有意思能力。比如,在法律行为的内容基本没有合理性时,可认为行为人没有意思能力。〔8〕参见[日]山野目章夫编:《新注释民法(1):总则(1)》,有斐阁2018年版,第391~393页。因而就会出现5岁小孩有意思能力、25岁成年人无意思能力的情形,也会出现同一人此时有意思能力而彼时无意思能力的情形。〔9〕参见[日]佐久间毅:《民法基础1:总则》,有斐阁2018年版,第82页。
就理论层面而言,这样的具体判断能精准地确定行为人对具体行为的理解力和决定力,从而真正实现意思自治。但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如从行为的外观难以判断行为人有无意思能力,在不少交易上也不易甄别行为人能否进行合理判断,由此导致意思能力法理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有效适用,此时适用简便的行为能力制度便应运而生。〔10〕参见[日]潮见佳男:《民法(全)》,有斐阁2017年版,第20~21页。具言之,为了便于社会交往和减省判断成本,日本民法对意思能力普遍较差的人进行了特定化,此即欠缺完全行为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为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在判断这些人所为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时,无需每次都对其有无意思能力进行识别,而是统一将这些行为规定为可撤销。〔11〕同前注〔4〕,新井诚文,第16页。由此可知,在通常情况下,行为能力替代了意思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意味着缺失意思能力,只要没有例外发生,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无法生效。法律之所以能这样直接确定,就是从大概率上看,行为人通常缺乏意思能力,意思能力因此实质上为行为能力提供了支撑。
日本民法的上述观念影响到我国台湾地区。学理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中的“识别能力”就是意思能力。〔12〕同前注〔4〕,史尚宽书,第107页;施启扬:《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而意思能力是一种事实上的心理内在,应就具体人、具体行为进行具体判断,但这样的甄别成本高,举证困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也为了兼顾表意人和相对人的利益,法律采用标准的行为能力概括并替代具体的意思能力,在满足特定标准后,不用再判断表意人在事实上有无意思能力。〔13〕同前注〔4〕,史尚宽书,第107~109页;刘得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这一认识与日本民法学理完全一致。
在德国,行为能力被当作最低程度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有行为能力的人对事物的理解力要达到最起码的标准。〔14〕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33版,张艳译,杨大可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行为能力比较研究》,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从逻辑上讲,是否欠缺行为能力应具体判断有无这种理智的意思形成能力,但这种做法与法律交往所要求的简便性和安全性格格不入,基于此,德国民法典对行为能力欠缺的情形进行了类型化。〔15〕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换言之,根据每一实际情况甄别行为人有无理解力和判断力不仅难度太大,不确定性也很高,德国民法就提出了地位原则,明确了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类型,使行为能力有了标准化的法律配置。〔16〕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218页。只要不拘泥于术语表达,基于制度功能的比较不难看出,德国民法实际上是以意思能力支撑行为能力,并出于实用考虑,以行为能力替代意思能力。
在瑞士民法,判断能力就是理性行为的能力,包括智力因素和自主因素,前者表明行为人有理性,后者是指行为人能根据理性行动。判断能力具有相对性,需要就具体行为进行判断。〔17〕参见[瑞士]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211页。《瑞士民法典》第16条规定了完全行为能力,判断能力是其构成要素,在此情况下,完全能将判断能力与意思能力等同。〔18〕同前注〔3〕,梁慧星书,第67页;同前注〔4〕,史尚宽书,第107页。瑞士民法的这种格局与前述法例完全一致,即意思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基础,并以行为能力替代意思能力。
我国《民法总则》第21~22条、《民法通则》第13条将辨认能力〔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5条将其表述为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作为行为能力的要素,缺失辨认能力的自然人没有完全行为能力。而辨认能力具有个性化,需要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予以判断,实际上就是意思能力,〔20〕参见刘双臣等:《精神疾病患者涉及合同问题时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等级划分》,《中华精神科杂志》2004年第1期;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就是缺乏意思能力。在此意义上,不妨说意思能力决定或构成了行为能力,行为能力以意思能力为基础。〔21〕参见李永军主编:《中国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及理由(中国政法大学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2014)绥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3民特48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4民终2604号民事判决书。
同样,为了便于社会交往,是否具备辨认能力并非行为能力的首要判断标准,年龄在此首先起着格式化作用,只要自然人满足特定的年龄基准,法律就推定其有与相应行为能力对应的辨认能力,也即相应的行为能力人,〔22〕参见《民法总则》第17~20条、《民法通则》第12条。对此提出反对主张者负担相应的举证责任。〔23〕参见李浩:《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而随着行为能力吸收和遮蔽意思能力,行为能力得以凸显,意思能力看上去只是推演品,有法官就认为自然人因有完全行为能力而有意思能力。〔24〕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桂市民四终字第839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四终字第00760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5427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1民终329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3民终345号民事判决书。其实不然,行为能力根本上的正当性在于其大致能概括与反映自然人的意思能力状况,若非如此,行为能力的价值就会颇受非议,实践也不会接受。正因为如此,才可谓意思能力支撑了行为能力,成为行为能力的基础。
法院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认定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即法院作出这一认定的基点是意思能力,诸如医院诊断证明、病历记录、鉴定机构鉴定等证据体现的是具体人内在心智的事实状态,〔25〕参见张钦廷等:《论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分级》,《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1期。可证明自然人对自己的行为普遍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判断能力,达不到正常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其逻辑是意思能力不完备,行为能力就不完全。〔26〕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1468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2015)曲民特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驻民二终字第128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4民初6455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知,法院所认定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实际上表明的是一种大概率判断的意思能力,说明某人对其通常的行为缺乏应有的辨认能力。若辨认能力完全缺失,如某人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即属于通常无意思能力的状态,与其对应的是无行为能力;〔27〕参见湖南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酉法民特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若辨认能力不完备,如某人精神发育迟滞,智力低下,理解和表达能力有限,不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环境,不具备解决复杂生活事件的能力,就属于意思能力通常不完全的状态,与其对应的是限制行为能力。〔28〕参见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9行终186号行政判决书。
正因为行为能力以意思能力为构成要素,意思能力通常完备的状态能为完全行为能力奠定坚实的根基,完全行为能力人能独立为有效的法律行为,享有由此产生的权利与承担义务,这体现了意思自治的本有意义。反之,意思能力通常缺失或不完备,行为能力就不完全,当事人也就不受法律行为的约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行为能力制度的目标在于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29〕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1701号民事判决书。所有这些均表明虽然行为能力吸收并替代了意思能力,但意思能力对行为能力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意思能力正是借行为能力这个“壳”而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这就是“借壳型”意思自治模式的内核所在(见图例一)。

图例一 “借壳型”意思自治模式
二、“绕道型”意思自治:意思能力对完全行为能力的补充
行为能力体现了大概率判断的意思能力,完全行为能力人因酒醉等原因对某一行为缺失意思能力并非不可能,在此情况下,不因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要对该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违法背俗进行审视,宜直接因其缺失意思能力而使该行为归于无效。此时,意思能力绕过完全行为能力而直接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故称为“绕道型”意思自治。在我国,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法院判决认定制度引发了不小的现实问题,“绕道型”意思自治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
(一)缺失意思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无效
完全行为能力人是能独立实施有效法律行为的适格主体,在社会交往中,其就是正常人的化身,由其主导并实现意思自治是保证社会常态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既然如此,在判断法律行为效力时,行为人是否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就是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只有符合这一标准才有必要对其意思表示有无瑕疵、内容是否违法背俗进行判断。在法律行为完成后,只要没有意思表示瑕疵或内容违法背俗的反证,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体现了《民法总则》第5条规定的行为人按照自己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自愿原则,其就不能再否定法律行为的约束力。
不过,心智健全的完全行为能力人未必一直都有适当的意思能力,因患病、服药、酒醉、吸毒等原因而缺失意思能力的情形并不乏见,问题是对此情形下的法律行为效力应如何进行判断。例如,完全行为能力人A因服药而一时陷入头脑混沌状态,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行为,在此情形下与B订立内容合法的买卖合同。由于A暂时缺失意思能力,而非处于辨认、识别能力不足的持续状态,不符合无行为能力的要求,〔30〕参见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8页。不能根据《民法总则》第144条认定买卖合同无效。A在订立买卖合同时没有辨认、识别能力,难以清晰认知该行为的意义,其成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徒有意思表示之形而无其实,不能适用有关欺诈、重大误解等意思表示瑕疵规范。据此应认定该买卖合同有效,从而能约束A,但这一结果显然背离了社会通常认识,与建立在正常理性基础上的意思自治不符。
为避免产生这一后果,应着眼于A对买卖合同缺乏基本辨认力的事实参照适用相关的意思表示瑕疵规范。若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和意思能力的B明知A缺乏意思能力的,可参照适用《民法总则》第148条有关欺诈规范或该法第151条有关显失公平规范,由A请求撤销该合同。但A的证明责任较重,除了证明自己在订立合同时缺失意思能力之外还要证明B有欺诈的故意,或B利用A无意思能力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在实践中要完成这样的证明并非易事;而且受制于除斥期间,A能否及时撤销合同也是未定之数。此际,也可参照适用《民法总则》第147条有关重大误解规范,勉强认定A对合同整体存在重大误解,这固然可减轻A的证明责任,其无需证明与B有关的因素,但《民法总则》第151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3个月的短期除斥期间仍对其不利。此外,即便A请求撤销合同,但重大误解是由于A缺失意思能力造成的,B对此没有过错,A应赔偿B的损失。〔31〕参见梅伟:《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304页;陈自强:《契约错误法则之基本理论》,作者2015年自版,第230~233页。很明显,通过参照适用意思表示瑕疵规范解决暂时缺失意思能力之人的法律行为效力问题,无论是在举证责任、撤销权行使期间还是在责任承担上对该表意人并不有利。
与此不同的另一处理路径是根据A暂时缺失意思能力的状态,径直认定买卖合同无效。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5条后半句规定,虽非无行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的属于无效。学理认为,该规定指向表意人在事实上缺失意思能力的情形,在表意人对此举证证明后,法律行为归为无效。〔32〕同前注〔12〕,施启扬书,第217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正常人的行为为标准,缺失意思能力之人的行为根本不能纳入正常行为之列,自然不能使其等同于正常行为。缺失意思能力之人的法律行为同样如此,它只有法律行为的名号和形式,究其实质不属于规范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当然不能发生效力。〔33〕同前注〔4〕,史尚宽书,第359页。这意味着尽管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存在紧密关联,但行为能力是在法律层面对自然人辨认能力的概括表达,而意思能力是自然人事实上的辨认能力,两者并不同一,有完全行为能力未必一定具有完备的意思能力,其间的差距必须要有对应的制度安排,此即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5条后半句的规定,它体现的是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结合。〔34〕同前注〔13〕,刘得宽书,第179页。与上一处理路径相比,这一处理路径对A这样的表意人更加有利,其证明对象仅限于意思能力的缺失,其对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在意思能力的缺失不可归责于表意人时,如A对因服药暂时丧失意思能力没有过错,参照适用无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优于交易安全保护的规范及法理,〔35〕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A无需赔偿B的信赖利益。此外,这一处理路径也符合意思自治的内在机理,更为可取。
从渊源上看,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5条后半句应是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产物,后者规定,“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或暂时的精神错乱中所为的,也属无效”。所谓的无意识和暂时精神错乱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晰,而此处的精神错乱与《德国民法典》第104条第2项规定的无行为能力人的精神错乱一样,均产生行为人不能自由决定其意志的后果。〔36〕同前注〔15〕,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14页。基于功能主义的考量,意思能力构成《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核心是不言而喻的。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上述规定表明,无意思能力之人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谈不上通过法律行为创设权利和义务,并无意思自治可言,这样的法律行为无效。这一点更明确地体现在2017年5月26日修订的《日本民法典》中,其新设的第3条之2规定,“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没有意思能力的,该法律行为无效”,这反映了日本相关学理和实务长期积淀的共识。
上述经验表明,完全行为能力人会缺失意思能力,在此状态下的法律行为要有专门的调整规范,《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就此规定,“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认可该条款的法律地位并妥当适用,可补充《民法总则》在此方面的规范缺失。〔37〕我国民法学理未充分关注《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通过检索北大法宝也未发现有适用该条款的司法裁判,表明该条款实际上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有学者呼吁焕发该条款的生命力,参见朱广新:《法律行为无效事由的立法完善》,《法学论丛》2016年第3期。其实,在《民法总则》颁布实施之前,一些地方法院在判断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效力时,已注重通过甄别意思能力状况进行论证。其中一则判决指出,上诉人未表明其当晚饮酒达到了影响其意思能力之程度。〔38〕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终6483号民事判决书。另一则判决也指出,根据出院记录,立遗嘱人陈某乙在因食管癌入院治疗时神志清、精神可,在出院时情况有所好转;另从两份遗嘱内容可知,陈某乙在立遗嘱时应未丧失意思能力。〔39〕参见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泰开民初字第00063号民事判决书。另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077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终185号民事判决书。将此司法认识与意思能力法理、《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高度融合,就能与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上述经验一样,在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上,以意思能力对完全行为能力进行具体补充和认定,使缺失意思能力的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从而在行为能力一般化调整的基础上,增加意思能力判断和个案微调的灵活性,以实现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法律与事实、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高度统一。
(二)与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认定制度衔接
在规范构造上,我国《民法总则》第21~22条、《民法通则》第13条之所以将意思能力内置于行为能力,是为了将以年龄为标准确定的行为能力降格。为规范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87~190条专门设置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特别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49条,当事人一方在其他诉讼中主张自己或对方的行为能力降格,则该诉讼应予中止,由利害关系人按照前述特别程序申请认定。〔40〕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914~915页。也就是说,根据意思能力标准对行为能力降格必须由法院依据特别程序加以判决。〔41〕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2251号民事裁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赣民终99号民事裁定书。这无疑是一种严格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机制,为此,未经法院依据上述特别程序判决,即便有医院诊断证明、病历资料、司法鉴定、证人证言等证据表明当事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没有意思能力,也不能认定其行为能力降格。〔4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苏民申字第638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监字第49号执行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闽民申字第829号民事裁定书。这有利于稳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状态,防止法官滥权,但由于认定行为能力降格的判决没有溯及力,〔43〕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申字第00732号民事裁定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闽民终字第164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申1668号民事裁定书。在判决之前即便当事人缺失意思能力,其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虑及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并为了保护意思能力缺失的表意人,在有医院诊断证明等可靠证据的支持下,有些法院不得不直接在诉讼中认定行为能力降格。〔44〕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浙民提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223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琼民申1467号民事裁定书。这种做法当然能妥当考量具体的个案情况,但有违法裁判之嫌,客观上也会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一致,不能为社会公众提供稳定的预期。
问题显然出在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认定制度上,其过于严苛以致不能稳妥应对实际需求。因此,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先后废止或修订与此制度类似的禁治产制度。而且有学者通过严密论证指出,从老龄化社会的实际情况、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要求以及成年监护的制度配套来看,该制度应予废除。〔45〕参见李国强:《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监护制度的协调》,《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未来我国如废除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认定制度,成年的表意人将被推定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欲否定主体适格就需证明其意思能力不完备,从而判断其不能承担意思自治的后果,法律行为由此无效,这样将使意思能力与意思自治的直接关联得以凸显。
在法律修改之前,实证法仍需得到尊重和实施,同时还需避免出现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为此,应将《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与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认定制度衔接起来,即未经法院通过特别程序判决认定,不能否定表意人的完全行为能力,但通过证明其意思能力缺失而使其法律行为归于无效,〔46〕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书。同样能起到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的效果。在实践中,当事人未经特别程序认定行为人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而径行主张降格表意人行为能力的,其目的旨在请求法院认定某合同或遗嘱等单一法律行为的效力,此时完全没有必要再转道求助于该特别程序,因为认定行为能力降格的判决没有溯及力,适用该特别程序对当事人的诉求根本没有意义,反而不如在个案中判断法律行为成立时表意人的意思能力更为实际。〔47〕在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针对具体行为认定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做法,这实际上就是在判定意思能力。参见邢学毅等:《81例民事行为能力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6年第5期;罗小年:《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几个问题》,《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3年第3期。
需要注意的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认定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通常以司法鉴定为基础,只要司法鉴定认定行为能力降格,判决就会有相应的体现。在此现实情况下,法院在其他诉讼中允许司法鉴定有溯及力,〔48〕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938号民事裁定书。或者以司法鉴定为准界定鉴定后和判决前行为人的行为能力状态,〔49〕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苏民申28号民事裁定书。看似也能在尊重行为能力降格必须经由法院依特别程序判决的实证法基础上,通过自由裁量灵活解决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似无必要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但实际上该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还存在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情形,如有的法院就否定司法鉴定的溯及力,〔50〕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申2757号民事裁定书。这也是司法鉴定界的认识,参见王健等:《55例精神疾病患者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分析》,《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4年第6期。应不足取。
综上所述,完全行为能力人未必在任何时候皆有意思能力,在表意人缺失意思能力时不宜纠结于其完全行为能力的状态,而应基于其没有意思能力的现实径直否定其法律行为的效力,惟此方能保护表意人,同时也能解决无行为能力与限制行为能力判决认定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这在老龄化社会尤显重要,因为行为能力是完全按照年龄标准采用“一刀切”的定型化方式予以确定,而老年人的判断能力是逐渐衰退的,无法以行为能力制度应对,〔51〕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 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更宜采用意思能力要素对老年人的行为能力进行个别化的调整和确认,从而增加制度弹性。这也意味着《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实际上是对《民法总则》有关民事主体行为能力和法律行为效力规范的一个重要补充,其实效性不容忽视。一言以蔽之,在同一自然人既有完全行为能力,又缺失意思能力时,只需考虑意思能力缺失的因素,其法律行为因此无效,完全行为能力由此被绕开,此即“绕道型”意思自治模式的核心意思(见图例二)。

图例二 “绕道型”意思自治模式
三、“促进型”意思自治:通过意思能力拓展行为能力欠缺人的行为空间
与完全行为能力人会暂时缺失意思能力的道理一样,行为能力欠缺的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会有意思能力。在此情况下,应为其留下自由行为的空间,即无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有意思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可独自实施法律行为,而有意思能力的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也不因其无行为能力而无效,只要意思表示没有瑕疵、内容也不违法背俗,就应例外认可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样就能在一般性地保护行为能力欠缺之人的同时,适度促进其社会交往能力和提升其社会融入程度,此即“促进型”意思自治。
(一)有意思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可独立实施法律行为
与德国一样,我国民法的行为能力制度采用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三分法,在具体制度上借鉴德国民法之处不少,但在限制行为能力人能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方面,我国的法规范有自己的特色。在德国,除纯获利益的行为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他行为均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参与。〔52〕同前注〔15〕,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22~438页。而在我国民法上,除了纯获利益的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53〕参见《民法总则》第22条、第145条第1款,《合同法》第47条,《民法通则》第12条第1款、第13条第2款。对这种法律行为的效力没有确定的刚性标准,需在个案中根据行为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予以具体把握。
从常态上看,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意思能力的法律行为多为日常生活行为,如购买图书、食品,或受托打扫房间等,这些行为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设定支付价款、提供劳务等义务,从而不同于纯获利益的行为,但其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生活紧密相关,限制行为能力人能准确理解该行为对自己带来的后果,且这种义务涉及的金额不大或劳务强度适中,不会给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不当负担。若不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这种行为,不仅与社会实际情况脱节,也不利于提升限制行为能力人必要的社会交往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77条也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可独立实施与其年龄及身份相适应、为日常生活必需的法律行为。与此同理,尽管在纯获利益行为之外,德国民法不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法律行为,但对于准用有关限制行为能力未成年人规定的受照管成年人(有心理疾病或身体、智力、精神障碍),《德国民法典》第1903条第3款第2句规定,在法院未要求受照管人的行为应经过照管人同意时,该成年人可在日常生活小事上独立实施法律行为。
在判断限制行为能力人能否独立实施法律行为时,法院通常会着眼于标的物的类型、价值,并甄别该行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生活是否相关,以及行为人对此是否理解并预见行为的后果,以确定该行为是否属于日常生活行为。如法院在某判决中指出,陈某作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购买与其本人生活、学习不相关联的价值为1.5万元的摩托车,无法理解并预见其作为购买后摩托车所有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后果,该买卖合同与陈某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其不能自行订立买卖合同。〔54〕参见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2民终67号民事判决书。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678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指出,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游艇买卖合同标的较大,内容复杂,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在另一判决中法院指出某房屋价值较大,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较大,不属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交易,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自行买卖房屋。〔55〕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5950号民事判决书。
需要强调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之所以能独立实施前述日常生活行为,是因为其对这些日常生活行为具有意思能力,与此状态一致,限制行为能力人有了自由行为的空间。因此,即便不是通常的日常生活行为,但只要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具有意思能力,不妨尊重其自由意志,认可其独立实施这种行为的效力。如在某案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张某将房屋赠与女儿,单就赠与房屋而言,在通常情况下不是日常生活行为,但法院认为张某基本上能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具备与人进行日常交流的能力,虽然他患有脑梗塞、脑萎缩等疾病,但这不足以导致其丧失或减少对女儿的父爱,以其当时的精神状况及理解能力,对该赠与行为的意义和后果也具备认识和判断能力。〔56〕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民终字第543号民事判决书。对此,比较法上也有相关经验,通过借鉴《日本民法典》第21条,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83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使用诈术使人误信其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或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该法律行为有效。之所以如此,重要的考虑点之一就在于诈术的方式足以表明该人有相当意思能力,对其无再加以保护的必要。〔57〕同前注〔12〕,施启扬书,第226页。
概言之,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意志,通过综合考量标的物的类型和价值、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生活认知能力、成立法律行为的手段、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等因素,如能得出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具体行为具有意思能力的结论,其就能独立实施该行为。
(二)有意思能力的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例外有效
为了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法律剥夺了无行为能力人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空间,无论相对人是否知道表意人无行为能力,其所为的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如果说完全行为能力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意思自治的一个方面,则其另一方面就是无行为能力人不受其法律行为的约束。既然如此,对于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效力,《民法总则》第144条足敷其用,法律行为的无效已然判定,无需再审视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违法背俗。这种制度构造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同时,又将其从社会中隔离出来,成为一类没有社会交往价值的特殊人群,成为社会人群中的“孤岛”,这无疑不能促进他们的心智成长或健全,不利于其融入社会,也不完全符合生活常识和社会观念。比如,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用其零花钱购买文具、零食,已成年的精神残障人士购票乘坐公交车都是常见行为,若使这些行为一律无效则过于脱离社会实际。对此,我国大陆民法学理认为,这类交易数额不大的日常生活必需行为与无行为能力人的年龄和智力相符,应为有效。〔58〕同前注〔2〕,王利明书,第238页。因此,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一律无效看似在保护无行为能力人,但其与社会普遍认知并不完全吻合,为迎合大众观念和社会现实,以致出现了例外有效的理论认识,而这种认识体现的还是意思能力法理。
从根本上讲,行为能力只是对意思能力的大概率判断,无行为能力人通常没有意思能力,但不排除特殊情形下的无行为能力人有意思能力。意思能力是因每个人和每个具体行为而异的具体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不考虑行为差异的概括性的抽象能力,二者的这种差异恒定存在,行为能力和意思能力因此未必完全和绝对地一一对应。正如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特定情形下会对特定行为没有意思能力一样,无行为能力人也会在特定情形下对特定行为具有意思能力,这其实是行为能力和意思能力关系的常态表现。一旦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不一致,就表明在特定情形下,就特定的法律行为而言,行为能力不能吸收和替代意思能力。因此,不宜将行为能力当作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决定要素,而是应立足于这种差异,以意思能力为坐标判断法律行为的效力。由于无行为能力人通常无意思能力,据此一般情形,可先判定其所为的法律行为无效,但在可证明无行为能力人具有意思能力的特殊情形下,除非有意思表示瑕疵或内容违法背俗,否则该行为例外有效。可以说,基于行为能力的一般性和意思能力的个别性,将无行为能力人在具有意思能力时的法律行为推定为有效,能增强法律规范的灵活性,从而更适宜地调整社会现实。
不仅如此,作为抽象的民法价值和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必须在每一具体个案中得以落实才具有正当性和生命力。而个案情形均有不同,在判断意思自治时,应根据个案的制约要素具体断定。就此而言,不仅无意思能力之人不受其法律行为的约束,对具体行为具有意思能力之人还应自负其责才能全面体现意思自治,〔59〕参见前注〔10〕,潮见佳男书,第20页;[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I 民法总则》,渠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在此指引下,只有考量具体人和具体行为才能得出其是否具备意思能力的结论,进而衡量其能否承担该行为的法律效果。在无行为能力人对具体行为具有意思能力时该行为有效,毋宁说是意思自治的内在要求。由此不难理解,尽管《德国民法典》第104条第2项将处于持续精神错乱状态的成年人定位为无行为能力人,但其在头脑清醒状态下作出的意思表示是有效的。〔60〕同前注〔15〕,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13页。
既然意思能力因每个人和每个具体行为而异,即便同一人也会因其具体行为的不同而存在有无意思能力的不同,进而存在法律行为有效与无效的差异,无行为能力人也会因其有意思能力而能使法律行为有效。德国民法上有部分无行为能力的类型,即某人在特定领域无行为能力,在其他领域有行为能力,例如缠讼者没有诉讼的行为能力,此外则有行为能力;又如,某人在结婚相关事务上具有行为能力,在其他生活事务上有无行为能力存在疑问;再如,依赖“电话性伴侣”的人因此是部分无行为能力。〔61〕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在我国台湾地区,无行为能力人所为的财产行为无效,但对所为的结婚、收养等身份行为有意思能力的,该身份行为有效。〔62〕同前注〔4〕,史尚宽书,第359页。两相对比,德国的部分无行为能力只是未采用意思能力的表述而已,套用我国台湾地区的这种认识思路,不妨说即便某人因缠诉、电话成瘾等倾向和症状而属于无行为能力人,但只要对其他行为有意思能力,仍应认可这些行为的效力。我国大陆司法鉴定界认为,应针对具体行为判定行为人具体的行为能力,若无行为能力人对某一具体行为有意思能力,如精神病患者即使处于不完全缓解期甚至发病期,但对某种民事行为的性质和意义能够辨认和理解,就应认定其具有为此种行为的能力。〔63〕参见谢志强等:《59例民事行为能力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中国民康医学》2012年第11期。
需要指出的是,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相比,无行为能力人存在年龄更小、智力更低下或精神状态更糟糕的情况,其有意思能力的法律行为应局限于经济利益微小的日常交往和生活行为,而不宜再扩张到其他行为。认可这些行为的法律效力,既有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社会基础,又对无行为能力人及其相对人影响不大,还能为无行为能力人必要的心智成长或社会回归铺平道路。而这种有利于无行为能力人心智健全和社会融入的目的导向,又为无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的例外有效情形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如《民法通则意见》第6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即体现了这样的目的考量。而2002年增订生效的《德国民法典》第105a条也同样规定,成年的无行为能力人因日常生活达成价额低微的交易合同,其本人及财产不会由此而遭受明显的损害危险的,只要给付一经完成,该合同就视为有效,其目的正在于强化无行为能力人的自负其责,并倡导其社会交往的自由。〔64〕Vgl.Koehler,BGB Allgemeiner Teil: Ein Studeinbuch,33.Aufl.,Muenchen 2009,S.132.
综上,对于行为能力欠缺之人有意思能力的法律行为,法律应推定其有效。如反对其有效应举证证明表意人没有意思能力、存在意思表示瑕疵或内容违法背俗,才能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以此为行为能力欠缺之人拓展必要的行为空间,此即“促进型”意思自治模式的内涵所在(见图例三)。

图例三 “促进型”意思自治模式
四、结语
在通常情况下,意思能力是通向意思自治的起点,但其需针对具体行为进行具体判断,判断成本很高,将其与每一法律行为的效力直接挂钩的可行性很小。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可操作性,法律以年龄为基本标准将意思能力类型化且提升为行为能力,即用格式化的手段将相应年龄段的人区隔为具有不同的行为能力,并以行为能力遮蔽和替代意思能力。由此可知,行为能力的基础是意思能力,意思能力因此能决定行为能力,而非相反。故而,在理解《民法总则》等法律有关行为能力和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时,不应忽视意思能力在其背后的支撑作用,此即“借壳型”意思自治模式的内涵。
作为意思能力的类型化表达,行为能力通常与意思能力保持一致,但并非绝对如此,二者在特殊情形下会存在偏离,完全行为能力人也会缺失意思能力,对此就应根据意思能力的缺失状态确定法律行为的效力,其结果是法律行为无效,此即“绕道型”意思自治模式的内涵。换言之,只要能证明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成立法律行为时无意思能力,也即《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所谓的“神志不清的状态”,就应认定其法律行为无效。这表明《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是关于完全行为能力和法律行为效力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因具有特别法的地位而得以优先适用。
行为能力欠缺之人同样也会有意思能力,若忽略这一点,体现的则是法律家长主义和消极保护的思想,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其权益。〔65〕参见郑晓剑:《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制度之缓和路径研究》,载易继明主编:《私法》总第20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只要其对具体行为具有意思能力,就应允许其独自实施该法律行为并推定该行为有效,此即“促进型”意思自治模式的内涵。对于具有意思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45条第1款已有明文,而有意思能力的无行为能力人因日常生活而必需的法律行为则缺乏规范基础,对此不妨类推适用《民法总则》第145条第1款,〔66〕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6页。推定其有效。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分工和各有适用场合,共同构成从自然人适格角度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规范体系。其中,《民法总则》第143条、第144条是一般规范,而《民法通则意见》第67条第2款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效力的特别规范,《民法总则》第145条第1款有关“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有效”的规定属于行为能力欠缺之人法律行为效力的特别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