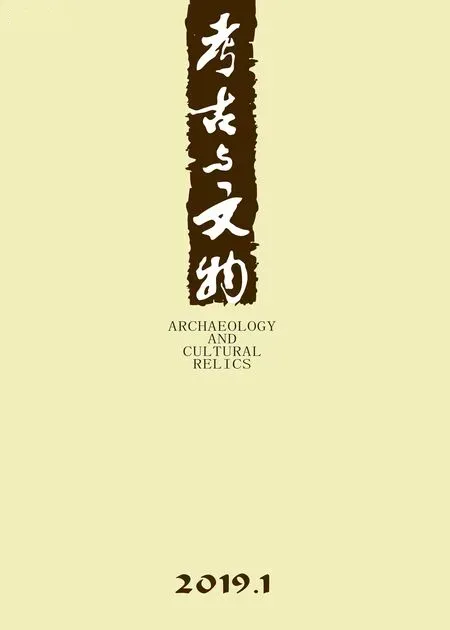陕西西安西白庙村南出土一批唐代善业泥
冉万里 沈晓文 贾麦明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2. 西北大学博物馆)
2002年3月,在西安市碑林区西白庙村南(唐长安城延康坊遗址)出土一批善业泥(图一),其中43件现藏于西北大学博物馆,图案清晰者21件。这些善业泥均为长方形,胎质呈橙黄色或橙红色,模制而成,火候不高。模印佛教造像的题材分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和施说法印的佛像、菩萨像、药师佛像、地藏菩萨像、燃灯供养菩萨像等六类,现将其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第一类:结跏趺坐佛像,施禅定印,共31件。均以泥块模制而成,形制相似,呈长方形,但大小厚薄不一,部分善业泥正面四周有低矮的凸棱。造像特征基本一致,仅细微处略有差异。均为居中佛像一尊,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之上,施禅定印。两侧各模印一座带塔刹的三层塔,塔刹中部有露盘,其上部为细长的摩尼宝珠,个别的塔刹尚可辨认出相轮的痕迹,刹顶各模印一株向头光两侧伸展的带有三个枝叶的折枝花。与这类善业泥完全相似者,个别的在背面模印有“大唐太和元年(827年)吴□□敬造佛一区”字样[1],为这类善业泥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现选取其中9件。
标本1,咼4.6、宽3.7、厚1.0厘米。正面长宽略大于背面。胎质呈橙黄色。佛像高肉髻,头光分为内外两匝。外匝呈菩提树叶形[2],内饰波浪状纹饰;内匝呈圆形,素面。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肩部及手部衣纹清晰流畅,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硕大的仰莲座上,袈裟一角覆搭于双手之上。莲座侧面下部刻有尖莲瓣。佛像两侧分别有一座带塔刹的三层塔,每层塔正面正中处均有一门洞。塔刹有细小的相轮五层,顶部有一露盘,盘上有一细长的摩尼宝珠。塔刹上部各模印有一枝伸向头光带花蕾的三枝叶折枝花,分布于头光两侧(图二)。
标本2,右下角残,高4.0、宽3.5、厚0.4厘米,善业泥是这类中的最小者。胎质呈橙红色。佛像高肉髻,头光呈菩提树叶形。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可见肩部及手部的衣褶。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硕大的仰莲座上,袈裟一角覆搭于双手之上。莲座侧面下部刻有细小尖莲瓣。佛像两侧分别有一座带塔刹的三层塔,刹顶部可见露盘,盘上隐约可见细长的摩尼宝珠。塔刹上部各模印有一枝伸向头光带花蕾的三枝叶折枝花,分布于头光两侧(图三)。
标本3,高4.8、宽3.7、厚1.2厘米。正面向背面逐渐内收,胎质呈橙黄色。四周有模制留下的凸棱。佛像头部残,头光呈菩提树叶形,凸起较高。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手臂处衣褶清晰,施禅定印,袈裟一角覆搭于双手之上,结跏趺坐于硕大的仰莲座上。莲座侧面刻有上下双层尖莲瓣。佛像两侧分别模印一座带塔刹的三层塔。塔刹细高,顶部可见露盘和细长的摩尼宝珠。塔刹上部各模印有一枝伸向头光带花蕾的三枝叶折枝花,分布于头光两侧(图四)。
标本4,两侧略残,高4.7、宽3.7、厚1.1厘米。正面长宽略大于背面,胎质呈橙红色,四周有模制留下的凸棱。因残蚀较严重,表面凹凸不平。佛像面部漫漶不清,可见菩提树叶形头光。衣饰不明,手部残,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侧面下部浅刻有单层尖莲瓣。左侧塔依稀可见塔身为三层,上部塔刹已模糊不清。右侧塔为三层,塔刹可见细小的数层相轮,刹顶部有露盘,盘上有一细长的摩尼宝珠。头光左侧的塔刹上部依稀可见模印的三枝叶折枝花(图五)。
标本5,右下角残,其余三个角磨圆或略残。高4.6、宽3.6、厚1.4厘米。正面长宽略大于背面,胎质呈橙红色,四周有模制留下的凸棱。泥块较厚,模印凸起较高。佛像高肉髻,头顶侧面有螺发痕迹。头光残,形状不明,可见头光内有断线状纹饰。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腹上僧祇支依稀可见。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侧面刻有上下双层尖莲瓣。两侧佛塔均为三层,模印清晰,凸起较高,上部有一细长塔刹,刹顶部有一露盘,盘上有一细长的摩尼宝珠。塔刹上部各有一枝伸向头光带花蕾的三枝叶折枝花(图六)。
标本6,左上角残,高5.0、宽4.0、厚0.9厘米。胎质呈橙黄色,四周有模制留下的凸棱。右上角残。佛像高肉髻,头顶侧面残留螺发痕迹。头光呈菩提树叶形。面部方圆丰满,依稀可见五官。身着袈裟,手臂处衣褶清晰,袈裟一角覆搭于双手之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侧面刻有上下双层尖莲瓣。佛像两侧各模印一座带塔刹的三层塔。左侧塔刹顶部可见露盘及其上部的细长摩尼宝珠,塔刹上部有一株花头伸向头光的折枝花。右侧塔刹顶部的露盘和摩尼宝珠已残(图七)。
标本7,破损较严重,残高4.1~4.6,残宽3.5、厚1.3厘米。正面长宽略大于背面,胎质呈橙黄色。四周平整,无凸棱。佛像有高肉髻,头部有菩提树叶形头光,凸起较高,上有细小的卷云纹,内侧边沿部分有两条断线状纹饰。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施禅定印,袈裟一角覆搭于双手之上,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侧面刻有上下双层尖莲瓣。佛像右侧塔已残,左侧塔仅塔刹、露盘及盘上的细长摩尼宝珠清晰可见,其余部分模糊不清(图八)。
标本8,高4.5、宽3.4、厚0.9厘米。正面长宽略大于背面,胎质呈橙红色。四周平整,无凸棱。佛像残损严重,头部模糊,可见高肉髻。头光为菩提树叶形,凸起较高。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仰莲座侧面刻有上下双层尖莲瓣。佛像两侧各模印有一座带塔刹的三层塔,塔刹顶部模印露盘及其上部细长的摩尼宝珠。右侧的塔刹清晰可见两层相轮,刹上部的折枝花依稀可辨(图九)。
标本9,右侧残,残高4.4、残宽3.3、厚1.0厘米。正面长宽略大于背面,胎质呈橙黄色。一边有模制留下的凸棱。佛像高肉髻,头顶侧面可见螺发痕迹,面部方圆,大耳。头光分内外两匝。外匝为较宽的菩提树叶形,高于善业泥表面,内饰略呈波浪状的纤细卷草纹;内匝为圆形素面。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衣纹清晰流畅,内着僧祇支。施禅定印,袈裟一角覆搭于双手之上,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侧面下部模印一层尖莲瓣。仅存佛像右侧的带塔刹的三层塔,塔刹顶部可见露盘和细长状的宝珠,隐约可辨认出三层相轮(图一〇)。
第二类:结跏趺坐佛像,施说法印,共3件。均以泥块模制而成,正面四周有模制时形成的凸棱。个体较大,正面与背面同长宽。其中一件较完整;一件可修复,微残;一件下部残。与之完全一致的善业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质地为泥质灰陶,背面模印文字,内容为∶“元和十年(sis年)合州令造像”[3],为这类善业泥的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
标本10,高6.4、宽4.5、厚1.3厘米。胎质呈橙红色。佛像头部残,可见高肉髻的痕迹。头光不清晰,略呈菩提树叶形。头光之上模印云头向下的散乱云气纹。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梗枝较细高的仰莲座上。莲座底部自梗枝两侧分别向上伸展出一枝波浪状带硕大莲叶的莲枝,分布于佛像两侧,每枝顶端有一个莲蕾(图一一)。
标本11,下部表面剥落,其余部分保存较好。高6.0、宽4.5、厚1.3厘米。胎质呈橙黄色。佛像高肉髻,面部残。头光分为内外两匝,均呈菩提树叶形,外匝略高于善业泥表面,内匝略高于外匝。头光之上模印云头向下的散乱云气纹。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底部已残,侧面模印有一层莲瓣。佛像两侧各装饰一波浪状的莲枝,顶端均有一个莲蕾(图一二)。
标本12,左侧及下部残,残高5.7~6.5、宽4.7、厚1.4厘米。胎质呈橙红色,正面四周有模印留下的凸棱。佛像高肉髻,面部丰满,五官不清。头光分内外两匝,外匝呈菩提树叶形,略高于善业泥表面,内匝略呈橢圆形,稍高于外匝。头光之上分布云气纹。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下部残缺,仅露出部分梗枝。佛像两侧各模印一波浪状带硕大莲叶的莲枝,莲枝顶端均有一个莲蕾。从佛像右侧的莲枝来看,莲枝应该是自莲座底部的梗枝伸展出来的(图一三)。
第三类:菩萨像,共3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以泥块模制而成,呈长方形。正面四周有模制时形成的凸棱。菩萨像的特征一致,均左手持净瓶,右手执杨柳枝,身披帔帛,跣足,站立于仰莲座上。这类善业泥上的菩萨像,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观音菩萨题材,其中一件菩萨像的发髻部分模印有化佛,更证明了这一点。
标本13,左上角残缺,高6.9、宽4.3、厚1.2厘米。胎质呈橙红色,正面四周有模制留下的凸棱。菩萨面部模糊,发髻较高,已残,左侧可见花瓣状装饰。头光分内外两匝。外匝呈菩提树叶形,略高于善业泥表面;内匝可见头部左侧的一段弧形,略高于外匝,形制不明。头光左侧模印带三个花头的折枝状云气纹。上半身袒裸,下身着裙,身披帔帛,帔帛自颈后绕臂并垂于身躯两侧。左手下垂执一腹部圆鼓带圈足的净瓶,手腕处佩戴有手镯。右臂呈上扬状,手部残缺。跣足,站立于带梗枝的仰莲座上,自莲座底部的梗枝两侧分别伸展出一枝向上的波浪状莲枝,延伸至菩萨像两侧,每枝上端有一个莲蕾(图一四)。
标本14,左上角及左下角残,高7.2、宽4.7、厚1.0厘米。胎质呈橙红色,正面四周有模制留下的凸棱,表面漫漶不清。菩萨右侧图案模糊。头光呈菩提树叶形,发髻较高,其上似有呈结跏趺坐状、带菩提树叶形头光的化佛。菩萨左手下垂,似持一长颈净瓶。右手曲臂上扬,执一舒展弯曲下垂的杨柳枝。跣足,站立于仰莲座上。莲座底部左侧伸展出一自下而上伸展的莲枝,顶端有一个莲蕾;自莲座梗枝右侧伸展出的莲枝已残(图一五)。
标本15,左上角残,高6.7、宽4.8、厚1.3厘米。胎质呈橙黄色,正面四周有模制留下的凸棱,表面残损,不甚清晰。菩萨高发髻,头后有头光印痕。身披帔帛,帔帛下垂于身体两侧。左手下垂,隐约可见手持净瓶。右臂曲臂上扬,右手已残。跣足,站立于带梗枝的仰莲座上。自莲座底部的梗枝两侧分别伸展出一枝向上的波浪状莲枝,分布于菩萨像两侧,每枝顶端有一个莲蕾。菩萨像身侧有云气纹(图一六)。
第四类:药师佛立像,共3件。其中2件下部残缺,仅存中上部或上半部;另1件较完整。均用泥块模制而成,正面四周有模制时形成的凸棱。3件善业泥上的佛像特征一致,均为高肉髻,头部有头光,左手持物(应为钵),右手持锡杖,站立于仰莲座之上。从身躯部分清晰的药师佛像来看,袈裟贴体而无衣纹,颇具笈多时期萨尔那特造像的特征。
标本16,右下角略残,高6.4、宽4.8、厚1.4厘米。胎质呈橙红色。药师佛像头部残蚀严重,漫漶不清。头光呈菩提树叶形,略高于善业泥表面,左侧有云气状纹样。身着宽袖袈裟。左臂下垂,左手平伸托钵,自钵中飘逸出一股云气纹分布于头光左侧。右手斜持一锡杖,杖头呈双股菩提树叶形,顶端模印一细长的莲蕾状装饰,两侧下端各垂一环,为双股双环式。站立于带梗枝的仰莲座上,梗枝细高,莲座侧面可见模印的尖状仰莲瓣。自莲座底部的梗枝两侧分别伸展出一枝向上的波浪状莲枝,分布于佛像两侧,每枝上端模印一莲蕾(图一七)。
标本17,仅存中上部,残高4.1~4.6、宽4.3、厚1厘米。胎质呈橙红色,正面右侧边沿有模印留下的凸棱,表面漫漶不清。药师佛像隐约可见菩提树叶形头光,身着宽袖袈裟,袈裟贴体而无衣纹。左臂下垂,左手平伸托钵,依稀可见自钵中飘逸出的位于头光左侧的云气纹痕迹。右手上扬持锡杖,杖头上部依稀可辨,一侧的垂环尚清晰,杖柄下半部已残缺不全,其剥落的细长痕迹很明显,可推测锡杖为双股双环式。身躯两侧残存可依稀辨认的莲枝痕迹(图一八)。
标本18,仅存上半部。残高3.0~3.8、宽4.3、厚1.9厘米。胎质呈橙红色,正面四周有模制时形成的凸棱。药师佛像头顶有肉髻,头光分内外两匝。外匝呈菩提树叶形,平面略高于善业泥表面;内匝呈圆形。身着圆领通肩袈裟,袈裟贴体无衣纹。左臂下垂,左手向外平伸托钵,自钵内飘出一股分布于头光左侧的云气纹;右手斜持锡杖。锡杖清晰可辨,杖头呈双股菩提树叶形,两侧下方各垂一环,杖头顶端模印一细长的莲蕾状装饰,莲蕾底部为一算珠形饰,整体为双股双环式。从药师佛像的姿态来看,应为站立状(图一九)。
第五类:地藏菩萨像,共2件。1件顶部及右上角略残,另1件较完整。均以泥块模制而成,正面四周有模制时形成的凸棱。从其坐姿和手持物判断,应为地藏菩萨像。均半跏趺坐于束腰座上,上部侧面可见莲瓣,下部则呈叠涩状。右手持一球状摩尼宝珠,宝珠上方有六道花瓣形云气纹,其中五道云气纹上端有一姿态各异的人物或动物形象,应象征“六道轮回”。
标本19,顶部及右上角略残,残高6.6、宽5.0、厚1.3厘米。胎质呈橙黄色。头部残,头光分为内外两匝。外匝因顶部残,形状不明,高于善业泥表面,中部略内凹;内匝呈圆形,素面,较平,略高于外匝。头顶无肉髻,呈僧人形。左手覆搭于左膝上;右手托一发光的球状摩尼宝珠,自其上方飘逸出六道花瓣形云气纹,云气纹位于地藏菩萨像身躯的右侧。除头光右侧的云气纹之上未见人物或动物形象外,其余每道云气纹上端均模印一姿态各异的人物或动物。自第二道云气纹开始,人物或动物的形象依稀可辨,依次为∶上半身残缺的站立人物(天人?)、结跏趺坐一双手上举一双手合十的阿修罗、人、畜牲(四足带尾的动物)、袒裸状饿鬼。菩萨身披帔帛,半跏趺坐于束腰座上,帔帛自颈后绕臂并下垂于莲座两侧,座底部呈叠涩状。座下方饰云气纹,左侧模印一株带花头的折枝花(图二〇)。
标本20,高7.2、宽5.4、厚1.9厘米。胎质呈橙红色。因表面侵蚀,模印显得漫漶不清。头光分内外两匝。外匝呈菩提树叶形,略高于善业泥表面;内匝呈圆形,基本与外匝齐平。头部无肉髻,呈僧人形。左手覆搭于左膝上;右手托一发光的球状摩尼宝珠,自其上方飘逸出六道花瓣形云气纹,云气纹位于地藏菩萨像身躯右侧。除头光右侧上方的云气纹之上未见人物或动物形象,其余五道云气纹上端均模印有一姿态各异的人物或动物。自第二道云气纹开始,人物或动物形象依稀可辨,依次为:站立的带菩提树叶形头光的天人、结跏趺坐一双手上举一双手合十的阿修罗、人、畜牲(四足带尾的动物)、袒裸状饿鬼。菩萨身披帔帛,半跏趺坐于束腰座上,帔帛自颈后绕臂并下垂于座两侧。莲座底部呈叠涩状,左侧残存部分模印的折枝花(图二一)。
第六类∶燃灯供养菩萨像,1件。标本21,下部残,仅存上部,残高4.5~5.2、宽5.4、厚1.3厘米,较规整。模制而成,胎质呈橙黄色。上部正中模印一菩萨,高发髻,上身袒裸,下身着裙,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头光分为内外两匝。外匝为菩提树叶形,略高于善业泥表面;内匝为圆形,基本与外匝齐平。左手置于左腿上,似作与愿印;右手残缺,但从残痕看,应为曲臂置于胸部。菩萨左侧站立一人物,面部模糊不清,上身袒裸,下身着短裙,右手高举一呈瓣状的曲柄华盖置于菩萨头顶,华盖上方正中为一宝珠状饰,四角下垂流苏状饰。右侧有一上身袒裸的供养人,双手捧一带高圈足的豆形灯于头顶,灯上有燃烧的波浪状火焰(图二二)。结合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与之类似的善业泥[4],可推知西白庙村南所出菩萨像的莲座之下原来应为奔走的狮子,那么,菩萨的身份应为文殊菩萨,进而可知文殊菩萨左侧持华盖的站立人物应该是狮奴,顶灯供养人的姿态应为双膝跪地状。
西安西白庙村南出土的善业泥,其形制特征与以往在唐长安城遗址中发现的善业泥相似。另外,橙黄色和红色的胎质,也见于唐长安城寺院遗址及其他唐代遗址中出土的善业泥、陶器,所以推断它们应为唐代遗物。由于这类泥制模印小型造像背面有的模印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字样,也被称为善业泥或善业泥造像。西白庙村出土的这批善业泥题材丰富,以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的坐佛为主,其次是一般意义上的观音菩萨和药师佛,最后是地藏菩萨和文殊菩萨,为研究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题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与其他题材的善业泥相比较,模印地藏菩萨像和文殊菩萨像者发现的相对较少,这也为探讨唐代长安地区地藏菩萨和文殊菩萨信仰提供了重要实物。西白庙村南出土的这批善业泥不论在模印工艺、胎质还是造像特征上,都较为一致,可知其年代也应该接近。
西白庙村所在的位置在唐代属于延康坊。据《唐两京城坊考》卷四云,该坊有两座寺院,分别是位于西南隅的西明寺和位于东南隅的静法寺[5]。而这批善业泥的出土地点——西白庙村南位于延康坊十字街西之南的位置,正好在唐西明寺的范围之内。在西明寺遗址发掘过程中也曾出土善业泥100余件[6],本文所云善业泥中的第一类(模印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的佛像)、第二类(模印结跏趺坐施说法印的佛像)、第四类(模印药师佛像)均可与西明寺遗址所出同类善业泥相对应,而且两者在胎质、形制及造像特征等方面也基本一致。这样一来,西白庙村南出土的这43件善业泥,不仅出土地点与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基本吻合,且两批其他方面的特征也基本一致。因此,笔者推测西白庙村南出土的这批善业泥可能为唐西明寺之遗物。诚如此,则为西明寺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从西明寺遗址发掘出土的善业泥来看,它们主要出土于唐代以后的地层(第③层),第③层叠压的建筑遗迹的年代属于唐代晚期,那么,善业泥应当是西明寺的唐代晚期建筑废弃后被扰乱而堆积于唐代以后的地层的,其年代应该与西明寺遗址的唐代晚期建筑遗迹相当或略早(善业泥在不损坏的情况下可连续使用)。结合前文所引国博藏“元和十年(815年)合州令造像”以及“大唐太和元年(827年)吴□□敬造佛一区”的善业泥来看,可知西明寺遗址及西白庙村南出土的善业泥年代属于中唐偏晚。考虑到唐代长安佛教造像的范式意义,一般长安地区流行的造像样式往往是由长安地区波及地方,自长安流传到地方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差,所以,将这批善业泥的年代初步推断为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初这一时期。
[1]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大阪企画部. 西遊記日本不会(三蔵法師道)図録[M].大阪:朝日新聞社,1999:307,图版155.
[2] 在以往的论著中,一般在描述头光时,往往将上尖下圆或略呈长圆形者称为“桃形”,笔者以为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似乎称为“菩提树叶形”更为合适。首先,菩提树在佛教中被认为是“圣树”和“觉树”,具有神圣性,是佛陀和佛教的象征之一。其次,头光是平面的,以圆球形的桃子来说明一个平面的头光,在文理上有不通之处。第三,菩提树叶的形状也是上尖下圆或略呈长圆形,与头光的形状完全一致。也与菩提树本身在佛教中的神圣意义相契合。鉴于此,笔者在此将上尖下圆或者略呈长圆形的在以往被称为“桃形”的头光,称之为“菩提树叶形”。以往的论著在描述头光时,可能由于描述者不熟悉菩提树叶,而更熟悉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桃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将雕刻或者描绘这一形状本来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给抹杀了,这是采用“桃形”这一概念的最大缺陷。其实,在佛教造像中也有完全按照菩提树叶的形状雕刻头光的实际例子,如在斯里兰卡城市、乡村各处所见的佛教造像的头光,就是模拟菩提树叶的形状雕刻而成,而且其正面清晰地雕刻出菩提树叶的叶脉,这是非常重要的旁证资料。因此,本文在描述头光的形状时,首次采用了“菩提树叶形”这一概念,同时,也建议在以后的论著描述中,涉及上尖下圆的头光形状时,能够釆用“头光呈菩提树叶形”这一概念。
[3] 吕章申主编.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0,图版035.
[4] Annette L Juliano, Buddist Sculpture from China∶Selection from the Xi’an Beilin Museum Fifth through Nine Centuries, Art Media Rescources, Ltd.2007:132.
[5]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07—213.
[6]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0(1):45—55.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85—191,214,图版八〇.该报告第190页图九五之2所绘制的善业泥佛像两侧的佛塔似乎有误,应为带塔刹的三层塔,塔刹上是相轮、露盘和摩尼宝珠,而不是六层的楼阁式塔。由于塔刹细长,其上所模印出的细密的相轮及上部的露盘很容易被看成塔身,而被计算到塔的层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