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产业终结了吗?
杨海燕 杨海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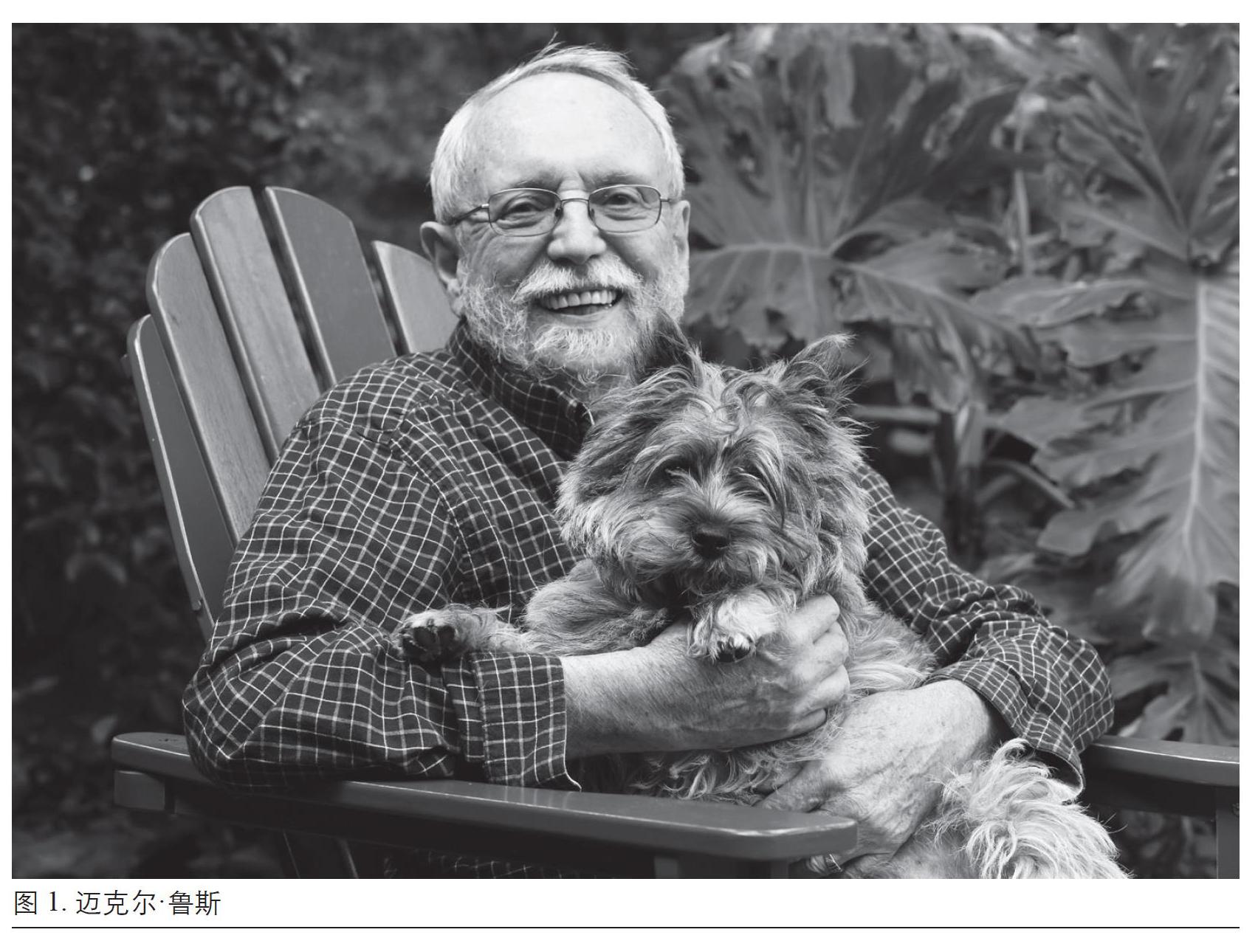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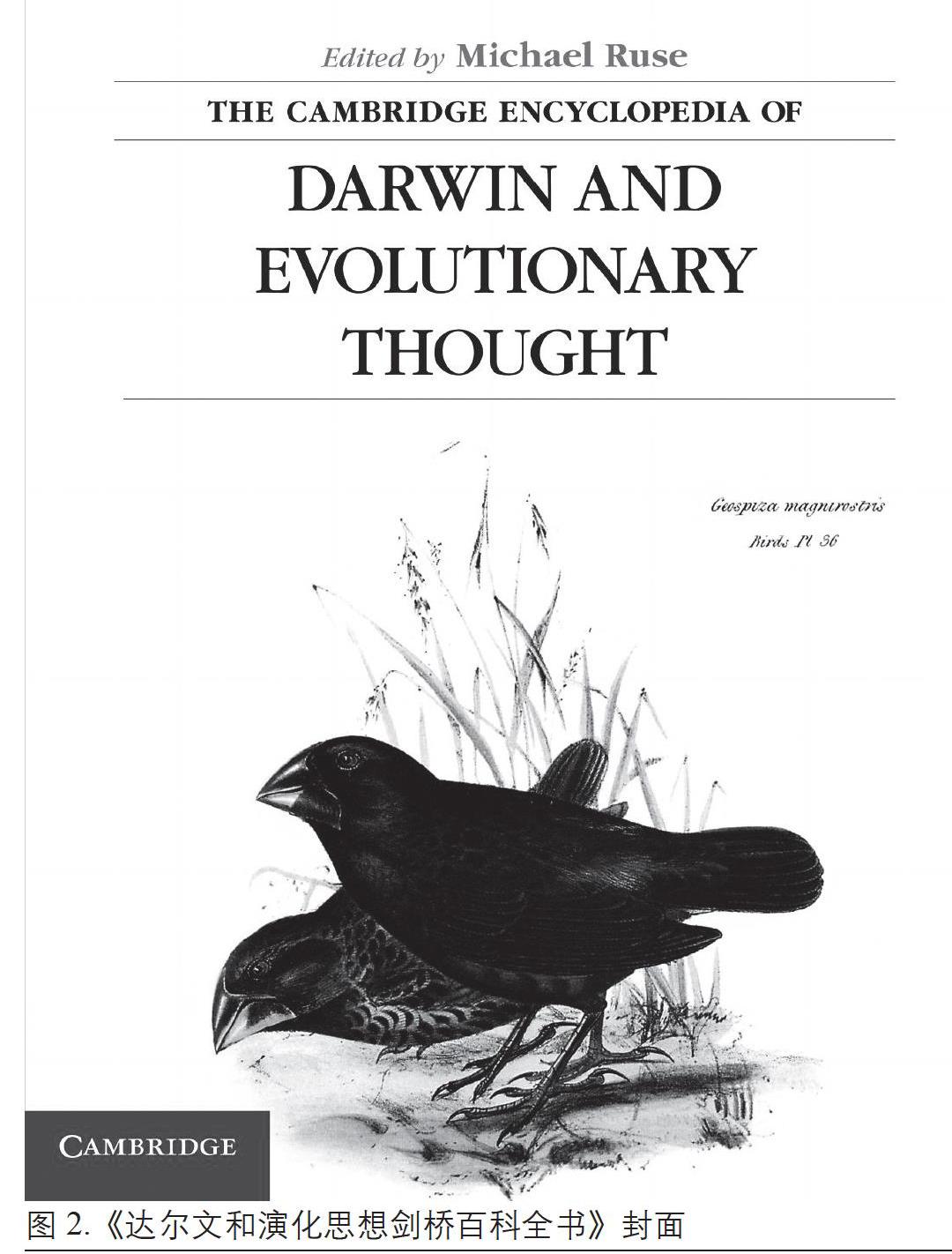
访谈整理者按 迈克尔·鲁斯(Michael Ruse,图1),1940年出生于英国伯明翰,1970年获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哲学专业)。他曾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任教35年,现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露西尔·韦克迈斯特(Lucyle T. Werkmeister)哲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主任。他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获得过挪威卑尔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伦敦大学学院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等。他创办了《生物学与哲学》期刊,现为荣休主编。研究领域为生物学哲学、伦理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相关领域著述颇丰。
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日
访谈地点: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一 达尔文产业:序曲
杨海燕(以下简称“杨”):1974年,《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杂志发表了您撰写的一篇评论,题为“达尔文产业——批判性评估”。您在什么情况下首先使用了“达尔文产业”一词?
迈克尔·鲁斯(以下简称“鲁”):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第一个使用它的人,但是我肯定在你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使用了它。其他人可能已经使用过“达尔文产业”一词,但我觉得我可能是第一个书面使用它的人。
那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初期,很多人正在开始认真研究达尔文,于是各种专著也出现了。我认为已经很明显,不仅仅是一两个人在做这件事,而是许多年轻学者正在进入该领域,并希望对此进行写作。那时有一本名为《生物学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的新期刊,人们在上面发表关于达尔文的论文。很多学者去剑桥大学查看达尔文档案。因此,我认为人数之众已达到一定规模,我想我是在这种背景下使用“达尔文产业”一词的。
杨:但是,有时人们会以负面的方式使用该词,对吗?
鲁:对,他们把它作为一个有点贬义的术语来使用,暗示正在做的工作太多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不过,这种用法应该是之后很久的事。我使用它,只是觉得它符合这样的想法,即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正在开始对达尔文感兴趣,并且从事相关研究。我认为人们应该已经谈论过牛顿产业或类似的措辞,所以我的提法并不是那么具有独创性。
二 横跨大西洋
杨:您出生于英国,然后移居加拿大,现在又定居美国。您能谈谈您的学术之路吗?您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鲁:我的生活是非常多样化的,因为我出生于英格兰,在那里接受教育,然后在1962年离开英格兰前往加拿大。我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倾盆大雨中到达魁北克市的,在一个饭厅改造成的移民中心里,一名感冒得很重的军官抬头看了看我的证件,在护照上盖了章——“已登陆移民”。
我的第一站是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我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令我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大概十年前麦克马斯特大学授予了我一个荣誉学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又回到加拿大,在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任教了35年。2000年我移居美国佛罗里达,担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主任,这样可以避免加拿大的强制退休法。我已经获得了两个新国籍——加拿大和美国,所以现在有三本护照!可以说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北美,尽管我的口音仍然英国味很浓。
我的教育背景的重点是哲学和数学。我于1962年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获得哲学和数学的学士学位。然后在1964年获得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在回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我一生中从未正式学习过生物学课程。在20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最顶尖的学科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然后是数学、物理、化学和德语,而最低的是地理、西班牙语和生物学。但是现在情形大不相同。我认为,特别是因为有了分子生物学之后,生物学的地位要比过去高得多,医学的地位也有很大改变。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不言而喻的想法是,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聪明的话就去学医吧,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突然每个人都想当医生啦,当然这意味着你必须先学习生物学。因此,生物学已成为比过去具有更高地位的学科。
三 对达尔文与演化论的兴趣
杨:您是如何开始对达尔文和演化论感兴趣的?
鲁:我想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产生了兴趣。像所有博士生面对论文选题时一样,我要找到一个“生态龛”,那里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并且已有一些文献,不过数量不是很多、质量也不是很高。我想从事科学哲学方面的工作,但不是类似于确证悖论(paradoxes of confirmation)那样艰涩的技术问题——我在硕士阶段做过一些。幸运的是,我的导师建议我研究与演化论相关的哲学问题,因为似乎还没有其他人研究过。我这样做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我读了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的《演化论》(The Theory of Evolution),发现这本书很让人着迷。我继续阅读导师推荐的其它书籍,从此再没有停止过。我之前从没读过《物種起源》,也从来不知道自然选择是什么,所以当我满怀兴趣去读它时马上就觉得这个想法很棒,我真的很享受阅读它的过程。因为我有数学学位,所以至少能够自学一下基础遗传学。我对此并不担心,我没有费力去学那些十分复杂、困难的部分,但是至少我学到了足够多的遗传学知识以便领会问题所在。我成为了狂热的达尔文主义者,现在仍然如此。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我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1970),而且写了我的第一本书《生物学哲学》(Philosophy of Biology,1973)。
杨:但是作为一名哲学家,您也意识到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对吗?
鲁:是的,别忘了那段时间正值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开始产生重大影响之际——他说要想做好科学哲学就必须研究科学史。因此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几乎一度考虑过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不过我也一样想成为一名哲学家,结果是我一直尽力平衡两者。我真正想做的是通过思想史研究来解决哲学问题,这是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经采取的方式——不过这完全不意味着我要追随他们特定的观点。我意识到,如果要认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必须投入一些时间专心致志。所以在1972年第一次学术休假时,我去了英国的剑桥大学,专门查阅达尔文档案。在资源上传到互联网之前,你可以手持达尔文的笔记本并研究它们。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阴暗的手稿室里。1979年,我的《达尔文革命:腥牙血爪的科学》(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Science Red in Tooth and Claw)一书问世,它是对整个达尔文图景的主要概述。
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要花所有的时间仅仅研究达尔文,我绝对不是一位达尔文学者。我的意思是,他很令人感兴趣,但我还想研究其它问题。我对哲学思想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整体文化一直非常着迷,我喜欢阅读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英国小说家的著作。所以我其实是把事情整合在一起,即把达尔文和演化论放在那个背景中加以考量。
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首先出现了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争论。社会生物学是为行为特别是人类行为提供演化基础的尝试。1979年,我为此写了一本支持性的书《社会生物学:真知灼见还是无稽之谈?》(Sociobiology: Sense or Nonsense? )。这真是给我带来了大麻烦,我陷入了和一些人的冲突,特别是那些认为必须用阶级冲突来解释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许多认为以生物学来解释行为的尝试会令人厌恶地联想到纳粹生物学的犹太人。接着关于神创论的争论浮出水面,我参与了有关科学和宗教的整个辩论,当然也就此写了书——这充分显示出我对争论的热衷!不过,同时我也在继续我的哲学研究。我写了《认真对待达尔文》(Taking Darwin Seriously,1986)——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法。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因为我提出了非常不受欢迎的哲学论点,即达尔文演化论可以解释伦理学(道德行为),因此到那时为止的所有关于伦理学的著述都是错误的!当时没有人相信我,如今我的方式得到了更多支持,我的观点甚至被冠以“揭露真相理论”(debunking theory)的称谓。这意味着它削弱了传统的观点,即道德是客观的,而不只是人性的主观性结果。
同时我也在研究历史,对整个演化论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当然结果就是我的大部头——《从单子到人》(Monad to Man,1996)。我将过去300年中演化理论的历史大致分为三阶段,几乎就像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所说的那样。《物种起源》问世前的150年,我认为更像是某种伪科学阶段,即孔德说的神学阶段;然后从1859—1930年,它更像是大众科学阶段,即孔德说的形而上学阶段;从1930年到现在是更专业的阶段,即孔德说的实证阶段。我当然不是以孔德的思想来写的这本书,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孔德是正确的。我认为我确实看到了理论的发展。在早期它更多是“进步”背后的一些流行的意识形态,1859年之后达尔文才真正使其成为一门受人尊敬的科学,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一门完全的专业科学。虽然当时专业工作正在进行,但这实际上还更多是一门博物馆科学(a science of the museums),直到1930年左右它才在很大程度上真正成为专业科学。我认为从专业科学的角度,费奥多西·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和E. B. 福特(E. B. Ford)连同其他人一起发展了新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这本书破例没有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而关于之前那些争议,我至今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四 剑桥百科全书
杨:您已经写了20多本书,还编辑了许多书——也有20多本,您最新编辑的大部头是《达尔文和演化思想剑桥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Darwin and Evolutionary Thought,2013,图2)。百科全书一开篇,您引用了达尔文1866年给美国昆虫学家本杰明·丹恩·沃尔什(Benjamin Dann Walsh)的信,他是《实践昆虫学家》(Practical Entomologist)的副主编,信中写道:“我很抱歉您是一位编辑,因为我总是听说编辑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麻烦和焦虑。”您能否描述一下您编辑书籍的经验,尤其是这部百科全书?
鲁:我一直时断时续地研究达尔文,但不是在专门研究达尔文。不过到了2000年,情势已经很明显,即2009年将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那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于是我开始针对达尔文以及围绕他进行大量写作,包括和罗伯特·理查兹(Robert J. Richards)合编的《剑桥〈物种起源〉文集》(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Origin of Species”,2009),即一系列關于《物种起源》的论文。他是我的好朋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我想一定是在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办事处的组稿编辑问我是否有兴趣做有关达尔文的大百科全书,或许我答应做这个项目很愚蠢。不管怎样,我开始寻找可以对此做出贡献的人,我邀请的人中显然有你。因为那年9月在葡萄牙天主教大学举行的“达尔文对科学、社会和文化之影响”国际会议上,我听到了你关于达尔文在中国的报告——我认为那正是我所需要的。那是一次非常愉快、非常有趣的会议。
我邀请到了一批学者,2011年左右终于设法让每个人都交了稿。由于这是一本百科全书,所以需要很多图片。我收到了大约350张,你也提供了若干张珍贵图片。正如你所知,这是一项艰巨工作,要查找每张图片的原始出处并获得许可。百科全书是全面性的,不仅关于演化论,它也是针对和围绕达尔文的。所以我们有一些论文分别论及作为地质学家、古生物學家的达尔文,他所做的分类学研究、藤壶研究,《物种起源》及其后续修改,然后是联合发现者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以及达尔文关于人、语言、伦理的思想,等等。接下来是达尔文及其理论在不同国家的境况——我们显然不能涵盖每个国家,该书涉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中国、拉美国家。其实应该有一篇俄国的文章,但是做不了那么多。拉丁美洲确实是达尔文研究不可忽略之处,那是达尔文、华莱士、亨利·贝茨(Henry Bates)和弗里茨·穆勒(Fritz Müller)到过的地方。然后我们继续进行到孟德尔遗传学和新达尔文主义,植物学、古生物学等的发展,社会生物学,达尔文和分子生物学,人类语言、文化、文学、哲学、认识论、宗教。在宗教部分,我们讨论了新教、特创论、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方面的内容。最后的第63章是关于演化医学的。
因此,该书最初的想法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组稿编辑。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出版界想要什么,并且非常热衷于建立自己独特的作者名单。除了组稿编辑,我们还有制作编辑、审稿编辑、销售编辑或代表。而我是负责约稿的学术编辑,要确保稿件质量以及准时提交。
杨:《达尔文和演化思想剑桥百科全书》获得了2013年PROSE奖的人文社会科学单卷本参考书奖。这个奖项全称是专业和学术卓越奖(Professional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由美国出版商协会的专业和学术出版部颁发。每年关于达尔文和演化论的著作数量颇多,该书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鲁:我对这本书的面世感到非常自豪,也很高兴看到人们对它的认可。该书独特之处在于,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带来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历史学家、哲学家之外,作者中还有一些科学家。作者们的年龄谱带很宽,既有资深学者也有新秀。另外,其中有12位女性作者——尽管我希望有更多,贡献了一些很棒的文章,比如玛莎·里士满(Marsha Richmond)的藤壶研究、波莉·温莎(Polly Windsor)的分类学研究以及你的在中国创造达尔文主义的研究。
所以说这是一项集体努力,当然我是负责人。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愿景,我拒绝了一些不够好的,最终自己写了三篇。我请有些作者重写了不少部分,因为我对他们提交上来的稿件不太满意。我非常挑剔,我希望这项工作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完成。最终的结果我是很满意的——所有参与其中的都是顶尖的学者,我希望其他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这部文集展现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头脑中的达尔文:一名非常重要的然而并不总是正确的科学家,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我来说达尔文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是一个文化人物。我说达尔文是革命者(revolutionary),指的是他提出的通过自然选择而演化的理论,但是他不是叛逆者(rebel),意思是他吸收了自己所身处时代的观念。我认为演化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理论——我希望给人们这样的印象,但其也是文化,而且不仅仅是彼时的文化,还是此时的文化。因此,该书不仅是关于达尔文及其演化论的,而且还涉及达尔文对于当今人们所称的达尔文主义有怎样的影响。
这本书相当于通常四五本书的体量,因此在问题覆盖面上它也独一无二,它使整个研究领域焕然一新。另外它有网络版本,人们既可以拥有精装本,也可以上网阅读。我希望它对学生们有用,因为在线内容更易于访问。达尔文研究已经成果累累,因此,如果你要从事某项研究,就必须先进行大量阅读。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研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就必须阅读吉姆·西科德(Jim Secord)的书,如果你要研究地质学,则必须阅读马丁·鲁德威克(Martin Rudwick)的作品。你想研究达尔文和人类演化,也有很多文献可供阅读。因此,像《达尔文和演化思想剑桥百科全书》这样的文集就很重要。我希望年轻的学生和研究者至少从我写的约2.5万字的导言开始入手,获知大家在谈论什么,然后再继续阅读具体篇章。我再次强调,该书的价值在于那些最高质量的论文贡献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欧洲人还是亚洲人,年轻人还是年长者。
五 科学与宗教
杨:当有关特创论的争议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时,您就卷入了法庭案件。您能就此再多谈一谈吗?
鲁:我在属于贵格会家庭中长大,我想我小时候肯定听说过特创论。如果追问下去,也许可以说出一点儿关于“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的事情:一位年轻老师因为在课上说《创世记》并不真实而被起诉。不过我那时就认为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出乎意料的是,我后来受邀和一些特创论者辩论。一方面,演化生物学的历史和哲学训练使我有备而来——我认为这要比单纯科学训练更好;另一方面,我的性格在十年间受到针对众多本科生的沉重教学负担的磨练,使我在台上能够挥洒自如,而且认识到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好笑话比冗长认真的辩论更有效。我不能说自己赢过任何一场辩论,考虑到听众性质之类的因素,如果我能赢那的确会是一个奇迹了。不过,我对特创论进行了很多重击。
1981年发生的是阿肯色特创论审判(Arkansas Creationism Trial)。当时该州通过了一项法案,坚持认为如果向该州学生讲授演化论,那么也必须讲授特创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对此提起了诉讼,理由是它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做到教会和国家的分离,最终该法案被宣布为无效。我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方的哲学见证人,与已故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已故的神学家兰登·吉尔凯(Langdon Gilkey)和人口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等人同一战线。在证人的立场上,我论证说一个人可以将科学与宗教区分开。达尔文演化论与特创论就分列在鸿沟的两边,后者即是人们经常听到的“创世学”(Creation Science)。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提出了一些科学划界标准,包括诉诸自然法则、可检验(或可证伪)等。更准确地说,我和同道们提出,科学的基本特征是:⑴它以自然法则为指导;⑵必须参照自然法则作出解释;⑶可以通过经验世界来检验;⑷其结论是暂时性的,即不一定是最终的定论;⑸是可证伪的。法官据此裁定:特创论未能满足这些根本特征。
一些人,包括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对我的证词内容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认为任何为科学划界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他们宁愿觉得,你应该论证说特创论是一门糟糕的科学并且已经失败了。这些批评者丝毫不考虑这样的论证方式在法庭上毫无用处——《第一修正案》禁止的是教授宗教,而不是糟糕的科学。在《但这是科学吗:特创—演化论争中的哲學问题》(But Is It Science?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troversy,1988)一书中,我收录了批评家的抱怨以及我的回应。
杨:您曾经说过,身为一名“调和主义者”(accommodationist),您颇感自豪,这个名称意味着什么?
鲁:我认为和宗教信徒一起进行某种形式的智识会谈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调和主义者”。我从未觉得那些法庭上的交锋由于个人差异而变得紧张。我们可能会在台上或广播中对彼此说出最可怕的言辞,但在台下每个人都一贯礼貌相待。我认为特创论确实令人不快,绝对不应在学校中传授。但是直到今天,我仍不会将特创论者或他们的后辈——智能设计论者——视为邪恶的人。他们不是希特勒。我认为他们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我想与他们抗争,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我可以看出他们为信仰所做的牺牲,的确是受到他们的信仰驱动的。我一直觉得,憎恨某个想法比憎恨某个人要更容易。除此之外,作为哲学家,我致力于理性和论证。一位科学家不和特创论者发生什么关联或许是正确的——我当然可以看出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古尔德这样高知名度的人如何不愿纠缠其中,但是作为一个没有那样知名度的哲学家,我觉得我必须继续投身于某种讨论之中。
我相信在美国,将演化论者与宗教人士聚集在一起在政治上是极为重要的,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在政治上是合宜的就为我认为是错误的立场辩护。我居住的美国南部地区的总体情况有点儿荒谬。在《物种起源》发表150多年之后,有人仍然认为地球只有6000年的历史,这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像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①这样的人都认为地球年龄要久远得多。像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以及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这样的人肯定相信年轻地球论,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知识。但是同时他们总是说,如果科学发展表明无法坚持这些信念,那么你就必须接受科学并且学会以新的方式解释《圣经》,以调和(accommodate)这两者。因此,我一直觉得传统基督教内部有很多资源可以用来应对从科学角度提出的众多批评。当然毫无疑问,对许多人来说,科学观点使宗教有点儿多余。不过,对科学的兴趣或对宗教的厌恶,这两者哪个居先并不好说。在达尔文那里,肯定不是科学使他成为一位理神论者(Deist)②。他不喜欢永受惩罚(eternal punishment)之类的想法,所以我认为情况远比科学与宗教单纯对立要复杂得多。
我坚持认为,应该与宗教信徒交流和对话。我与年轻的基督徒斯蒂芬·布利文(Stephen Bullivant)合编了两本关于无神论历史的书:《牛津无神论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to Atheism,2013),《剑桥无神论历史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to the History of Atheism,2020年即出)。此外,我与基督徒合著了一些书:与卫理公会教徒迈克尔·彼得森(Michael Peterson)合著了《科学,演化与宗教:无神论和有神论的辩论》(Science, Evolution, and Religion: A Debate about Atheism and Theism,2016),同长老会教徒爱德华·拉森(Edward J. Larson)合著了《信仰与科学》(On Faith and Science,2017),最近一本书是与天主教道明会神父布莱恩·戴维斯(Brian Davies)合著的《认真对待上帝》(Taking God Seriously,2020)。
杨:如何评价理查德·道金斯?他的著作在中国很流行。
鲁:道金斯是一位热情的演化论者,是那本确实伟大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他还是一位热情的无神论者,写了红极一时的畅销书《上帝的妄想》(The God Delusion)。我的意思是,道金斯认为,如果你热衷于科学,那么你就不会热衷于宗教。特创论者认为,如果你热衷于宗教,那么至少对很多当代科学就不会太热衷。任何一方我都不完全同意,我对此有自己的认识。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有很多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绝对虚无?意识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自己只是分子的集合,可为什么拥有这种分子所没有的自我意识?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层次上我们显然是动物,但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具有自我意识。我认为这些都是谜。这并不必然证明上帝的存在,至少不是基督教上帝的存在。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些是谜,谁知道答案呢?到底存在目的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运动中的分子?
我认为道金斯代表了一种极端主义,而这只会使美国的情况恶化,我完全不相信这会很有帮助。不过显然他有很多读者,其著作很热销。道金斯及其追随者非常推崇科学,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某种意义上他是在使用达尔文来促进无神论。我认为这会使达尔文感到非常不自在。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agnostic),固然不推崇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但对《上帝的妄想》一书肯定会感觉很不适。达尔文会觉得宗教更多是私人事务,他也非常不想让自己的理论与宗教直接对立。
我应该说我已经写了或合著了许多解释和捍卫自己立场的书。第一本是《达尔文主义者可以是基督徒吗?——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Can a Darwinian be a Christi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2001)。我论证道,在审视道德、奇迹和上帝之类的问题时,达尔文主义者可以是基督徒,但这并不容易。顺带一提,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于2011年出版。然后,我写了一本明确论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书《科学与灵性:在科学时代为信仰留出空间》(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Making Room for Faith in the Age of Science,2010)。我主张科学有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绝对虚无?”宗教可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在回应道金斯及其同道时,我先后写了《无神论:人人需知》(Atheis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2015),《一神论和当代无神论》(Monotheism and Contemporary Atheism,2019)。很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的修订版《演化与宗教:对话》(Evolution and Religion: A Dialogue)中,我写了一点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人物对谈。我分别引入了一位以道金斯为原型的人物以及一位以我为原型的人物。为了使讨论更有趣,我添加了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变性人,他基本上对我们两人的观点都不同意!
六 达尔文产业的终结?
杨:《达尔文革命》于1979年问世,1999年出了第二版,您增加了长达25页的后记,以强调20年间的一些新研究,比如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对达尔文的重要影响,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达尔文革命中的作用,达尔文何时认识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的意义,他对生物进步主义的看法,等等。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如今又过了20年,回顾过去,您如何评估其影响和价值?您会重新修订出版新的版本吗?
鲁: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我出版了《达尔文革命》,为我的那十年划上了一个句号。我总是将这本书描述为在我最初进入达尔文研究时希望读到的一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准确的特征定位。20世纪70年代末期相关领域已经发展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主要的思想和解释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于是我综合了它们。因此,尽管显然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但它基本上仍是可靠的,而且还在印刷,每年售出数目可观。我曾经考虑过要撰写一个全新的版本,但是其他写作项目总是会妨碍这个计划!但是,我今年写了一个短书《达尔文革命》,收录在我和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格兰特·拉姆西(Grant Ramsey)合编的《剑桥生物学哲学原理》(Cambridge Elements in Philosophy of Biology)丛书中。其中,我的确谈到了最近的发展。在前言中,我也回顾了自己撰写《达尔文革命》的缘起,尤其是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带来的思想冲击。
杨: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专业的达尔文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半个世纪。1996年,您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达尔文产业:指南”。2007年,您还为“书评座谈:达尔文的地质学——达尔文产业的终结?”贡献了观点。同时,作为《生物学与哲学》杂志的创办人,您对相关领域的文献非常了解。戴维·赫尔(David L. Hull)2001年甚至还就您15年间为该杂志“札记”(Booknotes)专栏撰写的138篇评论写过一篇文章——您的评论的确自成风格,言语相当犀利。现在,您对该产业有何看法?关于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研究是太多了吗?事无巨细以至于太过繁琐、失去意义?还是说该领域仍然具有产生深刻洞见的能力?
鲁:在我看来,达尔文产业已经完成了很多基本工作。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填补了很多信息。比如说我们早已清楚了达尔文的宗教观点,他年轻时就是一位理神论者。写作《物种起源》并没有使他变成无神论者,甚至直到生命晚年他才成为一名不可知论者。我们现在确实对达尔文的生活和他的思想有了很多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现新的东西——也许他在贝格尔号航行中有了一个私生子呢(我真得不这么认为!)。
实际上,一项新发现也许与达尔文的病有关。他年轻时非常健康,然后在30多岁时病得很重——头疼、胃痛等等,困扰了他的余生。过去人们认为这可能是他在南美感染了一种疾病所致。现在,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乳糖不耐症,即无法消化奶油、奶酪等乳制品。人类曾经在童年后就无法忍受乳制品,随着农业出现以及牛羊等产奶动物养殖业兴起,自然选择发挥作用,世界上产奶动物饲养多的那些地方的农民就能耐受乳糖。爱尔兰人几乎100%耐受乳糖,而少有亚洲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即使在乳糖耐受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也有一些人没有必需的基因。达尔文的病提示出他可能是其中之一。当他离家做水疗时,吃的是稀燕麦粥,病情得以好转。当他回到家享用妻子做的含有大量乳制品的厚重食物时,他就又病了。
有时,尤其是在2009年,有如此多的庆祝活动和如此多的出版物,你会感觉到商业性——人们是在用你所知道的来强调某种东西。比如,剑桥大学有一个大型的达尔文庆祝活动,不仅仅因为要纪念达尔文,也是为了纪念剑桥——那年恰逢剑桥建校800周年。实际上,我更喜欢剑桥1982年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因为它更侧重于专业领域的会议。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它更有意思。1982年在意大利有纪念活动,在西班牙等地方也有,但我认为在剑桥举行的活动特别有趣——因为人们专注于科学,实际上他们做了很多我正在尝试做的事情,即他们讨论了达尔文,而后讨论了自那时以来科学的发展。
在2009这一重要的庆祝年之后,仍旧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出版物。例如,戴维·塞科斯基(David Sepkoski)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古生物学著作:《重读化石记录》(Rereading the Fossil Record,2012)。他是古生物學家杰克·塞科斯基(Jack Sepkoski)的儿子。戴维的著作非常有趣,我非常倾向于从事类似这样的研究。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有语言天赋,我可能想研究达尔文与俄罗斯,或者达尔文与德国,甚至是达尔文与中国。因为我敢肯定,还有很多有趣的工作,有待于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来做。总之,我认为在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杨:是的,我相信至少对您来说,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进行相关研究。能否介绍一下您近期的研究工作?
鲁:我要说的是,作为学者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非常满意。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主要职责是担任老师,但我的确喜欢写作和想法的发挥。我现在已经快80岁了——我出生于1940年6月21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自1965年以来,我已经教了55年书。作为学者我可以确切地说:过去10年对我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首先,在2013年,我写了一本书《盖亚假说:异教徒星球上的科学》(The Gaia Hypothesis: Science on a Pagan Planet),讨论了世界是有机体的想法。我采访了许多人,包括非常热衷于争辩说“地球母亲是活的”的异教徒,他们喜欢在月圆之时裸身围绕橡树跳舞。遗憾的是,当我采访他们时,没人要求我脱下衣服!
2016年,我与之前提到的罗伯特·理查兹合作撰写了《达尔文之辩》(Debating Darwin)一书。他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将达尔文理解为一个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很大影响的人,而我的观点是,达尔文是自然而然从英国自然神学和工业革命刺激下的英国经济中出现的。2017年,我们又一起编辑了《剑桥演化伦理学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to Evolutional Ethics),为相关争论提供了最新的内容。
因为我喜欢19世纪的英国文学家——狄更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所以我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小说和诗歌如何展现达尔文的思想。许多世俗思想家对达尔文诞辰——“达尔文日”(Darwin Day)——大加庆祝,在我看来,就像耶稣日(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圣诞节)一样,这将达尔文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该书主题就此引发出来,即我们应当会看到达尔文主义者对上帝、人类、道德、罪恶和救赎大书特书——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宗教议题。在《达尔文主义作为宗教:关于演化,文学告诉了我们什么》(Darwinism as Religion: What Literature Tells Us about Evolution,2017)中,我证明了我的猜测是敏锐、可靠的。许多人,包括道金斯,都将达尔文主义视为对基督教议题的世俗宗教版回应。
2018年,我写了《论目的》(On Purpose)。我试图证明,与物理学不同的是,生物学是根据预期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仅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进行解释。你可以问为什么鸟有翅膀,并回答说它们是用来飞行的,即使你正在谈论的是仍在巢中的雏鸟。这种解释被称为“目的论的”,参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终极原因”。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必要的,也是好科学的标志。这正是生物科学不是物理科学的地方。
我注意到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这一事实,因此写了《战争问题:达尔文主义、基督教及其为理解人类冲突而进行的斗争》(The Problem of War: Darwinism, Christianity, and Their Battle to Understand Human Conflict)。我比较了基督徒和达尔文主义者对战争的论述。我认为,基督徒认为战争永远是一件坏事,但是因为我们被罪所污染,所以战争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过去的战争可能是件好事——毕竟通过演化导致了我们人类出现,但今天战争却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消除它。我重申了之前有關达尔文主义与文学的那本书中的主张,即我们面对的是两种竞争性的宗教——基督教和达尔文主义世俗宗教。
最近,我写了一本小书《生命的意义》(A Meaning to Life,2019)。我很高兴它受到了很多关注。我认为你不必是基督徒、拥有永生的承诺,就能过充实而令人满意的生活。真正重要的是你此生做了什么。我认为达尔文主义表明我们是社会动物,因此在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并为所有人的福祉做贡献时最幸福。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追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我自称为“达尔文主义存在主义者”。萨特说,重要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上帝是否相关。他说上帝是不相关的,我们必须以人类的方式生活。我同意他的观点,并且我认为用来描述我本人及所过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术语是:“唯一真正快乐的人就是给予他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