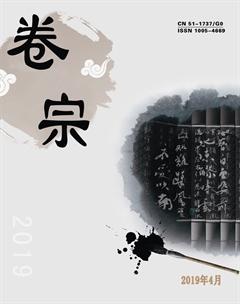古蜀面具之眼睛形象
摘 要: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各式青铜眼器形,从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令世人瞩目,这与古蜀文化背后的巫文化、地域文化、民族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古蜀人对“眼睛”符号的崇拜,是巫文化的产物,将巫师赋予了与自然沟通的灵性与神性,察常人不可察,从中获得庇佑,进而成为一种信仰,这种特定的思想崇拜具有跨民族性的特征。
关键词:古蜀;三星堆文化;眼睛崇拜;巫文化
古蜀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境内,它虽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中国川西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以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的重大发现为标志,向世人敞开了一座公元前14-11世纪古树文明的神秘殿堂。三星堆祭祀坑中器物种类丰富多样,“倾倒”在两个长方形土坑里的除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象牙器物外,还包括铜神像、铜人像等之前未发现过的器物。其中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数目众多、形式各样的青铜眼形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独立的眼形饰件,可以分为菱形、勾云形、眼泡等形式。菱形眼形器共出土71件,有菱形、钝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种形制。菱形眼形器长约五十多厘米,直边,作斜坡形,中部眼球呈圆形凸起,四周下凹,左右两侧有棱脊,四角各有一圆孔;钝三角形眼形器为菱形眼形器沿长轴方向剖开的一半,周边斜平,中部眼球凸起,呈半球状,三角各有一圆孔,眼球周围内凹处各有一稍大的圆孔;直角三角形眼形器则是菱形眼形器沿纵、横轴方向剖开的四分之一,略呈直角三角形,可由四件組成菱形器,眼球边沿内凹处及一个锐角各有一圆孔。勾云眼形饰,中部为呈圆角方形外凸的瞳孔,两侧的眼角作勾云状向下弯曲,饰件四角均共出土8件,因其形状的变异而分为两种亚型,有的单眼复原后的长度可达1米左右。铜眼泡共出土33件,有圆柱形、扁泡形、圆角方形等种类,成双成对,基部各有二三个穿孔,似是表现瞳孔。[1]此外,除了许多独立的眼形饰件,许多青铜面具上(如附图)也都有突出的纵目,为什么三星堆中会出土这么多与眼睛相关的器物?笔者认为这与古蜀人的巫术崇拜有关。
1 眼睛崇拜背后的巫文化
眼睛,在人的器官中是神奇的,因为我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都源于眼睛。在中国巫史文化中,有很多关于“目”的记载。《春秋演孔图》云,“仓颉四目”“舜重瞳子”。《南史·隐逸传下》“陶弘景”篇云,“眼方者寿千岁”。笔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奇怪的眼形器,与古蜀人的巫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在《华国志·蜀志》中记载,古蜀第一神王蚕丛被想象地描绘为“纵目”,可以猜测古蜀人以崇拜“眼睛”的方式来表现对祖先的崇拜。但笔者认为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出土的眼形饰件并不只是简单地对个人偶像崇拜的艺术产物,换言之,眼睛崇拜只是表象,真正的本质是古蜀人对巫术的崇拜。古蜀人创造出那么多的眼形饰件,对此的热衷可以说根源于巫文化对巫师特异视觉或眼睛巫术的推崇。以常人的视角而言,我们眼睛所观看到的界域是有限的,然而巫师本来就被赋予了与自然和神灵沟通的神性,笔者认为古蜀人铸造这些怪异的眼形器或者说将这些怪异的眼形器附在青铜面具之上,就是想让巫师有所借助,就像我们现在参加假面舞会一样,只要戴上面具就可以变成自己想要表现的那个人,虽然两者的目的并不一致,但也可以试想出如若是巫师戴上面具,就真的可以观常人所不能观,察常人所不能察。古蜀人通过对此巫术的崇拜,就可以以“有限”测“无限”,受到大自然及神灵的指示,从中得到庇佑。
朱狄先生在谈到神像起源时曾提到,非洲利比里亚人有种用于丧葬的黑木面具。面具沉重怪拙,伸出的圆形眼球;巫人用它在葬仪过程中洞察、识别、驱吓那些利于死者魂灵的精魅,防止它们祟乱。[2]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美洲土人面具中大量圆柱体眼睛,那是巫师夜间对付邪魅的,圆柱体的巫眼代表巫人的神秘视觉,并有辟邪防身的左右。特林吉特人的神话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乌鸦离开印第安人前警告过:等它们回地球时,谁敢看它们谁就会变成石头。所以印第安巫人用白菜叶卷成圆筒套在眼睛上窥探乌鸦并制杀它们。这也极能说明问题。似乎美洲巫文化思维中,也尤其强调巫者的神灵化视觉功能,而眼睛上出现圆柱体或圆筒状正是巫灵化视觉的特别模拟。[3]此外,形状怪异的眼睛(包括各种禽兽的眼睛)在古代法术文化中,本身就是一个巫灵符号:《渊鉴类函》259卷引《韵对》云:“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时幼窃呑之…乃炙鱼眼以厌之。借宿之间,珠随便出…”这里的“炙鱼眼”即为一种消灾弥祸的厌胜巫术。《佩文韵府》四十五卷“眼”字条引《佩楚轩客谈》云,古蜀人织“十样锦”,图案中多为“象眼”,以为铺在家中可辟邪;与北美印第安人服饰布满眼纹用意相近。所以可以大胆地推测,眼睛崇拜是古蜀人推崇巫术崇拜的产物,是巫术崇拜的表象特征。
2 眼睛崇拜形成的原因
笔者认为首先是地域因素。我们都知道,古蜀国地处内陆四川盆地,这里水土丰饶,物产富饶,也曾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的后花园。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这个地区是一个相对中原比较闭塞的,虽说在很多层面上可以体现出古蜀文明和外界的交往,譬如陶器的形制、纹饰和用途,以及青铜文化,但是对于眼睛崇拜,笔者更倾向于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主流宗教都是当地气候、地理和生产力阶段的反映,是地区主流意识的凝聚。[4]而且,在三星堆发掘出的青铜面具、摇钱树等文物在中国其他地区是极为罕见的。古蜀人对眼睛崇拜的神圣心理,体现在“法器”上,用于各种祭祀或者仪式。不管是纵目面具还是眼形铜饰器,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形成的,同非洲和美洲发掘出的关于“眼睛”的文物相比,古蜀的“眼睛崇拜”更倾向于祭祀礼仪中所需要的器物崇拜。古蜀文化应该是地方色彩鲜明的区域性文化:中国的“眼睛”造型威猛,线条强劲有力,并附有狰狞和庄严之美,诙谐与凶猛之美。而非洲的“眼睛”倾向于几何形,但是表现力度却比古蜀“眼睛”更为强烈。封闭的地形使古蜀人民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惑转化为对某种特定精神层面的寄托,眼睛崇拜作为古蜀人信仰的一部分,并且以面具为载体体现出来。自然环境对于人们视觉上的刺激和心灵上的触动远比社会心理、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5]从地域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文化都建立了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审美心理结构,从而在艺术传统中留下了一套审美程式密码,并且作为一种生物遗传基因得以世代相传。[6]纵目面具的发掘震惊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个“大眼”的种种猜测。由于地形的封闭,层层山峰环绕,笔者猜想青铜纵目面具的解释除了古文记载的之外,是否有人们渴望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的期望在里面,因为人们希望和需要看到更远的地方。将眼睛刻画为向前伸展的形象,是为了适应大自然中的生存而特意表现出来的。“千里眼”的这个称谓应该就是来自于此吧!不能苟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特定的地理环境确实对一个地区的风俗宗教信仰的形成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出土器物中对眼睛的刻画而言,“大眼”“菱形”“不规则三角形”这些眼睛的形象,在已知的世界各国古代文明中,还没有那个民族像古蜀人这样如此崇拜“眼睛”,着重对眼睛作各种夸张或者寓意。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有必要从自然环境在人类艺术风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自从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人们逐渐相信古蜀文化是开放的。但是事实情况是这个地区的封闭地形导致由本土而生的特色的宗教信仰的盛行——眼睛崇拜。
3 眼睛崇拜的影响
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眼睛崇拜赋予了“蜀”的特定意义和来源。学过古汉语的人都知道,古文字中“蜀”字造型特别突出眼睛的意象。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蜀”是带着小卷尾的大眼睛,可以让人联想到兽面具下颚的眼睛的形状,也可以联想到三星堆立人像冠式的侧视面。许慎《说文》中说:“上目象蜀头形”,意思是以“目”来表象“蜀”这个神怪的头的形状。这个解释正好可以和三星堆出土的各类面具、眼饰相印证。“蜀”字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为什么会出现“蜀”?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猜测是当时对某種特定现象或者代表这个地区的某种标志的记录。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面具可以看出,当时盛行的对祖先崇拜的方式——以大眼,巨头的特征表现出来,夸张眼睛的威慑力。甲骨文中出现的蜀是否是商人对这一盛行信仰的认可,认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可以以“蜀”代表,因此便出现“蜀”。《从眼睛崇拜谈蜀字的本意与起源》中谈到,蜀字的产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纵目神”崇拜在早期蜀人精神世界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因而“蜀”成为了该人群、该民族、该国家、该地区的标准称呼,并一直影响后世,沿用至今。[7]由此可见,眼睛崇拜对整个古蜀地区的生活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古蜀文明的神秘逐渐被揭开。
4 眼睛崇拜的跨民族性涵义
作为宗教背景下的一种思想崇拜,眼睛崇拜并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在巴蜀文化才存在,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之间也广泛存在着,即具有跨民族的普遍性。“跨民族性”是源于中外宗教信仰中存在着用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和艺术表现形式去表达同一个主题。正如前文提到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美洲印第安人发掘的面具中存在很多圆柱型眼睛,是一种特殊的视觉,能够驱除邪魅”。非洲利比里亚人有种用于墓葬的黑幕面具,同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相同的是,这类面具沉重笨拙,并且是圆柱形眼球。据考察,这是当时用于在葬仪过程中,洞察,识别,驱吓不利于死者灵魂的鬼魅。很显然,这些圆柱式眼睛不会是蚕丛,也不会是会发光的眼睛。这是否是早期人类社会的心理成长中具有的某种公共性的东西呢?不可否认,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会在宗教崇拜上有一些相似之处,是人类思想在特定阶段的特定反映。这样来看,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会出现相似的宗教崇拜是宗教信仰跨民族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结合人类文化学,宗教学以及社会学来看,“眼睛崇拜”的形成并非偶然。不管是上古时代还是文明时代,宗教信仰是人们心中神圣的殿堂。“眼睛崇拜”仅仅是某个缩影,还有其他信仰支撑着每一代人。而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摸索和探究。本文重要以面具为例,分析眼睛崇拜的广泛意义。在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对眼睛的崇拜仍有体现。“眼睛”的形象,还常常独立出现于人像、动物纹饰的中心部位。如大立人像的龙纹法衣上,双肩各用一个巨大的“眼”形纹饰作为主题。立人像头顶华冠的两侧,也呈橄榄型眼睛。“象首人像”头戴高耸的冠饰,清晰地刻划出一对勾云状巨眼。
从面具的“眼睛”中我们嗅到了从遥远的古蜀国时代飘来的那种文明气息,这股带着神秘的香气令我们这些后世来访者着迷。或许透过这种独特的文明气息,古蜀文化留给我们后人的不仅仅是对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生活的向往,还有对那个时代的些许思考。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三星堆祭祀坑.成都:文物出版社,1999.
[2]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列维·斯特劳斯.面具的神秘(中译本),1992.
[4]刘湘东.地理环境与艺术风格[J].美术观察,2009,(01),第110页.
[5]宋正海.回归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J].2000(02).第7—8页.
[6]李育富.地理环境与中国宗教思想转型[J].宗教学研究,2010,(01),第204—205页.
[7]赵殿增.从“眼睛”崇拜谈“蜀”字的本义与起源──三星堆文明精神世界探索之一[J].四川文物,1997.
作者简介
刘家鹏(1983-),男,苏州大学艺术学院2015级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