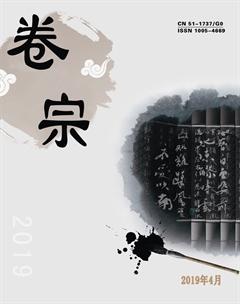《徐公文集》版本源流考
张书侨
摘 要:《徐公文集》是南唐与北宋之际的著名小学家徐铉所撰的一部诗文别集,全书共三十卷,不仅对世人研究徐铉的诗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且版本保存尚好,源流颇为清晰。据《四库丛刊》、《宋史·艺文志》、《藏园群书经眼录》等文献可证《徐公文集》在宋代已产生刻本,此后元明清三朝承袭宋代旧本持续流传,并于明清两代增加了影写本、抄本系统,至清末民初刊刻影印格外盛行促进了《徐公文集》的海内外传播。本文主要以历代文献书目为线索,全面梳理《徐公文集》的成书经过与版本流传情况,尤其考究作为后世翻刻祖本的明州公库刻本,以此全面把握宋本的整体版本状况,这对建构《徐公文集》的版本体系、保存古籍图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徐公文集;版本源流;宋刻本;历代版本流传
《徐公文集》又称《骑省集》、《徐骑省集》、《徐常侍集》,为五代宋初文学家、语言学家徐铉的诗文集。徐铉,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生于五代后梁贞明三年(917),卒于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仕南唐至吏部尚书充翰林学士,入宋官至左散骑常侍,淳化初因事贬静难军行军司马。在南唐为官期间以文辞翰藻闻名,尤工小学,精通文字音韵,曾获诏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解字》。且擅长李斯书法,十分精通隶书,与其弟徐锴并称为“二徐”。[1]《徐公文集》前二十卷在南唐所作,后十卷在宋初所作。李昉《东海徐公墓志铭》说:“所著文多遗落,今其存者编为三十卷。”陈彭年《故散骑常侍东海徐公集序》说:“公江南文稿,撰集未终,一经乱离,所存无几,公自勒成二十卷。即归中国,入直禁林,制诏表彰,多不留草。其余存者,子婿尚书水部员外郎吴君淑编为十卷,通成三十卷。”[2]由此可观,《徐公文集》是徐铉本人与吴君淑合力编纂的结果,最终定型于北宋,这也是后世进行翻刻的底本。
现存《徐公文集》最早的版本为明州公库本,藏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明州公库本属宋刻本,与胡克顺镂版一起构成了宋刻本的两大分支。而后世元至清朝无论是钞本,还是影写本,都依据绍兴明州本。元、明两朝并不流行刊刻,有关《徐公文集》的记载存在于《文渊阁书目》、《绛云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等古籍文献里。而钞本與影写本却在明清时期盛行,据现存书目考证,国内遗留的著录多达二十余种,其中不乏善本。众多钞本、影写本的出现与整个社会对书籍的接受程度提高密切关联,诸多藏书家亦增加了收书。清末民初的影印本及刻本更是达到高潮,数量庞大,质量精美。由此看来,《徐公文集》版本可大致分为三个系统,其一是宋代刻本系统;其二是明、清两代钞本、写本系统;其三是清末民初刻本、影印本系统。鉴于《徐文公集》并未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严重散佚状况,虽有具体卷数的缺漏瑕疵,但整体脉络便于人们把握与考辨。
1 《徐公文集》宋刻本
1.1 胡克顺本
据李昉《东海徐公墓志铭》与陈彭年《故散骑常侍东海徐公集序》得知《徐文公集》三十卷成书于北宋初期,由徐铉及其婿吴君淑先后整理而成。而李《墓志铭》与陈《序》皆作于太宗淳化四年(993)七月,此距离徐铉辞世近乎一年,所以文集底本在此之前便已编撰完成。二十三年后,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胡克顺于陈处得文集予以刊刻。北宋著名诗人晏殊为之跋,称胡氏“早游骑省之门,深蒙乡里之眷,宝兹遗集,积有岁时,镂版流行,庶传永久。”晏殊在此说明了陈彭年收集徐铉遗书的事实,同时交代了当时版本刊刻的社会状况。次年(天禧元年)刻印成,胡克顺上表奏明:“数年前,故参知政事陈彭年因臣屡言,成臣夙志,假以全本,并兹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镂版。竹简更写,无愧于前修;綈几回观,愿留于睿览”。真宗批答,称所进新刊《文集》两部,“计六十卷,共十一二册”,则是分为每部三十卷,分装六册。此即天禧胡氏刻本,为后来各种版本的祖本,也是依据相关文献记载证明的宋代第一刻本。
1.2 明州公府本
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知明州、提要学事徐琛重刻该集于明州公库,跋之曰:“《骑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间尚书都官员外郎胡君克顺编录刊行,且奉表上进。…年世忧远,兵火中厄,鲜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库镂版以传。”此即明州公库本。《徐公文集》刊刻以后,官修书志和私人藏书对此均有记载。如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十八著录《徐铉集》三十卷,称其“幼能属文,尤精小学。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预作。有欲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按“文思敏速”至此,原无,据《文献通考》卷233引补)”[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曰:”《徐常侍集》三十卷,徐散骑常侍广陵徐铉鼎臣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余十卷,归朝后所作也。”[4]晁、陈二人所见,应当不出天禧、明州二本。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四亦从之。《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著录二十卷,疑“二”乃“三”之讹[5]。《宋史》卷二百零八《艺文志七》著录为三十二卷,疑连附录。这些官修或私人书录对《徐公文集》的著录均以徐铉生平经历以及刻本的刊行情况为依据。
《徐公文集》在元明两代无覆刻本,但宋明州刻本得以流传。明《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徐骑省文集》一部十册,现存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据严绍璧《日藏汉籍善本目录》载:“《徐公文集》三卷附录一卷,宋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府刊本共十二册,日本大仓文化财团藏本,按每半页有界十行、行十九字。白口。版心下有刻工名姓,如施章、刘仲、徐彦、胡正、洪光、朱礼、王实、王伸、陈忠、洪茂等。此本系据北宋天禧中胡克顺刻本重刊。末有提学徐琛撰《明州重刊徐骑省文集后序》。大字大本,惟缺卷一第十九页,卷十缺第十四、第十九两页。卷中有‘应奉危素读过手书墨笔,并有‘文渊阁、‘徐建庵、‘乾学、‘曾在定邸行有恒堂、‘梦曦主人等印记。”[6]可见该本卷一与卷十存在缺页情况。经元代危素珍藏,为《文渊阁书目》所载之本,后归清徐乾学所藏,《传是楼书目》载:“徐常侍文集三十卷,宋徐铉三本”[7],后经定府行有恒堂递藏。据《徐乃昌日记》云:“《徐公文集》定本系定府收藏,后归徐梧生,徐殁归董授经所得,售于日本大仓氏,非内府藏本(内府藏本当无缺页,当年编《全唐文》多出二编,因知无缺。)此乃乾据授经之言不足据,盖所缺者诗,而《全唐诗》并未多出只字也。”以此推断应有另一宋本,但苦于文献记载尚不充分,况且前人理论存在疑误性,我们暂且不能找到《徐公文集》存在其它宋本的相关证据,因此另一宋本的基本情形我们尚未得知。
2 《徐公文集》明清写抄本
2.1 明抄本
现存文献对明《徐公文集》抄本记载甚少,最早的可追溯至的是崇祯年间钱谦益从史馆影摹的南宋大字本。《绛云楼书目》载:“徐铉骑省集四册三十卷。”[8]而后迂斋金侃据之传抄,萧穆《敬孚类稿》卷六《跋徐骑省集迂斋手钞本》云:“徐骑省三十卷,近世未见刊本,此钞本五册,乃国初吴门金迂斋手笔。据其自记系虞山钱宗伯于崇祯闲从史馆印摹南宋本,字颇大,予缩以小字,钞本存之。”[9]整体来看,抄本甚少。又《箓竹堂书目》卷三亦有十册,《脈望馆书目》载《徐常侍集》四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下有《徐常侍集》之目,而《徐氏家藏书目》卷六、《绛云楼书目》卷三陈注皆为《骑省集》三十卷本。众本所载卷数不一,乃传抄之常态。
2.2 清抄本
清代《徐公文集》各种钞本相对丰富,但主要由宋本辗转著录。我们可依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划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北京图书馆五部。其一为朱彝尊校对补抄之本,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三以为原本系明钞,该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记载,该本每半叶十行二十字,有人依据宋本用朱笔校正过。其中二十一至二十三卷为朱竹垞彝尊手录本,张芷斋有跋曰:“竹垞先生手钞三卷,内《韵谱序》颇有讹脱,从元刻本校正(按“元”通“原”,当指宋本),乙未季夏芷斋曝书,偶记于观乐堂中。”[10]卷末有“道光辛卯岁武原马氏汉唐斋书藏书籍”蓝色木记,有识语道:“《骑省集》六册,秀水朱太史故物,卷中丹黄皆竹翁亲自点勘,其手录半帙书法古雅,较之漏板恶钞,真同霄壤。后归花山马寒中先生,甲辰、己巳间,南楼图籍云散,予乃得而有之。览兹妙墨,不胜盛衰今昔之感。小山丛桂书斋识。”该本有朱彝尊、马思赞等诸多藏书家收藏刻印,后经归安陆心源、江阴缪荃孙等人相继递藏;其二为黄丕烈校跋本。嘉庆庚申三十九年(1560)黄氏题跋,称书友自锡山顾家得到钞本,相对破旧,“行款亦与影宋本(暗指所借周锡瓒藏本)大同小异。爰竭数日功,手校其误,虽缩本仍然,而宋本面目略约可见。”[11]此本为涵芬楼影印后收入至《四部丛刊初编》,《四部丛刊书录》曰:“此旧钞本,黄荛圃以影宋钞本校并跋,改正笔画,钩勒行款,纤悉必遵。”“卷十缺十四、十九两页,卷一缺诗九首,当不止一页。宋本亦然。”[12]其三为清乾隆三十九年卢氏抱经堂钞本,清卢文弨校正并附上序跋。卢氏跋曰:“余从鲍氏借得此集,乃虞山冯舒手校本,余又为正其所未尽者。录成,复请江阴赵敬夫曦明覆审,又得数十条。其本脱者尚无从补正之,然此已可信为善本矣。”其四为清邵恩多校跋本(亦以周锡瓒影写本校);其五为清贝氏友汉居抄本。
二是南京图书馆三部。其一为鲍氏知不足斋抄本,盖出于冯舒手校本。有抄配,乃丁氏旧物,《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六著录道:“《徐公文集》三十卷,知不足斋抄本。右依宋本缮录,行款避讳悉同。前帙间有鲍廷博校字。”其二为清陶氏笃素好斋抄本。此本经王晚闻、丁丙相继递藏。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六载“吴兴陶氏抄本,格版心刊‘笃素好斋藏书六字,有‘十万卷楼、‘晚闻居士两印。”[13]其三为经锄堂抄本,亦经丁丙收藏。为湖州经锄堂倪氏绿格精钞本,书法整齐划一,便于人们欣赏。三部书目均被丁丙收藏或在书志中收录,同时并未有大幅度校勘与订正,故据此可认为三种版本内容应无明显差异,并与祖本存在一定联系。
三是上海图书馆藏两部。其一为清康熙五十一年翁栻抄本。此本卷端附“金元功藏书记”、“延庚外史”印、卷末有康熙五十一年翁栻跋,附“栻”“又张”“天爵太湖公”印。卷一、卷十亦缺页。该本与上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黄丕烈校跋本十分相似,均存在卷一与卷十的缺页情形,而翁栻抄本产生于康熙年间,早于嘉庆,故黄丕烈本或与翁栻抄本相承;其二为清陈揆朱笔校抄本。此本存二十二卷,陈氏据影宋抄本校正,经张金吾、沈养孙等藏。且该本附有“稽瑞楼”“张月霄印”“爱日精庐藏书”“秘册”“碧山柏士”“曾在海虞沈氏希任斋”“彦民过眼”等印。由此可推断此本著录者陈揆在撰书过程中参照各版本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订正校勘,同时该本亦经多处收录流传。
除上述以外,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均藏有影宋抄本。如上师大藏本三十卷,经徐乃昌旧藏,卷端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盱眙王氏十四间书楼藏书印”朱文长方印。此本卷一、卷十亦有缺页情况,与以上版本相同。
细究众多版本文献流传情形,所有影宋、依宋抄本皆有共性,即存在缺页现象,与前述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所藏明州公库本相同,知并源于该宋本。如下表所示:
以上四本均源于宋明州公府本,除黄丕烈校跋本、翁栻抄本与徐乃昌旧藏本外,其它《徐公文集》版本虽未明确说明缺损情况,但其与上述几种版本存在密切联系,多数历经转藏或借阅,故这些版本或许亦有缺页情况。
然而亦有源于另一宋本者,即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影宋抄本。陆心源《影宋明州本骑省集跋》曰:“《徐公文集》三十卷,从宋绍兴中明州刊本影写,题曰‘东海徐铉撰。……每页二十行,行十九字。每卷有目,连属篇目。各家藏本卷十《烈武帝庙碑》‘告贞符下缺三百八十字,《三清观记》‘其守固者其事举下缺五十余字,此本皆完具,洵善本也。”[14]李英元《重校徐骑省集后序》以为陆氏本所据宋本,当与各家藏本所据宋本不同,“盖诸家所抄、所藏者,大抵皆据宋版最后所印脱爤之本,陆氏旧钞所据、所传者,犹是宋版初印之本故耳。”[15]李氏在此认为陆氏抄本产生时间早于另一抄本,最接近宋代《徐公文集》初印本。而萧穆则于《跋归安陆氏所藏徐公文集旧钞本》云:“归安陆存斋观察心源所藏徐公文集旧钞本,其脱伪亦复不少。其卷第二十四序赞铭论共二十篇各本皆同,惟陆氏本此卷……共七篇,卷二十五此本卷首有《大宗李公德政碑文》,此陆本无之,以下碑铭四篇亦与诸本次序不同。其二十八卷记十首诸本皆同,此陆氏本惟有前记六篇。……其同出绍兴十九年明州重刊本则一也,何以诸旧钞本篇目皆同,此本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凡三卷何以与诸本参差不一、多寡不同如是邪?又第十卷《武烈帝庙碑铭》中缺三百七十六字……诸本皆同。此陆氏本特全有之,字句且无一差伪。”[16]陆氏抄本与诸抄本缺卷情况不同,因此萧穆在此基础上认为该本亦出于明州公库本,大致分为两个抄本系统。由此可推断李英元的说法并不准确,陆氏版本同样有误差缺漏之处,不能简单认为是宋本初印。但考究現存文献,尚不能证明在日本藏宋本与陆氏旧钞本之前还有其它宋本,所以当下只能暂且将抄本划分为这两个分支。
3 清末民初刻本、影刻本
《徐公文集》在清末、民初的刻本均由抄本继承而来,其中以李宗煝、徐乃昌版本最为显著,以徐乃昌综合借鉴前代各种钞本及写本而又进行反复校雠的版本为代表,因该本指出宋本《徐公文集》的疑误脱讹现象并予以订正而被纳入到古籍善本之中,成为民国以来被集中延用的版本。国内著录近二十部,且在日本京都大学亦有藏本。依据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两大分支:
其一是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黟南李宗煝自徐乃昌家借出所藏明抄本,由金陵书局镂版印行。徐乃昌在《影刊宋明州本徐公文集跋》中回忆,当时任校事者“奋笔蹈隙,遇有脱讹,任意增改,迹近专辄。”宗煝子英元《重校后序》亦谓当时请旧交朱孔彰为之校勘,“朱君以原抄本脱讹颇多,又无别本参校,仅就己意与所见各书有关此集者,据以校正,凡二百余事,各为札记,附于本集之后。”如此粗率,校勘质量可想而知,故李宗煝亦认为其“终以不能精美为憾”,对此予以批评。宗煝死后,英元取初印本细阅之,“知脱讹之字,各篇皆有。乃遍作字告诸同志,及江浙诸藏书家,先后假得桐城萧氏文征阁所藏吴门高氏金迂斋侃手抄本,又藉诸暨孙问清太史廷翰假得江阴缪筱珊太史荃孙新得秀水朱竹垞先生抄本,又得乌程蒋氏维基所藏钱牧斋尚书影写明内阁宋本,最后又假得会稽章小雅处士善庆传抄本,并归安陆存斋观察心源校宋本,瑞安孙仲容部郎诒譲旧抄本,互为对勘,正讹补脱,先后刊改三千余条。仲容部郎又为详考旧籍,并据所见,又为校定三十余条,大致完美。”可见李英元于该集重校时参考以前众多版本再三斟酌辨误、校对,反复订正,治学恭谨勤勉。由于重校使用善本众多,其中如钱谦益影写明内阁宋本、陆心源抄本等,版本价值很高,有些版本至今已不复流传,故重校本之校勘有相当可取之处。李氏刻本当今在国内著录二十余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亦有藏本。
其二是民初本乃民国八年(1919)徐乃昌以所得影写宋明州本。跋称“因宋本而知抄本之讹脱,又因雠校宋本而知宋本之不能无讹脱。管窥所及,别为《校记》一卷。复从《宋文鑑》、《会稽掇英集》、《全唐文》等书辑得佚文六篇,并附刻焉。”影刊十分精美,收录也相对全面,堪称善本。《全宋文》即以此本为底本,用来校正各本。徐氏影刊本国内著录近二十部,日本京都大学亦有藏本。
4 结论
《徐公文集》的版本流传相对清晰,以南宋绍兴年间的明州公府本为代表的刻本对后世各抄本、刻本乃至影印本产生重大影响。其在流传过程中尚未受政治或战争影响而亡佚,即使在传抄过程中存在部分缺页或讹脱等现象,但并不妨害世人对《徐公文集》历代各版本系统的梳理。此外,即便是后世无论明清抄本亦或是清末民初的影印本都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所藏明州公府本相衔接,以宋祖本为尊,但陆心源抄本内容勘误、缺损情形与通行流传抄本依据的宋本存在显著差异,不可不在此审视《徐公文集》抄本的源头,这对文献辨伪、辑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元]脱脱主编.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Ml.北京:中华书局,1999:6.
[3][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M].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
[6]严绍璧.日藏汉籍善本书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M].续修四库全书.第9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M].丛书集成初编本.
[9][清]萧穆.敬孚类稿:卷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15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11][清]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补遗[M].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六).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清]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3][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M].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七二[M].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宋]徐兹徐骑省集序[M].清光绪十六年(1890)李元英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16][清]萧穆.敬孚类稿:卷六[M].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张书僑(1994-),女,满族,山东,硕士,河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